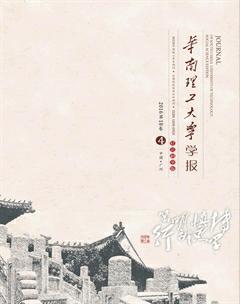大型城市广场踩踏事件应急管理:典型案例、演化机理及应对策略
卢文刚 田恬

摘 要:城市广场具有能够自由进出以及能提供巨大的活动场地的特点,成为城市人群聚集的重要场所。正因如此,对其进行公共安全管理的难度也较大。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广场和公共空间以及人群聚集踩踏事件的文献梳理综述,对上海外滩2014年跨年夜踩踏事件、沙特朝觐者踩踏事件、纽约时报广场跨年活动等正反典型案例分析比较,揭示人群聚集踩踏事件成因和转化演变的机理,对大型城市广场人群聚集踩踏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城市治理;应急管理;城市广场;人群聚集;踩踏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4-0085-12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4.012
一、引言
大型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截至2014年末,我国共有6座大型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1]城市广场,指在城市中心人为规划设置的、为市民公共活动提供空间和场地的一种开放性空间。[2]广场是城市中民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的空间,通常是大量人流、物流、车流集散的场所,场地开阔,交通方便。在广场中或其周围一般布置着重要建筑物,往往能集中表现城市的艺术面貌和特点。[3-4]如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海人民广场、天津银河广场、重庆朝天门广场、广州花城广场、深圳市民广场等。
近年来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日益凸显。而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生活、经济、文化的主要活动载体,承担着举办各种商业以及市民文娱活动等的功能,满足人们人际交往和精神活动的需求。城市广场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它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央,是建设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以方便市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开放性空间,往往是城市的代表性或地标性地点。而正是具有开放性,广场能够作为真正象征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往往也是标志性和具有特殊意义的景点,在重大节日往往成为市民聚集庆祝的场所。与此同时,人流在短时间内的大量聚集,使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增加:人群聚集的场所往往成为各种风险因素和安全隐患集中凸现和爆发的场合,人们在环境极度拥挤甚至呼吸困难、神经紧绷和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即便是微小事件的发生,都能很快改变人群整体的情绪,引发焦虑和恐慌情绪的蔓延和相互感染,导致推挤、踩踏、现场失控严重的群死群伤事件,给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害。并且由于现场人数众多,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伤亡惨重,增加了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性,给城市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带来挑战。
二、文献综述
(一)人群聚集研究
1.国外研究
一般认为,法国社会学家 Le Bon(1896)最先开始对人群的聚集行为进行研究,在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他对从个人聚集成为人群的过程及在过程中个体内心心理以及外在表现行为上的差异转变进行了研究。对在灾难过程中影响聚集人群安全的重要因素——从众现象进行阐释,认为人群中的个人的心理及行为由于群体整体以及其他个人的引导或感受到了集体倾向性一致性的压力,而向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转变,从而提出了从众理论。Smelser(1963 ) 在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中对从众现象中的个体心理以及行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从众行为是一种非理性行为,是导致事故灾难的重要原因。David(2000) 在Following the crowd中也对从众行为进行解释,并基于从众心理学提出了循环反应理论。
Brown R W(1954)在Mass phenomena中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和风险,人群最典型的反应方式便是处于自保进行对抗或者逃避,而这种反应可以称之为恐慌。恐慌情绪既是导致人群聚集事故的重要原因,又是使得事故后果扩大化的重要因素。Anthony R. Mawson(2005)在Understanding Mass Panic and Other Collective Responses to Threat and Disaster中提出了恐慌人群以互助和协作为主导的理论 。Pan. X. Han(2005)在Human and Social Behavior in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Egress中把恐慌中人的行为分为适应性行为和非适应性行为。Helbing (2000)在Simulating dynamical features of escape panic中对疏散过程中的恐慌与从众现象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 Le Bon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力模型,认为人群中的恐慌情绪不断积累达到一定量,人群会表现出从众行为。Baron 等人(1994)在Human aggression中从周边环境的角度对影响骚乱情绪的因素进行研究,指出在人群聚集、人流密度很大的集会中,少数人若发生异常状况,真实信息传播不畅,秩序发生混乱,一个人的突发意外会迅速弥散到周围的人群,从而演变成大规模的恐慌和混乱行为。
2.国内研究
我国对于集体心理的研究不多,尚缺系统的自主研究,主要是对外国成果的介绍和总结。如谭芸(2006)在《群体心理行为模拟的探讨》中对群体心理行为的计算机模拟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认为当群体丧失理性,行为表现出暴力和失控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影响社会安全。研究群体心理有助于预防骚乱的发生。姜姗姗等(2012)在《聚集人群的心理学因素及典型行为分析》中分析了影响人群行为的心理学成因,重点分析了处于公共场所中的人群聚集情况,研究了人群的心理以及行为特征,包括人群的从众现象和交叉流现象等。
国内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很多是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如颜珂和胡丹丹(2009)在《群体性事件心理学分析》中运用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对群体事件发生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储召红(2010)在《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中,认为从众、相互感染、去个性化,同质化等社会心理机制导致群体性事件规模扩大,对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发展进行分析,认为一般人群聚集和情绪转变的几个阶段,需要有一定的刺激和激化。[5]
(二) 公共空间及城市广场相关研究
1.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对公共空间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在政治哲学领域。如Arendt(1958)的The Human Condition认为排除包括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获益方面的考虑,挣脱政治权力压制,脱离了公权与私利的束缚、不受何组织和机构的干扰,自发、中立和完全自由的领域才是真正具有公共性属性的公共领域。她对公共领域进行的这个概念界定,被许多学者接受,Habermas提出了公共领域理论,对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公共领域为公共对话和交流提供开放自由的机会,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是中立和完全自由开放的,对所有公众不设任何限制。是否能够容纳自由的社会交流,让公共交流舆论不受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压制,在自发和自觉中进行,关乎健康政体的形成。
Arendt和Habermas的公共领域理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城市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产生了广泛影响。Sennett(1990)在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 the design and social life of cities中指出,随着人口的聚集,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来自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的个体共同生活和活动。而这正是公共空间的意义所在,为多元化的群体和个人提供相互交流和互动的机会。Carr(1992)的Public Space指出,公共空间为人群进行共同活动提供场地,增加个体的互动,增强群体凝聚力。在公共空间中,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其功能性,即是否能够满足市民的需求。此外还应被视为一项权利,人们在此之中应该具有自由出入和自由行动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和干涉。Nadai(2000)的Discourses of Urban Public Space强调认为公共空间的魅力以及最重要存在意义以及其与私人空间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可达性。公共空间中的限制和干扰很少,对于任何公众都是开放可达的。
2.国内研究
国内关于广场以及公共空间的研究许多是从建筑的设计与规划,以及生态、环境、景观等角度进行的。如王建国(1998)认为广场是城市空间里最具公共性、最富艺术魅力、也是最能反映现代都市文明和气氛的开放空间。[6]周军(2004)从城市公共空间整个系统的背景下对城市广场进行研究,根据广场在历史上功能和未知的变更以及现有城市规划中广场的地位两方面的因素为未来城市广场的设计和建设提出建议。[7]张琳(2008)提出城市的广场设计需要更多地在选址和设计中考虑市民的实际需求,包括活动场地需求和心理需求等,发挥广场公共空间的效用。孙连鸿(2013)认为城市广场目前的建设中缺乏对文化因素的考量,城市广场应该反映出城市的气质和文化,需要在设计中就融入文化的因素,使广场成为市民文化空间。
也有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角度进行了研究。倪伟(2000)指出城市广场的建设和设计与公共权力的形式有着很大的联系。王维仁(2002)对广场的公共活动进行探讨,指出广场是公众体现制度和机制允许之下的公共自由的场所。郭昊羽(2003)对我国各地兴起的广场建设热进行反思,指出政府和专家都对这一过程造成了影响。陈锋(2003)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广场形态的影响,认为我国转型时期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环境下,公共空间建设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尚未完全形成协调互动的态势。李德英(2003)对近代成都城市公园的兴起和公园社会冲突进行考察,将公园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揭示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与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的关系。陈竹和叶珉(2009)对国外的公共空间相关研究做了介绍,对公共空间概念的产生和价值判定进行研究,回顾了西方公共空间理论的发展。金访(2010)认为广场的出现和存在首先是出于特定的城市公共生活的需要,不是单纯的景观观赏物,它是城市生活和建筑的运作逻辑,又兼有传统市民中心特点的公共空间。[8]
(三)踩踏事件研究
1. 国外研究
目前国外对于人群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人群动力学,即通过构建相关的宏观或微观模拟模型对正常或紧急状况下的人群行为进行分析。如Lighthill 和 Whitham (1955)在A Theory of Traffic Flow on Long Crowded Roads中提出运动波理论,将车流的流体力学应用到对人流的研究当中,认为人流的运动可以用类似车流的特征和规则进行解释。Henderson(1974)在on the fluid mechanics of human crowd motion中提出了宏观模型,将人看作近似其他流体分子的个体,假定人不具有思考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在运动中近似流体分子自由运动,提出了元胞自动机模型。Blue(1998)在Emergent fundamental pedestrian flows from cellular automata microsimulation中研究了人在正常异动情况下与发生意外时紧急疏散状态下行为特征的不同,应用元胞模型进行了研究。Fang(2003)在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wd Density and Movement Veloeity中研究了个体在群体中的活动受到周边的影响,尤其是前后两个方向的影响。Heigeas等(2003)在A Physically-Based Particle Model of Emergent Crowd Behaviors中研究了人群聚集所产生的一些非协商性紧急状况下的人群聚集现象。Lee 和Hughes (2005)在Exploring trampling and crushing in a crowd中利用人流模型进行了定量分析,并且结合心理学对人群的移动进行研究。
2.国内研究
与踩踏事件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群行为研究与人群疏散上,且多集中于数学建模和行为仿真两个领域。这些基于数学应用的计量方法的研究成果为人群行为的预测和拥挤踩踏事件的预防提供了理论技术参考。如陈宝智等(1999)进行的人员疏散群集行为规律模拟研究,建立了对人群行为的计算机仿真模型,预测在疏散时人群活动和流动的状态及行为倾向。杨立中等(2003)认为应充分考虑人群中单个人员的个体行为特征, 认为人员在选择逃生路线时将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包括人员对建筑物结构的熟悉程度、对紧急情况发展的了解程度以及周围人员之间的引力和斥力作用。秦文虎等(2008)针对人群疏散时多个出口的选择问题,提出了把出口拥挤状态与个体心理慌乱状态相结合的出口选择方法。
也有学者从管理学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吴晓智、徐强(2006)以及王起全、金龙哲(2007)提出了要对大型公共活动从方案评估、静态评估、管控能力分析及应急能力等方面进行全过程的动态分析。叶明海、稽方(2006)对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的原因进行分析,从组织结构和各个部分的职责上对大型社会活动安全预警系统进行了尝试设计。胡志莹、叶明海(2006)提出预警是大型社会活动人群拥挤事故防范的基础,提出了活动前、中、后三位一体,各部门全力参与的预警体系组织模式。孙超、吴宗之(2007)对公共场所踩踏事件原因进行分析,指出踩踏的发生与公共场所的性能设计、人群素质和人群聚集密度、人群的管理和控制、人群的信息交流有关。张青松等(2009)提出了人群拥挤踩踏事件风险理论,对在人群拥挤踩踏事件发生过程中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进行了描述。刘洵等(2012)认为紧急状态下,个体的非适应性行为增加了事故风险,恐慌心理的产生加强了个体的紧张程度,体现出从众、竞争和趋光等行为特征。恐慌群体在逃生过程中易堵塞,进而演变为人员跌倒和拥挤踩踏。卢文刚等(2016)对美国时报广场和上海外滩跨年活动中的应急管理举措进行比较,分析了上海外滩应急管理的不足和美国时报广场跨年活动应急管理的启示,以期提高大型群众性活动踩踏事件应急治理能力,确保城市公共安全。
总体而言,由于人群聚集踩踏事件的多发、频发已引起学界和社会的重视,但目前少有通过对系列典型事故内部规律的总结分析来对其成因机制、机理以及防控进行综合性揭示的研究。
三、典型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防控踩踏应急管理分析
(一)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1.事件概况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的陈毅广场发生一起严重的拥挤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的严重群死群伤后果。
2.事件分析
(1)人群在相对狭小区域内的大量聚集
2014年12月31日晚8点开始,上海外滩出现了人潮的大量涌入,公众自发向景区聚集。据综合监测显示,事发当晚外滩风景区的人员流量,8到9点时已经达到了12万人次,9点至10点达16万人次,10点到11点时暴增8万达到了24万人次,过了11点之后,已经突破30万人次,达到外滩风景区的容量上限。陈毅广场附近交通便捷加之其与黄浦江观景平台相连,是外滩风景区最佳观景位置,也是跨年当晚外滩风景区成为人员流量最大、密度最高的区域。但陈毅广场面积较小,公共活动面积约为2877平方米。
(2)对聚集人群数量及现场应急预防准备不足
2011年起,上海连续三年在外滩举办了跨年活动。但在2014年,出于对保障公共安全、维护活动现场秩序等诸方面的考虑,上海方面考虑暂停在外滩的活动,另行择地举办,并且计划将参加活动的观众控制在三千人左右。2014年11月13日,初步的活动计划由黄埔区政府向上海市政府请示。有关部门未根据前三年举办外滩灯光秀的经验和活动中获取的人流数据,做好今年的人流预估。
外滩的跨年活动已连续举办了三年,这三年中人流、秩序和公共安全得到了良好的维护。但在2014年的跨年活动中,上海将活动现场转移到“外滩源”,仅将“外滩”作为活动外围现场进行了常态管理,而且并没有对周边交通进行限制。然而“外滩源”的活动设计入场人数只有三千人,往年参加跨年活动的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上海方面并未对超出部分人流的流向作认真考虑,只是认定没有组织活动的情况下不会有太多人来到外滩。在对人流没有做好预估的情况下,现场人流的组织分流引导工作乏力。然而上海“外滩”作为著名景点和开放性的广场,平日便是游人如织的景象,在跨年这一特殊的有纪念性的时间节点,民众会选择到这里来聚集庆祝应是可以预见的。
连续举办了三年的新年跨年活动,举办地点突然进行了变更,但并没能在第一时间让已经形成了惯性思维的公众知晓,表明事先信息传播工作不到位,有关部门对于公众认知习惯可能造成的情况没有准确预估。
资料显示,黄埔区在12月30日上午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活动相关信息。从中午开始,媒体向外报道相关的活动安排,但是并没有对关键的活动地点以及人流限定信息进行报道,告知公众,而是着力强调现场活动的内容以及效果,使公众对活动的期望值上升。在这种宣传和渲染之下,公众产生了信息混乱,正确和错误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再加上两个名字相近的举办地的信息干扰,公众难以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确定最终的活动举办地更改。并且黄浦区公布的信息缺乏细节性的通告,例如对活动人数的限制、如何获得入场资格、在什么范围内可以看到灯光秀、交通管制范围等,导致大多数公众对活动的举办情况一片茫然,部分公众主动向政府进行询问时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准确答复,进一步增加了信息的模糊性。官方公告的模糊不清给公众带来了信息获取上的混乱,而且消息选择在活动前一天发布,没有给公众留下足够的获取信息的时间,最终导致了公众的盲目参与。
事故当晚,外滩旁的地铁二号线甚至出于方便市民出行和回家的考虑,延后了末车的收车时间,相比平日多运行了1小时20分钟,而不是像往年一样在下午就进行封站。对地铁进行封站限制是限制人流进入特定地点的有力措施,跨年是一种闲暇活动,闲暇活动的特点之一是具有便利性才会吸引公众的兴趣、提高参与度。如果采用封站措施,去外滩的便捷性降低就会直接导致人流的减少。而上海地铁方面不但没有封站,反而还延时提供交通便利,这就更加引导人们向“外滩”聚集。
现场人流监控和路线引导出现问题。到“外滩”跨年的民众绝大部分是下地铁之后自行步行至“外滩”景区,沿途没有任何活动相关指示牌。现场没有权威信息引导,促使现场的人盲目自由移动、引发人流对冲。有一些知道灯光秀在“外滩源”的人去了外滩源,但由于没有票进不去灯光秀活动的现场,再加上认为“外滩”也可以看到一部分灯光,故转移至“外滩”;而另一部分以为灯光秀在“外滩”的人,在“外滩”现场被民警或者其他人告知灯光秀在“外滩源”,因此又试图往人群外挤,想去“外滩源”。原本只要控制住进行单向通行,流线交叉人流对冲的危险就可以避免,但上海并未做好流线设计和控制。[9]
(3)陈毅广场存在人流对冲点
陈毅广场上,3.5米高的人行道、4.7米高的平台广场、6.9米高的观景平台,形成了 “三级高差”,不得不用一些坡道或台阶来连接彼此。事发现场位于陈毅广场东南角通往黄浦江观景平台的上下人行通道阶梯处,由于台阶过窄引发拥堵,出现了人员阻滞,在台阶处出现了大批人员的停留,人群冲破警戒带逆行拥上台阶。上台阶和下台阶的两个方向的人流出现了推挤冲撞。
(4)导火索事件的发生。
通过监测系统发现了事态严重的警方调派警力至此开始维持秩序,采取强行介入的方式希望分散人流,但由于人流过于拥挤,成效不大。加之此前设立的警戒带被拥挤的人潮冲破,失去了分流的作用。不久之后台阶底部出现了有人跌倒的状况,由于巨大的压力和四周的拥挤,出现了连锁反应,引发人群中多人跌倒并且相互叠加,导致了踩踏事件的发生。
(5)事发后应急疏散及救援困难
事故现场由于过于拥挤,加之未事先留有应急救援通道,给第一时间展开应急疏散和救援带来了困难。但事故发生后观景台上的群众自发开始进行救援,配合警方维持现场秩序,齐声引导事发现场的人员退后,清理出疏散通道和救援场地。
现场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对伤员进行了急救,十分钟后陆续有急救车赶到现场,并且开辟了应急救援通道,还有不少社会车辆自发加入运送伤员的队伍,将在踩踏事件中受伤的人员转移至上海各大医院进行救治。2015年1月1日凌晨,现场的秩序基本得到了恢复。
综上,聚集庆祝是人类的共通天性,人群聚集在一起迎接新年、分享喜悦,是大众普遍存在的需求。政府应当尊重普通市民享受低成本娱乐的需求。因为担心人流量过大现场失控突然取消了举办多次的跨年活动,却恰恰造成了组织者和管理者的缺位。让大量没有组织自发聚集的人群陷入了无序的状态,更容易导致失控。影响信息传播力度和效果的三个重要因素,分别是信息本身的质量、信息传递的渠道以及信息传递的环境。当传播者越能够减少信源抵达民众的中间环节,传播效果就越好。而信息本身的内容是否足够清晰、是否连贯重复放送,也会影响传播效果。这次上海的官方通知内容含糊,不易被受众准确认知,宣传重点也没有注重强调活动地点的更改,传播时间也过短,再加上错误信息制造的噪音,信息并没有成功传递给受众。组织的缺位、信息传递的不到位、现场管理引导的不充分,三个主要因素叠加在一起,暴露出上海城市广场公共安全管理的短板,特别是对无主办单位无组织方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风险评估不足,准备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最终酿成了这次造成严重群死群伤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
(二)“9·24”沙特朝觐者踩踏事故
1.事件概况
2015年9月24日,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进行每年一度的朝觐活动。当地时间上午9点,朝圣者准备举行投石仪式,大批朝觐者从距离麦加数公里的米纳帐篷城步行向射石驱鬼仪式地杰马拉特进发,快到目的地时,因为一些朝圣者没有按照官方要求行事,在射石地驻足停留而后方的人急于向前,不断推挤,导致人群开始格外拥挤,出现了冲撞和推搡,最终导致踩踏事故发生。沙特当局出动超过200部救护车和4000多人,到场展开应急救援。为了避免意外扩大,沙特当局把人潮分散,并指引朝觐者从其他不同通道前往圣城。根据沙特的数据,踩踏事故造成769人死亡。
2.事件分析
(1) 参加朝觐人员在朝圣地大量聚集
由于朝觐人员数量众多而且构成庞杂,人员素质层次不齐,相互之间沟通不畅。人群因某种相同诉求聚集在一起往往容易自我失控,形成典型的所谓“乌合之众”,从众现象出现。这时个人理智和思维迅速退化、相互传染,整个群体变得不理智、易受极端情绪的感染和暗示。而参加朝觐的人员往往是虔诚甚至狂热的信徒,在朝觐过程中往往会身不由己、失去了判断方向、判断危险的能力,接收不到危险信号,整个群体会爆发出巨大的热忱和能量。很多人在事故到来时还浑然不知,感受不到危险的来临。同时参加朝觐的很多都是老年人,体力不支加上炎热和过度拥挤,更易发生意外。
(2)对人流量的管控以及现场安全保障
沙特在事前规定,每个国家,每100万穆斯林中只能派1000人参加,在事先就试图对人流总量进行控制。
当局每年出动6万名警察维持朝觐秩序;2015年增加到10万警力。警方在朝觐路线上和朝觐现场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监控,在控制室内通过监控系统动态了解最新的情况;并有直升飞机巡逻,以便根据人流分布情况、人流量的变化以及人流密度的变化,观察人群行为以及心理状态的变化,随时调动警力进行现场应急处置,维持秩序。沙特当局调拨了在麦加地区各医院的近3万名医护人员和400多辆急救车在朝觐现场以及周边待命,以第一时间应对突发情况发生时对医疗救护资源的需求,确保朝觐人员的生命安全。
沙特当局将踩踏事件,归咎于过度拥挤,同时认为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朝觐者没有遵守安全机构和朝觐部的指令。但从资料来看,沙特的现场处置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朝觐初期并没有对朝觐者如何进入朝觐地点进行限制和引导,在事发后才采取补救措施安排大巴统一前往。此外,配置大量警力的目的就在于对现场人流进行控制和引导,即使出现个别不听指令的朝觐者,沙特警方也应及时采取强制性措施进行干预,避免意外的发生,但从意外发生的结果来看,现场警力的秩序管控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强制性作用。
(3)道路拓宽及疏散通道的设置
在2014年沙特当局就对朝觐地朝觐路线上的道路进行了拓宽,并且增加了紧急疏散出口的数量。沙特官方拓宽道路意在拓宽朝觐者行走通道,消除可能出现的瓶颈,减少流线交叉人群交汇,从而避免踩踏等安全事件的发生。紧急出口的设置不但有利于应急撤离疏散安置,方便警车、救护车等救援力量的安排,为有序高效的应急处置提供保证,而且可以在人流密度上升至预警状态时就开始人群的分流和疏散,避免过度拥挤导致踩踏的发生。
(4)导火索事件的发生
踩踏事件发生在米纳广场上举行的投石仪式上。根据伊斯兰教传统,所有的朝觐者必须在朝圣第三天日出日落前投中石柱,而每个朝觐者只有一次靠近石柱的机会。因此,为了让自己在日落之前在两百万个朝圣者中抢先完成神圣的投石任务,很多虔诚的信徒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造成的危险可想而知。在推挤中有年老体衰者跌倒,周围的人层层叠压,最终引发了惨剧。
(5)事后应急救援处置
事故发生后,沙特民防和急救部门出动4000多人、200多辆救护车和14架直升机参与紧急救援。在踩踏事件发生后,沙特当局不再允许朝觐者自行前往仪式地点,安排专程大巴接送朝觐者统一前往投石驱邪桥,运力目标达到每小时通行50万人,以确保朝觐者能够按照沙特当局的安排进行朝拜活动,最大可能地减少人群自由的无秩序参与和流动。[10]
(三)纽约时报广场跨年活动
1.活动概况
从1904年开始,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每年除夕举行迎新年活动,1907年起增加水晶球降落倒数计时活动,每年皆能吸引超过百万民众到现场观看。2014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倒数计时活动从下午3时一直进行到午夜过后,数十万人到现场参加了活动。[11]
2.活动分析
(1)信息提前公布
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活动由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进行策划和实施,跨年所有活动,都由他们统一管理。从12月中旬开始,市政府、警察局就开始在各地方电视台、网站等媒体提前广而告之,通报广场附近道路车辆限行的具体路段、时间、聚会的注意事项等,让所有计划前来参加活动的游客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比如,由于交通管制,必须乘坐公交车到达附近区域等等。而运营机构每次活动前,也都会提前公布信息,包括活动路线的规划、活动时间、游客注意事项、应急逃生要点等。
(2)现场划分区域
纽约时报广场活动当天将广场分割成许多区域,每一个区只允许一定数量民众进入,且人数饱和时只出不进,保证了人群的单向流动,避免出现人流对冲。警方在所有区中间都设立只有警察和救护车可进入的应急通道,确保所有的区在发生意外时,警察和救护人员能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同时留下的通道也可作为应急疏散通道。活动结束后,人群散场也是按区域有序放行。当前面街区的人在撤出时,后面街区的人被要求等待。铁围栏一个接一个慢慢地开放,避免了过多的人群集中流入街道。
(3)充足警力全程监控
划分好的区域之间有铁围栏进行间隔,警察在一旁监督观众入场情况,控制人流速度和人流总量,不允许停留,根据人流情况及时关闭入口限制人数。还有大量警察混入人群,随时对人群的行动状态现场监管和调整,在发现过激行为和突发状况时第一时间进行警告和处理,人们见到警察也自动会形成一定间隔空间,有助于减少拥挤。
(4)提前进场,交通管制
12月31日凌晨到来年1月1日凌晨,南北向的第六大道、第八大道之间,东西向的三十三街到五十九街都禁止停车。从12月31日早上4点开始,部分街区就开始禁止车辆通行。大约早上10点,人群开始进场。进场持续6个小时,到下午4点左右,参加活动的民众基本已进场完毕,警方开始对现场的出入口严格管制。错过这个进场时间的民众难以进入活动中心场地,只能在周边地区感受活动氛围。从12月31日晚上7点钟开始,时报广场附近的地铁站出入口都会暂时关闭,直到1月1日零点再重新开放,地铁也不再在这几个站停留,从而保证不会有更多的人前往该地区。[11]
以上三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的比较如表1所示。
四、人群聚集踩踏事件一般成因及演化机理
由以上三个正反典型案例不难看出,2014年上海外滩跨年活动和2015年沙特朝觐都出现了严重的踩踏事件,而这两个地区都是经济条件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应急管理意识和水平。对于上海,从
活动筹备阶段就暴露出风险意识严重不足,对活动的风险没有清晰的分析和认识,导致了应急准备和现场的应急力量缺乏,在人群完成了聚集阶段的积累、变得拥挤时,有关方面仍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未能及时增派警力,打断人群向下一阶段发展,最终导致现场事态的失控。警方决定增派警力时,赶来增援的警力已经无法控制现场的人流流动,人群冲破了警戒线,在台阶这一高危人流对冲点最终发生了意外事件。而沙特有关方面虽然具有风险意识,对人群聚集风险进行了识别,试图通过限制人流增加通道等方式进行疏解。虽然由于参加朝觐活动的人数众多,现场人群的大量聚集难以避免,但可以通过适当的引导,保持人流的持续流动性,避免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避免出现争抢和推搡,从而力求避免停滞阶段以及拥挤阶段的出现。然而沙特当局在活动现场缺乏应有的秩序控制,对人流路线的规划和引导出现了问题,未能强制性维持好现场秩序,最终也导致了现场的失控。与二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活动年年成功举办。
从三者的经验和教训中可以看出,大型城市广场活动的安全保障和应急管理环环相扣,从事先的应急预案编制准备及演练到现场的秩序控制、应急监测预警、应急力量协调调配、交通后勤保障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全面和全过程科学的规划和应急管理。一旦在某一环节某一阶段有所疏忽,人群的聚集风险就会增加,并且在活动过程中破坏性能量不断积聚,人群的聚集向着踩踏事件的发生转化。如果在发展转化过程中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节和干扰打断,踩踏事件最终就会发生,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损失。而从以上典型案例也不难分析出人群聚集踩踏事件的一般成因及演化机理。
(一)人群短时间内在相对狭窄空间大量密集
相关研究指出,人群密度与踩踏事件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人群在静止状态下每平方米站有7个人,在人群走动情况下每平方米5个人,就会到达人体的极限值,极有可能发生意外风险。此时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极度狭小,会出现呼吸困难、心慌心悸等严重反应,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反应能力,甚至出现意识的丧失,昏迷倒地,导致踩踏事件的发生。[12]因此在到达这个极限值前就要及时疏导人群,否则随后的人群密度就更加难以控制,灾难也就不远。
人群密度过大会引起个体的不适感。个体希望与周围的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太近会引起心理上的厌恶情绪,而这种逃离人群的冲动加上身处人群之中难以对现场情况做出全面正确的研判,会使人群的秩序出现波动,发生意外的风险性增加。
同时,在人群聚集中,单个人的运动受前后左右人群密度和间隔空间的影响,即受周围人群的影响,主要是前后人群的影响。由于人们的目的和任务不尽相同,个体之间的身体素质和行为之间的差异较大,行走速度会有较大差异。如果人群密集程度较低,其他人会试图绕过运动速度较慢的人;而如果人群密集度很高,或者后面人群形成的压力较大,人们难以绕开人群寻找自己的行进路线,而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又很难统一步调,很容易发生跌倒或绊倒的现象。而紧急状态下,相对狭窄处的有限宽度不仅增加了人群的密度,而且限制了人群快速通行的需求,造成了拥堵,拥堵又增加了事故的紧急程度,此时人群行为可能陷入混乱,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
(二)对聚集人群的数量和场地环境估计不足
广场作为开阔的公共空间,是有人流最大承载量上限的,超出广场最大承载量限制的人群会给广场的公共管理和公共秩序与安全维护带来沉重的负担:超出了承载能力的人流量会破坏广场系统的有序和稳定,给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人群参与爆炸首先带来的是现场人群密度的上升,本身就是极大的风险隐患。对人群的过度涌入和无序参与估计不足可能会导致现场管理人员和设备的不足,无法对人流进行有效的疏导,同时也导致周边交通管制、现场人流准入等措施的不足甚至缺失,最终造成现场的失控。而场地环境中的障碍物的多少、布局结构的差异、疏散出口的设置及提示、现场人群人员结构(性别、年龄、应急训练状况等)及心理承受能力的差异等具体情况的不同,都会影响活动现场安全人流承载量。
(三)广场中的人流对冲点的状况
广场的出入口、拐角处、台阶、坡道、狭窄等处是容易出现人流对冲情况的重要风险点。在高密度或紧急情况下人群总是选择走最短路径达到自己认为最安全的目标,当现场人群行进的路线发生交叉时,来自不同方向的人群相互冲突、“顶牛”、相互阻塞,严重时相对行进的两股人流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情绪失控,形成对抗,极易出现拥挤和践踏而造成大量伤亡。[12]
其中台阶和坡道处往往是最危险的人流对冲点,在台阶和坡道上,一旦有人不慎绊倒,后面的人失去重心就会倒下去、压上去,而后方的人群无法第一时间得知危情,会造成人群的推搡挤压,人群往往会向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续跌倒,堆挤叠压,极易酿成严重后果,造成严重群死群伤。
瓶颈地带也是拥挤踩踏事故的高发区之一。人群从宽敞的空间拥向较狭窄的出入口时,除了正常的人流之外,许多人会从两侧挤入,妨碍正常的人群流动。[13]
由于人群密度增加而在出入口处形成拱形的人群,所有人挤在一起无法顺畅通过。各个方面的力量相互推挤,如有人由于突然失去平衡而被挤倒,就极可能被急于出去或者不明真相的后来者踩踏。
而拐角处由于道路交汇,人的视觉盲区存在,让人难以观察到别的方向人群的流动情况,造成人流在不知情以及无防备情况下的交汇和碰撞推挤,增加了踩踏发生的隐患。[13]
(四)导火索式特殊事件的发生
导火索式特殊事件指会对人群状态造成进一步影响的特殊事件,如发生火灾、现场设备设施坍塌等意外事故或者有人突然弯腰、跌倒亦或者是人群中出现人们争抢的目标如钱币、礼品等。导火索式特殊事件是一种诱因事件,其作用结果是导致人群的不稳定,包括人群出现心理上的波动,人群出现逃避或者争抢的情况,人流行进方向发生摆动,人群行进速度突然发生改变等。
而这种突然的改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正确信息无法得到广泛的传达,会造成人群中信息交流的失效。位于人群后方或者正在排队前进的人群可能不知道前方人群已经积累的压力,继续向前运动,甚至因为收到了错误的信息更用力地向前挤,增加拥挤程度的同时容易使现场秩序失控,进入无序挤压状态,这时便容易发生踩踏事件。
(五)应急疏散通道的不足
由于城市广场作为公共场所,具有场地的开放性、普遍的可达性以及功能的多样性,从而导致参与活动人员的不确定性,而且活动中具有人群密度大的特点,因此在发生紧急事故进行疏散时,多数人往往不熟悉现场救生设施和疏散通道的布置,或者疏散通道不足或疏散通道被堵塞,导致疏散困难。人流的密度过大而得不到及时的疏解,给踩踏事件的发生带来重大的隐患。
在人群大密度聚集的情况下,一旦发生踩踏事件,若不能保证及时有序的疏散,给伤者的及时救援带来了困难,延长救援时间的同时也不利于及时阻止事态的发展,就可能增加伤亡人数,甚至带来更多更大范围的拥挤踩踏,其后果的严重性不堪设想。
五、大型城市广场人群聚集踩踏事件应急管理改善策略
(一)人员方面
1.科学测定城市广场人流承载容量
首先应对城市广场的人流承载容量进行科学测定,不仅要考虑物理容量,还要考虑到举办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安保能力、配套服务能力、天气情况,同时考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等。举办活动前可根据以往的举办经验,对参加者数量及群体结构进行预先的研判,使得活动方案、应急预案更具针对性。常态下和非常态下都可以从运营商的手机定位数据中、监控录像中或通过其他的技术手段大致估算出广场上的人流密度,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人流密度。尤其是在人群进出广场的区域,要确保通道和出入口的时刻畅通。
2.动态关注人群行为情绪,实时监控
在活动现场要对人流分布、人群行为以及情绪进行实时关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参与人数超出预期,活动开始人群兴奋激动,出现了人流留滞堵塞情况等,都要予以格外的重视和警惕。如果影响到了现场的秩序,人群中出现了骚动和不安,发生推挤的现象,无论有没有已经发生事故,都要及时启动应急预警,控制现场秩序避免出现失控,及时通过广场广播等手段播放人流引导和预警信息,及时传递正确有效的信息,避免人群中产生不安、焦躁等情绪。
3.改善民众自救互救安全教育及宣传培训
如果参加活动的人员具有一定的应急求生意识和知识技能,就能够有意识地规避风险,避免往人流密集处移动聚集,万一有意外发生也能在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等救援力量赶到前展开自救和互救,减少生命财产损失,自发维护现场秩序。
在举办活动及节庆日前,需要将相关信息,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内容形式、参与方式、人数限制、交通情况、应急措施等准确全面地覆盖到每个受众,保证群众有足够的时间接受准确充分的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对限制广场出入的情况做好说明解释,避免群众产生不满。
针对公众的安全逃生教育和安全意识的培养要通过常态化的教育和宣传。包括电视、网络、广播等,其特点是覆盖面广、影响面大。[14]可向大众宣传安全行为知识,尤其是对于一些即将举办的涉及到大规模人群聚集的活动,在前期可利用新老媒体对安全行为应急知识进行反复深入的宣传,在宣布活动信息、宣传活动时融入安全教育的内容。可在广场周边地铁站、附近小区、广场入口等特定区域向人群发放安全宣传资料,张贴海报。在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新媒体上发布宣传信息,以保证宣传能覆盖到最广的群体,从而达到公共安全宣传教育目的。
注重宣传方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宣传内容的选取,对高危时间高危地点高危情境进行告知以及特别提醒,增强群众的风险防范和风险规避意识。重点要对群众进行安全逃生及自救互救教育,万一有突发事件如踩踏发生时自己要有自保的能力,学会逃生技巧,在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同时力所能及地利用所学应急知识技能积极展开自救和他救,恢复现场的秩序,避免更大伤亡。
(二)设备方面
1.建立和完善人流监测系统
利用监控探头、手机定位等技术手段,结合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现场安保警卫力量的经验判断,对广场人流量和人流密度以及人群行为进行动态监控,监测现场拥挤程度。通过相应的指标做出预警,根据现场情况调整安保措施,在人流高峰期适时采取措施,必要时及时启动预案进行应急响应,分流疏散人群,确保人群在公共场所内任何区域都不会出现过度拥挤滞留的状态,从而避免拥挤踩踏事件的发生。
2.改善应急信息广播系统
应急信息广播系统方便对人流进行引导,指挥人流的移动和方向,及时发布实时人流情况和广场活动情况,对人流量进行调节,避免人群过分聚集,同时可以及时传递准确的信息,避免人群在拥挤状态极度紧张或者兴奋的情况下,因谣言的传播造成恐慌,及时对人群情绪进行安抚,在拥挤踩踏发生时也可以有效进行疏散引导。
不良的信息传递能导致人群停滞、异向人群相遇、阻塞道路、路标路障被破坏。没有收到信息或者收到错误信息的人们会变得急躁。因此,良好的信息管理有利于人群的分流与疏导,减少事故的发生。要善用大数据手段,充分利用广场上已有的广播系统、指示标志,通过广播播放、现场扩音号召、群发信息、新媒体信息发布、现场电子屏显示等多元信息传播手段,及时、准确发布活动信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人流量预警、警示信息等。
(三)设施方面
1.优化重大节庆等高风险时段广场流线设计
在有大型活动要举办、重大节庆等时间节点上,不管广场是否有庆祝活动的举办,人群很有可能自发地大量聚集进行庆祝和娱乐休闲,往往需要进行非常态管理加以应急应对,对人群进行分流引导,使人群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尽量均衡,缓解人群拥挤。
对路线进行规划和控制。利用护栏警戒线等对现场人流路径进行引导和限定,确保人流的单向通行,避免有行走方向不同的人流相遇,造成推搡拥挤。控制人群走动的速度,禁止逆行,禁止长时间停留。路线中尽可能避开人流对冲点,避免出现路线交叉、异向人群聚集等现象。
2.科学设置疏散通道和引导标识
应急疏散通道是群众在发生踩踏事件时撤离现场、到达安全区域的必要途径。设置应急通道不仅有利于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而且在发生意外的临界点来临之前就可以对人群进行及时分流引导,降低现场的人流数量和密度,避免意外的发生。同时也是对区域空间的补充,留有人员流动的余地。[15]
指示标志是引导人流和开展安全疏散的重要设施,尤其是对于广场场地环境和各项设施不熟悉的游客来说,指示标志的清晰指向性、设置地点的选取、放置的数量等都会对广场上的人群造成影响,合理的设计和放置有利于最优路径设计的实现和迅速安全疏散撤离。
3.严格管理出入口
广场的出入口设置要尽可能科学合理,理论上是出入口越多越有利于疏散。在可以预见的人群聚集期间,还要保持出口和入口分开,保证不会出现反向人流的相遇发生冲撞。并且要根据人流量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如果人流量过多风险增加时,可以适时关闭入口,只出不进,控制广场上人群的增量,防止人流过度涌入,避免危险的发生。
4.排查人流对冲点
排查人流对冲点,将踩踏风险降到最低。拐角、台阶等人流对冲点是最容易造成视觉盲区、最容易发生人群拥挤碰撞的地方,需要予以特殊关注,在路径设计时尽量避开,无法避开的的风险高发地点需要加强警力戒备,在现场维护秩序,避免人群的滞留和相向而行,避免冲撞推挤的发生,确保人群有序安全通行。
(四)管理方面
1.加强现场警力配置
增加警力配置有利于维护广场现场秩序,对现场的人流进行一定的引导,提高人流通行效率,避免拥挤骚乱的发生以及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及时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可以将广场的安保任务划分为若干个安全区,分片分区维护现场秩序,明确责任人负责该区域的安保工作,有效提升对区域情况的掌控和应急能力。要注重对安保人员的应急能力培训,加快应急反应速度,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2.加强周边交通管控
必要时对周边交通包括公共交通进行控制和引导,采取临时定点设卡、重点巡逻等方式,加强疏导管控。出现车流、人流过于集中情况时,及时采取限行、单行等临时管控措施,对公共汽车和地铁封站停运等。通过加强周边交通的管控,降低广场的便利可达性,对人流和车流进行分流,避免人群在广场的过度聚集。
3.加强演练,优化预案
加强应急疏散科学演练,动态优化应急预案。注重平战结合,在日常就应着重加强对聚集踩踏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相关知识的宣传培训和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强化广场管理工作人员和警方、医疗部门等人员和机构的应急培训,将应急协同疏散演练列入日常员工培训必修内容,增强员工应急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应急培训效果和落实,为城市公共安全提供保障。
同时应根据公共安全形势的变化及应急预案演练情况及时修订和动态调整应急预案,加强情景模拟,根据演练的实际情况和应急管理需要的变化,确保应急预案的针对性、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实战性,真正能够为广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防处置提供行动指南。
六、结 语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广场和公共空间以及人群聚集踩踏事件的文献梳理综述,对上海外滩2014年跨年夜踩踏事件、沙特朝觐者踩踏事件、纽约时报广场跨年活动等正反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比较,揭示人群聚集踩踏事件发生成因和转化演变的机理规律,对大型城市广场人群聚集踩踏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建议。
参考文献:
[1]陈竹, 叶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3):44-49.
[2]王维仁. 关于城市广场公共性的思考[J]. 新建筑, 2002(3):15-16.
[3]陈锋. 城市广场公共空间市民社会[J]. 城市规划, 2003(9):56-62.
[4]J.哈贝马斯. 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J].社会学研究, 1999(3):37-38.
[5]徐建芬.基于社会心理视角的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
[6]王建国.现代城市广场的规划设计[J].规划师,1998(1):67-74.
[7]周军.城市广场的规划设计[J]. 山西建筑,2004(8):10 -11 .
[8]金访.城市广场和公共空间与人的活动[J].山西建筑,2010(7):28 -29 .
[9]卢文刚,蔡裕岚.城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应急管理研究——基于上海外滩“12.31”特大踩踏事件的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5(5):118-124.
[10]王波.麦加踩踏事故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EB/OL].(2014-09-24)[2016-06-10]http://news.xinhuanet. con/world/2015-09/24/c_1116671295.html
[11]卢文刚,黄小珍,田恬.中美大型群众性活动应急管理比较研究——基于美国时报广场和上海外滩群众性跨年活动的比较[J].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6(1):101-109.
[12]白锐,梁力达,田宏.人群聚集场所拥挤踩踏事故原因分析与对策[J].工业安全与环保,2009(2):47-49 .
[13]寇丽平.群体性挤踏事件原因分析与预防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6-22 .
[14]余树华,周林生.社区应急管理的定位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46-56.
[15]白锐,梁力达,田宏.人群聚集场所拥挤踩踏事故原因分析与对策[J].工业安全与环保,2009(2):47-49.
[16]卢文刚,田恬.城市广场人群聚集防范踩踏应急管理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6(05):216-221.
Abstract:As a public space and an opening area,city square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gatherings of people,and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nduct the public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public space and the stamede,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Shanghai New Years Eve Stampede,2015 Hajj Pilgrimage Stampede and the New Years Eve in Times Square,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causes and the mechanism of stampede,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emergency disposal of city square stampede is put forward.
Keywords:Urban Governa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City Squares;Gathered Crowds;Stampe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