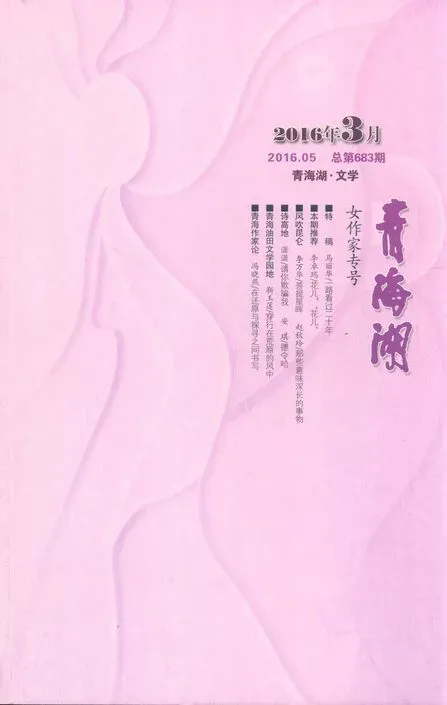坐在菩提树下听雨(散文)
古岳
坐在菩提树下听雨(散文)
古岳
老家宅院里有三棵树,一棵是丁香,另两棵也是丁香。只是一棵是紫丁香,另两棵是暴马丁香。暴马丁香在青海也叫菩提树,此菩提非彼菩提。它应该不是当年释迦牟尼坐在树下觉悟成佛时的那种菩提树,那种树原名叫荜钵罗树,因释迦牟尼在树下证得觉悟而得菩提之名。在植物学分类上,那是一种常绿阔叶乔木,在青海这等高寒之地绝难成活。不过,暴马丁香的确也叫菩提树,塔尔寺就有一棵这样的菩提树。塔尔寺原本是宗喀巴大师的出生地,他被佛界誉为第二佛陀。如此说来,又当是,此亦菩提,彼亦菩提。
乙未年四月,母亲病重,医院告知已无良方。期间,好友提供信息,说云南有良医,便急赴昆明求医问药。回到西宁,遂护送母亲至故土老宅,整日陪伴左右,煎药熬汤,希望能出现奇迹,母亲转危为安。三年前,比这个季节稍晚些时候,父亲也病重,医院也曾告知已无良方,我也将父亲护送至故土老宅静养。一个星期后,他居然能下地走路了,之后,一天天好将起来,我感觉是故土的滋养起了作用。所以,护送母亲回去时,我丝毫没有犹豫过。
其时,芒种刚过,夏至将至,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老宅庭前屋外,也是一派缤纷艳丽。这使我想到了母亲,由母亲又想到了一个听来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俄罗斯盲人乞丐,正坐在莫斯科大街上乞讨,身前摆放着一块牌子,上面有一行文字,只字未提乞讨的事,却写着一句诗一样的话:虽然已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所有行人都被这句话吸引,便停住脚步,向他伸出友爱之手。母亲虽然眼不盲,但因为一直躺在病床上无法起身,也看不到百花盛开的样子。所以,一天午后,我们把母亲小心地抱到一张轮椅上,推到门外,让她看花开的样子,晒晒太阳。在一块开满油菜花的地边,还稍稍停留了一会儿。再次回到屋里躺下后,母亲告诉我,现在她一闭上眼睛,眼前全是油菜花,一片金黄。之后的几天里,只要天气晴好,我们都会推着她到田野上转转,有时候,也会在院内的花园前坐上一会儿。直到有一天推她回来之后,她好像很累的样子,才停了一两天。
老宅门前,除了绿树花园就是庄稼地;庭院里面,除了一小块水泥地坪就是一座花园。房前屋后的绿树少说也有二十几种,大都是乔本类开花植物,其中也有多棵菩提树,有两棵还在开花,其香仿佛紫丁香,却远比紫丁香沉着幽远,清雅耐人。花园里也有十几种植物,都是草本和木本类观赏花卉。这些绿树花草是父亲与我共同经营培养的结果,父亲栽种的大多是中用的品种,而我栽种的那些几乎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所有绿树花草,平日里都由父亲照看,而我只在回到老家的时候才有机会打理它们。所以,在老家陪伴母亲的这些日子里,除去守在慈母身边的时间,其余时间,我大多在这些树木花草跟前,给它们松土浇水。
忙完了这些事,而母亲也正好睡着的时候,我就会静静地坐在花园前的那棵菩提树下,喝茶歇息一会儿。几乎每天,我都会有好几次坐在那菩提树下的空闲时间。第一次坐到那菩提树下时,几滴雨落了下来,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我抬头看了看天,天上几乎没有云彩,初夏的阳光照彻山野。侧耳倾听,已经没有了雨声。就那么稀稀拉拉地落了几滴之后,雨再没有落下来,但我依然在静静地听,希望能听到雨声,可是没有听到。再听,又似乎听到了,雨声好像并不在近旁,而是在很远的地方——感觉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正有大雨滂沱。
我忽然想到了两个字:听雨。近一段时间里,这是我第二次想到这两个字,第一次想到这两个字是在一个人的葬礼上。那天,当人们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刚挖好的地穴里,准备填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地穴深处或许有一扇门,那扇门隔开了两个世界。一扇门特地为一个人打开了,从那里进去之后,他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地穴所在的山坡上哭声一片,泪雨纷飞。这时,“听雨”两个字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雨声来自另一个世界。故乡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亡故之后,送葬的队伍里最好没有哭声和泪水,说生者的每一滴眼泪都会化作冰冷的雨点打在亡者的身上,那是凄苦的雨。可是,顷刻间骨肉分离,生者无法挡住眼泪。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亡者正在一个门洞里,回过头来望着我们微笑。一束阴冷的光从那门洞的另一侧照进来,很刺眼。那光芒塞满了整个门洞,以至于他看上去就像是被那一束光托举着。那门洞很深,像一个隧道——抑或是时光隧道吧。很显然,那门洞的这边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那么,门洞的那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他或许已经看见了那个世界,所以,才回眸一笑。可是,除了那一束光芒和那个门洞之外,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当然,这只是我的凭空想象,也许那光芒的实质不是光明,而是黑暗,它挡住了一切,阻隔了一切,使我们无法看到里面的真相——那也许就是死亡的真相,也是生命的真相。
我很清楚,这只是一刹那间闪现在脑海中的一个景象。佛经上说,一念之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生生死死的轮回随时都在进行,须臾不曾停歇过。而在那一刹那里,我甚至想到过,站在那门洞里回头微笑的那个人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孩子,而是我自己。我在我自己的葬礼上。我听到了雨声。雨季如期而至,雨铺天盖地,大大小小的雨滴落下来,我在无边无际的雨中艰难前行。那个世界里没有动物,没有植物,甚至没有泥土,没有你曾熟悉的任何物质——那个世界里的物质看上去更像意识。雨落下来,却不知道落到哪儿去了,没有在地上溅起水花,也没有漂起水泡,它们好像直接钻进地缝儿里,穿越而过,落进了另一个世界里。雨滴不停地落在我的身上,我知道,那其实并不是真的雨,而是另一个世界里人们的眼泪。它穿越时空,纷飞而至,飘落在另一个世界里就成了雨。它从我的身内穿过去,像子弹那样,我甚至能听到它从我身体里呼啸而过的声音。
可能与自己的年龄有关,感觉一过了五十岁,生活中的葬礼一下就多了起来,好像刚刚从一个葬礼上回到家里,又听到另一个葬礼要举行的消息。这当然不是现在亡故的人比以前多了,以前也一定有人从这个世界上不断地离开,而是因为你还年轻,从你身边离开的人还不是很多。即使有,也是隔了足够长的时间,会让你有一个从悲伤中走出来的间隙。可是,这两年不一样了,好像随时都有一个葬礼在等着你。于是,雨声不断,生命中的雨季已经来临。
宅院里有两排木头房屋,一排朝南,一排向东。坐在菩提树下时,我面朝向南的屋子,背靠花园。花园中间有一棵碧桃长得茂盛,它先开花,后长叶子,花早已败去,现在只剩叶子了。还有六棵牡丹,三棵芍药,一棵野生皂角,两棵野生核桃,五六棵大丽花,两棵荷包花,一棵圆柏和一棵大叶杜鹃。点缀其间的是几棵菊花和一溜金银花。有几棵牡丹是今年新栽的,刚长了新叶子,其余几棵牡丹,花也早已开败,最后的一两朵牡丹也在那两天败落了。所有开花的植物,现在只有那几棵芍药。刚回到家时,它们才开始打花骨朵,只几天时间,都已竞相开放。花园的墙上爬满了一种藤类植物,有十几株,是我从城里买回来种在那里的。当时,我是能叫出它们的名字的,现在却都已经忘了。它们有五片像花瓣样很大的叶子,厚厚地覆盖着砖墙。菩提树冠如伞盖,再强的阳光都照不到树下。树下放了两块平整的石头,正好当茶几,抬一把椅子、端一杯香茶坐在树下,就可以安静下来了。
从四月底到五月初的好些天里,都会落下几滴雨来,却一直没有像样地下过。只有两次,淅淅沥沥地下了不到半个时辰。我都站在那菩提树下听过雨,仔细听过之后,我发现,它落在不同的地方所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在那树下,我所听到的其实并不是雨声,而是树叶的声音。雨滴落在水泥地上时,一开始,一落下就干了,慢慢的,水泥地都被淋湿了。再后来,竟然积了薄薄一层雨水。而落在花园泥土里的雨滴,一落下就钻进泥土里不见了。因为久旱未雨,那点细雨对土地来说起不了什么作用,半个时辰之后,那泥土也才泛起一点潮气。
有一次下雨时,我还走出院子,到前面的田埂上去听过雨声。一走出门前的花园和菜地,就是大片的庄稼地,大部分种着麦子,也种了几块油菜。麦子正在抽穗,油菜刚进入花期,金灿灿的油菜花开得正艳。我俯身麦田,将耳朵伸到麦子地里细听,听到的是很轻柔的雨声。雨滴顺着麦秆滑到下层的叶片上,结成了露珠。少顷,又侧身油菜花地倾听,听到的却是很清脆的雨声。雨滴先落在顶端的花瓣上,而后从那里轻轻滑落,落到下层宽硕的叶片上,汪在那里,像一颗颗珍珠,晶莹剔透。想来,那雨滴落下来时一定非常细碎,因为,它落在那一片露珠大小的花瓣上时,那花瓣只是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不仔细看,甚至看不出它曾颤动过。
从田野上回到院中,再次站在那棵菩提树下时,雨已经停了。望着花园里的那些开花植物,我想到一句青海“花儿”的唱词:花开花败年年有,人身才有几遭哩?这是一个设问的句式,但它并无意追问,而是在慨叹人世间的聚散何其珍贵。它提醒人们,对芸芸众生而言,无论你经历过多少次的生死轮回,人生都可能只有一次,转瞬即逝。还不如那些开花植物,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只要到了开花的季节,它们都会如期开放。由此想到母亲,想到父亲,想到一家老小十几口人,今生今世能聚在一个小小的院落里是何等样的奇缘和造化呢?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一大家子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这该是怎样漫长的修炼才能得来的缘分和福报呢?
我是个俗人,俗人总是放不下各种烦恼。母亲病中,守在病榻前,回想母亲一生的经历时,感觉她的烦恼要比快乐多很多,为饥荒、为儿女、为家庭、为年景和收成,甚至为牛羊和天气烦恼。可是,我相信,在她生命最后的这些日子里,她一定感觉到了正是这无尽的烦恼才构成了她珍贵的人生记忆。如果把这多烦恼一下从她的记忆中抹掉了,她会更加烦恼,而不会只剩下快乐。对一个肉身俗人来说,没有任何烦恼的人生不是真正的人生,能放下一切烦恼的人也能放下一切快乐。我想,那就是觉悟了的人,而觉悟了的人就是佛了。
当然,我并没有像佛祖一样一直坐在那菩提树下。每天,我还有一小段时间是坐在自己屋里的。这一小段时间里,一般我都会做同一件事,就是用一管小楷毛笔在一张早已裁好的宣纸上抄写《心经》,至少每天一遍,有时候也会多抄一遍,有一两幅抄好以后就贴在墙上了。《心经》上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很多时候,快乐就是烦恼,烦恼亦是快乐。没有烦恼何来快乐,没有快乐又何来烦恼?
这样下来,一天当中的闲暇时光已经所剩不多,我就利用这点有限的时间观察花草树木、鸟虫飞絮。一天午后,我看到一朵盛开的粉白色芍药里有一只很小的蜜蜂,想必是去采蜜的。它先是向纵深探寻而去,后又在花蕊中间穿行,之后又在一片花瓣上向上攀爬,几经努力,均无功而返,跌落在花心里。它显得很紧张,像是要急着逃出来的样子。我决定帮它一下,便拿一根很细的树枝伸到它的面前,它像是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一样,一下就抱住了小树枝,我轻轻地取出树枝,刚一到外面,它就飞走了。看来,它真是在逃命。可我不知就里,蜜蜂采蜜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怎么会心生恐惧呢?过了一两个时辰,再去看那一朵芍药时,我仿佛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朵盛开的芍药所有的花瓣已经再次闭合,将花蕊深藏在里面。也许它会再次盛开,也许这是败落的一个前兆。如果那只蜜蜂还在里面,它肯定是逃不掉了。于是,对它心生敬畏,它竟然在几个时辰之前就能预知危险之降临,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后来的几天里,我才发现,一朵盛开的芍药,每天傍晚来临前就会重新闭合,至次日早上太阳出来时,又会重新绽放。很显然,蜜蜂们早在我之前就已深谙其中的奥妙。
也是在这天下午,我刚坐在那棵菩提树下,便被几声悦耳的鸟鸣声所吸引,确切地说是两只鸟的鸣叫,一只是布谷鸟,另一只是喜鹊,它们的鸣叫声均来自屋后那一排高大的白杨。那几天,每天的某一个时刻,它们总会站在中间的那棵杨树上叫个不停。那棵树上有一个喜鹊窝,好几年前就已经在那里了。当布谷鸟站在一根树枝上开始鸣叫时,又总会听到喜鹊的声音。我猜想,喜鹊可能正在孵小鹊,而布谷鸟说不定已将自己的蛋偷偷产在了鹊巢里,盼着孵卵的喜鹊替自己孵出一只小布谷来——这是布谷鸟一贯的习性和做法。喜鹊则不知所以然,还以为布谷鸟眼馋它的鸟蛋——其实,布谷鸟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可能早已实施完毕——于是,喜鹊在自家门口叫骂,让布谷鸟离远点,布谷鸟却装出一副被冤枉的样子大呼小叫,无论喜鹊怎么威胁,它就是不肯离开。
我可能有十几年没有听到布谷鸟叫了,这次回老家再次听到布谷鸟叫,感觉是一个吉兆,我希望与母亲的安康有关。这些年因为封山育林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故乡的山野又一派葱茏,曾经砍伐殆尽的树木重新又长满了山坡。加之,农田里施用的农药比以前也有所减少,一些记忆中的鸟儿又回到了故乡的山野。除了麻雀没有以前那么多之外,鸟的种类和数量甚至比我小时候还要多。其中有好些长着五彩羽毛的鸟儿,以前,我只在深山老林中才见过的,现在却在房前屋后飞翔着,鸣叫着。一种俗名野鸡的雉鸟,甚至常常飞到人家的院子里咯咯地叫着。有一天,我还看到两只胖嘟嘟的布谷鸟就在门前的空地上悠闲地漫步,我跟在后面走了好远,它们只是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而后依然不紧不慢地径自走去,直走到一块油菜地边上,才晃晃悠悠地钻进了油菜花丛中。无论是对故乡的山野,还是对那山野以外的大千世界,这都称得上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将目光从屋后的白杨树上收回时,又被庭院中飞来飞去的一群小精灵给截住了。便侧目望向庭院上方,这一看却令我大吃一惊。那个小小的庭院中竟然飞舞着无数个幼小的生命,这还是肉眼所能看到的——而肉眼所无法看到的一定会更多。这些飞行者大都是一些飞虫,但也有一些杨絮之类的飞行物,其中有一只像蜻蜓那么大的黑色蚊子,它是小院飞虫中的独行侠。杨絮如果漫天飞舞,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它们会落得到处都是,像雪花,却远没有雪花那样讨人喜欢。但是,如果只有几点杨絮在半空中轻轻盈盈地飞舞,那却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它居然也能自由地飞翔,甚至在落到地面之后也能重新飞舞起来。
坐在那棵菩提树下时,不断有五颜六色的飞虫落在你的手上、脸上、鼻子上,甚至直接飞进耳朵里,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有的甚至会叮咬,让你感到轻微的疼痛。这天下午,无意间,我还看到一条足有三四米长的蜘蛛拉的丝线,从一棵丁香树直接拉到了对面的屋顶上,看上去就像是一丝流云,令人叹为观止。且不说它拉这样一条直线有什么用——也许是一座蜘蛛用的高架桥吧。我惊讶的是,它是怎么做到的,难道它能凌空飞渡不成?要么它们一定也有远距离高空作业的特殊装置了,要不,以人类的常识而言,这是绝难做到的。
很多时候,坐在那菩提树下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人,有老有少。但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我,只有父亲。与他坐在那树下时,他只默默地坐着,不说话。我能看出来,他很担心母亲的病,但并不表现出来。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树下对他说,你去看看母亲呗。他先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像是没有听见。我看了他一眼,他才轻轻点了点头,之后向母亲的屋子方向望了一眼,便不做声了,我也没再说什么。我知道父亲的秉性,他能把天大的事都装在心里,而不露出半点神色。沉默。再沉默。这是他不变的神态。任世界风云变幻,潮起潮落,他自岿然不动。
五月初的一天,又下了一点雨,前后也不到半个时辰,下得也不大。我又坐到那菩提树下听雨,直到雨过天晴。雨停的时候,一只小蜜蜂一直停在我眼前,飞快地拍打着一对小翅膀,好让自己能保持飞翔的状态而停留在半空中。如果你不细看,根本看不出它是在飞,而更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吊在了半空中。它朝着我发出轻柔的嗡嗡声,两只小眼睛一直定定地盯着我看。我觉得,它就是几天前我帮着从花心里逃生的那只小蜜蜂。后来,我才发现,它也并非一直停在一个地方不动,只要有什么蚊虫飞近它的领空,它会立即作出反应予以攻击。那反应之敏捷、攻击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攻击之前,它几乎不做任何准备,需要攻击时,直接弹射出去,像一支箭。它所攻击的对象,有些我是能看见的,有些我是看不见的。所以,它在我面前停留飞舞的那一会儿里,其他蚊虫皆不得靠近。只有一只黑蚊子在它下方超低空飞行——那可能是一种隐蔽方式——它比前几日看到的那一只黑蚊子稍小一点,但也有一只小蜻蜓那么大了。
足足有半个多月时间里,尽管很多天的天气预报都说次日有雨,但是,雨一直没有下下来。我想,它可能落在了远方,譬如法兰克福或巴黎,譬如巴西高原或智利山地。这使我想到,智利有一种民间手工艺品或者说是一种民间乐器,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听雨。它是用仙人掌的枝干做成的,里面装有细沙,两端封死之后,拿起来置于耳边,使其倾斜,便会发出沙沙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是雨点落在树叶上发出的声音,美妙至极。那年去上海看世博会,在智利馆巧遇此物,很是喜欢,买了一根把玩,至今爱不释手。有它在,即使看不到雨,即使在没有雨的季节,我也能听到雨声了。
直到端午节前一日,一场像模像样的雨才下了起来,从大清早开始到午夜时分一直在不停地下,虽然不大,却也细密。临睡前,我还煞有介事地到那菩提树下站了一会儿,听雨。因为有菩提树的伞盖,雨滴不会直接落在身上,落到身上的是菩提树叶上的雨水。这时,我所听到的雨声已不那么清脆悦耳了,因为树叶都被淋湿了的缘故,雨滴落在菩提树上所发出的声音,多了些零乱,而少了些韵致。
人生苦短,行色匆匆,难得有专门听雨落、听雪落、听风过、听花开、听鸟鸣的时间。久而久之,我们已然忘怀了雨落、雪落的声音,也想不起风吹、花开和鸟鸣的声音了。可是,也许这些才是生命里最值得聆听的声音。
我无法预知,母亲能否过得了这个坎儿——也许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一个坎儿,也不知道日后,我还会不会坐在那棵菩提树下听雨,但可以肯定的是,父亲、母亲,还有我自己,最终都会走进一场如期而至的雨,消失在绵绵不绝的雨幕中,无影无踪。那么,谁还会坐在那菩提树下听雨呢?谁又会站在那雨幕中回眸,拈花微笑呢?好在那棵菩提树一直会在那里,只要有人坐在那树底下,就会听到雨声自远方纷纷而至。
责任编辑唐涓
作者简介:古岳,又名野鹰,本名胡永科,藏族,1962年生人。高级记者,青海省作协委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近百万字文学作品发表出版,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散文》《散文选刊》《新华文摘》等刊物,并收入多种选集和沪教版初中语文课本,出版《谁为人类忏悔》《写给三江源的情书》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