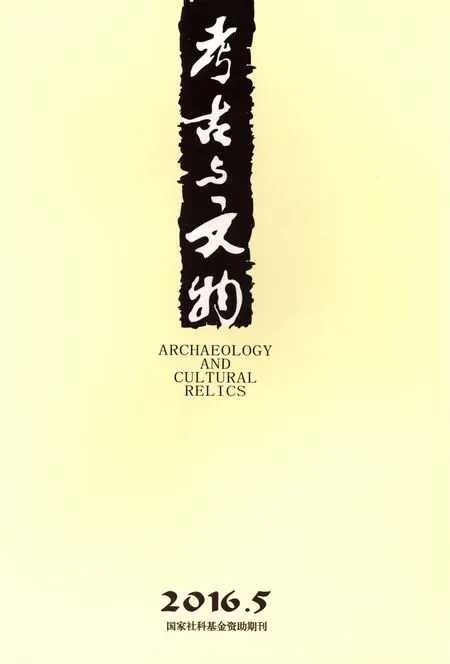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死因蠡测*
——关于史前灾难事件的探索与思考
朱永刚吉 平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死因蠡测*
——关于史前灾难事件的探索与思考
朱永刚1吉 平2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哈民忙哈,房址,人骨,史前灾难,鼠疫
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一系列重要发现,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数座房址内揭露出大批人骨遗骸,场景之震撼在我国史前考古中极为罕见。种种迹象表明遗址是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那些罹难者为何集中于房址内?本文通过凝固历史瞬间保存下来的情境观察和人骨反映的死亡年龄统计,结合自然环境与生业方式分析,在排除地质灾害、人为杀戮等灾难后,提出距今5000多年前科尔沁沙地曾暴发过瘟疫。导致哈民忙哈居民群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应缘于一场肆虐的鼠疫,并由此引发了辽西新石器文化的变迁。
哈民忙哈(蒙古语意为沙坨子)遗址位于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艾勒村东,西北距舍伯吐镇约20公里,南距通辽市约50公里,是迄今在科尔沁沙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史前聚落。2010~201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总计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54座,灰坑57个,墓葬12座,经钻探确认环壕2条[1]。
遗址经三次发掘,已基本掌握聚落规模和布局特点。从遗址已揭露部分来看,所有房址门道设于东南,朝向同一,成排分布,虽然个别房址在排列中位置略有参差,但基本整齐。灰坑和墓葬散布于房址周围,外围已确认有环壕,显然整个聚落经过周密的规划设计。初步探明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规模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中心聚落。该遗址的层位关系简单,表土层为0.15~0.9米的风积沙土,最厚可达1.25米,第2、3层为文化堆积(因风蚀作用局部缺失第2层)[2,3]。所见各类遗迹皆开口2层下,除发现个别灰坑打破房址外,房址之间没有确认的叠压打破关系,出土器物组合亦没有明显差别,基本可视为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所有房址结构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有凸字形门道。居室面积一般在15~20平方米左右,最小的仅6.8平方米,最大的一座36平方米。圆形灶坑位于居室中轴线偏向门道一侧,灶坑内残留有陶具或陶片等支撑物,灶底见有草木灰。柱洞有明柱和半壁柱两种,一般沿房址穴壁内侧排列,分布较规律。多数房址居住面摆放有完整陶器及成组的石器[4]。

图一
哈民忙哈遗址的数座房址内揭露出大批人骨遗骸,本文拟通过人骨观察及情境分析,结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推究其原因。
一、情境观察
截止2012年,在已清理的54座房址中有8座房址居住面上发现有人骨,F32、F37和F46,F40和F44,F48和F45,F47分属五排,彼此相邻,除F32位于发掘区中部,其余均偏于遗址东侧,距环壕(G1)13~30米不等,出土人骨的房址在聚落布局中位置相对集中。人骨鉴定报告对F40、F32和F37进行了详细的性别与死亡年龄统计[5]。
F40室内面积18.5平方米,居住面上最小个体数为97具,除西南角外,堆弃的人骨层层叠压,场景触目惊心。出于对现场的保护,无法对叠压的人骨全部鉴定统计。在可观察的个体中,性别明确者21例,男性7例,女性14例,男女性别比例为1∶2。年龄段明确者58例,未成年个体12例,成年个体46例,未成年个体与成年个体的比例为0.26∶1。人骨姿态除个别能看出侧身、俯身、仰身外,头向面向各异,无明显规律。其中东北壁至少有9个颅骨聚拢在一起,在房址中部偏北也有类似现象,尤其灶坑至门道之间不足4平方米的范围内,骨架上下叠压,多达三层。在有限的空间里,出土人骨的密度如此之高,显然不是正常现象(图一)。
F32室内面积约36平方米,出土人骨13例。性别明确者1例,为男性。年龄段明确者5例,其中24~35岁1例,36~55岁4例,未成年个体与成年个体比例为0.14∶1。房内堆积保留着大量纵横相交的炭灰条,经仔细逐层清理出的木架构痕迹,可基本对屋顶的建筑结构进行复原。现场观察,人骨架紧贴居住面上,位于房址中部偏西的一具为仰身,近于门道的一具为侧身屈肢,灶坑周围聚集的人骨不少于5~6个个体,其余散见的人骨姿态难以辨认。该房址因失火而焚毁,大多数人骨被坍塌的木架构所叠压(图二)。
F37室内面积16平方米,共出土人骨22例。性别明确者,男性3例,女性1例。年龄段明确者14例,其中3~6岁2例,7~14岁2例,15~23岁1例,24~35岁7例,36~55岁2例,未成年个体与成年个体比例为0.42∶1。F37居住面上的人骨大体可分为四组。第一组,4、5、7~14、20号人骨集中在灶坑周围,颅骨聚拢;第二组,位于房址后部,16、17号身体卷曲,一个仰身一个侧身,15、22号只保留有下颚部和肢骨。第三组,在灶坑左侧,6号为头骨,簇集的肢骨不少于2个个体,姿态难辨;第四组在灶坑右侧,可识别的人骨不少于4个个体,除2号为侧身屈肢外,均不完整(图三)。

图二
其余几座房址的鉴定结果:F44人骨14例,死亡年龄明确者,4~12岁4例,25~30岁3例,35~45岁3例;F46出土人骨22例,可鉴定死亡年龄6~8岁1例,30~40岁5例;F47出土人骨10例,可鉴定死亡年龄5岁左右1例,10~11岁1例,35~50岁3例;F45和F48只发现1~2例人骨[6]。
通过进一步观察,我们还注意到以下情境。
1.出土人骨的房址皆由居室、灶坑和门道组成。遗物集中出于居住面上,在人骨周围既有摆设的生活器皿也有成套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房内堆积包含遗物很少,室内未发现举行某种仪式活动的特殊设施,与一般房址比较在建筑结构和形式方面没有明显差别。
2.所有人骨遗骸均紧贴于居住面上,聚集在同一房址内的死者是否属于一个家庭或有直系的血缘关系尚无法解释,但大多数人骨方向不一,姿态零乱,甚至上下叠压、堆弃,而非刻意摆放。于此可以判断房址内出土的人骨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居室葬。
3.已清理出的几座木质结构坍塌的房址内多有人骨遗骸,如F32、F37、F44、F46等,尤以F32保存的最为完整。这些房址都有过火痕迹,房屋似失火或有意焚毁而废弃的。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人骨的房址内大多发现玉器,其中F37出土6件、F44出土2件、F47出土8件,数量最多的F45和F46各出土16件,种类有圆形璧、圆角方形璧、双联璧、钺、勾云形玉佩、玉匕、齿形器、玉璜、玉坠等饰物,数量可观,制作精致[7]。这些玉器具有红山文化的形制与风格,不同的是红山文化玉器一般只见于墓葬和礼仪场所,而哈民忙哈遗址的玉器均发现于房址内,或见于人骨的颈部,或散落腰腹间,应该是随身佩带之物。玉器除作为装饰品外,还有祛灾祈福的功能,也表明所有者的身份与地位。从这几座房址内佩带玉器的人骨姿态分析,体位并非有意摆放,故判定他们不是自然死亡,死因当与突发事件有关。
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共发现人骨181例,在对罹难者死因作出判断之前,有必要对当时的人口数量作粗略的估算。根据2010~2011年发掘的43座房址居住面积统计,10平方米以下的房址9座;10~15平方米房址22座;15~20平方米房址6座;20平方米以上的6座。其中最大一座36平方米,平均面积为14.4平方米。参照新石器时代早期贾湖遗址,面积大体相同房址的居住人口为3~11人[8],推算哈民忙哈遗址已发掘的54座房址,人口规模在162~594人之间。按仰韶文化晚期大河村遗址,每座平均14.8平方米的房址住7人左右计算[9],哈民忙哈遗址的人口数量大约为378人。如果这样一组数字能基本反映当时的人口规模,那么哈民忙哈房址内出土人骨181例(最小个体数),已经超出了理论推算人口数值的下限,或者占到了可计算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如此高比例的死亡率显然不是正常现象。综合前面对房址内人骨数量、位置、姿态、死亡年龄段和出土遗物的分析,充分证明哈民忙哈房址内大批人骨属于群体性非正常死亡,而堆弃人骨的房址应为罹难场所。

图三
二、非正常死亡分析
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指人为或外力作用导致的非自然死亡。依情境观察,哈民忙哈罹难者相继死亡时间不长,而短时间内造成大批死亡的原因,不外乎血腥暴力的聚落间争斗、人殉人牲的祭奠和地震、水灾、火灾以及瘟疫等灾难事件。
哈民忙哈遗址介于西辽河及其支流新开河之间,地处西辽河平原东部科尔沁沙地的腹心地带。遗址坐落在一片沙岗上,西北部被一条古河道所环绕,东南部地势平坦,四周为绵延起伏的沙丘,草甸、泡沼错落其间。由于过度垦殖放牧和持续干旱,现地表水已完全干涸。遗址被较厚的风积沙土层掩埋,所揭露的房址周围活动平面上散布有较多动物骨骼和少许陶片,其下为土质致密很少含遗物的白沙土。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各探方、房址堆积均没有发现淤土、水渍层和被洪水裹携的堆积物。这里距新开河直线距离约15公里,遗址周围既无突兀陡峭山石,也不见泄洪沟壑,更没有发现地震形成的断裂、错落、移动等层面构成现象,所以应该排除该遗址因不可抗拒地质灾害毁灭的可能。
一般古代居民非正常死亡最直接的判断就是观察骨骼是否异常,哈民忙哈人骨组鉴定结果,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肢解、创伤、钝器砸击等痕迹,找不到杀戮行为造成群体死亡的直接证据。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遗址部分房址坍塌的木构架可见明显过火痕迹,是意外失火还是有意焚毁不好判断。但从F40高密度堆弃的人骨和F37、F44、F45、F46、F47、F48几座房址内发现有佩带玉器的罹难者分析,似乎也不支持意外失火原因导致的大批非正常死亡。如果房址为有意焚毁,那么一定是遭遇突发事件的仓促之举,乃至于当事者还随身携带着珍视之物。
哈民忙哈居民大批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排除地质灾害、火灾和人为杀戮行为外,我们认为最有可能是瘟疫导致的灾难事件。就这一立论,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哈民忙哈遗址已发掘的12座同时期墓葬,除2座(M6、M12)合葬墓外,其余均为单人仰身叠肢葬,即下肢叠折于胸前,似有意捆绑后入葬,这种葬俗很特殊,且少有随葬品。这些墓葬位于发掘区的东南部,大多散布于房址周围,目前在遗址外还没有发现专门的墓地。与正常死亡埋葬不同,更多的人骨发现于房址居住面上,姿态各异方向不一,甚至出现F40那样人骨层层叠压不可思议的现象。可以想象当灾难发生时,人们还可以把死者按已有习俗单独埋葬在房址周围,而随着灾情扩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利用房址抛弃尸骨。后期因暴戾肆虐,整个聚落更是陷入极度恐慌中。房址内尸体堆积的现象是逐次拖入的结果,而且越靠近门道处叠压愈厚,正是这一情境的真实写照。是什么原因导致哈民忙哈居民在较短时间内相继死亡,瘟疫流行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其次,根据哈民忙哈人骨死亡年龄统计,居民平均死亡年龄为26.8岁。其中,15岁以前的未成年期占24%,其他几组不同年龄段死亡率分别为,15~23岁青春期为10.4%,24~35岁壮年期为35.4%,36~55岁中年期为30.2%[10]。死亡年龄段主要集中在未成年期、壮年期和中年期三个年龄段,其中未成年期按正常理解死亡率偏高。考虑到婴幼儿骨骼钙化程度低和易受潮湿、酸性土壤腐蚀等因素,估计这一年龄段的实际死亡率可能会更高。由于未成年个体缺乏免疫力,是传播系统中最容易受病毒感染的群体,当灾难发生时必然导致高死亡率。在目前已发掘的史前灾难性遗址中,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庙子沟遗址具有代表性。通过对庙子沟遗址房址包括室内窖穴出土人骨(20例)年龄统计,平均死亡年龄22岁,15岁以前未成年期占35%,15~23岁青年期为20%,24~35岁壮年期为30%,36~55岁中年期为15%[11,12]。与哈民忙哈各年龄段相比较,庙子沟组未成年期死亡率更高,壮年期两者较接近,中年期哈民忙哈组高于庙子沟组。两者的共性特点是,未成年期死亡率较高,表现异常。有学者认为庙子沟遗址的废弃是因瘟疫爆发造成的群体死亡事件[13]。哈民忙哈与庙子沟两地虽相距近千里,但自然环境背景相近,按逻辑推理,与庙子沟组死亡年龄结构相似的哈民忙哈群体,也可能处于同样原因导致的灾难。根据1950~2009年我国各年龄段鼠疫发病死亡统计结果,儿童(0~9岁)和老年人(60岁以上)鼠疫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各年龄组[14]。这也一定程度反映出某种瘟疫死亡率在不同年龄段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可以参照不同年龄段死亡率的相似性来推测死亡原因。
第三,如果判定瘟疫是导致哈民忙哈群体性非正常死亡的原因,还应该重点关注食物来源和生业方式。哈民忙哈遗址动植物遗存丰富,食物来源具有广谱性特征。通过对遗址出土近万件动物骨骼的种属鉴定和分类统计,包括哺乳动物、爬行动物、软体动物、鸟类和鱼类,五大门类共38个种属[15]。哺乳动物占可鉴定标本总数的三分之二,种类有东北鼢鼠、大林姬鼠、黄鼠、鼠、黄鼬、麝鼹、野兔、獾、貉、狐狸、狼、獐、狍、梅花鹿、马鹿、猪、牛、马等18种。按统计数量排序,野兔标本达5003件,最小个体数315个,远超其他哺乳动物;猪骨980件,最小个体数29个;狍骨195件,最小个体数为16个;东北鼢鼠117件,最小个体15个;狐狸39件,最小个体4个;狼38件,最小个体3个。遗址出土的猪骨数量占到哺乳动物的15%。野猪与家猪区分的标准,通常以臼齿的长度值作为比较参数。经比较研究,哈民忙哈遗址猪的M3长度明显大于家猪,与野猪对比组数值接近。从猪群的年龄结构来看,在40件可判定年龄的标本中,1岁以下占15%;1~2岁占42.5%;2~3岁占20%;3岁以上占22.5%,各年龄段分布较均匀,数量差不大,可以进一步确认该遗址出土的猪骨为野猪[16]。哈民忙哈遗址动物遗存研究认为,经鉴定的所有标本均为野生动物,尚未发现饲养动物。研究者还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进行了统计,精略计算出獐、狍子、梅花鹿、马鹿、野猪、牛、马、野兔、环颈雉等9种动物产肉量为4138.5公斤。其它动物如各种鼠类、鸟类、贝壳类、鱼类,虽然个体较小,但采食量较大,对肉食的贡献率也不可忽视。从已掌握的材料分析,哈民忙哈居民经常性捕食动物以中小型哺乳动物和水生动物为主,其中,野兔的数量惊人,按统计数据占到哺乳动物总数的75%,东北鼢鼠和其它啮齿类动物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兔和鼠都是草原动物,繁殖力极强,且易于捕获,是能够提供收益的重要食物来源,然而对这类动物的大量捕食却潜藏着致命危险。
在哈民忙哈遗址发掘过程中,植物考古学者对房址、灶坑、灰坑、环壕的土样以及部分陶器内的包含物进行了全面提取。经浮选鉴定,人工栽培作物有粟、黍、大麻;野生植物包括蔾、狗尾草、野稷、马鹿、大籽蒿,另外还发现碳化的蕤核和香蒲等[17]。粟和黍是燕山南北地区旱地农业的主要种植品种,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因发现人工栽培的粟,被认定已出现了原始农业[18]。哈民忙哈遗址发现的农作物以黍为主,黍与粟相比,更耐旱、更适于瘠薄土壤。然而,从浮选结果来看,黍仅占0.08%的比例,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十分有限。在野生植物中,大籽蒿的出土数量最多,约占浮选植物总量的99.9%。大籽蒿也称“白嵩”,籽实为瘦果倒卵形,可食用[19]。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阿鲁科尔沁旗蒙古族就大量采集野生植物作为粮食代用品,在经常食用的13种野生植物中就有大籽蒿[20]。通过对石器工具的研究,有证据显示哈民忙哈居民强调植物根茎与坚果类食物的利用,如蕤核、香蒲,尤其是富含淀粉的蕨根类植物。蕤核系果仁类,味甘、性温、含油;香蒲是一种水生植物,其根茎烧烤后可直接食用;蕨根经浸泡、捶捣、过滤沉淀后,可制成食品。面对科尔沁沙地气候、环境诸多不利因素,在可利用资源的条件下,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生业方式和文化适应的反映。
综上所述,狩猎在哈民忙哈遗址的生业方式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以采集、捕捞为补充。从浮选结果来看,农业是存在的,但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有限。总之,哈民忙哈居民对攫取型自然经济的依存度较高,食物来源具有广谱性特征,包括捕食在干旱、草原地带活动的啮齿类动物。就微生物寄生条件而言,各种啮齿类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因大量捕食就有很大机缘转移给人类宿主,一旦被感染的个体迅速传播开来,必然导致大面积的发病和死亡,使整个群体遭受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最终酿成可怕的灾难。
三、推导与蠡测
疫病学理论认为,人类的许多传染病与动物密切接触有关联,是因卷入动物内部的病原循环体系而发病。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指出:“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的关注”[21]。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通常只感染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传播。在穴居啮齿类动物群体中,这种病原体可以长期延续下去。由于同一洞穴可能交替混居着不同的啮齿动物,所以感染源可成倍放大。鼠疫的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其宿主是种类繁多的啮齿类动物。当人类猎捕、剥食甚至不经意接触携带疫菌的动物时就会被感染,历史上鼠疫爆发的惨剧曾多次上演。
人类记载的世界性鼠疫大爆发有三次。第一次公元6世纪,流行中心在地中海沿岸,所谓“查士丁尼瘟疫”可以确定为腺鼠疫,持续时间达五六十年,“流行极限期每天死亡达五千到一万人”[22]。第二次流行始于14世纪,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爆发,造成了当时欧洲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第三次鼠疫流行于19世纪末,源于中国云南,后经广西、香港传向世界各地,据称其流行的速度、范围都超过了前两次[23]。中国东北是鼠疫的多发地区,1910~1911年鼠疫大规模流行,最初源于满洲里捕获旱獭被感染的狩猎者,后沿铁路由北向南传播,横扫东北,波及河北、山东共六省83县、旗,因疫死亡人数多达6万余[24]。鼠疫大流行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仅黑龙江省双城府,“疫病流行后,人民死亡之多,亦如十四世纪之伦敦。疫行最盛之时,小镇中每日死者三四百人,双城府人口约六万余,不及一月染疫而亡者六千”。“尚有乡间村落患疫而死者,多至不可收拾,防疫队以火毁全村而已”[25]。
地处西辽河流域的科尔沁沙地属于栗钙土半干旱草原地带[26],草本植物以禾本科占优,其次为蒿科[27]。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疾病,其储存宿主是种类繁多的啮齿类动物,科尔沁沙地生态环境具有典型鼠疫自然源地的特点。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虽然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但这一地区仍具备鼠疫自然疫源的条件,只要携带疫源体的各种啮齿类动物世代相传,一旦环境适应就可能形成新的鼠疫流行。根据通辽市下辖6个旗县,98个苏木(乡、镇)疫源地检测报告,近些年时有鼠疫发生,仍潜在大规模流行的危险[28]。
由于鼠疫或其它急性传染病的致命性和短时间特征,很难在骨骼上遗留可观察的痕迹,而目前分子考古学也不具备从年代久远的人骨中提取能够证实鼠疫疫菌的古DNA技术。所以史前鼠疫的研究,往往因缺乏直接证据,还是一个未知领域。但这并不等于无计可施,理性思考决定探索的深度,哈民忙哈遗址群体死亡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基于该遗址房址内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的观察与情境分析,结合生业方式并以民族志材料佐证,我们认为距今5000多年前的科尔沁沙地(也可能波及更大范围)曾暴发过瘟疫,造成哈民忙哈居民群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应缘于一场肆虐的鼠疫。
四、结论
哈民忙哈是近年在科尔沁沙地经大规模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其陶器组合以筒形罐、斜口罐、小口双耳壶、斜直腹盆和弧壁浅腹钵为主,兼有少量的三足罐、带流盆、圈足盘。尤其是麻点纹、方格纹看似在陶器表面滚压形成的纹饰,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点。条形石镐、有节石杵、长方形厚体磨盘、拱背磨棒,以及为数众多的敲砸器、石饼等石器工具也与周邻已知考古学文化不同。鉴于该遗址文化面貌独特,发掘者将其命名为“哈民忙哈文化”[29]。该文化除具有较强的自身特点外,还发现少量的之字纹、彩陶等红山文化陶器和形制风格十分相似的玉器,这表明以筒形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和与辽西地区最发达红山文化的联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在科尔沁沙地只发现一些零星分布的考古遗存,其中没有任何有关这支文化来源的线索。
哈民忙哈遗址所处的科尔沁沙地,位于辽西、松嫩、吉长几个考古学文化区之间,新石器时代这里是连接内蒙古东部与东北地区不同区系考古学文化的交汇地带。科尔沁沙地气候变化敏感,生态环境脆弱,决定了史前人们活动空间与时间的波动性。一般认为陶器风格和器物组合的变化是文化认同变迁或文化更替的反映,但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往往与生业方式的改变有密切关系。哈民忙哈遗址代表的群体,几乎以狩猎采集为生,文化面貌与高度认同的农业型红山文化差异显著,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他们是插入到科尔沁沙地的一支特殊文化群体。目前,红山文化晚期年代认定为公元前3500~3000年左右[30],这与哈民忙哈遗址已测定的一组碳十四数据年代跨度基本一致[31]。共存关系和碳十四数据相互印证,可以判定哈民忙哈遗址年代大体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或处于最晚阶段。
哈民忙哈遗址透视出的史前灾难事件,引发了我们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变迁的思考。从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到小河沿,辽西地区已构建起完整的文化序列。但学者们注意到红山文化在取得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之后突然“崩溃”,继之的小河沿文化使这一地区的发展陷入低谷。从考古调查情况来看,小河沿文化遗址分布稀疏,聚落规模变小[32]。就遗址发现数量和面积而言,与红山文化相比形成明显反差。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口数量骤然减少。是何原因改变了辽西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进程,多年来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全新世(5000~4000aBp之间)的降温事件,使生态环境恶化,导致文化衰落[33,34]。那么是否有另外一种可能,由于哈民忙哈遗址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戛然而止和小河沿文化发展的停滞,与史前波及这一地区的瘟疫有关。本文对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非正常死亡原因的蠡测,或许为这一课题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揽胜—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60年重大考古发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1-31.
[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2(3).
[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的发掘[J].考古,2012(7).
[4]朱永刚,吉平.探索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史前文明的重大考古发现-哈民忙哈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学术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4).
[5]周亚威,朱永刚,吉平.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人骨鉴定报告[C]//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表二,三,四.
[6]朱泓,周亚威,张全超,吉平.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人骨的古人口学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表2.
[7]同[1].
[8]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8.
[9]同[8]:45.
[10]同[6]:表3.
[1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545-558.
[12]刘建业,赵卿.浅析史前居室埋人现象[J].江汉考古,2012(3).
[13]同[11]:539.
[14]刘振才,周晓磊等.中国各类疫源地鼠疫病死率对比分析[J].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第25卷),2010(6):表3.
[15]陈君.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3.
[16]同[15]:61-63.
[17]孙永刚,赵志军,吉平.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研究[J].华夏考古,2016(2).
[18]赵志军.从兴隆洼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C]//东亚古物(A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88-199.
[19]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种子组,形态室比较形态组编著.杂草种子图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246-247.
[20]裴盛基,淮虎银著.民族植物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72-73.
[21][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22]纪树立主编.鼠疫[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2. [23]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年)[J].历史研究,1997(1).
[24]吉林省档案馆.全宗33卷2-563.转引自田阳.1910年吉林省鼠疫流行简述[J].社会科学战线,2004(1).
[25]汪德伟.追记满洲防疫事[J].东方杂志(第10卷),第10号:23.
[26]西北师范大学等.中国自然地理图集[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4:95.
[27]内蒙古草场资源遥感应用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自然条件与草原资源地图[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28]孙巴图,李晓东,罗进才.通辽市鼠疫疫源地疫情现状分析中[J].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2006(4).
[29]同[2].
[30]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234.
[31]采自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5个木碳标本,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测定,树轮校正后年代在公元前3600-3100年之间(半衰期为5568年)。
[32]滕铭予.GIS支持下的赤峰地区环境考古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16.
[33]夏正楷,邓辉,武弘麟.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J].地理学报(第55卷),2000(3):329-336.
[34]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J].科学通报(第46卷),2001(20):1725-1730.
(责任编辑 张鹏程)
The Hamin Mangha site , House foundations, Human remains, Prehistoric catastrophic events, Plagu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 cant discoveries at the Hamin Mangha site in Inner Mongolia is a large amount of human remains found in a few house foundations, which are very rare i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China. All the releva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human remains were abandoned in a sudden even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otential causes and reasons of this event. The authors synthetize evidence from archaeological features, age profi le of human remains, and economic subsistence at the site. After ruling out potential causes such as earthquake and warfa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large death toll might have been caused by a plague in the Horqin Sandy Land 5,000 years ago. This natural disaster also led to a series of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Neolithic Western Liaoning.
*此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哈民忙哈——科尔沁沙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与综合研究” (批准号:12&ZD191)系列成果。碳十四测年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之课题3500BC~1500BC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研究” (编号:2013BAK08B01)的资助。
—— 以岱海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