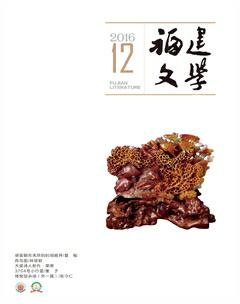完粮
王善余
粮食是土地施与人类的恩惠,这一说法似乎不太确切。实际上,借助土地这个母体,有了阳光、雨露和汗水的合作,历经艰辛、琐碎的流程,才有喂养生命的粮食。一粒粮食,比如稻子、麦子或玉米,不仅有阳光的肤色,还有汗水的光泽;甚至,在风怒雪舞的隆冬,抓起一把粮食,人们也能闻到一股阳光与汗水的气味。也可能想起犁铧的瘦削和牲口的喘息。对此,庄稼人虽不能像诗人那样去描述,却心知肚明。
粮食是有使命的,其使命之重大,可谓无与伦比。这一使命转嫁到庄稼人身上就是辛劳。辛劳像一把利器,插入庄稼人的命运,框定庄稼人的一生;也像一根藤,紧紧缠绕,让庄稼人几近窒息,任何摆脱的企图都是徒劳。
所以,庄稼人唯有顺乎天意,以隐忍和温驯臣服于土地,像牲口那样,风吹日晒,披星戴月,只为一年一度的收成。
若以为庄稼人在土地上挥汗如雨,躬身劳作,任由风雨摧折,日月盘剥,让自己变得衰老而丑陋,只为养家糊口,那是可笑的——地里打下的黄灿灿的粮食,却往往让庄稼人陷入饥饿的恐慌。或许,从未与土地耳鬓厮磨的人,或者说,对乡村生存状况知之甚少的人,对粮食的去向问题,有了热切的关注。
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庄稼人几乎无法累计年月的总数,他们要赶在每年的夏秋两季卖粮,不是在自由市场上的交易,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卖粮的地方是镇上的粮站,出售斤数和价格由公家确定。卖粮是官方的说法,庄稼人有自己的说法,叫完粮,完公粮,缴皇粮。这是一项任务或义务,钢铁一样坚硬,类似于当下的招商引资,无人可以违抗和篡改,除非你沦为乞丐或更换国籍。
完粮是农事之外的仪式。庄稼人拉着平板车,推着独轮车,或担着挑子,扛着袋子,浩浩荡荡,负重缓行,如同走在朝圣的路上,心,无一例外地指向镇上那个粮囤林立的圣地。
完粮,收获慰藉,也收获忧愁。
据我所知,早期完粮不是庄稼人个人行为,而是以生产队为单位,以集体的形式,统一到粮站完粮。那时候的完粮指标由县到公社到大队再到生产队一级级下达,不因天灾人祸而降低,否则,完全有可能牵出政治问题。所以,在完粮上,各级干部都保持着比狗还灵敏的政治嗅觉。那时,每个公社都设有一个粮站,在诸如建筑站、搬运站、食品站这样的七站八所中鹤立鸡群,令人仰视。粮站在编人员统称会计,个个养尊处优,举止和气质绝不会让你误以为他们是建筑站或食品站的职工,就是临时雇用的搬运工或勤杂人员也是一脸冷漠,像受戒的教徒,绝不和你多说半句话。在这个囤积皇粮的神圣之地,他们趾高气扬地接受进贡和礼遇。镇上的饭馆是粮站干部职工常去的地方。店家肩挂毛巾,笑容绽放,孝子一样地迎接。一番觥筹交错、酒足饭饱之后,店家拿到的不是现金,是或多或少的粮食。当然还有额外的收获,这一收获在日后收粮的秤杆上才能兑现,自然鲜为人知。
每逢公社粮站开磅,也就是粮站开始收粮了,各路完粮人马纷纷赶来,聚集在粮站院内的水泥晒场,很像规模盛大的聚会。每个生产队由会计带上几个精挑细选的庄稼汉子去执行完粮任务。往往是,经过一天的等待和烈日暴晒,汗水流得差不多了,况且要遭遇验粮员挑剔的牙齿,司磅员秤砣上的克扣,巡视员睥睨的眼神,双方间唾沫横飞的交涉,粮食才能过磅进仓。这是幸运的事。时运不济者,不是粮食湿度超标就是成色不够,过不了验粮员这一关。如果粮食是一只货船,验粮员的嘴就是船闸,能否通行就在那张嘴上。轮到验收了,验粮员手持一把貌似刺刀的粮食探子,按麻包上一戳,抽出,倒在掌心,拈几粒稻子或麦子,猛扯脖子,扔进嘴,上下牙齿一磕,动作专业娴熟,无可挑剔。这一刻,卖粮人提心吊胆,屏声静气,目光怯怯地随着验粮员的一举一动游移,等着宣判。验粮员是个瘸子,在粮站招募验粮员中,凭着一口坚硬的牙齿脱颖而出。这一特殊的身份让验粮员霸气十足,在四肢健全的庄稼人面前,完全忘记了肢体上的残缺,目光笔直地指向天空,嘴角一歪,阴着脸说,不行,回去再晒两个太阳。拉回去,队长获悉缘由,问给烟没,会计搓手不语。队长怒不可遏,骂会计实心眼,不会办事。
过了验粮员这一关不能说粮食已经脱手,司磅员正盘坐在木椅上,叼着烟,手指敲着秤砣。递上一支烟,显然让司磅员不屑一顾,他的耳朵根、手指间已夹了烟。会计,粮食验收过了。当事人虾着腰,贴着司磅员的耳朵说。司磅员斜睨他一眼,喷着浓烈的酒气,没看我这忙着吗?这一声喝激活了对方的悟性,很快,那人买来一条烟,用报纸包了,塞进司磅员的裆处。司磅员不动声色,秤星上也有些出入。
完了粮,一帮人要到附近的农户家吃饭。这是队长的吩咐,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管饭的人家事先都会得到一个信儿——完粮人中总有一个熟人或亲友——某日某时准备一顿饭。这是一个天大的喜讯,管饭人家喜出望外,认为这是一笔不小的生意。
男人早早扛上鱼罩或渔网,到河里弄一串鱼回来。女人到镇上割一刀猪肉,打几斤散酒,菜园里、鸡窝里一番寻找,东拼西凑,一桌酒席就成了。这天的傍晚,女人在灶房里头顶毛巾,热汗淋漓,出出进进,脚步轻盈,很像在欢度一个节日或筹办一桩喜事。烟囱里的炊烟比往常更有精神,院子里的菜香几乎覆盖了一个村庄。卧在草垛跟的狗抖了抖虚弱的身子,女主人稀缺的笑容,灶房里飘出的菜香,让它有了美好的预测。
一群人来了,有人肩上扛着笆斗,那里装着粮食。这一天,左邻右舍的女人妒火中烧,不是骂男人没本事,就是追鸡撵狗愤愤不平。饭桌上,劣质散酒让一群庄稼人既亢奋又愤怒,说那帮人就是祖宗,对你的粮食吹胡子瞪眼,挑肥拣瘦,比他妈皇上选妃还上心;说瘸子欺人太甚,简直是骑在你的脖子上撒尿……一群人趔趄着出门,男人跟上来递烟上火。女人潦草地收拾下饭桌,小跑着跟到院外,扯着会计的衣角说,下次还到咱家吃,保证伺候好。会计剔着牙,顺手在女人腰上捏一把。
父亲曾为弄到粮食殚精竭虑。
麦收过后,队里的口粮还没分到手,家里的粮袋像饥饿者肚子一样匮乏。在饥饿追杀的时日,为了细水长流,母亲会把红薯煎饼放进竹篮,用绳子系着,吊在房梁上,饭口上才解开绳子让竹篮徐徐降落。母亲像发放救济粮那样,每人给一张煎饼。这是家庭里的计划供应体制。往往是,生火做饭的时候,母亲如临大敌,手伸进粮袋掏了又掏,试图有所发现;但母亲的手僵住了,希望被叹息和愁苦淹没。一张张嘴,连成一堵墙,岌岌可危,随时会砸着父亲;又像刑场,父亲看到了冷酷的枪口。苦楝树上悬着的苦果,敲打着父亲的愁怨,父亲猛地垂下头,像被恐惧掐断了脖子。闭了眼,父亲会梦幻般地看到粮食,像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遥不可及。
终于,一线希望的微光闪了一下,父亲有了主意。粮站收粮的时候,父亲喜不自胜,他要到村外的路口碰碰运气——那是完粮人必经的路口。
往回走的时候,父亲的脚步显得格外异常,快而富有力度。我们像得到某种喜讯的暗示,赶在父亲前头向母亲报告。赶紧准备,晚上有人来吃饭。父亲说。父亲从木箱里拿出那把沉默已久的唢呐,用毛巾轻轻擦拭,唢呐在父亲的手里闪着铜质的光泽。这是父亲钟爱的乐器——在农闲的时候,父亲会吹出或喜或悲的曲子,安抚焦灼的心,也安抚贫弱的村庄。
日落时分,完粮人不仅在我家吃得口齿生香,耳朵也得了一笔恩惠。领头的会计对父亲说,平日不是庄里死了人,哪里能听到这个。喇叭要收好,秋后完粮,饭还安在你家。听母亲说,父亲就是靠这只唢呐,说服了完粮人,赚回半笆斗麦子,断了的口粮又给续上了。
平时,粮站门可罗雀,收粮了,则大有不同。收秋粮的时候,小商小贩就在粮站门前摆摊设点,经营的多是苹果、梨子之类的水果,也有卖花生、瓜子的,多是上了岁数的老人。水果多是装在荆条筐或麻袋里,搬运方便,也防第三只手。这样的交易只在水果贩子和完粮人之间进行。水果贩子卖出的是水果,赚取的是粮食。完粮人在交易中空前豪爽,大大咧咧,拥有江湖人的风度,从不在秤星上计较得失。粮食是集体的,心疼什么?水果贩子凭职业的敏锐,似乎早就看出商机,觉得贩卖生涯里,还是粮站门口大有可为,一度成为多年以后津津乐道的追忆。
但这样的投机取巧也会给水果贩子带来隐患。夜色来临了,粮站里依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里的作业还在延续。门外竖起了竹竿,竿梢挑着100瓦的灯泡,马灯也亮起来了,卖瓜子的老人守着寂寥的摊子,手插在袖口里,斜着眼看水果贩子们忙碌的背影或过剩的笑容。附近村庄的人借着夜色,在水果摊前相互挤压碰撞,像一群求生的溺水者。一群妇女孩子貌似挑拣水果,讨价还价,实则暗度陈仓,顺手牵羊。有的水果贩子眼疾手快,抓住了女人的手脖子,恶语相向,说女人偷了他的苹果。女人矢口否认,解开衣扣以示清白。贩子手伸进女人的怀里寻找,女人一个耳光过去,那贩子脸上火辣辣的像着了火。女人旋即离开,转怒为喜了,指着隆起的下身,对另一女人说,你以为我会把苹果藏在怀里吗?瞧,在这儿哩。孰料,女人身上另有玄机——裤衩内侧特意缝制一个口袋,成了水果们的藏身之处。此举比鲁迅笔下的杨二嫂更胜一筹。对这一意外收获,女人舍不得动嘴,转而拿到完粮人那里兑换粮食——瘦骨嶙峋的病人,饥肠辘辘的孩子,嗷嗷待哺的牲口,等着粮食去拯救。
那时,在粮站,监守自盗时有发生,也让人们看到凄凉的悲剧的面孔。
那年冬,镇上粮站发生盗粮事件。案情并不复杂,几乎没让公安出面,案子就破了。盗粮的汉子是粮站临时雇用的保管员,据说是个光棍。这是一个有名的厚道人,将手伸进公家的粮仓让人惊诧。一个老实人,又有这么好的差事,咋就把手伸到粮库了呢,人们说。粮站的另一职工说,是他上早班时,在一个粮囤边发现了端倪。他发现粮囤下处草苫子有些异常,撩开,看到一个洞,地上撒落着稻子,稻子弯弯曲曲向职工宿舍方向延伸。他顺藤摸瓜,来到了工友的住处,他看到了床底下一袋稻子。事情败露了,工友跪着跟他说,媒人为他介绍一个寡妇,说只要给对方一袋粮食,这亲事就能成。为了女人,工友铤而走险了。这哪成?分明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政治觉悟征服了恻隐之心,职工向站长汇报了实情。站长组织人员进行突审,固定证据,形成材料。此后,这位偷盗者被五花大绑,挂着牌子,游街示众。那个寡妇,因涉嫌用婚姻腐蚀粮站职工,在盗粮事件上与粮站职工系同流合污,亦受牵连。
汉子不堪羞辱,一瓶农药终结了生命,葬在粮站对面的河滩上。时光匆匆从坟墓上走过,走出萋萋芳草,留下隐隐阵痛。一年以后,告密者不知是鬼魂附体,还是良心发现,成日疯疯癫癫,不知所终。
生产队的粮食源源不断地流进了高耸的粮囤,庄稼人分到的口粮却捉襟见肘。在艰辛的劳作之余,在饥饿的围剿下,他们注定在浸润着他们汗水的麦香里反刍着惆怅。粮站囤积着粮食,庄稼人心里囤积着哀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它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存在形式和运行规则生死与共。
课堂上,老师领读“冬天麦盖三层被,来来枕着馒头睡”的农谚时声情并茂,喜形于色。我们对此提出质疑:年年五谷丰登,我们枕的是稻草,啃的是窝窝头。老师一脸鄙夷,说白面馒头是城里人吃的,乡下人只能啃窝窝头——你们有城里人的命吗?
我问过母亲,粮站收的粮食哪里去了。母亲说粮站的粮食是公家的,是公家人和城里人的口粮,吃不到咱庄稼人的嘴里。母亲说得千真万确。每年夏收和征缴粮食,我都会看到公社的干部,膘肥体壮地摇着纸扇,走在田埂上或站在粮站的院子里,像视察,又像检阅。他们生着馒头一样的皮肤,长着肥厚的嘴唇。命运,塑造着一个群体,规划着一种人生。将生命嵌入土地的庄稼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时代的推进更换了生活的剧目。土地承包了,各家各户有了自己的责任田,而完粮仍未终止。家家有一个由上面统一发放的本子,上面写着责任田的面积和完粮的任务。它像一张欠条,一笔债务,需一年一度去偿还。庄稼人有了自己的土地,可以在土地上用超常的劳作,甚至透支体力去获取最大的收成。
夏秋两季,地里打下的麦子和水稻,色泽光鲜,颗粒丰腴,产量可观。一堆堆形如山包的粮食,给了庄稼人精耕细作的理由,也给了庄稼人奔向好时光的信心和底气。庄稼人不再为日子操心,不再为口粮发愁。这是上苍的恩赐,似乎又是命运的转机。
夏季栽完水稻,秋季种下麦子,庄稼人就要到粮站完粮。
一袋袋粮食从家家的粮仓里走出,男人牲口一样伸头拉车,女人、孩子后面推着。老人走出门,泪眼汪汪地看着粮食远去的背影,像送别出嫁女。路上,蜿蜒着完粮的队伍,粮站内外停着驴车,挤满了粮农。他们抓住了难得的契机,交流农田的管理、产量和粮食的品种。以此为铺垫,他们的话题集中在粮价上。粮站的粮价低于市场价,这是无须争议的事实,虽然吃了亏,却也别无选择——种地完粮,自古有之。这是一项布满历史痕迹的制度,庄稼人无法追溯这一制度的起源,却足以认定它是一具枷锁。
庄稼人想通了一些事理,脸面上就多了一些宽慰。让他们担忧的不是粮价的高和低,也不是家里剩余的粮食多和寡,而是粮食能否顺利出手。验粮员跛着一条腿,提着粮食探子,穿梭在高高码起的口袋间,一探子进出,几粒粮食入口,上下牙齿一磕,足以对远道而来的粮食生杀予夺。
盛夏,没有风,空气近乎板结。太阳愤怒着,用灼热的刀挖掘人们每一寸肌肤里的汗水。蝉声铺天盖地,同烈日合力围困粮站内外的人群。粮站院内人头攒动,叫嚷声,争议声,哀求声,愤怒的,讨好的,卑微的,彼此交错,绵软无力。一车车粮食在阳光下原封不动地码着,如待嫁的剩女,分外愁苦,又那么碍眼。粮车长长地排着,从站内延伸到门外,像饱食的牲口吐出的舌头。驴和骡子卧在车边,鼻孔里喷着热气,鞭痕处滚着硕大的汗珠。它们不忍闭目休憩,它们的眼里充斥着对主人的担忧与悲悯。在无法容忍的炙热里,它们期待着和庄稼人共同经营的果实走进粮囤。
验粮员在粮车间穿行,他的背影成了庄稼人共同的追寻。他像救世主一样的神圣,又有鬼魅般的阴邪。有的粮食过不了关,只能在粮站露宿,在水泥场上晾晒。田里的稻秧等着栽插,蚕房里的蚕茧等着摘取……金贵的时间在粮站里流失,一大堆的活儿都让位给完粮。粮站,还有粮站里管事的人,无不让人切齿——他们打乱了庄稼人的农事安排,破坏了有条不紊的劳作秩序。此刻,庄稼人的心在冒火,在诅咒,在祈祷好运的来临。然而,在繁忙的收粮现场,在权力支配的流程里,他们只能冒火、诅咒和祈祷而已。饥饿、焦渴和困乏,轮番挤压,他们倚着粮食,或盘坐在地上,睡了。梦里,他们看到验粮员的笑脸,听到司磅员的召唤,一袋袋粮食顺利出手,乘着输送带,像奔跑的河流,金灿灿地流进了粮仓;也可能是扛着粮食,在通往粮囤的跳板上疾走,像玩杂技一样险中求稳,轻巧利落。脚下的力量是异乎寻常的。于是,觊觎粮仓的鸟,汗渍里跋涉的蚂蚁,还有卧着的牲口,看到一抹微笑和着口水,在嘴角处流淌。
在这阔大而拥挤的院子里,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交涉往往无果而终。在男人的暗示下,女人就出面了。众目睽睽下,女人毫无顾忌地拽住验粮员的衣角,喋喋不休地阐述种地人的辛苦和急于完粮的理由,声音颤颤的,似乎只要验粮员不予通融,就完全可能转化为哭声。有的眼里汪着泪,像云里兜着雨,随时会有泪水的垂落。验粮员每到一处,女人们簇拥过来,撒泼的,数落的,诉苦的,媚笑的,无所不有;验粮员手里举着粮食探子,像举着一种命运,咧着嘴,似笑非笑,一粒金牙闪着坚硬的光芒。验粮员去小解,有个女人就跟上去了,堵着厕所的门,解开上衣纽扣,说这儿没人,你想咋办就咋办吧……
水分超标的粮食就地摊开晾晒。这么一来,场地就紧张了,人们往往为争抢一块晒场惹出口角,乃至大打出手,头破血流,成了粮站的另类景观。天像戏剧里的脸谱,说变就变。刚刚还是烈日炎炎,蓦然间,乌云骤起,深深浅浅地滚过一阵雷声,一场暴雨来得猝不及防。人们在暴雨中抢救粮食,他们提着口袋,端着脸盆,跪着,匍匐着,与苍天争夺粮食,与暴雨进行撕扯。这样的劫难中,雨水中的庄稼人,仿佛听到粮食的啼哭,他们的哭声扭结在一起。而且,在巨大的雨的声响里,他们听到了一粒粮食的召唤,他们听到了痛切和体恤。这是人与粮食之间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接触。雨水将他们置于一场狂暴的洗劫现场,几乎将他们的汗水、辛劳和残留的希冀洗劫一空。他们陷入空前的忙乱,任由暴雨将他们的念想一点点肢解。暴雨将他们抛入深不可测的水域,他们的心里回响着人世之外的声音。他们丧失了视力,被暴雨裹挟着,撞击着,无法辨认自己的位置,无从追寻粮食的踪影。
扣除提留款、灌溉费、教育附加费、治安保护费……庄稼人到手的是一张白条。这是一种新生事物,它以一副冰冷的面孔出场,它让庄稼人认识了它。家家户户的本子里夹着白条,夹着一笔没有归期的赊欠。花花绿绿的票子近在咫尺,又相当遥远。
白条消亡的时日,村部的喇叭里传来了喜讯:种地不完粮了,种地有补贴了。
庄稼人如逢大赦,奔走相告,振奋不已,他们试图让每一位饱受完粮之苦的庄稼人,在第一时间感受这姗姗来迟的政策关怀。
粮站在风剥雨蚀中荒废。验粮员黯然退场,游走在失落与疚痛里。那把粮食探子锈蚀了,成了去向不明的权力符号。
完粮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庄稼人卸去了命运的枷锁。完粮的辛劳,只能在生命的光影里回望,在感喟与感恩中咀嚼。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