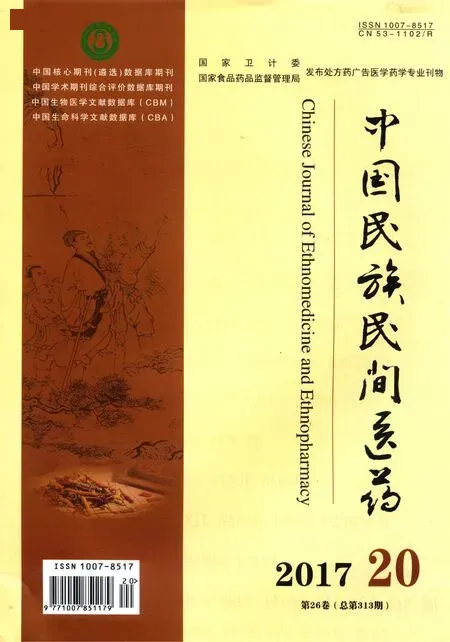苗族巫医文化的心理学分析
吴小勇 陈 瑶
贵州省中医药(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理论研究
苗族巫医文化的心理学分析
吴小勇 陈 瑶*
贵州省中医药(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苗族巫医文化的起源与苗族文化中的鬼神信仰或迷信联系密切,但其延续不仅与苗族的鬼神信仰或迷信有关,与巫医治疗的实用功能以及苗族社会长期形成的求助于巫医治疗疾病的行为惯性也密不可分。苗族巫医治疗中所使用的符箓、咒语及操作方式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以此实现对患者的心理暗示,其隐喻的内容则体现出苗族文化的核心特征。笔者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苗族巫医文化,以供参考。
苗族巫医文化;社会心理基础;隐喻
苗族巫医历史悠久,西汉刘向在《说苑·辨物》有言:“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举面来者,皆平复如故”。现代史学家普遍认为,苗父是指远古时代的苗、黎两族居民的巫师[1]。多数研究者认为巫医治疗属于心理治疗的范畴,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对巫医的心理治疗机制进行了分析[2],但是少有研究通过心理学视角分析巫医的文化现象,故笔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旨在分析苗族巫医文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及其表现形式的心理特征。
1 作为文化现象而存在的疾病
疾病不仅是一种生物学、生理病理学现象,也可列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传统观念的独特性,族群成员对所遭受的疾病症状的认识往往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比如,苗医治疗中的沸汤灌顶、沸油抹擦、履蛋等治疗方法在其他中医疗法中几乎未见,置于在西医文化中更是难以解释。特定族群成员遭受的疾病症状可从其文化中找出病因,并以一种具有文化特色的方式进行诊断、预防和治疗。文化解释模型认为,疾病只是一种解释的模型,不同文化语境下疾病有不同的解释与分类方式[3]。
在特定文化圈内,关于疾病的命名、分类、解释和治疗等都与该地区的文化密切相关。苗族医药体系是苗族先民千百年来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抗争的成果,“巫医一家”、“神药两解”是其鲜明的文化特色,苗族巫医的出现应与苗族先民对疾病的理解和体验有着密切联系。当把疾病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时,苗族巫医的出现和延续就有了客观依据,从而对苗族巫医文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及其表现形式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就有了可行性和必要性。
2 苗族巫医文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2.1 鬼神观念 苗族信鬼好巫,早在传说中的上古时期,苗族先民便已生活在一个弥漫着鬼神观念的世界中。《国语·楚语下》有言:“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由此可知,与苗族渊源颇深的“九黎”、“三苗”部落群体,很早便有广信鬼神的传统。苗族长期延续和保留这一传统观念可能与多次饱受苦难的迁徙、恶劣的居住环境以及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有关。对鬼神的信仰一方面造就了苗族“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让苗族通过鬼神的方式去认识身边的事物,比如湘西苗族有“山有山神,树有树神,岩有岩神,花有花神”的说法[4]。这种鬼神观念同时也树立了苗族对疾病的认识。苗族先民认为自然界各种物质都有一种自我生成与护卫自身的精灵之气,将能侵袭人体致病的邪恶之气称之为鬼,在苗族巫医中有“无鬼不生病”之说,把能扶助和护卫人体精灵之气的称之为神[5]。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苗族先民往往会祈求神灵保佑来治疗疾病,这为巫医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
鬼神观念属于超自然信念,原始社会的人们对风雨雷电等各种自然现象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与此同时又心存恐惧和疑惑,会让其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着一切[6]。苗族巫医正是借助人们所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来祛病强身,通过巫医治疗中所呈现的咒语和符箓可以发现其充满了诸如“太上老君”、“邪魔”、“杂神野鬼”等超自然力量的概念,在治疗方式上完全迎合了人们对于鬼神的认识,也印证了人们对于疾病致病原因的理解。巫医治疗在仪式上所产生的心理意义,远大于在治疗效果上产生的实际意义。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苗族巫医的产生和延续并不取决于其治疗效果,而是取决于苗族民众对于鬼神文化的信仰或迷信。
2.2 巫医治疗的实用功能 虽然苗族巫医产生和延续与其治疗效果可能没有必然联系,但这并不否定苗族巫医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有着明显的疗效。目前多数研究者认可巫医在心理治疗上的作用,巫医治疗过程中的咒语、符箓、角色扮演等充满各种心理暗示,通过潜意识层面改变患者的情绪和心境[7-8],同时,巫医治疗过程中的仪式本身就可以起到转移患者注意力的作用,利于降低患者焦虑或恐惧的情绪[9]。苗族巫医中的“化水术”、“禁咒术”等所起到的止痛止痒、镇定安神、安胎催生的治疗效果就源于此理。另外,心理神经免疫学认为心理行为因素在调节免疫功能中存在重要作用[10],在接受巫医治疗过程中,信奉鬼神的苗族民众战胜疾病的信念会被强化,这对疾病治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助益。在心理治疗上存在的这些实用功能会使苗族巫医赢得苗族民众的信任和认可,从而为苗族巫医的发展和延续注入活力。
2.3 风俗习惯 随着苗族地区与外界的持续交融,西医在苗族地区不断为民众所接受,苗族民众对于鬼神的观念趋于淡化。但现代苗族民众仍会寻求巫医治疗疾病,认为寻求巫医治疗是一种“理所当然”[11]。目前作为支撑苗族巫医产生和延续的基石——鬼神观念正不断消融,苗族地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巫医治疗的习俗成为苗族巫医得以延续的另一个支点。风俗习惯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其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相对地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社会发生变革,风俗习惯也不会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消亡[12]。
3 苗族巫医治疗中的隐喻现象
苗族巫医文化的特色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主要通过隐喻的途径得以表现。隐喻是人们借助具体的、有形的、简单的始源域概念来表达和理解抽象的、无形的、复杂的目标域概念,从而实现抽象思维,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13]。与此同时,隐喻具有明显的文化特性。首先,对隐喻概念的理解会依赖于人们的文化经验;其次,隐喻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在较高水平上反映文化的内容[14]。反而言之,特定的文化需要以隐喻为载体,植根在人们的内心之中。苗族巫医作为苗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在治疗过程中可以通过咒语、符箓和具体操作体现出“万物有灵”、“图腾崇拜”以及鬼神致病观念[14]的苗族文化内容。苗族巫医主要通过操作系列的隐喻以达到心理暗示的效果。
3.1 咒语 苗族巫医治疗所用的咒语往往以具体形象的鬼神来隐喻人们心目中各类的超自然力量,其中包括代表“善”的超自然力量,诸如太上老君、仙神、仙师、祖师、王母、观音等神灵,这些形象多与苗族的图腾有关;还包括代表“恶”的超自然力量,诸如邪魔、杂神野鬼、瘟、毒、凶神恶煞等邪恶形象,这些形象多与苗族民众所认为的致病因素有关。咒语往往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描述了“善”驱除或战胜代表“恶”的过程,这一过程映射了苗族医疗的基本观点,即去除破坏机体健康的因素。苗族素有“无毒不成病”的说法,此之“毒”即为侵袭人体的邪恶之气,为“恶”。
3.2 符箓 “符”是道士书写的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箓”是记天曹官属佐吏之名,又有诸符错杂其间的秘文。道教声称,符箓是天神的文字,能治病、镇邪、驱鬼、召神[15]。苗族巫医的“化水术”和“禁咒术”中咒语末尾往往附上“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一句[1],可见苗族巫医治疗与道教方术有一定关联,与道教方术一样,苗族巫医同样使用符箓作为治疗手段之一。大部分符箓主要由文字辅以图腾、星象、神秘符号等元素,该文字多属于“拆字”后的重新组合,其寓意往往跟其中的图形符号和被打散的文字原意有着某种关联,但又常常并非望文生义、望图生义所能释义[16]。在图文结合的符箓形成之前,有个漫长的“图腾”时代,人们以绘画的方式表达类似符箓所表达的意愿,可以说图腾是符箓的前身。苗族巫医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符箓中往往会出现日、月、牛、马、雷、雨等文字,这些文字所代表的形象都与苗族先民的图腾存在关联,隐喻了图腾所具有的超凡力量和作用。日、月可以带来光明,驱散黑暗,消除恐惧;牛、马则代表了家畜兴旺[16],苗族巫医“化水术”中的安胎水符箓的中间显著位置写着牛、马字样[15],这隐喻了人丁兴旺的愿景;雨、雷代表了御鬼驱邪的无穷力量,其中雷具有迅疾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威慑力,为邪晦所惧[15]。
3.3 治疗操作 苗族巫医的隐喻现象不仅表现在治疗中使用的咒语和符箓上,也表现在治疗的操作方式上。落翳术是苗族巫医治疗眼翳的常见方法,主要通过搬动家具使眼翳脱落,苗医首先看患者的眼翳形状、位置后指导患者回家以后移动或者清扫一些物品[1]。这种方法通过移动或者清扫家中物品来隐喻清除眼翳,达到心理暗示的效果。除此之外,苗族巫医中的“什针术”、“捆扎术”[1]的操作方法也具有类似的隐喻特征,对患者起到心理暗示的效果。
4 结语
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的方式映射了其群体的文化特征,苗族巫医文化的起源与苗族文化中的鬼神信仰或迷信有着密切关联,而在医疗科学化的现代,苗族民众在治病求医中仍然求助于巫医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是苗族巫医在心理治疗上存在的实用功能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认可,二是巫医治疗的习俗在苗族延续千百年,长期形成的行为惯性使得人们继续求助于苗族巫医。
苗族巫医治疗中,主要通过隐喻实现对患者的心理暗示,其隐喻的内容体现出苗族文化的核心特征。该方式可能与苗族先民的思维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苗族先民对人体的认知理论中可以发现,其思维方式存在着显著的“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特色,这与中国传统思维“象思维”高度一致。苗族“三要素论”的气、血、水以及“三界学说”的树界、土界、水界都以具体的形象来指代高度抽象的意义,这种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阴阳五行等方式表达对世界万物的理解亦是相类同的。可能正是苗族先民这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特征决定了巫医治疗中往往采用隐喻的方式来传递或表达各类意象。
[1]杜江,邓永汉,杨惠杰.中国苗医绝技秘法[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14.
[2]尹绍清.古代中国人心理健康维护的社会性支持与自我支持的方法[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1, 30(3): 97-100.
[3]黄锋.民族医疗中的“神药两解”现象解析——以粤北一个“排瑶”村庄为例[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35-40.
[4]张卫华.浅析湘西苗族巫术文化的特性[J].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4,15(2): 43-45.
[5]石志权,吴言发.略论苗族万物生成论对苗族医药文化的影响[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9(6):60-61.
[6]陈永艳,张进辅,李建.迷信心理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进展,2009,17(1):218-226.
[7]孙时进.巫术的心理学分析和批判[J]. 心理学探新,2001,21(4):16-19.
[8]许华尧.中国巫术文化和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9(3):79-83.
[9]吴利华.苗族巫医的文化内涵及其功能——以凤凰县两头羊苗寨巫医为中心[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08.
[10]林文娟. 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2006,14(4):511-516.
[11]徐雯栋. 制度与文化中的少数民族村医——基于古村苗医张孝祥行医史的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3.
[12]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3]殷融,苏得权,叶浩生.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理论[J].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2): 220-234.
[14]尹新雅,鲁忠义.隐喻的具身性与文化性[J].心理科学,2015,38(5):1081-1086.
[15]曾召男.符箓[J].宗教学研究,1983(2):58.
[16]颜开.小议湖湘巫术“符箓”的内容构体[J].装饰,2010,204(4):114-115.
R29
A
1007-8517(2017)20-0001-0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苗医药文化价值体系及现代转型研究”(17XMZ040);贵州省重大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黔科合J重大字[2015]2002号);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项目(2015JD072)。
吴小勇(1982-),男,汉族,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苗族医药文化。E-mail:ahxywu@gmail.com
陈瑶(1965-),女,汉族,硕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文献研究。E-mail:ahxywu@gmail.com
2017-08-31 编辑:程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