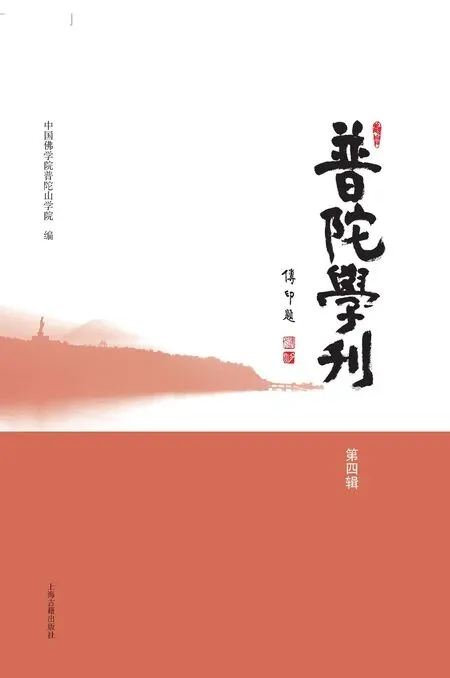论后世俗社会与宗教的现代性
刘久清
(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绪 论
无论如何界定宗教,都无法否认这是一发生于社会中的现象,也就必然与社会有密切互动。现代性(modernity)既为当代社会变迁之主要方向、社会发展之主要目标(虽然不同社会有不同原因、考虑与不同发展方向、状况),则宗教势必无法自外于斯。
只不过,发起于西欧的现代性,虽以基督宗教为其思想主要根源之一,现代性发轫之初,基督宗教思想也是其主要动力。然而,随着现代性之持续发展,宗教却逐渐遭遇困境,甚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被认为因现代性之高度发展而面临趋于消亡之威胁。宗教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理论即为此一认知的最主要代表。
当然,事情由一开始就不是那么简单,对于现代性是否必然包含世俗化,始终有着争议。主要的争议在于如何看待宗教、宗教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与如何理解宗教与现代性的互动。
即便如此,要讨论宗教的现代性,终无法避免讨论世俗化,但也不能只是讨论世俗化。而是在面对当代社会日趋现代性的发展中,讨论宗教的因应之道,与宗教所可发挥的积极功能。
对此,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post-secular society)概念,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模式。对此一可能加以检视,正是本文主旨所在。
然而,如果只做以上讨论,难免陷入将今日全球社会的发展走向乃普世趋同的错误。因为,现代性发展至今,我们已清楚认知,所发展出来的并非单一现代性,与“后世俗社会”相应的,乃是“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故而,还必须进一步讨论个别社会在面对现代性时遭遇的独特问题,方有可能比较彻底的解决以上问题。
此所以,要充分铺展本文主旨,检视后世俗社会实践的可能模式,就必须紧接处理一个主题,也就是在后世俗社会的概念框架下,讨论我国在追求现代性发展时所面对的宗教问题。
一、 世俗化与后世俗社会
既然要讨论宗教世俗化,首先就必须确认何谓宗教与何谓世俗化。
世俗化理论主要倡议者之一,贝格尔主张要以实质定义宗教,*贝格尔(Peter L.Berger)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1991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4页。因而将其定义为“人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33页。由于“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进行建造世界的活动”,*同上书,第7页。在进行一种“秩序化的活动或法则化的活动”,*同上书,第26页。而宗教就是“用神圣方式来进行秩序化”。*同上书,第33页。其中“神圣”意指:“一种神秘而又令人敬畏之性质,它不是人,然而却与人有关联,人们相信它处于某些经验对象之中。”*同上。
由于“宗教所设定的宇宙既超越于人,又包含着人。神圣的宇宙作为超越于人的巨大有力的实在与人相遇。然而这个实在又向人发话,将人的生命安置在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秩序中。”*同上书,第34页。就此而言,“神圣”的反义词即“世俗”,意指“神圣性质的匮乏”。也就是“所有并未‘突出来’成为神圣的现象都是世俗的。日常生活的程序都是世俗的,除非能够证明它们在后来被认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输入了神圣的力量(如从事神圣的工作)。”*同上。
因此,贝格尔将“世俗化”描述为:社会与文化部门脱离各种宗教机制与象征宰制的历程,就西方现代史来看,其表现即为基督宗教教会撤出过去控制、影响的领域,如教会与国家分离、剥夺教会领地、教育摆脱教会权威等。不仅如此,世俗化也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出现愈来愈多不依靠宗教解释来看待自己所处世界与生活的个人。*同上书,第128页。
世俗化的思考源自启蒙运动,其主要意涵在于认为世界日趋现代即益形世俗且愈不宗教,甚至最终导致宗教消失于社会之中。*Peter L.Berger, ‘Faith and Development’, SOCIETY, 2009, Volume 46, Issue 1, p.69. Peter L.Berger and Albert Mohler, ‘Rethinking Seculariza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Berger’ 2010, in AlbertMohler.com, retrieved at 2013 1202 from www.albertmohler.com/2010/10/11/rethinking-secularization-a-conversation-with-peter-berger-2.其所以如此,在于相信科学进步与随之而来的合理性将取代不理性甚至迷信的宗教,*Peter L.Berger, ‘Secularization Falsified’, 2008,in firstthings.com, retrieved at 2013 1201 from 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08/01/002-secularization-falsified-1以及上一段指出的社会功能日趋分工,使得一些原本属于教会的功能,不再由教会承担。*Peter L.Berger and Albert Mohler, ‘Rethinking Secularization’.
这样的发展,正是现代性的呈现。Max Weber(Karl Emil Maximilian “Max” Weber)借用Friedrich Schiller(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用语将现代性诠释为“解除世界魔咒”(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一个以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合理化(intellectualization)为其特质的历程。*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1946, pp.129-1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http://mail.www.anthropos-lab.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12/Weber-Science-as-a-Vocation.pdf RETRIEVED AT 2014 0506.
道博莱尔以时钟的引入为例,说明合理性化如何促进世俗化:*道博莱尔(Karel Dobbelaere)著,李华伟译:《世俗化的意义与视野(The Meaning and Scope of Secularization)》。《宗教社会学》,2013年第一卷,第90页。
12世纪以来,科学、工业和贸易扩张的发展,不能再依靠修道院以打铃来计时的时间序列。人们需要更精确的时间度量方式,最终在14世纪之初以时钟的发明而得以实现,时钟放置在城市最高的塔上,每个人都能看到,如此,引入了世俗的时间秩序。教会时间失去了其重要性,时间也剥离了其来自上帝赋予的神圣特征,这种神圣特征转而由日晷来提供。一旦时钟开始管理时间,它就由人控制并从宗教时间的时代中脱离出来。19世纪,铁路系统要求时间必须严格协调一致,之后收音机也是如此。
然而,身为世俗化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贝格尔对世俗化的见解却以上世纪80年代为分水岭,他先是在90年代宣称世俗论正在退却*Peter L.Berger, ‘Secularism in retreat’,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6, Vol. 46. retrieved at 2013 1201 from csrs.nd.edu/assets/50014/secularism_in_retreat.html.,更在进入本世纪后宣布世俗化理论已被证伪(Falsified)*Peter L.Berger, ‘Secularization Falsified’ 2008, in firstthings.com, retrieved at 2013 1201 from 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08/01/002-secularization-falsified-1.。
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道博莱尔在其发表于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由发表于本世纪的两项经验研究结果显示,”“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几年里欧盟国家的显性世俗化程度将会增加。”*道博莱尔:《世俗化的意义与视野》,第99页。此一迹象之明显,可以下述事例说明:*同上。
在西班牙,关于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堕胎合法化的争论很激烈,在一些地区所谓的消极的安乐死已经得到管制。在法国,安乐死的问题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公共话题。这两个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原则曾经被广泛认为是宗教社会的核心特征,现在却在直到近来还被认为是最典型的欧洲天主教国家中受到挑战。在“天主教”国家巴西,堕胎的合法性也正受到激烈的争论。
道博莱尔对厘清是否存在宗教世俗化问题所做的研究,以(如同Peter L.Berger所主张的)为宗教下实质性定义入手。他将宗教定义为:“一种与超验和超验实在相关的信仰和实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宗教权威编制了超验和超验实在并将所有追随它的人们统一在一个单一道德共同体内。”*同上书,第86页。
他认为要厘清世俗化理论能否成立,需由宗教的社会角色入手,亦即世俗化显示的是宗教在社会角色上的变迁。因此,世俗化这场社会变迁的范围虽遍及宏观社会系统、中观次系统(组织)与微观(个人)三个层次以及此三层次间的互动。*Karel Dobbelaere, ‘Toward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f the processes related to the descriptive concept of secularization’ Sociology of Religion, 1999, 60, no. 3, pp.229-47.要能(跨文化地)有效评估宗教社会角色的变迁,依上述他对宗教下的定义,就必须由宏观的社会系统面将世俗化定义为:*道博莱尔:《世俗化的意义与视野》,第86页。
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旧的包罗万象的、超越性的宗教系统,被限制为一种与其他子系统并列的子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系统失去了其对其他子系统的重要权利。也就是制度性宗教的权威失去了对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家庭、教育和法律等——的控制,这些社会子系统开始自主化,例如政教分离、科学发展为自主的世俗观点、教育从教会权威中解放出来。从而导致了功能性理性(functional rationality) 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现代性展现于其功能的分化,以致发展出许多子系统,如经济、政治、科学与教育。这些子系统既相同(社会对它们有同等需要)又不同(各自履行其特有的功能: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有效知识的生产与教授)。由于
这些子系统的功能自主性依赖于其环境以及与其他子系统的沟通。要确保这些功能得以正常履行及与其他系统的沟通,组织(商业公司、政党、研究中心、学校)就被设立了。在每一个子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中,沟通的达成要依赖于子系统的媒介(金钱、权力、真理、信息以及专有技术)。每一个组织也根据子系统的价值标准(竞争与成功、权力的分离、可靠性与有效性、真理)以及特定的规范进行运转。这些组织宣称其自主性并拒斥由宗教制定的规则,也就是子系统的自主化。例如政教分离、科学发展为自主的世俗观点、教育从教会权威中解放出来。在分析宗教对所谓世俗子系统的影响力之丧失时,宗教组织的成员最先讨论世俗化——世俗领域摆脱宗教控制而实现自主化。*道博莱尔:《世俗化的意义与视野》,第87页。
道博莱尔指出:随着“宗教权威对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式微——社会子系统的自主化——导致了功能性理性(functional rationality)的发展”,其结果就是前述的“解除世界魔咒”与其各个子系统的社会化(societalized, gesellschaftlich)。后者意指一个组织化的世界乃立基于各种非位格性的角色、关系与各种技术的协调合作,其行为模式的本质是形式性与契约性的,个人德行既不同于角色义务也就不重要。*同上书,第88页。
道博莱尔进而详细论述了随着社会子系统的持续分化,宏观的社会系统、中观的社会次系统(甚至是宗教组织)与微观的个人是如何与为何一一走向世俗化发展。*同上书,第88—96页。
此外,为证明世俗化并非只是一典型的西方现象,道博莱尔引用Enzo Pace的研究,指出:即便在伊斯兰世界也可看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相互支持的世俗化发展历程,甚至即便在欧洲、南亚、东南亚涌现伊斯兰激进主义浪潮,以反对年轻人的世俗化趋势,然而“这些年轻人可能仍然将自己的身份与伊斯兰教传统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仍然是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价值资源,但是他们不再具有常规的宗教实践”。*同上书,第97—98页。
然而,道博莱尔的研究所显示的,并不表示贝格尔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世俗化的论断就是错的。
因为,贝格尔固然做出我们生活于世俗化世界的假设是一错误的论断,*Peter L.Berge, ‘Secularism in retreat’.却也不认为世俗化并不存在。重点在于对现代性的误解:现代性的必然趋向是多元(pluralizing),而非世俗。现代性的特征是在同一社会中出现日趋多元(出现各种不同信仰、价值与世界观)的发展,而多元性并不必然挑战所有宗教传统。*Peter L.Berger, ‘Secularization Falsified’.正是由于多元性的发展,以至于道博莱尔甚至指出,“世俗化不仅仅是‘人造的’,也是可逆的。”*道博莱尔:《世俗化的意义与视野》,第91页。
此所以,贝格尔自承在其身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中,犯了一项大错:误以为现代性必然导致宗教衰微;并提出了一项大的洞识:多元论削弱了各种各样理所当然的信念与价值。贝格尔将多元论解释为:人们在进行社会互动时,所凭借的信念、价值与生活形态极其不同,却同时并存。这样的多元论对人们的影响,不在其信仰什么,而在如何信仰。*Peter L.Berger, ‘Protestantism and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The Christian Century, 1998 August 26-September 2. retrieved at 2013 1201 from www.religion-online.org/showarticle.asp?title=239.
然而,一旦肯认现代性具备多元论性质,就无法再如贝格尔仍停留在一种现代性中的多元论,而必须进一步肯认多元现代性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又使我们必须面对不同文明、宗教如何共处、互动的问题,进而需面对有无可能因此发生“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这个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论题。对此联合国也高度重视,其大会更于1998年决议将2001年——本世纪伊始——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
具有讽刺意味,且更不幸的是,就在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攻击,一个迫使我们必须面对且深入探讨此一论题的事件。“9·11”恐怖攻击发生的第二个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颁发德国出版发行业联合会和平奖,得主哈贝马斯以“信仰与知识”(Faith and Knowledge: An Opening)为题发表演讲,其内容即在响应此一事件,并因而提出“后世俗社会”——在一个持续世俗化的社会中,始终有着宗教共同体存在的概念。*Jürgen Habermas, 2001 ‘Faith and Knowledge: An Opening’, trans. by Kermit Snelson, post on netime retrieved in 2013 1010 from www.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0111/msg00100.html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著,朱丽英编译,《信仰和知识——“德国书业和平奖”致辞(Faith and Knowledge: An Opening)》,《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2年第3期,第75—79页。
演讲一开始,哈贝马斯即指出今日世界存在着世俗化发展下的科学与宗教二分,与二者间存在的张力。而“9·11”恐怖攻击虽是以宗教信念发动,却是一现代性产物——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用的虽是宗教语言,却全然是仅见于现代的现象。*Jürgen Habermas, ‘Faith and Knowledge’.
因为,在那些伊斯兰恐怖分子身上所看到的,其手段与目的上的惊人不平衡,反应的是他们祖国为追求快速、激进现代化所促成在文化与社会上的不平衡:传统崩溃与政治上政教分离,均为他们带来羞愧感。面对消除市场边界的全球化历程,很多人都希望政治能回归另一形式,但不是回到与警察、情治机构乃至军队紧密连结的全球安全国家,而是凭着对理性的苍白希望与一丝丝的自觉,要回到广及全球的文明力量。*Ibid.以此为引,他开始讨论世俗化。
二、 后世俗社会与宽容
哈贝马斯指出,由于世俗化与一般性的文化、社会现代化绑在一起,于是出现以下两种对世俗化发展的判断:首先,是取代模式,认为世俗权力成功驯化了教会权威,亦即宗教性的思考与生活方式已为立基于理性且其成果更为高明的等价物所取代,也就对将宗教世俗化的作为赋予进步、乐观的意义;其次,是征用模式,意指无根的现代性在理论设想上的崩坏,亦即教会权威被非法挪用,以至于将现代的思考与生活模式视为因受到非法占用而腐化。*Jürgen Habermas, ‘Faith and Knowledge: An Opening’.
这两种对世俗化的诠释犯了相同错误:误以为世俗化是受资本主义驾驭的科学与技术的生产力与宗教、教会紧紧掌握的权力间的零和游戏。忽略了受民主、启蒙的常识,以平衡于科学与宗教间文化冲突的第三方参与者角色持续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所能扮演的开化角色。*Ibid.
在领取德国出版发行业联合会和平奖后的另外一场讲座中,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世俗化假设立基于三个考虑:首先,科技进步使世界解除魔咒;其次,社会次系统的功能分化,使教会与其他宗教组织不再能控制政治、法律、公共福利、教育与科学,从而走向私人化、失去其公共影响力;最后,社会发展使福利增加、社会更为安全,生活风险减轻,生存保障提高,个体不再需要与一个彼岸或宇宙力量交流以掌握不受控制的偶然事件。*Jürgen Habermas, 2008, ‘Notes on a post-secular society’, signandsight.com-let’s talk European, retrieved at 2013 1201 from print.signandsight.com/features/1714.html.
哈贝马斯指出,这些考虑已不适用于今日这个“后世俗社会”。以此出发,他主张在自由主义国家中,唯有从自身认识出发、放弃强行贯彻自己的信仰、放弃强迫自己的成员做违心之事、特别是放弃操纵自我戕害行为的宗教团体, 才有资格被称为是“理性的”。*Jürgen Habermas, ‘Faith and Knowledge: An Opening’.
这样的理解源自信仰者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对其自身立场的三重反思:首先,宗教意识必须要能在认知上处理与其他宗教、信仰的接触;其次,认可科学在社会中独占的知识权威;最后,必须以参与立基于非神圣概念的道德的宪政国家为前提。哈贝马斯认为缺乏这一反思的推动,一神教的教派将在一个无所顾忌的现代化社会中发展出破坏性潜能。*Ibid.
要进行这样的讨论,关键在不同文明间如何相互理解,其基础在我们如何自我理解。然而,其中所预设的乃是国家需与教会分离的信念。因为国家权力的世俗化发展正是源于多元论——为响应西欧在近代早期的宗教战争所发展出来的宗教多元论。
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见维基百科的“南特敕令”条所做说明。取录于2014/05/0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7%89%B9%E6%95%95%E4%BB%A4。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也是第一部承认新教徒信仰自由的敕令,从而在法国出现了自罗马帝国后,欧洲史上第一次的宗教并存。
该敕令之起源为:自Martin Luther推行宗教改革,新教的加尔文教派(Calvinisme;Calvinism)逐渐在法国境内活跃。1559年,法国国内的新教教徒组成了雨格诺(Huguenot)集团,对抗捍卫天主教的统治阶层吉斯家族(Maison de Guise)。1562年,双方爆发武装冲突,开启历时30年的“法国宗教战争(Guerres de religion)”。至由雨格诺派改宗天主教的亨利四世(Henri IV)登基,致力于修复国内分歧,以避免再次引起战火。遂于1598年4月13日在布列塔尼的南特城签署了此一敕令,当时称为和平赦令。这条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国内的雨格诺教徒能够享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干扰,亦有权建造教堂及参与宗教事务。此外,他们也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亦可以和天主教徒一样分享同等的政治权利,可以担任各种官职,亦允许这些教徒保有城堡及军队,以保卫自己。
接下来,国家在宗教改革后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一个信仰分裂的社会建立秩序,以维持和平稳定。意即“国家权力必须平息争执中各派的敌对情绪,为互相敌对的教派之间和睦相处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并监督这些教派之间危险的关系。”*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著,李琲琲译:《世俗化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9年,第17页。
这样的努力,不能只是立基于宽容,诚如Margriet de Moore所指出的:“通常宽容与尊重密不可分,可是我们那植根于16、17世纪的宽容却不是以尊重为基础的。相反,我们互相仇视对方的宗教,天主教徒与加尔文教徒一点儿都不尊重对方的观念。”*哈贝马斯:《世俗化的辩证法》,第16页。
同时还存在的一路循环是润滑油在油分离器实现分离后,借助油泵输送至各润滑点,确保轴承等零件的润滑与降温。
此所以,颁发南特敕令并未就此使法国走向真正信仰自由,即便饬令中宣示其为“永恒”、“不可废”,终仍在其颁发87年后的1685年10月22日,为亨利四世之孙路易十四(Louis XIV)所颁步之“枫丹白露敕令(Édit de Fontainebleau)”将其正式废除,以在法国实行宗教信仰一元化。*对南特敕令被废除的原因所做分析,见陈文海:《论法国“南特敕令”的废除》,《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总第(66)期,第66—71页。
为了真正确保公民的宗教自由。哈贝马斯主张将“宗教的宽容”理解为“对怀有别样拯救思想的另类世界宗教的宽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著,章国锋译:《我们何时应该宽容——关于世界观、价值和理论的竞争(Wann müssen wir tolerant sein? Über die Konkurrenz von Weltbildern, Werten und Theorien)》,《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3年第1期,第108页。其重点为不同宗教在认识论上存在分歧,宽容即倾向于避免因分歧产生的冲突。
然而,必须小心的是:“每一个宽容的行动都隐含着它的反面特征,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恩赐,因此,宽容同时意味着划清界限。”而且,“没有一种接受不包含着排斥。”一旦划线转化为极权的强制,变成一种单方面采取的手段,“宽容便难以逃脱随心所欲的排斥的负面特征。”*尤尔根·哈贝马斯:《我们何时应该宽容——关于世界观、价值和理论的竞争》,第108页。
因此,“只有划定一种使所有相关者均认同的宽容领域,才能拔掉扎在宽容之中的那根不宽容的芒刺。”也就是说,“如果要让所有可能的相关者对相互宽容的前提达成共识,就必须促使他们彼此承认并接受他者的视野。”*同上。
这意味着,只有在“相关者认为自己的真理信仰与他人真理信仰的冲突‘无法通过协商’来解决,但又为了在政治共处的层面上维持一种交往的共同基础而必须将分歧搁置起来”。由认识论层面看,就表示“这类冲突是无法消除的,因而必须以某种方式‘冷冻’起来并在行为的有效性方面被中性化,甚至,为了在社会互动的意义上维持联系,它必须受到克制”时,宽容的政治美德才能起关键作用。*同上。
此所以,哈贝马斯强调“只有在对另类有效性要求的拒绝具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宽容才有意义”。这意味着不可将宽容与偏见、歧视混淆,因为要求一个种族主义者宽容,即意味着肯定它的偏见与歧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求他表现出宽容,而在于要求他放弃种族主义立场”,“只有在消除了对少数人歧视的偏见之后,宽容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同上书,第109—110页。
之所以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性别沙文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或有排外倾向的种族中心主义者的言行称为“偏见”,其关键即在于“赞同国家公民平等的普适主义尺度”,也就是“不但要求一个政治共同体平等地对待其每一个成员,而且要求所有的公民彼此作为‘有同等价值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相互承认。”*尤尔根·哈贝马斯:《我们何时应该宽容——关于世界观、价值和理论的竞争》,第110页。
也只有贯彻这一普适主义原则,彻底铲除歧视,“在规范性一致的基础上,不同世界观之间在认识论层面上存在的矛盾,才可能在国家公民平等的社会层面上得到解决。而只有这时,宽容才能在无歧视的状态下被谈论。”*同上。
这是由于信徒关于正确生活的观念,“受到普遍认同的善或拯救的模式所支配”,从而“产生一种认为陌生的生活方式不但另类而且邪恶的看法。”也就是说,一旦陌生的伦理道德既关系到价值判断,又涉及真理或谬误问题,则“给予每一个公民——不论其伦理的自我理解和生活方式如何——以同等尊重的要求,便同时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对自己的伦理判断保持克制。”*同上。
哈贝马斯因而强调:对每一努力按照伦理价值且遵循伦理真理来规划自己生活的人而言,一旦遭遇“体现异己信念的生活方式”,必然对这种信念加以拒绝,就在此时,“他恰恰应该表现出宽容。”*尤尔根·哈贝马斯:《我们何时应该宽容——关于世界观、价值和理论的竞争》,第111页。
哈贝马斯指出:由各种涉及存在的世界观彼此无法调和的认识层面的信仰,向(自身的伦理道德至多同社会的法和道德在认识论上有某些契合之处的)实践层面过渡时,“宽容起着对这些信仰进行过滤的作用。”*同上书,第111—112页。
从宗教多元主义来看,“宽容的前提是一种无法调和的信仰分歧的存在”,以至于“宗教信仰自由对于其他的平等文化权利的贯彻,无疑起着示范的功能”。“从这一模式中产生的宽容概念,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中,并不仅仅因此而在处理非宗教团体充满紧张的共处中得到运用,最终,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与世界观的多元化密不可分。”*同上书,第112页。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流露出独断论的倾向。任何一种文化都必然表现出这样一种性质:它试图涵盖一切思想,为的是判定哪些信仰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事物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不但世界观的多元化呼唤宽容,具有强烈同一性特征的语言和文化生活形式,如果它们在其总体信念的基础上,不仅在生存意义的视角下,而且在真实性和正确性的有效性层面上必须作出判断的话,同样需要宽容并必须表现出宽容。*同上。
也就是说,既然涉及文化生活,则不只是宗教,世俗面也需调整。
三、 后世俗社会与世俗理性
哈贝马斯主张必须区分世俗者(secular)与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世俗者对宗教有效性要求持不可知立场;世俗主义者则以科学主义为依据,对那些尽管缺乏科学根据却仍有其公共影响力之宗教学说进行论战。*Jürgen Habermas, ‘Notes on a post-secular society’.
虽然如此,世俗主义者仍坚持主张将所有公民平等吸纳入公民社会,各个不同宗教的宗教公民与各个宗教团体不能仅在表面上和睦相处,更需在自身信仰的前提下认同世俗共识的合作法。毕竟,不能只是把民主制度强加给它的承担者,宪政国家更要让它的公民期待一种超越单纯遵守法纪的国民伦理。*Ibid.
此所以,哈贝马斯认为,一个同时服从法律统治和人民民主意志的宪政国家,要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宗教自由,就必须使公民不再封闭于各自宗教团体的自足生活世界中互不往来。各种亚文化必须允许其个体成员从其文化氛围中抽离,以便这些亚文化成员在市民社会中可以被相互承认为国家公民,也就是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担当者及成员。亚文化的成员以民主国家公民的身份为自己立法,根据这些法律,作为一个私人领域的社会公民,他们能够保持其自身在文化及世界观上的认同并且相互尊重。*尤尔根·哈贝马斯:《世俗化的辩证法》,第17页。
这意味着普遍论与特殊论其实并不矛盾。
哈贝马斯指出:现今这个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面对的是各自承受强大宗教特征影响的多元的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ies)。而要在一个多元文化世界社会的未来政治框架中进行富有希望的文化交往,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中立、在此意义上是世俗层面的理解。*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著,任俊、谢宝贵译:《宗教、法律和政治——论文化多元的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哲学分析》2010年第1卷第1期,第110—111页。
在一个后世俗社会中,问题不再是宗教会否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注定将从公民心灵中消失并失去它的公共意义,而是在世界舞台上碰到的活力不衰的诸个世界宗教。同时,围绕现代性筹划之意义而产生的持久冲突,只在现代社会间展开。世界舞台上已不再有任何前现代社会。*尤尔根·哈贝马斯:《宗教、法律和政治——论文化多元的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第111页。
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特殊历史、社会发展与文化背景,都平等面临以下相同基本事实:“市场经济和官僚行政向传统生活方式施加个人化与合理化的压力”;“建制化的法律商谈、经济商谈和科学商谈产生出可错的凡俗知识”;尤其还要加上“在这些社会内部存在着的那种多元主义,构成这种多元主义的是作为这些社会中的多数人文化的信仰和气质之替代物的种种世界观和生活形式。”*同上。
因此,面对这些普遍性的基本“现代性事实”的现代化与世俗化关系,可能是在多元文化的世界社会里朝着多种宗教功能分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在不损害政治和法律的世俗的、“独立”的合法化基础的情况下,维持自身的公共意义,才可能实现国际法的宪政化。*同上。
这就有赖于将“理性”视为并非各种相互冲突的世界观的最小公分母,而是本身即为一权威的世俗理性*同上书,第113页。——一个在多元文化的世界社会中由各个相互竞争的世界观相互达成之重迭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这是Habermas借自John Rawls的概念。所界定的概念。*尤尔根·哈贝马斯:《宗教、法律和政治——论文化多元的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第114页。
为说明世俗理性所能发挥的作用,哈贝马斯提出了一项思想实验:
假定所有主要的宗教共同体都已经达到了进行自我反思所需要的水平,并在多元文化的政治社会的某种政治宪法上达成了文化间的共识。这个过程无疑是漫长和充满挫折的,但最终结果则应该是各个宗教共同体都接受了宪法化的国际法规则和程序,尽管对什么是现代性的正确的自我理解仍存在分歧。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出现一种特定的论证,也就是一组概念的、经验的、科学的、道德的和法律的论证,这些论证在现代生活的共同经验的背景下有足够的力量说服所有方面,尽管他们的世界观彼此冲突。*尤尔根·哈贝马斯:《宗教、法律和政治——论文化多元的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第113页。
然而,除了宗教共同体,尚须处理遍布于所有国家的公民社会之中世俗公民和宗教公民(或精英)间的分歧,其关键则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世俗理性本身。*同上。哈贝马斯认为世俗理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宗教或形而上学命题的伦理意图和潜在的真理性内容的贬抑。作为一个自主权威的狭义的世俗理性概念,是允许有一种温和的不可知论的。”*同上书,第114页。
这样意义下的世俗理性,绝不会将宗教视为“仅仅是科学上业已祛魅的幻象,并且把宗教的存在当作社会发展的已被超越的阶段的残余”,否则就无法做到使各个宗教共同体在对真正拯救之道的寻求中,“至少能设想它们自己在为同一个目标而竞争,能够承认彼此为同一项人类事业的‘当事者’(stakeholders)。”,从而建立起相互承认的基础。*同上。
要发展多元现代性,使“几个主要的受宗教影响的文明,沿着一些发展道路,得出基于相同社会基础领域的不同的现代性版本和许多相互冲突的现代性的眼光”,其整合成功之道,“不仅依靠所有的宗教共同体开始乐于接受对现代性的基本事实的反身性理解,而非屈服于原教旨主义的诱惑。”更在于它是在后世俗社会中的“一个互补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会质疑那种执著于自己观点的世俗理性的狭隘的自我理解”。*尤尔根·哈贝马斯:《宗教、法律和政治——论文化多元的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第114—115页。
此所以,哈贝马斯主张:
后形而上学思想应该在不损害其世俗的自我理解的情况下,对宗教同时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和乐于接受的态度。对世俗思想者来说,信仰仍具有他既不能否认也不能简单地予以接受的晦暗不明性质。世俗理性应该坚持在信仰的确定性与可公开批判之有效性主张的确定性之间的区别,但要避免以此来评价宗教本身的合理性或非理性。当然,这样一种反思的不可知论的认知约束,是一个互补的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从政治上说,它可能只有利于那些反过来也学会承认民主、宗教多元主义和科学的世俗权威的宗教。*同上书,第116页。
然而,这样的世俗理性却必须面对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过度片面强调合理性化,遂失落了对道德与伦理问题解答的能力。无法再合理回答:“我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因为其中涉及认同问题:“我们该怎样看待自己?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想要成为什么人?”于是就无法回答“我们为什么都应该是道德的”的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之道需赖宗教,他以Kierkegaard思想为例说明此点:以其新教徒身份与后形上学思考,Kierkegaard对何谓正确生活方式问题的解答,是以救赎的诺言将绝对的道德与自我操心之间建立起积极连结,主张唯有扎根于宗教的自我理解的道德意识,才能结晶成一种自爱的生活方式的核心内涵。*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卫东译:《后形而上学能否回答“良善生活”的问题?》,《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2006年05期,第1—7页。
此所以,哈贝马斯会说:
后世俗社会对宗教执行着宗教曾经对神话执行过的使命, 虽然并不怀着敌意的取代企图, 却意在立足于自身, 阻止日益紧缺的意义资源逐渐丧失。经过民主启蒙的健全理智还必须警惕媒体对价值差异的无害化和喋喋不休的庸俗化。其实, 只要为那种几乎被遗忘的、但内心怀恋着的东西找到一种拯救性的表达, 迄今为止仅在宗教语言中充分得到精确表达的道德情感便会获得普遍的共鸣。一种并非毁灭了一切的世俗化应该发生在转换的过程中, 而这便是作为世界性世俗化力量的西方能够从自身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尤尔根·哈贝马斯:《信仰和知识——“德国书业和平奖”致辞》,第79页。
必须注意的是,依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模式讨论宗教现代性,其主轴仍是世俗化的架构。
诚如曾庆豹指出的:宗教进入此一架构后,要想涉入公共领域,不受限于私人化,就必须将其原本采用的宗教语言去脉络化,翻译为人际经验与存在经验中所具有的世俗意义,也就是一种公共语言,方得能为世俗所接受。*曾庆豹:《论哈伯玛斯的“后世俗社会”与世俗化中的宗教问题》,收录于《从对比到外推:沈清松教授祝寿论文集》,2009。北县: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第251,256页。
后世俗社会固然绝非一没有宗教或彻底世俗化的社会,然而其凭依的多元论,乃意指在公共领域中存在着多元主义的生活方式,以致于宗教要获公开承认,必先转译成公开认可之意义。以至于后世俗社会实为一以转译方式再次促进宗教世俗化的方案。*曾庆豹:《论哈伯玛斯的“后世俗社会”与世俗化中的宗教问题》,第251页。
于是,原本基督宗教彼岸或“外在超越”的上帝,被转换成“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的主体。其中“内在”意指交互主体的语言性的社会认知行动,“超越”则只合乎规范的理性,因上帝即逻各斯。*同上,第256页。
童世骏也认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是“在世俗化背景下重新开发宗教资源的一种方案,是对基督教传统的‘超越性’作内在化的处理。”*童世骏:《“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页15。
他指出:哈贝马斯宗教观的核心观念是“内部超越(transcendence from within)”*同上,第7页。,其特点是在对此观念作语言学或语用学的解释。*同上,第9页。
他主张:依哈贝马斯的观点,“我们作为能力健全的说话者在日常语言交往的语境中进行交往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超越性的、越出特定语境之外的隐默的预设。”以至于“我们的语言交往和由语言构成的生活世界中,已经存在着一个内置的超越性环节:‘任何人只要为达成理解而使用一种语言,他就使自己面对着一个内部的超越。’”*同上,第9—10页。
除了将宗教由外在超越转化为内在超越,还必须注意哈贝马斯也承认后世俗社会的前提是一已然世俗化的社会,所面对的是多元现代性。然而,正因为现代性的多元化,使当代尚未全然发展出现代性的社会,得以获致抗拒西方现代性的正当性,不再以西方为范式,而能自求发展。如此一来,是否可能发展出非世俗化的现代性社会模式,是可以思考的方向。却也因此,后世俗社会模式是否能适用于这样的社会,则需再做进一步检视。
正是依于此一多元现代性的思考脉络,我们得以提出、建构中华现代性的概念,并以之检验、反思前两节所论析的世俗化与后世俗社会理论。毕竟,就社会之功能分化与多元论而言,中国社会早已世俗化,甚至因此一度被认为是一无宗教的社会。
四、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胡适在民国十七年所著《名教》一文中,开篇即说:“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胡适:《胡适日记全集5:1928~1929》,2004年。台北:联经。页232。金耀基指出,此一观点“恰恰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对中国宗教的基本态度”。*金耀基:《序言: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收录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200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页。
这意味着在中国开始思考如何迈向现代性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定位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杨庆堃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给此一定位问题负面答案,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对宗教的认知,“在欧洲、印度和中国这世界三大文明系统中,唯有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最为模糊”。*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1页。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虽然在中国民间社会可以看到大量巫术、神秘信仰的活动,却无法由这些信仰仪式表面看出明显伦理意涵,以致由最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开始,即认定中国人是一群迷信的人。*同上。再方面则源于在中国社会、政治居主导地位的,并非西方的宗教教义与神职势力,而是世俗取向、持不可知论的儒家传统。支配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是儒家伦理,而非如西方基督教的宗教伦理。*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1—22页。
第二个原因则是呼应全球的世俗化潮流,一方面随着以科学挑战、蔑视从而动摇宗教地位的理性化时代来临,追随西方因而高扬科学大纛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会把握时代精神,避开宗教论题。*同上书,第24页。另一方面,则因于面对西方政治、经济优势,中国知识分子唯有通过强调中华文明伟大才能满足其心理需求。既然在理性主义至高无上的时代,普遍轻视宗教,尤其是巫术崇拜,自然会觉得社会中存在富神秘色彩、被视为巫术宗教的道教并不光彩,是民族的羞耻,当然要强调中国社会非宗教。*同上。
经过前两节的论析,可明显看出,以上两个理由中真正具关键性的是第一个。
中国宗教的模糊性,源自在中国社会制度框架体系下缺乏一个结构显著、正式、组织化的宗教,一般百姓的宗教仪式被视为是非组织性的,且宗教在中国社会与道德秩序中似乎也不重要。以致Max Weber(Karl Emil Maximilian “Max” Weber)认为中国民间信仰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同上书,第34—35页。
杨庆堃指出:之所以会对中国宗教作这样的诠释,主要原因是在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现象时,是以基督宗教世界的模式为参照。*同上书,第35页。因此,他试图摆脱西方模式的制约,以中国的宗教经验来定义宗教,尤其是找出可恰当诠释迥异于西方社会宗教的中国宗教特性的方法。*金耀基:《序言: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第9页。
杨庆堃先援引瓦哈(Joachim Wach)的结构性视角与田力克(Paul Tillich)的功能性视角,将宗教定义为:
信仰系统、仪式活动和组织性关系,其目的是处理人生面对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比如那些可能会破坏人类社会关系的现实威胁:死亡的悲剧、不公正的遭遇、难以计数的挫折、无法控制的战争等;而教义的证明就是用以应付来自实际经验的矛盾现象这些问题超越了有条件、有限的经验和理性知识世界,作为人天性的一部分,不得不在非经验领域中,从信仰之处寻找支持,而非经验领域作为精神力量在人的超自然经验中获得灵感。*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19页。
他并因而强调明显存在于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的超自然因素的重要性。指出:
在中国人现实的宗教生活中,宗教是建立在对神明、灵魂信仰和源于这种信仰的仪式行为、组织的基础上。对宗教典型的中国式论述,是将超自然因素作为中心对象,区别宗教与非宗教的标准。民众宗教生活是以神明、灵魂的观念为中心的,而现在对宗教批判的主要观点就是宗教含有超自然信仰的成分。看来,忽略了超自然因素,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概念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客观内容。*同上书,第20页。
进而在受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分散性(Diffuseness)与特殊性(Particularism)概念的启发下,*同上书,第17页。以结构功能法分析中国社会时,分辨出两种宗教结构:一是存在于西方社会,有自己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之外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它自成一种社会制度,有其基本的观念和结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35页。
另一则为存于中国社会,其神学、仪式、组织是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分散性宗教的信仰和仪式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成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宗教以分散的形式发挥多种功能,并以组织方式出现于中国社会生活中。*同上。
诚如金耀基所指出的,杨庆堃提出分散性宗教的概念,既为何以宗教在中国社会极为重要,却未如欧洲、阿拉伯文化般成为一独立因素而存在(中国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是分散性宗教,制度性宗教则相对薄弱)做出解答,还为中国宗教形式界定出一符合社会学规范的范式,更使那些存于中国民间生活中的信仰仪式得以被视为中国宗教来检视。*金耀基:《序言: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第9—10页。
然而,金耀基也指出,对于杨庆堃此一创见,中外学者有着不同认知。中国学者多无异议,甚至肯定“以‘分散性’来给中国宗教以理论界说,使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进行平等的、文化层面上的对话成为可能。”*同上书,第12页。
有些精通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却不以为然。金耀基以欧大年(Daniel Overmyer)为例,指出欧大年认为由于diffused一词在英文的理解上有劣等之意,以之指称中国宗教,遂带有明显贬意,暗含将中国宗教视为劣等之意。欧大年进而主张,我们不可以西方基督教模式的宗教理解来判断中国人的信仰活动。*金耀基:《序言: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第12—13页。
欧大年自己是这么说的:
杨氏认为“制度性”宗教意指与国家、寺院的僧侣、道观的道士以及民间宗教教派相关的仪式与信仰。问题在于他的“分散性”宗教的提法,“分散性”意味着缺少组织结构。实际上,寺院和民间小区的祭祀仪式都是以家庭和乡村生活的秩序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相关的,根据家庭和寺院的传统,它们精心地安排各种计划、组织各种活动。因此,这种融入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宗教是深深地制度化的,并且不断延续着。它们不是个别的、分散的现象,而是制度化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16页。
金耀基认为,这是将欧洲文化概念强行移植于远东文化的复杂过程所造成的后遗症。*金耀基:《序言: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第3页。也就是中国在列强威迫下追求现代性发展的结果。
针对此一发展过程,金耀基先是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虽存在类似西方观念指涉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现象,问题在中国文化无法以其心智结构(structure mentales)确切表述出这些属于欧洲文明的概念。*同上书,第13页。进而指出,此一中西文化在心智上差异的重要性,并未受重视。原因在于上述来自欧洲的概念,自引进后,经数代知识分子消化,早已成为他们心智世界的一部分,且十分娴熟地将其运用于本土文化。*同上书,第13—14页。
更复杂的地方在于,西方范式世界化,使上述概念本身即代表某种价值。经由如此转化,遂使西方在理解中国时有了偏差,西方对中国宗教的各种解释,及伴随这些偏差而来,“结果是以儒教来置换中国的宗教实践,却排除了一个巨大的民间宗教实践领域。”*金耀基:《序言: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第14页。
其实,“宗教”一词不见于中文古籍,以之翻译英文religion,据说是首先出现在1869年美国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抗议公函中。*李庆:《“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儒教”说》,《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4卷第4期,第9页。作为一个翻译过来的概念,诚如金耀基前所指出的,以传统中国文化的心智概念其实无法将其加以确切表述。
此所以,杨庆堃在藉西方宗教概念提出中国宗教的中心内容为超自然因素的设想后,还必须以之与“教”、“道”、“宗”、“门”等“传统中国宗教的概念”做比较,指出这几个有关宗教的名词之共性为“引导人生”,在辞意上其实缺乏明显的超自然思想,要在中国人以神明、灵魂观念为中心的现实宗教生活中才能找到证据支撑。此外,还必须将超自然因素与“迷信(superstition)”、“巫术(magic)”的关系做一说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0页。
此所以,杨庆堃故如前文所引,指出中国的宗教实践为儒教所置换。此一论断却必须面对“究竟是儒家(儒学)还是儒教?”的检验。
五、 究为儒家还是儒教
杨庆堃指出,西方文献常将儒学视为宗教。其站得住脚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基督宗教传统的影响,相对于基督教所具以其系统性与道德价值的强制性主导传统社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居主导地位且被广泛接受的则是儒学的道德价值;其次,以功能论视角将儒学视为宗教,则因儒学确发展为一带终极道德意义的体系,而给了处理生活终极意义的无神论信仰体系一个正式宗教地位。*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40页。
事情却非如此简单即可结束。
儒家是否为宗教,乃一跨越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的问题。
就时间言,“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议最远可一直上溯至明末清初开始长达超过三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如果说此一争议是由西方来中国的传教士发起,则至迟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等组“保国会”标举以“保国”、“保种”、“保教”为设会宗旨,由国人开启了儒学是否为宗教的争议。*段德智:《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第17—18页。就空间言,则不只中国,至少19世纪中叶以降的日本,其争议就一直延续到今天。*李庆:《“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儒教”说》,第5—13页。
对于此一争议,我们且以一篇评论与一篇回应为引来说明。
陈建洪2000年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发表了一篇对刘述先以田力克(Paul Johannes Tillich)的终极关怀论证儒家具宗教性的评论。文中除不止一次指出刘述先的英译不准确、有问题;指出刘述先在使用“超越”与“内在”二词时,用的是自定义,与基督教语境中的原来用法大不相同,致生混淆;在谈终极关怀时,更主张刘述先只是运用这个词,实质上与田力克所讲终极关怀几乎毫不相干;该文最后则指摘:刘述先只讲儒家具宗教性,对儒家到底是不是一种宗教的问题,态度相当暧昧不清。*陈建洪:《终极关切与儒家宗教性:与刘述先商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总第五十八期,第87—93页。
刘述先在该刊次期对陈文作了回应,他指出:陈文中所谓的不准确,其实是陈氏自己标新立异或未能适当掌握英文语意或作者原意;接着指出,一个文化与异文化接触,通常会用自己熟悉的文字概念去疏释外来东西,却不可能完全一致,何况他只是借西方东西以对比方式阐发自家义理;中文与西文不同,陈君对中国思想方式十分睽隔,对中文的理解也有问题;最后,刘述先指出关于宗教这样复杂论题,不可能有简单明了答案,完全不适合二择一的方式,何况儒家还有其他宗教没有的一种特殊暧昧性,至于他对儒家的论断则为儒家不是组织宗教,但有宗教性,是一种相当于宗教信仰的东西。*刘述先:《对于终极关怀与儒家宗教性问题的响应》,《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总第五十九期,第115—117页。
以上两位的短暂交锋,正显现了我国社会文化在追求现代性时会遭遇的问题与会有的反应:一方要求既是引用西方理论、概念,就一切应以西方为基准(无论自己是否做得到);另一方则主张与西方接触最重要的是证成自己,引用西方概念,乃所以厘清、说明自己。
李庆则展示了另一必须注意的现象:文化不同、语境不同,即便所用文字相同,其所指涉内容亦告不同。中日两国对儒家是否为宗教的讨论即其例。*李庆:《“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儒教”说》,第10页。
他指出,儒教的说法在近代流传,和日本有更直接关系。这是因为18世纪中叶日本的儒家学者为争取自己的存在权与对日本社会的领导权,与当时的神道竞争。神道系人士首先强调自己为宗教,于是儒家学者亦自称为宗教之教。唯日本主要是在伦理道德层面接受儒学,以致日文之“儒教”一词生成于伦理语境,其“教”意指“教育、教化”,故“儒教”即“以孔子为主的教学,儒学之教”的意思。20世纪后,日文文献中常以“儒教”为“儒学”之同义词,而逐渐定着为日文化的一个专门词汇。至于在汉语中,则“儒教”一词有更多神学、宗教色彩,而儒学较世俗。*同上书,第9,10页。
大陆对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则自1978年争议迄今。段德智将其整理总结出:尽管争论伊始双方观点似水火不容,到最后则无论对儒学是否宗教持何立场,绝大多数学者都对儒学具宗教性方面大体达成共识。*段德智:《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第24页。
由于主张儒学虽非组织宗教,但具宗教性的,始自当代新儒家。因此,对儒学何以具宗教性的论析,需引用当代新儒家的讨论。
如前所述,刘述先主张儒学自汉代以来即为“朝廷意理(state ideology)”,儒家信仰可以安身(心)立命,为田力克所谓的“终极关怀”,故将儒家视为一“精神传统(spiritual tradition)”是合宜的。*刘述先:《先秦儒家之宗教性》,《哲学与文化》,2012年第卅九卷第五期,第5—6页。
此处以刘述先论析孔子思想的终极关怀为例来说明。刘述先指出:孔子面对周文疲弊、世衰道微,主张“复礼”,其意不在恢复古礼,而是要人克制自己以回归吾人生命内在本有的礼仪,也就是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12)。他的终极关怀为比生死重要的“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15),而内在的仁展示出来就是礼——“仁内礼外”。*同上书,第6页。
虽倡导一彻底现世主义的思想,却不否认鬼神存在。孔子一生对天敬畏,但他所认知的天不像西方上帝般彰显意志,而是全无人格神特征的“无时无刻不以默运的方式在宇宙中不断创造的精神力量,也是一切存在价值的终极根源”。*同上书,第8—9页。
进一步,刘述先认为,要理解孔子,不可以二分法在俗世(seculrr)与神圣(sacred)、理性(reason)与信仰(faith)间划一不可跨越之鸿沟,而是在俗世的日用常行中贯串着神圣的魔法作效。因此,可以“内在超越”来阐发孔子思想。*刘述先:《先秦儒家之宗教性》,《哲学与文化》,2012年第卅九卷第五期,第7—8页。
于是可说:孔子相信由天(超越)到人(内在),由己及他,只是一个道理,也就是他那“仁内礼外”与“天人合一”的一贯之道。*同上书,第10页。
杨祖汉则诠释唐君毅的思想,指出:
说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间之伦理道德,而不重人对神之宗教信仰,此并不错。但此一说法并不必涵重人间伦常道德而不重人对神之信仰者,为没有超越的宗教感情。中国文化精神,很可以是就在伦常的道德实践中,表现了超越的宗教性感情,而此宗教性之超越之情,因直接由伦常实践而发出,故不必藉对作为超越之信仰之对象,即上帝之崇拜而表现。此超越的感情,因即于伦常实践而表现,故并不突显其超越相,超越者与现实之践履融而为一,即中国文化之重人间性,亦表现了其超越性,亦可以说是由人与人间之实践,给出了一条真实接触超越者之途径。此“超越而内在”之说,是当代新儒学理论之核心义旨。*杨祖汉:《儒学的宗教性》,《鹅胡学志》,2008年第四十期,第78—79页。
当然,也有人主张不宜强调儒家的宗教性,李庆即主张这是欲将儒学宗教化的一种企图,其重点不在真去考证过去儒家学说是宗教,而是着眼于在过去学说中发觉宗教内涵,将儒学解释为宗教,冀图在未来使儒学以西方religion形态发挥对人终极关怀的作用,使儒家学说得以在未来发挥作用,从而恢复中华传统文化。然而,这样做是在异化自己也异化别人。*李庆:《“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儒教”说》,第11—12页。
李庆甚至指出:过度强调儒学的宗教性,易在与不同文化交往时产生误解,促成偏激的宗教情绪。“套用西方的模式,重走日本从‘宗教’的角度,强调儒学的‘宗教性’,以此介入现实社会的道路,对于正在逐步走向复兴、走向世界的中国,并非是一个好的方法。”*李庆:《“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儒教”说》,第11—12页。
确实,所以会强调儒家的宗教性,与现代性有关,其参照点是西方社会。西方社会之伦理道德是以基督宗教为基底,Habermas甚至以此为基督宗教在受自然科学冲击下的多元现代性后世俗社会中最能发挥价值的部分;中国社会之伦理基底则在儒家思想。所以杨祖汉会强调唐君毅先生认为:
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没有独立的教会组织,并不是缺乏宗教精神或超越意识,而是宗教精神与伦常实践等活动不隔之故,人若于人生种种活动上尽其所当尽,随处可见神圣之价值,而表现了宗教之精神。表面的宗教之缺乏,其实是因为道德与宗教一体相融之故。*杨祖汉:《儒学的宗教性》,《鹅胡学志》,2008年第四十期,第81页。
杨祖汉甚至进而激越地主张:“吾人其实可以即道德即宗教,伦常实践即是超越的宗教精神之表现处来规定宗教,以此彻上彻下之形态以言圆满的宗教形态,为什么不可以呢?何必事事以西洋为标准?”*同上书,第83页。
其实,只要回到杨庆堃对两种宗教形态的建构,即可知道杨祖汉的论述,相当程度上是源于以为只要是宗教就必须是制度性的。
杨庆堃指出:“制度性宗教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运作,而分散性宗教则作为世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功能。”*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69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
制度性宗教在神学观中被看做是一种宗教生活体系。它包括(1)独立的关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神学观或宇宙观的解释,(2)一种包含象征(神、灵魂和他们的形象)和仪式的独立崇拜形式,(3)一种由人组成的独立组织,使神学观简明易解,同时重视仪式性崇拜。借助于独立的概念、仪式和结构,宗教具有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故而成为制度性的宗教。另一方面,分散性宗教被理解为: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68—269页。
“在中国,制度性宗教主要表现为普世性宗教,诸如佛教和道教,以及其他宗教和教派团体。”*同上书,第269页。至于儒家,杨庆堃认为以下论述不无道理:
儒学作为社会教化准则经过千百年来的贯彻实行,已经为广大民众下意识地接受,既是理性教化的实体,也是一种情感态度,就这一意义而言,儒学可以被视为一种信仰。但是儒家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因为它不设偶像,也无超自然的教义作为其教化的象征。然而,这并不意味著作为理论体系或制度性功能架构的儒学缺乏神学的感召力。*同上书,第225页。
儒家所以能在过去2000年成为支持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结构运转的制度化正统学说,即因其思想兼具理性主义与宗教面向。*同上书,第236页。
此处以儒家为例,讨论中国社会中宗教的现代性议题之所以合适。固然是因为儒家思想具宗教性,更因为对于儒家是否宗教的辩论,乃至对其作出虽非宗教却具宗教性的论断,均使我们得以确认世俗与神圣、理性与信仰这类二分法思考下的认知,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
偏偏现代性与世俗化密切相关,要理解世俗化却必须先确立对宗教的理解。如以中国社会的宗教形态主要属于分散性,则中国社会其实并无世俗化使宗教消逝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社会不乏宗教宽容,在追求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也不会激起宗教原教旨主义式的反弹。
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宗教完全不受现代性影响。只是其影响面向,不同于西方。也就是说,在多元现代性的认知下,我们可藉由试行理解民间宗教此一我国宗教现象的特质所在因发展现代性而变迁的现象,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现代性模式——中华现代性。对此,本文乃以对台湾地区民间宗教所做研究与成果为例,于下节略做探述。
六、 世俗化与台湾宗教的发展
关于台湾宗教,首先应注意到其具备多元与模糊的特质。
多元,是据台湾内政部门统计,迄2014年为止台湾地区主要的宗教类别就有21个,这还不包括归类于“其他”项目中,未列入统计类别之宗教。*见台湾内政部门民政司宗教辅导科在网页上公布的“台湾地区宗教类别统计说明”http://www.moi.gov.tw/dca/02faith_001.aspx。
这一数目,如果不以宗教而改由依人民团体法立案之宗教性社会团体来检视,则目前台湾性宗教社会团体大约有1,000个,地方性宗教社会团体约有900个。*台湾内政部门指出:目前台湾宗教团体的组织形态主要有“财团法人”、“寺庙”与“社会团体”3类,唯其所收集之“财团法人”资料,是针对前述21个宗教,关于寺庙的资料则有13447笔,主要属佛教、道教与一贯道的寺庙,故本文只举出社会团体之数据以显示宗教之多样性。见http://religion.moi.gov.tw/Home/ContentDetail?cid=001-2&ci=1。
同样在2014年,丕攸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宗教与公众生活计划(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Project)公布全球宗教多样性报告,以宗教多样性指数(Religion Diversity Index)10分为满分,就全球23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其中指数最高的是新加坡,拿下9分,中国台湾以8.2分名列第2。*见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Table: Religious Diversity Index Scores by Country’ http://www.pewforum.org/2014/04/04/religious-diversity-index-scores-by-country/ 此一报告所指涉的宗教,除了基督宗教等世界性宗教,还包含民间信仰,乃至无宗教认同者。见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Global Religious Diversity’ http://www.pewforum.org/2014/04/04/global-religious-diversity/。
模糊,与多元相关。
以丕攸报告为例:该指针显示:在2010年台湾的23,220,000人口中,基督宗教徒居5.5%,佛教徒有21.3%,民间信仰占44.2%,穆斯林、印度教徒与犹太教徒均少于0.1%,此外,除其他宗教信仰有16.2%,更有21.3%的人口是属于无宗教认同(Unaffiliated)。*丕攸报告以该词指涉自认对诸神或超自然存有缺乏信念者、不可知(怀疑)论者以及没有特定信念者。
这样的宗教人口分布,如以美国国务院最新(2014年)发布的《201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2013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对台湾宗教人口概况所做描述,则可看出:
美国政府估计台湾人口约为2,330万人。根据“内政部”宗教辅导科2005年进行的全面调查显示,台湾人口中有35%自视为佛教徒,33%自视为道教徒。虽然自此之后“内政部”未再对宗教信仰的状况进行追踪,但内政部表示此一统计数据大致上没有改变。
虽然绝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人或是信佛教,或是信道教,但是也有很多人自认既是佛教徒,也是道教徒。
很多人除信仰有组织的宗教外,还信奉中国传统民俗宗教,包括某些面向的萨满教、祖先崇奉、及动物崇拜等。研究人员与学者估计,有多达80%的人口信奉某种形式的传统民俗宗教。这类民俗宗教可能与个人信奉佛、道、儒教、或其他中国传统宗教同时并存。
在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台湾社会变迁全记录”网站中,其“台湾民众信仰类别的变迁”条*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E5%8F%B0%E7%81%A3%E6%B0%91%E7%9C%BE%E4%BF%A1%E4%BB%B0%E9%A1%9E%E5%88%A5%E7%9A%84%E8%AE%8A%E9%81%B7.更进一步论析出:
宗教的分类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因此在探讨台湾的宗教信仰时,在类别上必须加以适当调整。然而这项分类工作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很大的困难存在,主要是在“佛教”、“道教”、“民间信仰”这三种宗教类别上。很多实际上拜关公、妈祖、土地公等神明的民众,会自称“佛教徒”,有的会称自己信仰的是“道教”,这是因为这类信仰是一个没有宗教认同可以用来指称的信仰系统,而“民间信仰”只是学术界的术语而已。譬如“内政部”的《内政概要》里,就没有“民间信仰”这个分类,因此根据该概要至九十三年底的统计,“道教”信徒有767,906人,成为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
另一方面,什么是真正的“佛教徒”也很难认定,虽然在实际调查的时候,学者曾经用“是否皈依法师”、“吃素”、“做早晚课”等指标来界定真正的佛教徒,但也仍然有争议。而在另一方面,自称“无宗教信仰”者,也未必就是无神论者,可能是比较弱化的民间信仰者,也就是不会主动去拜神明,但是可能会跟着别人拜。
其“变动中的台湾宗教信仰”条*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E8%AE%8A%E5%8B%95%E4%B8%AD%E7%9A%84%E5%8F%B0%E7%81%A3%E5%AE%97%E6%95%99%E4%BF%A1%E4%BB%B0.亦指出:“在台湾社会里,没有宗教信仰、民间信仰、道教和佛教这几种信仰,彼此之间在认同上容易产生混淆,也很难有客观的认定标准。”
这种重迭、模糊的宗教信仰现象之所以可能,乃因前文所指出的,我国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是民间宗教——杨庆堃所提出的分散性宗教,制度性宗教则相对薄弱。也就是说,当试图以西方制度性宗教的概念来掌握我国宗教人口时,表面上当下可见的是,台湾人对自己所信宗教为何,在认知上极为模糊;进而检视其所以如此的成因,则可知,关键在于以外来概念套用于本土社会所促成的扞格。
对于台湾地区宗教,第二个必须注意的特质是,其发展与世俗化密切相关。
瞿海源与姚丽香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指出,台湾地区宗教在1950年至1979年的三十间有着明显的兴衰变化,然而各类宗教面对相同社会变迁却有不同反应形态,其关键在世俗化。*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一):台湾宗教研究、术数行为研究、新兴宗教研究》,2006年。北县:桂冠。第1页。
该文将世俗化界定为“信徒将宗教与世俗日常生活结合的强度,结合愈强表示世俗化程度愈深,反之愈浅。”,并以此定位宗教。指出,民间信仰世俗化程度最深,天主教次之(但二者有很大程度差距),主流基督教会与长老会又次之,真耶稣教会乃世俗化程度最浅的基督教会,佛教则为世俗化程度最低者。*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一)》,第24—25页。
随着台湾整体社会变迁所促成世俗化趋势,世俗化极深且十分普遍之民间信仰并无衰落情形,世俗化极浅的佛教与真耶稣教会维持稳定或缓慢持续成长状况,至于天主教与基督教其他教派则因其中度世俗化而有先盛后衰情形。*同上书,第25页。
此外,台湾地区新兴宗教的发展也深受世俗化影响。
瞿海源在其后续研究中,引用卡萨诺瓦(José Casanova)的世俗化论述,指出世俗化最关键的主题(正如本文前所述)是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ciation)*卡萨诺瓦主张世俗化包含社会分化、宗教衰落、宗教私人化等三主题。但是,瞿海源指出,第二、三个主题在晚进社会发展中已无法维持,宗教非但未衰落,反倒有兴盛趋势,且在现代宗教在许多社会,趋向于愈来愈频繁地涉入公共领域与事务。转引自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二):基督宗教研究、政教关系研究》,2006年。北县:桂冠,第2页。在西方社会,促成社会分化的因素大体有四:宗教改革、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兴起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其中宗教改革乃世俗化之原动力。*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二)》,第3页。
不同于前文所论述Dobbelaere以社会分化促成世俗化的论点。瞿海源指出:新兴宗教之发展,有些是因于世俗化,也有是因于对世俗化的反弹。*同上书,第5页。
其关键在自由化。这是因为台湾社会不曾出现宗教改革,而政治朝自由化发展之历程,既促成多元化,更因而确立了宗教宽容政策,使宗教得以自由发展,新兴宗教从而得以合法化;资本主义在台湾的主要发展在促成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其对宗教的影响,在使商品逻辑渗入宗教,且使几乎所有宗教本身均商品化地投入宗教市场,其中以新兴宗教表现得尤为突出;科学发展与普及本为世俗化的重要力量,但科学发展不能解决人的心里、心灵问题,且现代科学本身的不完美,更提供有异于正统科学的另类科学知识发展空间,从而促成新兴宗教。*同上书,第7—10页。
当然,也有因不满于上述发展(对现实世俗政治、市场逻辑的利益动机、科学发展所生问题的不满)而出现极端强调神圣性的新兴宗教,或产生主张回归传统的基本教义派。*同上书,第5页。
瞿海源指出:台湾新兴宗教的发展,除了前述社会因素,还必须注意到信仰者个人的心理需求、宗教的领袖、灵验性与组织。
由于自由化一方面带动社会结构急遽变迁,再方面则既带来更多自由、选择,也带来强烈不确定感;市场化使个人在经济上亦面临不确定感;现代尖端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更使人在应用时充满不确定感。
为消灭不确定感,祈求宗教、术数的机会遂大增,从而提供新兴宗教发展机会。*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二)》,第14, 18, 24页。瞿海源指出:当世俗方式无法排除不确定感时,个体会寻求以下三种另类方式因应:首先是更深入挖掘本身文化或引入外来文化,这基本上仍是世俗的;其次,从非世俗宗教寻解决;最后,从古今中外的术数中求解决。后两种促成了兴宗教与术数现象的兴起、发展。见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二)》,第16页。
除上述心理需求,新兴宗教领袖具有独特魅力,除提出简单、有说服力的教义,更有特殊神奇能力,致几乎被当作神佛崇拜,又能传授神奇、易学的修行功法,使弟子也能获得超凡能力,从而构成宗教整体且具扩散性的灵验性,透过膨胀中的信徒网络传布。*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二)》,第18—20, 24页。
在快速、富裕的社会中,人们迫切寻求增进身心健康并消灭不确定感。新兴宗教领袖多有一至数种功法、心法,简单易学而难精,但一学就有效,使信徒身心状况得以改善,信徒因此而生的报恩心加上团体效应,遂成就若干盛极一时的新兴宗教。*同上书,第25页。
例如,“青海无上师世界会”(正式登记的名称为“中华民国禅定学会”)的两大核心因素为:教主青海被相信具有特殊能力、特质与世界性历史使命,青海教给信众的一套独特修行方法。除此之外,大部分信徒即便参加教团,仍对教义无太深刻了解,其教义也只以个人身心平衡与成长为主要考虑,并不特别强调社会道德问题。*丁仁杰:《社会分化与宗教制度变迁——当代台湾新兴宗教现象的社会学考察》,2004年。台北:联经。第527—528页。
另个例子是真佛宗。这是个集合各种仪轨、咒术有高度融合性的教团。这些仪轨既能用以召请神明相助产生灵验效果,又有助于个人通往救赎的身心修持,前者类似于民间信仰,后者则近似具灵修性质的瑜珈。此外,这种融合性,使其既可与民间既有传统做广泛连结,又可自立宗派、成立新教团,不受既有组织、个别传承的限制。*丁仁杰:《社会分化与宗教制度变迁》,第542,545页。
丁仁杰指出,以民间信仰灵验性为基础,以仙佛认定的济世度生代理人自居,并能在此基础上提供较完整的修行模式、动员方案,实是卢胜彦能在民间广受欢迎原因。民间信仰在适应现代社会所特别需要强化的自身正当性基础、系统性知识体系与组织动员工具,真佛宗都能提供,这正是它得以快速蓬勃发展的原因。*同上书,第593页。
以上现象所以发生,关键在于国人面对宗教的基本心态是高度功利性,也就是世俗性的。
在“台湾社会变迁全记录”的“信仰宗教的目的”条显示:*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E4%BF%A1%E4%BB%B0%E5%AE%97%E6%95%99%E7%9A%84%E7%9B%AE%E7%9A%84.
在1994年、1999年、2004年的“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调查”问卷中,都有一题复选题,询问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您为什么会信目前这个宗教?”
高达将近七成的受访者回答是“跟父母信的”,是全部选项中占最高比例的一项。
占次高比例的是“寻求平安”,有四成多的受访者选择这一项。而回答“寻求精神寄托”的也有两成多。至于和宗教教义或者宗教修行有关的,譬如“寻求真理”、“寻求救赎或忏悔”、“了解生命意义”、“寻求智慧”、“减少烦恼”、“解决特殊困难”、“寻求安慰”等原因,回答的比例都不是很高,大约在一成到两成左右的受访者这样回答。
这一调查结果,尚可用以修正前述瞿海源对新兴宗教领袖魅力的解析。因为“这三个年度的问卷调查数据都显示,只有2%左右的受访者是因为宗教师的吸引力而信仰目前这个宗教。”*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E4%BF%A1%E4%BB%B0%E5%AE%97%E6%95%99%E7%9A%84%E7%9B%AE%E7%9A%84.这意味着,所谓领袖魅力,重点不在其人格特质,而极可能是在其所拥有的特殊神奇能力。
此所以,要理解台湾地区的宗教,最具代表性的,乃是民间宗教。同样地,要理解台湾地区宗教的现代性转型,亦宜由民间宗教的变迁着手。
七、 台湾民间信仰的现代性转型
瞿海源与张珣于1989年发表的论文,以对访谈记录进行内容分析为依据,整理得出民间信仰具有以下特征:*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一)》,第101—105页。
首先,民间信仰以灵验为本位。神格高低固可影响寺庙香火,更重要的是神祇灵验与否。只要灵验,无论是什么神明、也不论神明由来,都会不远千里去拜。因此,通常不会固定拜某一特定神明,也由什么神都拜衍生出包容性强的多神信仰。
其次,民间信仰对神明缺乏清楚观念。不少人甚至只是跟着拜,说不出神究竟是什么。在界定神明时,大多数人认为神明是提供心灵安定和寄托的,也有人认为神是伟人善士死后被追奉为神来祭拜,另外有人认为神是超凡万能、具有法力能救济众生。
因此,神佛属于什么教什么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庙都得有个人形神佛偶像可供烧香膜拜,有杯茭、签诗作为与神灵直接沟通的工具。这种民间信仰的态度,甚至影响到制度性宗教,不但佛教寺庵不得不有这些道具,连原本在日本的教堂中只以镜子作为其神“天理王命”象征的天理教,在日据时代传到台湾后,有些教堂不但有杯茭,甚至雕刻神像以代替象征性的镜子。*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一)》,第385页。
民间信仰的忽视教派、佛道不分,可以清水祖师的教派归属为例。民间一般供奉的清水祖师着袈裟、戴僧帽(未戴帽则光头)、盘腿而坐,座下一双僧鞋。但在道教文献中,称清水祖师原奉道教,是为抗元兵入侵才着僧装劝化国人反元,故应为道教神。于是清水祖师被认为是亦佛亦道的神。*同上。
此外,祀奉关胜帝君、天上圣母、孚佑帝君及王爷等道教神祇的庙,有被认为属于佛教的;也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地藏菩萨等纯粹佛教神,被当成道教神的。*同上。
总之,就一般人宗教行为看,区分宗教并无意义,只要是庙中祀奉神佛偶像,就有超自然神力,就能拜。重点是灵验,被认为最灵的神明,就会得较多香火。*同上。
再次,民间信仰是较具功利性的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信众所求最普遍的是平安——生活安顺无事(家庭和睦、健康、家道兴旺、家无变故)。不一定有事才去,而是一种生活习惯。平安是信仰中心,神明即在守护信众生活。对神佛多无超越性终极关怀,民间信仰乃以求实际生活平安乃至富裕安适为其功利取向之基调。其次要部分,才是寻求内心寄托、智慧解脱与广植福田。当然,也有只是习惯性地去寺庙参拜。
最后,信众固求神明保佑平安顺利,仍主张需自己努力才有成功机会。只是在神明指示下,更有可能成功。
瞿海源以此为基础,指出民间信仰因现代性发展而呈现的变迁:*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一)》,第63—68页。
首先,民间信仰是凝聚地方认同感、团结力的重要动力,因民间信仰而在地方结合的社会组织,是极少数民间自愿团体中最重要的一种。在早期汉人移入台湾垦殖的艰辛过程中,民众高度依赖民间信仰,一以庇佑个人、家庭,再则以宗教信仰相同为前提,奠定、增强地方族群势力的内在整合。
祖籍神在台湾早期拓垦社会的重要性,显见于各地历史。随着现代性促成的社会流动、都市化、教育与生产形态的变化,祖籍神信仰虽有减弱趋势,但仍随处可见其为地方信仰中心,同时,也如其他神明,逐渐不去考虑其祖籍,而较重视其灵验性。
特别的是一些大多在城镇区、闻名全台的寺庙,不但对地方事务有重大影响,甚至对整个台湾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只不过,随着外地信众大量增加,寺庙固然仍控制在并非宗教人士、神职人员,而是有世俗成就的地方人士手中,但这些人的世俗化程度更胜以往,以致宗教愈形世俗化,甚至在许多地区宗教势力与地方派系紧密关联。
其次,民间信仰强调灵验性已如前述。只是由于只重灵验,以至于原本各有专司、彼此无法取代的不同神明,其特殊性已经模糊,神明功能有普及化、扩散的取向,以致神明类别愈来愈不如灵验性。有应公之类阴神,在台湾早期因开发艰难与族群械斗而为人普遍祭拜,还不至于公然企图利用。随着大家乐、六合彩流行,使有应公因其有求必应的非伦理特性,既强化民众对阴神的信仰,更是信徒迫切企求即刻现世利益的心态暴露无遗。
再次,民间信仰具强烈功利性本质亦如前述。这种功利性格随着台湾经济快速发展而变本加厉。先是1980年初,十八王宫庙异常兴起,接着1986年起大家乐与后续的六合彩开始流行,民众多相信是神明有灵才会出示明牌,于是求神者众,又以阴庙最受欢迎,因为这些由孤魂野鬼转化的阴神,被认为有相当高的灵验性,只要有人供奉祭品,就会帮助这个人达成所求心愿。
此外,一些规模较大、香火较盛的庙,为求进一步发展以有效吸引全台信徒,多各自强调其神灵显赫,以盛大庆典夸耀,并配合媒体报道,使大庙益形闻名遐迩,香火愈发兴盛,寺庙财力愈形雄厚。台湾民间信仰即在此浓厚功利色彩下蓬勃发展。
最后,如前所述台湾民间信仰既求神助,也强调人本身的努力。神明有助消除疑惑、不安,使人在许多可能途径中知所选择,并以积极态度去行动。在此影响下,民间信仰者仍强调工作勤奋的重要价值。随着功利导向与金钱竞逐,这种工作伦理受到腐蚀。*所以会得出如此明显价值批判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者本人态度相关。瞿海源自承:身为外省子弟,少有可能成为民间信仰信徒,又自年轻时即有改革的企盼,又认为民间信仰为一应加导正的保守现象,故对为所有既存制度辩护的功能学派保守立场有所不满。因此,乃以改革为基点,对民间信仰持强烈批判态度,迥异于本省学者维护民间信仰之立场。
上述民间信仰的功利本质,可具体见于民间信仰固有的仪式意涵,随社会变迁,而由简单转为多元功能。仪式不但有新变化,甚至有新生命。例如:礼斗(拜斗)仪式即出现新功能,以满足信众的宗教心理需求。*张家麟:《台湾宗教融合与在地化——以民间宗教仪式为焦点》,2010年。台北:兰台,第29页。
萧登福指出,拜斗出于道教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的星神信仰,旨在祈求北斗七星君为吾人消灾解厄、延年益寿。世人在本命日、生辰、三元、八节与每月北斗下临人世的日子祈拜北斗自己所属的本命星君,可以治病延生、扶衰度厄。《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已有吕蒙病重,孙权“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的记载。由于拜斗可以延生、治病、散祸、消灾、忏罪,所以世人常设斗供以祈求一家平安、生意兴隆。*萧登福:《道教与民俗》,2002年。台北:文津,第50—55页。
张家麟的研究则发现:台湾地区各宫庙的拜斗法会,为普遍、常态、持久的年度活动。但是,除了本质上维持礼斗仪式崇拜星斗以求禳灾延寿的基本形式、功能;谦卑礼神的疏文、经典、咒语的内涵与宗教态度;每日诵经忏悔以求神降临赐福,累积个人功德以成就人生终极救赎;圆斗(完斗)时普施鬼魂,期待鬼神不再附身,礼斗参与者得以平安。*张家麟:《台湾宗教融合与在地化》,第60, 94页。
随着自由化的发展,其他的传统部分:二十四小时诵经与跟拜,除少数宫庙仍坚持,其他多已改为早午诵经与自由跪拜;又由于缺乏制度化科仪,宫庙(甚至鸾堂)负责人多属经营型领袖不知礼斗如何进行,必须外包,以致在法会上执行仪式的儒释道三教神职人员都有,原本由效劳生主持仪式的鸾堂,转为既可由道长、道姑、男女法师,也可由和尚来主持拜斗仪式;所诵经典除“五斗真经”外,涵盖儒释道三家,除大多必颂与所供奉主神及陪侍神相关经典,也念诵佛教经典;传统诵经以个人为主,现在出现团体诵经,乃至法师与信徒一起读经的作法,其诵经方式也加入了梵呗诵经、道教诵经、汉语诵经;至于其进行的仪式,甚至有加入祭祖、解冤释结、消灾祈福仪式者,前述普施鬼魂,也是超乎拜斗本意的一项仪式;至于法会所写、所颂疏文,传统为贯首文、对联、骈体文,现在有改为白话文者,传统由资深效劳生代读,现在有改为信徒自己朗读后集体焚化给神的。*同上书,第60—87页。
拜斗法会因市场化而起的变迁,最典型的表现在所拜之斗,由星斗崇拜转化为神斗崇拜(神祇崇拜)与满足信众各种需求的功能斗崇拜。随着宫庙主事者自己的想法、发明与揣摩信众需求,创造出各种斗的名称,虽大部分与宫庙供奉主神、陪侍神有关,更多在满足一般大众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宗教心灵需求,使拜斗法会的功能提高到万能。*张家麟:《台湾宗教融合与在地化》,第74—75,41页。
例如松山慈惠堂有金母正斗、金母副斗、玉皇正斗、玉皇副斗、地母正斗、地母副斗、紫薇正斗、紫薇副斗、三官正斗、三官副斗、东华斗、斗父斗、斗母斗、东斗、南斗、西斗、北斗、中斗、观音菩萨斗、文昌帝君斗、关圣帝君斗、天上圣母斗、中坛元帅斗、玄天上帝斗、福德正神斗、福寿斗、如意斗、平安斗、天官赐福财神爷斗、文财神爷斗、武财神爷斗、南山通利财神爷斗、北府纳库财神爷斗、招财童子斗、进宝童子斗。*同上书,第75页。
至于信众,则不明白也不在意拜斗的原始意涵,只知道有拜有保佑,拜斗是求神,目的在保平安。祈求事业发展就拜“事业斗”、希望金榜题名有“文昌斗”、渴望结为连理拜“婚姻斗”、梦想发财参加“财神斗”……以致颇为认同且愿意持续参加法会,甚至推荐亲友参与。*同上书,第76,42页。
尤有甚者,宫庙不但创造各种神斗、功能斗,还将斗分为总斗首、斗首、副斗首、斗等阶级,不同阶级需交不同金额给宫庙。于是,既满足信众宗教心灵需求,又达充实宫庙财务之效。*同上书,第76页。
此外,张家麟对鸾堂现在所遇发展困境的研究,则指出:现代鸾堂面临信徒老化、鸾手青黄不接、信徒捐献减少等困境,主要原因来自外部的世俗化冲击、台湾威权体制压力、民主政体教育功能取代鸾堂教化功能、福利社会取代鸾堂社会服务、现代医学取代鸾堂消灾功能,以及内部的宗教仪式与宣教人才不足、缺乏行政人才、为信众消灾祈福与安定信众心灵的能力不佳、组织义工效能不臧。*同上书,第306页。
由于张家麟主张宗教团体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教主魅力、教义符合社会需求、宗教仪式与时俱进以及宗教灵验事迹。因此,为鸾堂解决困境所开处方为:要使鸾堂的扶鸾仪式、鸾书出版、社会救助、鸾文教化、消灾解厄、念经持咒、收惊、祭解仪式等能在现代传承,除维持其神圣性、合理性与神秘性外,需使这些仪式能为具现代科学知识的民众以同理心接受。因此,最重要的是培养仪式人才,应效法制度性宗教的人才培养方式,唯有培养出具领袖魅力的宣教师与合理的宗教仪式,才能吸引信众投入宗教活动。*张家麟:《台湾宗教融合与在地化》,第306—307页。
张家麟所提建议,虽有经验调查为依据,依循的却明显是市场逻辑,并蕴含将民间宗教制度化的意图。
究竟台湾民间宗教是否真如瞿海源所论因过于功利而斫丧伦理价值,或如张家麟所建议应遵循市场逻辑、转型为制度性宗教方得继续发展,都必须做更深入的检验。
例如,张家麟对民间信仰中的善书代表作——《太上感应篇》所发挥社教功能的研究,即指出台湾地区民间信仰者对《太上感应篇》的认同度高,会认为实践儒家伦理道德就是修道,以致实践其中的儒家伦理(包含家庭、社会与政治道德)与部分道家思想,将可带来社会稳定。*同上书,第265,268页。此一结论就相当程度否证了瞿海源民间宗教日趋丧失伦理价值的认定。
至于张家麟的建议,由“台湾社会变迁全记录”的“变动中的台湾宗教信仰”条*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E8%AE%8A%E5%8B%95%E4%B8%AD%E7%9A%84%E5%8F%B0%E7%81%A3%E5%AE%97%E6%95%99%E4%BF%A1%E4%BB%B0.所显示的来看,似不无道理:
“国科会”委托“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执行的“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调查”,其中第二期第五次(1994年)、第三期第五次(1999年)、第四期第五次(2004年)的调查,有一组问卷题目同时询问受访者“目前的信仰”和“以前的信仰”,结果发现有不算低比例的民众,目前的信仰和以前的信仰并不相同,显示这些民众的宗教信仰在过去曾经经历改变,也就是这些民众曾经有过“改宗”。1994年这项比例是18.36%,1999年是26.80%,而2004年则是15.30%。
我们将三次的调查资料合并分析,信仰变动的方向方面,从“流入”的角度来看,信仰改变者主要是改变到佛教,自称目前信仰佛教者当中,有26.9%是从其他宗教信仰类别改变过来的,其中主要是来自于原先是“没有宗教信仰”者和“民间信仰”者。从“流出”的角度来看,“没有宗教信仰”者是最大宗的信仰流出者。在三次调查资料中,自称原本是“没有宗教信仰”者,目前只有47.6%还说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另外的两成二目前已经是信仰佛教,而一成三目前是民间信仰者。由此看出台湾宗教版图的变动方向,乃是往组织化的宗教方向移动。这和国外的研究,认为宗教变迁是从有组织的宗教往“无形的宗教”移动,有很大的不同。
瞿海源指出民众面对社会变迁的不确定感,也会造成信仰变迁,尤其是对于有明确教义的佛教,也就是有组织的宗教,需求因而增加。另外,相对于民间信仰,佛教这类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在传教活动上更为积极,也造成宗教版图往佛教方向移动。
但是,瞿海源的解读,则可由在此一调查所针对的时期之前,台湾地区民众所一度呈现的明显改宗现象来检视。
瞿海源针对1945年到1980年基督宗教在台湾地区的发展趋势所做研究指出:天主教的发展以1963年为转折点,自1953年到1963年信徒成长率每年大都超过10%,这十年的总成长率是876%,同时期的人口成长率是36%,1963年之后则停顿成长,由1963年到1979年,全台湾人口增加39%,而天主教信徒只增加32%。同样地,基督教在1950年到1964年也有298%成长率,1964年到1979年则仅成长29%。
对于此一现象的成因,瞿海源的解释为:因为世界次序的大变动,台湾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局面为之动荡,从而促成极强烈的反世俗化趋势,此时西方宗教势力随着台湾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重新调整,而得以迅速兴起。*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二)》,第62—63页。
随着两岸分立,不仅为数众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与一部分基督徒转进、迁移到台湾,更有上百万大陆籍同胞离乡背井来到台湾。由于局势动荡,政治局面、经济情况乃至一般社会秩序均不稳定,生活清苦不安,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极大负担,而传统民间信仰因无法与地缘、血缘社群关系分割,因大陆来台同胞频繁迁移、混居岛上各地,以致脱离可以落实之聚落,又无标准化经点仪式,终使大陆来台同胞愈来愈疏远民间宗教。而佛教、道教偏于出世,无能在危机状况帮助大多数人世应变局,加上入世性的天主教有甚多来台神职人员,不断迎合大陆籍同胞与原住民的需要设立许多区堂、传道所,基督教也有许多教派传入台湾,更配合发放美国救济物质,乃掀起归主热潮。*同上书,第40—41,62页。
但是,黄克先在对这些改宗者选取三十位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他们入教的契机,在于原本习以为常、按表操课的实践世界突遭变故而中断,使周遭人脉中基督宗教的传教力量有机可乘。至于如何进入基督宗教,则因不同教派特色而有不同,如身在居民间有着绵密社会网络的眷村,就较容易在实践世界中断时被社会网络动员,而讲究灵异体验、以本省人为主的教会,则因于华人宗教医疗传统与对灵异经验的渴求,吸引到原身在同族裔的信徒。*黄克先:《原乡、居地与天家:外省第一代的流亡经验与改宗历程》,2007年。北县:到乡,第220页。
黄克先认为,流亡造成既有社会结构的重大断裂,使他们疏远了传统信仰,不必然意味着会去追求新宗教,单有社会网络,也不足以解释改宗的启动。必须将改宗视为一历程,重视改宗者过去继承的宗教性、遭遇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脉络,强调行动者本身实践世界的特性,才能避免过渡化约的解释。*黄克先:《原乡、居地与天家》,第222页。
黄克先也主张,不宜将改宗者只是视为意义追寻者。意义并非行动者进入宗教的主因,而是进入宗教后的副产品,改宗者在入教前鲜少是意义追求者,往往在入教后才吊诡地成为意义追求者。也就是在成为心口合一的改宗者后,才会在论述中以宗教性意义回溯组织自传情节以聚焦宗教意涵、突显上帝旨意的结果。促使改宗的主要因素不在功利考虑(小孩照养、财物援助、社会归属感等实用的非宗教因素),而是如前所述,因实践世界的生涯中断使社会网络得以动员。*同上书,第224,228页。
因此,黄克先认为,宗教虽如一般所言提供人生终极问题的答案,但更关键的功能在它先教导信徒如何提问,说宗教抚慰追寻意义者的心灵,忽略了其作为一个思考赋予系统的全面性。因此,将宗教比喻为一架接受原料、转化成粉、产出产品的机器,远较一本提供种种问题解答的意识形态百科,要恰当许多。研究宗教不宜满足于“宗教是供给面、信徒是需求面”的静态单向分析,宜注意信徒如何在宗教场域习得惯习、如何与宗教产生动态协商关系。*同上书,第224页。
因于改宗论述与改动力的讨论,黄克先主张对以主观意义理解宗教的取径——如前文所述贝格尔以宗教为人类尝试建立神圣宇宙的努力——加以反省。认为对现象的理解绝不能停留在个人心理或主观层次,意义的理解必定是在关系性的社会情境中以及动态的社会过程里,而不仅仅是抽象、独立、既定、静态的文本。应将文化视为可观察的行为,而非主观意义的生成系统。*黄克先:《原乡、居地与天家》,第228页。
由以上论析可知,要以固有西方宗教概念、理论来理解、分析乃至评估中国台湾地区的宗教现代性发展,实有其限制与不恰处。而宜在中华现代性的框架中,重行就其位于整个中华文化系统的脉络中所呈现之宗教表现,来加以检视,进而建立概念理论,当更可能有相应的理解。以之与西方的概念理论进行对话,则更能彼此丰富、成全。
结 论
宗教而言现代性,源于其与所置身社会互动之外部需求,而今日全球社会均迈向多元现代性发展。
现代性源于合理性,合理性化促成社会部门分工,宗教也就必须开始面对世俗化。由于社会的现代性发展是走向多元,而世俗化仅为其中一部,社会中同时亦可见到高度活跃的宗教共同体,于是有后世俗社会的模式概念。
后世俗社会之多元性,使宗教必须面对与其他宗教、科技以及宪政国家互动之需求,于是必须谈面对分歧的宽容、谈多元并存的制度架构、谈世俗理性、谈宗教公民与社会公民。
多元现代性,落实到中国社会就是中华现代性。
要发展中华现代性,首先必须自我了解,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与西方互动,既学习西方的知识、引进西方的学说,又回顾、反思既有的知识、学说,从而结合引入的知识、学说发展出能忠实反应中国社会、能对中国社会有如实了解的概念、学说,并能对西方有所回馈。也就是在普遍与特殊间寻得一适于中国社会的平衡,从而促成全球社会更适当、合理的多元现代性发展。
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宗教形式为分散性,因此中国社会早已是一后世俗社会。宗教之间如何共处、互动,尤其是相互宽容、对话,固然必须关心,也必须努力促成宗教与科技、宪政体制的良好互动。真正关键的问题,却在如何在中国社会中发展出科学、技术与适合中国的宪政国家体制,有此基础,再谈宗教与它们的互动,当更能切合我们今日追求中华现代性发展之需要。
至于哈贝马斯为了使后世俗社会有效发展,将基督宗教的超越性转化为内在超越性所可能激起的反应与问题,在中国却因儒家本有着内在超越的性质,而无形化解。
当然,以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概念为今日社会伦理、道德建构价值基础的思考,也是我们面对因现代性发展而陷入之困境,所必须努力尝试的一项可能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