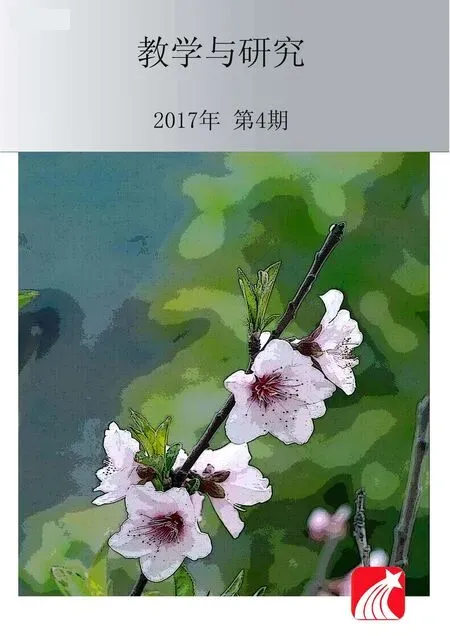数码记忆的政治经济学:被脱与境化遮蔽起来的延异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
张一兵
数码记忆的政治经济学:被脱与境化遮蔽起来的延异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
张一兵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脱与境化;非领土化;远距在场;机器意向
在斯蒂格勒看来,今天已经覆盖全球的电子信息网络已经解构了人们传统生存的领土化概念,模拟-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所生成的先天综合构架,造成了存在本身的脱与境化和光速急迫的突现特征,这种对此在在世的非现实重构,远程登陆的在场性同时消解了空间意义上的领土和现实关系中的人的在场状态。今天,资本正是利用这种全新的先天综合构架布展其获利的阳谋。
德里达的弟子斯蒂格勒*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早年曾因持械行劫而入狱,后来在狱中自学哲学,并得到德里达的赏识。1992年在德里达指导下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技术和时间》)。于2006年开始担任法国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主要代表作:《技术和时间》(三卷,1994-2001);《象征的贫困》(二卷,2004-2005);《怀疑和失信》(三卷,2004-2006);《构成欧洲》(二卷,2005);《新政治经济学批判》(2009)等。2015年,斯蒂格勒首次来到南京大学,我与他就马克思的工艺学理论和当代技术批判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形成了一些可合作研究的方向。2016年,他再一次来到南京大学,开设《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从人类世纪说的角度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课程,并与我们共同举行了相关主题的学术工作坊。本文的写作得到他直接的帮助。是当代法国最重要的左翼思想家,他的《技术与时间》的中译本陆续在中国出版*[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1卷,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卷,赵和平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此书是他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这本书的第二卷中,斯蒂格勒明确指出,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存在方式和基本质性,模拟-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所生成的先天综合构架,造成了存在本身的脱与境化和光速急迫的突现特征,这种对此在在世的非现实重构,远程登陆的在场性同时消解了空间意义上的领土和现实关系中的人的在场状态。这是一种全新的消除延迟事后性的电子记忆的政治经济学,在所谓在线的真实时间建构中,存在的延异本质被遮蔽起来。也是在这个构境层面,弗洛伊德、拉康、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同时被重写。
一、脱与境化下的非领土化与领土治理
斯蒂格勒认为,今天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网络信息技术改变了整个社会生活,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则是存在本身的脱与境化(décontextualisation)。当远程登陆的数字化比特成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时,“谁”(人)与“什么”(技术)的关系再一次纷繁复杂起来。这里的“脱与境化”是非领土化的改写,因为面对的构境层面不同,所以强调的构序侧重也相异。不过,此处的décontextualisation不能译成“去语境化”,因为这不是在讨论文本结构中的上下文,而是存在论中的现实关涉性与境。所以,“脱与境化”可能更贴近斯蒂格勒的思考原境。斯蒂格勒说:“如今,‘谁’与‘什么’的关系问题以脱与境化为特征。脱与境化导致了持存有限性的全新工业综合,它在空间上的实效体现为非领土化(déterritorialisation),即把“谁”的种族决定性连根拔起(arrachant);它在时间上的实效则是实时(temps réel),文字上和历史上‘延迟的时间’消失了,认知的价值同时也消失了。”[1](P163)
今天在我们身边就可以看到的以智能手机和电脑终端为落地入口的网络信息技术,让“低头看”和“电子界面”式的生活成为一种浮在空中的虚拟存在,这种虚拟存在造成的最大质变就是脱与境化,使人的存在从具体发生的一个民族文化和国家的现实与境中超拔出来,以形成没有依存与境的全新实在。这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因为,丧失了具体文化与境的人会在网络存在中坠入资本制造的数字化共同体,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网购中的跺手点击、网游中的无尽装备、网络视频直播中的贡品,已经成为资本盘剥无根存在者的无底深渊。如果仍然挪用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构架,现在的先天综合构架是由数字化资本主义的记忆工业造就的,所以斯蒂格勒将其指认为“新的工业综合”。因为网络传播的是由模拟-数字化综合过的记忆,“网络技术的范型或许等同于记忆综合之编程形式的范型”。[1](P164)这是一个双重座架:一是这种全新的模拟-数字化的第三持存(rétentions tertiaires)*这是斯蒂格勒原创的概念,他从胡塞尔的意识时间现象学中的第一记忆/持存(当下体验)和第二记忆/持存出发,指认了外部物质载体中的第三持存。记忆,以数字化操作软件为编程生产工具、编程员为劳动者,创造出各类无限的影视产品、多媒体产品和游戏产品;二是再加以光速发生的网络技术的布展,制造出一种全新的先天综合构架,它让我们自动看到、听到和买到的新世界。今天,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种全新的先天综合构架布展其获利的阳谋。
斯蒂格勒认为,这种虚拟记忆综合构架使得原来在一定的领土与境上发生的在场事件得以重构:一是它使得存在的空间表现为非领土化。也就是当智能手机持有者和上网者远程登陆同一个终端界面(如“脸书”或微信)时,登陆者在哪一个大洲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什么地方从“淘宝”、“京东”上购物,具体地点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这种非领土化的网络虚拟存在却将每一个“谁”的种族性被连根拔起,由此,“谁”失去了与生存真实与境的直接关联。这里的领土概念是晚期福柯生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而“连根拔起”是海德格尔的用语,然而,如果在海德格尔那里,这只是一个隐喻的话,而在斯蒂格勒这里则已经成为残酷的资本主义新现实。二是虚拟记忆综合构架也使得由数字化媒体建构起来的直播实时成为时间的存在方式。现在,在每一个具体时区发生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你可以不认识同一幢公寓中的人,也可以不知道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可是你却会认识和知道每天在电视和手机“朋友圈”里露面的人和事情,人们更习惯于在直播中看到一个事物和现象的当下存在,这种电子当下根本消除了由文字记载形成的事后性延迟。这样,人们在传统认知方式中采用的历史有效价值也就不再具有意义。一句话,网络信息技术的先天综合遮蔽了存在上的延异。斯蒂格勒这里的深刻性在于,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来说,这可能都会是一件极为重要的重新构境事件。因为,当此在去在世的方式变成与存在者没有直接关联的数字化存在时,上手性关涉将粉碎于虚拟关联,而环顾世界的发生已经是由网络信息的编程链接起来的,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畸变,进而使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遗忘从根本上失去踪迹,这将是存在遗忘的二次方;而电子化虚拟存在已经不再需要德里达式的故意涂抹,它本身就是瞬间出现和消失的,那么,德里达所指认的存在之延异*延异(diffêrance)为德里达自造的词,由法文“差异”(diffêrence)改变而来,德里达在此模仿海德格尔对Sein(存在)的改造——Seyn(存有),将diffêrence中的后一个e改成a,以构成一个新词diffêrance,以证伪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中假设的不变意义的在场性,一切意义都是延迟到场和差异性再现的,即延异。本质上则不再具有戏剧性的深刻性。这真的需要我们在哲学上认真思考。
这里,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即脱与境化下的非领土化和领土整治。
首先,信息网络技术所造成的非领土化。在斯蒂格勒看来,今天已经覆盖全球的电子信息网络已经解构了人们传统生存的领土化概念,而远距通信成为新的表征存在空间的概念。
一般来说,不论其“物质”如何,网络都是在远距离连接、同步,既向远方敞开又把远方拉近:通道、插口和连接使领土结构自身抽象化,领土的单一统一性因而受到影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用途。[1](P163-164)
原来,我们所有人的现实生活都依存于一定的具体环境中,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境之中的此在之上手世界。可是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从物质实在层面上看,今天你的确仍然在一个具体的客观现实生活条件中生存,吃喝穿住于特定民族、国家、文化地区之中;不同的是,你的具体生存的主导性因素已经是由“通道、插口和连接”的网络建构起来的远程登陆平台决定的,即你如何吃喝穿住,从哪里获得需要的东西,都决定于远程登陆的网络虚拟存在,这使人的具体生存与境条件(“领土”)丧失了在虚拟存在中的首要性。今天的存在本身发生了奇怪的翻转,似乎“没有网络就没有领土,始终存在的只有网络和网络结构,领土的统一性纯属虚构”。[1](P163-164)这并不是说现实空间不存在了,而是现实的空间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网络空间成为人们每时每刻挂在其中的持存,当我们的电脑和智能手机没有了网络连线倒会让人丧魂落魄。新的哲学判断是,“只有在自身之外,存在才具有‘社会性’。这里说的自身之外具有基础首要的含义,它意味着领土和分享领土的共同体在网络化的同时也改变了其先前的用途,只有在“非现实”时才能完成。领土在网络化,地球上只会有网络-未来”*参见[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2卷,第164页,赵和平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中译文有改动。Bernard stiegler,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2:La désorientation.Éditions Galilée,1996,Paris,p.168.。
“在自身之外”这一观点是拉康哲学的支撑点,他最早发现,人的自我-主体存在是由自身之外的他性来反向建构的*参见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在网络时代,海德格尔的此在去存在只有在非现实的虚拟空间才能实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也只有在网络关系中获得社会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变成了网络关系的总和,人的生活共同体现在是由远程登陆实现的虚拟网络共同体。由此,整个地球的未来是属于网络存在的。显而易见,斯蒂格勒是在反讽的构境中提出上述断言的。
其次,资产阶级在网络条件下的数字化工业所进行的非领土化中的领土治理。在斯蒂格勒看来,传统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的基本特征是领土治理(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即从自然环境转变为人工物质环境,一部资本主义工业的进步史就是世界的非自然化的治理过程。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当资产阶级将控制和支配自然的工具理性转过来管理社会的时候,启蒙的解放就翻转为对人的奴役,“管理世界”也是资产阶级对社会存在的科学治理。“我们都知道,治理问题是福柯晚期生命政治学中的关键性概念(不过福柯多用gouvernement——治理和police——治安),这种区别于传统专制社会强制的治理是福柯关于资产阶级新型权力理论中一个关键性的范畴。概言之,所谓治理,就是资产阶级所发明的以毛细血管和神经突触方式布展的新型积极权力”*参见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政治的话语构境》,第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然而,斯蒂格勒要我们注意的新情况为:当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起来之后,数字化生存使得资产阶级原来的领土治理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今天数字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数字化、网络化的先天“综合以实时运作,支配整体发展,且被影响所有当地时间性的电讯网络传播到各处。于是,全球性问题成了非领土治理(l'aménagement de la déterritorialisation)中的领土治理”*参见[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2卷,第164页,赵和平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中译文有改动。。非领土治理是通过网络技术实现的全球治理,我们只要想一下,微软和苹果公司与资本同谋后对全世界的超越一切主要国家的渗透和隐性支配,就容易理解了。
我这里想补充一点想法:斯蒂格勒此处的讨论主要是激进的批判语境,但应该首先看到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作用。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构境中去,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不再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简单地否定资产阶级的雇佣关系,而是首先看到商品-市场对人的社会存在的解放作用,即原来依存于土地农耕经济的宗法时空结构被商品流通彻底打破,人的生存和观念空间第一次获得了广阔的天地。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作用与资产阶级将这种生产力发展畸变为资本的力量是有所区分的。斯蒂格勒此处的问题就在这里,网络信息技术本身并不是恶魔,它的出现首先将商品-经济已经打开的生存时空进一步拓展了,然后,才是网络信息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问题。这样的分析会更加科学一些。不过,后来斯蒂格勒践行的数字化共产主义是十分可贵的努力。
二、远距在场中此在的非实现化
斯蒂格勒让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每天通过网络远程登陆智能手机和电脑界面的时候,存在论构境中的此在发生了什么?可以说,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不同时区中的主体在异地空间中建构的虚拟现实中的远程在场(téléprésence)。斯蒂格勒认为,这会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présent non-présent)”,并且,这种远程在场将成为存在论新的基始性(premier)的在场。这又过于形而上学了。这里,我来概要说明斯蒂格勒这一并没有充分展开的重要观点。
首先,一切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实现的在线操持都是真实主体不在关涉现场的虚拟在场。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比如当我们从中国和世界的各地登陆微信(或“脸书”)平台的时候,我们上传相片、音乐或者转发他人的评论,所有朋友圈里的微信使用者看起来都相聚在一个共同在场状态中,但其实却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场所中面对面的会聚,而是我们在通过远程登陆完成的虚拟共在。因为,我们在智能手机和电脑终端中的“同时同地”的在场,在空间维度中是在全球各地不同地点的非领土化和脱与境化中发生的,而在时间维度上,也是排除了真实时间(“北京时间”、“格林威治时间”和“美国东部时间”等)的电子实时。转换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构境,在线此在去在世时遭遇的已经不是真实关涉的上手性及物,而是网络上手,此在与其他此在的共在也成了网络共在。世界,则披上了网络信息的虚拟环顾性。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基础在这里会被彻底改写。
其次,虚拟在场中主体的电子面具式的伪装和本真在场。一方面,我们都知道网络生存的一个原则是匿名性,在线登陆的真实主体通常会采用假名和多重马甲,性别和年龄也会是虚拟的。由此,远程登陆中的主体在真实性上首先会是一个伪主体。这是拉康伪主体论的一个漫画式的网络版。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沉默寡言的个体,而在网络生存中却会生龙活虎地表现自己。这也就是说,虚拟伪主体的网络在场恰恰又能使主体在现实超我高压下隐匿起来的本我之真彻底解放出来。斯蒂格勒对此提出的思考是,“如果我的身体的属性是其不可撤换性(inamovibilité),且只有在此意义上它才是我的,那就成了自我格(mienneté)的问题。真实身体的不在场又给“自我格”、自我性(ipséité)和特有语言(idiome)留下了什么可能性呢?或者说“自我格”、自我性和特有语言的可能性不正是远程在场和虚拟现实的可能性中并与之有绝对关联吗?”[1](P174)
这是说,如果真实主体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正是在与他人的现实交往中,他的自我人格、自我属性和只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特性使主体性实现出来,而在远程在场和虚拟现实中,这种主体性当然会发生根本性的畸变。在后面这一构境点上,弗洛伊德的自我结构论在网络存在论中则会被大大改写了,本我在匿名性中直接在场,超我却成了被捉弄和反讽的对象,而自我则成了虚假的画皮。进一步看,拉康的象征大他者无意识认同关系中的伪主体论也有可能在网络生存更深一个构境层中被改写。在拉康那里,在镜像阶段,小他者的镜像占据了个人主体原初的空位,自我已经是一个镜像之无。进入语言教化的大他者象征域之后,作为空无的自我进一步以存在不在场的能指关系作为主体建构的通道,当每一种能指关系通过教化围在主体身上时,其实质都是用缺失补在缺失之上。拉康仿佛正处在那个看到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天真孩童的处境之上,当然,他此刻并不满足于不知所以然地高声道出真相——“他们没有穿衣服”。他更进一步发现,在用象征性能指链“衣服”缠绕起来的人类主体内部,竟空空如也。拉康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具可笑的空心木乃伊,只不过我们无法自知罢了。现在新的问题是,拉康的双重他性认同关系都被网络信息构架重构了。在数字化生存中,自我认同的小他者镜像恰恰是由虚拟世界中的游戏和动画故事建构起来的,而象征域就是数字化的符码大他者。这是一个更加令人恐怖的主体空心化过程。
再次,虚拟在场中主体潜能和欲望的虚假实现。正因为网络生存建构了一个脱离了真实领土和客观时间的不在场的虚拟世界,所以,真实主体由于披上了伪装,这就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做到的事情得到实现的可能,人们无法在真实生活中满足的欲望就可能在网络游戏和“直播”中制造的财富占有、战争杀戮和色情欲望的“闯关”中得到虚假满足。对此,斯蒂格勒分析道,在网络交往和电子游戏中,“虚拟现实的各种义肢都是由‘显像银幕眼镜(lunette écran de visualisation )’和‘数据手套(gant de données)’组成的,眼镜中呈现的虚拟空间要么根本不存在,而只是从其整体物理特征上模拟出来;要么存在于别处,但在眼镜与手套使用者的真实所在地被虚拟复制(reproduit virtuellement)出来”。[1](P173-174)
其实,所有网络“直播”和电子游戏的参与者都知道这种虚拟存在的本质,但他们就是想获得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欲望对象,实现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冲动。这可能是大多数沉浸于“自我欺骗”网络游戏的孩子和坠入“直播”不能自拔的成人内心中的秘密。在这一构境点中,拉康的“我们总是欲望着他者的欲望”的观点,干脆被直接对象化了,这一次,他者直接穿上了电子装备,帮着“直播”观者和游戏者梦想成真。当然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做法。令人震撼的是,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6年12月20日报道:专家预言,2050年机器人与人类的婚姻将成为现实,“由于人工智能的进步,人与机器人做爱会比与人做爱更有愉悦感”*参见《机器人与人类结婚并不遥远》,《参考消息》,2016年12月25日,第7版。。
令斯蒂格勒焦虑的事情是,如果这种远程在场中的虚拟性成为网络存在论的核心,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会发生什么?他认为,远程登陆的存在论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海德格尔的已经在此问题”。现在的存在论分析必须从后种系生成的角度重构,虚拟存在使得此在在场、世界和共在的意义从本质上是成为网络信息技术的产品,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新的理解和认识。因为,不能真实地看清这一重要的存在论改变,我们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会无的放矢。
三、虚拟存在论差异与机器意向性
斯蒂格勒有一种做法,即每当他提出一种新的观点时,都会吁请大师到场为他作证。于是,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和胡塞尔那种被拉长或变形的身影。
斯蒂格勒认为,要理解上面我们已经提及的远程在场所导致的存在论重构的意义,首先还是要回到海德格尔关于技术问题的追问上来。在海德格尔的《传统语言与技术语言》中,他已经开始关注光速运转的现代技术与知识关系的深刻改变。当“光速时间的技术信息这一范例可能像控制论那样成为当代技术的知识”,这将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结果产生了对认识的科学与技术的双重定义:其中,一切事物都不再是一目了然的现象了。当有认识潜力的技术与科学相结合,并因此与科学一道具有实际的认识能力时,掌控与主宰的计划便得以实现,自然界就被迫在可计算的客观性(康德语)中呈现”*参见[德]海德格尔:《传统语言与技术语言》,转引自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204页,第2卷,赵和平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
这是海德格尔对今天我们遭遇的网络信息技术世界的哲学预言。当以光速时间为基本传播方式的知识综合构架成为我们面对自然的主导性前提时,我们不再能够通过感性器官直接看到自然现象,原来存在于神性支配中的掌控和主宰世界的异在欲望第一次成为人支配自然的现实,因为,现在自然界向我们的“涌现”只能呈现于可计算的客观性中。这一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斯蒂格勒数字化先天综合构架的构境线索了,是海德格尔更早发现了光速时代现代技术中的康德命题。斯蒂格勒是将海德格尔已经发现的观点进一步推进到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的虚拟存在中,人们只能通过网络信息化的记忆工业制造的脱与境化和实时综合构架看到世界。海德格尔所指认的可计算的客观性已经畸变为一个庞大的数字化虚拟世界,现在存在论危机已经不是自然界向我们涌现,而是被彻底替代。这恰恰是数字化资本主义在存在论上的本质。
其次,网络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编程工业通过创造时间客体所导致的人的意识流构成的改变。这当然是在向胡塞尔致敬。在斯蒂格勒看来,胡塞尔曾经极其深刻地阐述了意识的意向性和原生持存中的大当下(grand maintenant)问题。“胡塞尔的卓越贡献在于提出了原生持存和纵向意向性的概念。如果说他未能考虑到工业时间客体,那是因为他在意识流的构成中排除了客观综合的记忆。我们若不借助于对工业记忆诸领域的研究,就很难对工业时代作出认真的思考”。[1](P278)
一句话,斯蒂格勒认为深刻的胡塞尔已经落伍于今天的信息时代,也就是说,胡塞尔虽然看到了存在于意识结构中的原生持存记忆和纵向意向性,但是他没有能够即时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建构的新的时间客体,这导致了胡塞尔没有真正跳出直接体验(第一记忆的当下体验和回忆中的第二记忆)中的持存范围,由此排斥了直接意识活动之外的义肢性持存记忆,这样他就无法进入到今天人之外到处被数字化网络装置中介过的“客观综合的记忆”,无法解释由数字化装置重构过的机器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 machinique)。言下之意,大师胡塞尔没有超出的这一步将由斯蒂格勒自己勇敢地跨出。
这样,斯蒂格勒信心满满地认为,第一,胡塞尔已经关注的意识中的原生持存(当下体验)与第二持存(回忆),可是,他没有看到意识之外由义肢性载体实现的第三持存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今天资本主义记忆工业化和网络信息技术建构的先天综合构架中,原来胡塞尔所强调的连续持存中的“听到”与境被彻底消解和破坏了,“记忆的工业化使脱与境化全面泛化(décontextualisation généralisée)”,而虚拟了一种数字化与境,斯蒂格勒将其指认为虚拟的“再与境化(recontextualisait)”。[1](P278)具体说,也就是胡塞尔讨论的只会发生于音乐会现场的直接看到和听到的音乐旋律响起时发生的原生持存,在现在的数字化视频和音频第三持存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一部智能手机和电脑上制造出“再与境化”。我觉得,斯蒂格勒的得意中内含着一种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逻辑悖结,即他所建构的外部客体持存与重新激活构境的关系。因为,九泉之下胡塞尔如果要反驳他真的很简单,从CD上从视频中看到听到一首音乐旋律,排除这首音乐的发生机制,对于人的感官意识来说,仍然是直接的当下!
第二,好像斯蒂格勒听到了我替胡塞尔发出的上述质问,所以他立刻说,显然,“胡塞尔的意向性与机器的意向性相去甚远,因为后者对胡塞尔来说只能是‘图像’流、数字流或无意识的文码流、记录流”。这是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的意向性,先把当下建构的存在论基础限定在主体意向中,再来排除当下建构的歧义。斯蒂格勒认为,在网络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数字化存在中,“既没有在场的生命,也没有生命的在场,亦没有呈现时间客体之大当下活的在场(présent vivant)”。[1](P216)道理很简单,因为由电子数字建构起来的当下是模拟的假物,它只是一种义肢性的虚拟存在,它的意向性和持存也是替代性的非实现。
斯蒂格勒最后的结论是,这种由网络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先天综合构架——虚拟存在,根本改变了康德的认识论先天综合判断的基础,也通过“在时性装置(dispositif d'intratemporalité)”彻底遮蔽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构境中,数字化技术将彻底“扭曲了人类认识”。[1](P216)这种改变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如果说,在工业文明和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康德已经天才地发现了相对于个体经验统觉中的先在观念构架的自动整合机制,那么,今天资本主义数字化存在中,一种全新的远程网络多媒体综合已经建构了先在于一切实际存在的虚拟技术综合,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听到世界,而让资本主义的市场空间和资本对世界的支配与控制插上了神话般的翅膀。
[1]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M].第2卷.赵和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孔 伟]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igital Memory:Delay and Differance Covered by Detached Situation——Interpretation of Stigler’sTechnologyandTime
Zhang Yib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3)
Stiegler;technologyandtime; separation and environment; non territorial; remote presence; machine intention
In the view of Stigle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network that has covered the world today has deconstruct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e territorial in which people exist.Simulation and digital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enerated by the integrated framework has resulte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ence of a detached situation and an urgency of light speed.This kind of non realistic reconstruction, the presence of the remote landing has de-constructed the spatial meaning of the territory,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presence in the re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Today capital is designing its profit-making plot by making use of this brand new synthetic framework.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号: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
张一兵,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3)。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