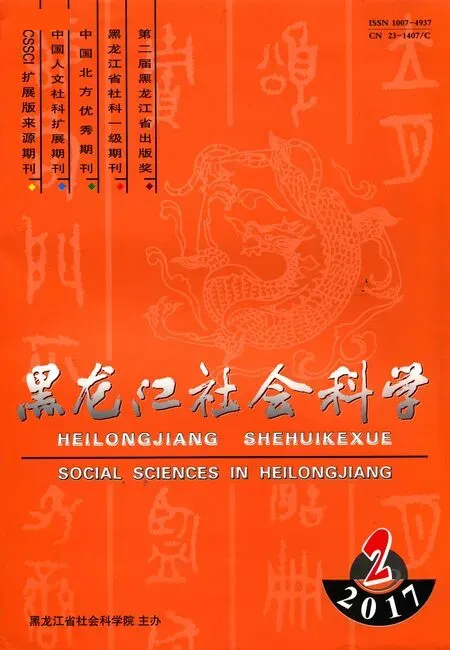蒙元诸帝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尊崇与认同
孙 红 梅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蒙元诸帝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尊崇与认同
孙 红 梅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不过,很多人认为元朝的统治民族蒙古族对“汉文化”并不重视,“汉化”最浅。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曾说:“元代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习汉文者亦少也。”[1]日本学者羽田亨也指出,元朝奉行“蒙古主义”,汉文化及汉人皆不受尊崇[2]。这里的“汉文”“汉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其实,蒙元诸帝并非粗朴不文、只讲武功不论文治,无汉文化修养的统治者,对此,国内外学者亦已多有关注[3]。不过,尚无专文系统论述关于蒙元诸帝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尊崇与认同的问题。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因撰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蒙古太宗、宪宗时期优待儒士的政策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的主要目标是对外征战,以掠夺资源、扩大领地,这一时期儒家的思想文化虽未能真正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成吉思汗也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他注意收罗人才,如征召耶律楚材为侍从“以备咨询”;耶律楚材曾言“治天下需用治天下匠”,得到成吉思汗的赞扬。
太宗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由于耶律楚材的屡次谏言,统治者开始关注儒士、儒学。耶律楚材不时向窝阔台“进说周孔之教”,并陈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上深以为然。国朝之用文臣,盖自公发之”(《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4]。太宗遂命封赠孔子后人、修建孔庙,并于燕京设国子学,编集经史以及举行“戊戌选试”——太宗四年(1232)三月,蒙古攻占金中京,“书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5];五年(1233)六月,“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十二月又“敕修孔子庙及浑天仪”[6]32-33;八年,“复修孔子庙及司天台”[6]34。关于在燕京初设国子学,史载太宗六年,“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6]2029,其学习内容即包括儒家经典。八年六月,“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6]34。同年,耶律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窝阔台闻罢即言:“果尔,可官其人。”随后,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6]3461。此次选试,符合条件的儒士单独设立户籍为“儒户”,并免徭役差发,使得儒士的地位有所改善。萧启庆先生评价说:“戊戌之试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在于举拔官吏,而在于救济流离失所及陷于奴籍的儒士,使他们以‘儒户’的身份,取得优免赋役的特权”,“元代儒户的诞生,原是为救济在兵燹中流离失所的儒士。一方面使他们与僧、道相等,取得优免赋役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为国储存人才之意,并不是有意压抑儒士。”[7]戊戌科举取士中选的儒士不仅在窝阔台汗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还成为忽必烈统治时期的杰出名臣。尽管戊戌之选后科举取士中断,但窝阔台汗时期所实行的政策和措施,使蒙古统治者越来越认识到儒士的重要性,为此后施行优待儒士的政策奠定了基础[8]。
宪宗蒙哥汗即位后,原西夏人高智耀曾向其力陈以儒治国之道:“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蒙哥汗问:“儒家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宪宗道:“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于是“诏复海内儒士徭役,无有所与”[6]3072-3073。可见,蒙哥此前并不太清楚“儒学”的含义及作用,经过高智耀的一番阐释才使其明白儒学之重要,于是蒙哥汗立即采取了免除儒士徭役的政策,以表明其优待儒士、崇礼儒学的态度。
二、元世祖对儒学的认同与以儒治国思想的确立
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蒙古帝王,“爱养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元]郝经《复与宋国丞相论本国兵乱书》)[9]。《元史》则盛赞元世祖说:“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6]377忽必烈时期,对儒学的尊崇和认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崇儒重道,重用儒士。忽必烈在潜邸时即“思大有为于天下”,结交中原文士,招揽重用儒士,关注儒家思想文化。如乃马真皇后称制元年(1242),时为亲王的忽必烈闻赵璧名而召见之,“呼秀才而不名”,赵璧遂为忽必烈讲解儒学,忽必烈对其“宠遇无以为比”[6]3747。两年后,忽必烈闻原金朝状元王鄂贤能,遂“遣使征至,问以治道”,王鄂于是进讲以儒家经典及齐家治国之道[6]3250。定宗贵由汗三年(1248),忽必烈曾问汉人张德辉曰:“孔子庙食之礼何如?”对曰:“孔子为万代王者师,有国者尊之,则严其庙貌,修其时祀。其崇与否,于圣人无所损益,但以此见时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忽必烈曰:“今而后,此礼勿废。”[6]3824同年,张德辉再次觐见忽必烈时,“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6]3825,又言“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忽必烈亦从之。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忽必烈以皇弟之亲,总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此后他更加重视崇儒揽士,广罗人才,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了以汉人为主的幕僚集团:“上在潜邸,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10];当时一些著名的汉人儒士都曾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6]57;郝经亦云,忽必烈“聘起儒生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元]郝经《复与宋国丞相论本国兵乱书》)[9];“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元文类》卷四一《礼典总序·进讲》)[4]。
忽必烈即位后,继续推行崇儒之道。至元十三年(1276),元灭南宋、统有全国后,元世祖便多次派人到江南求贤,“常以名取士,尽得故国贤能而用之,尤重进士”[11];“起文雅通练之士知名一时者,以慰民望”(《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太平文学黄敬则之官序》)[12]。至元二十四年,程钜夫“奉诏求贤于江南”,“帝素闻赵孟藡、叶李名,钜夫临当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后程钜夫又荐举赵孟兆页、余恁、万一鹗、曾晞颜、孔洙等二十余人,“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6]4016。事实证明,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抱负的实现,确实得益于聚集在其周围可“问以治道”的众多儒士。
其次,以儒治国成为忽必烈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礼”与“仁”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为政以德”是儒家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基本主张。忽必烈在潜邸时,即曾召姚枢、刘秉忠、许衡等大儒问以治国之道。姚枢“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录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远佞,次及救时之弊”[6]3711-3712。刘秉忠则“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基调向忽必烈陈说治国之道。许衡、郝经等人更直接向忽必烈建言“行汉法”“行中国之道”,确立以儒治国的统治方略。许衡称:“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熟,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6]3719郝经则认为“今日能用士,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9],并具体建言“下明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13]。郝经还指出:“天无必与,唯善是与;民无必从,唯德是从”,“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辨微论·时务》)[9]
故而,忽必烈即位后,即将以儒治国的思想理念切实付诸在统治政策和治国方略上。史载:“世祖皇帝建元中统以来,始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官制》)[4]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向刘秉忠“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6]3693。同年,设立十路宣抚司,李德辉、徐世隆、宋子贞、张德辉、姚枢、张文谦等汉儒以及深习儒家文化的畏兀儿人廉希宪等被任命为各路宣抚使及副使。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向汉儒徐世隆询问“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取《书》所载帝王事以对”,世祖大喜过望曰:“汝为朕直解进读,我将听之”;书成之后,“命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6]3769。当时,在朝中任职者多是耆德宿儒,中书右丞相蒙古人线真遂“与诸儒臣论定朝制”[6]3173。
最后,注重蒙古子弟儒家文化的学习,广置学校推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忽必烈“深知儒术之大”(《道园学古录》卷五《送李扩序》)[12],在潜邸时便命蒙古贵族子弟从学于赵璧、王鄂等人:“命蒙古生十人从赵壁受儒书”[6]3747,命阔阔等近侍子弟从学于王鄂[6]3250。忽必烈之子真金早年曾先后从学于姚枢、许衡、李德辉、赵壁等汉人儒士,真金本人对儒家文化也是热爱至深:“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辄讲论经典,若《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王恂、许衡所述辽金帝王行事要略,下至武经等书”,并面谕汉人何玮、徐琰:“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6]2889-2890真金曾设学堂于春坊,以赞善王恂“养教宫府侍卫之子孙”,王恂卒后,又命处士刘因和耶律有尚教之。中统二年,在翰林承旨学士王鄂的建议下,忽必烈特下诏曰:“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导之。凡诸生进修者,仍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要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14]
元世祖至元七年,藩府文臣张文谦和窦默请立国子学,遂任命大儒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贵胄子弟教育之”[6]3697;许衡“专以成均之教责成焉,凡勋臣贵戚之子弟及海内名士咸从受业”[15]。至元二十四年,元朝正式设立国子监“而定其制”,“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6]2029。国子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6]2029, “儒风为之丕振”[6]4064。同时,还陆续兴立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至元八年,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选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中子弟俊秀者入学,用以蒙古语翻译的《通鉴节要》等书为教材[6]2027。蒙古国子学生源还有诸路府官员子弟及民间子弟,“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此外,地方郡县学也逐步设立起来。史载:“世祖皇帝既立国子学以教国人及公卿大夫之子,取其贤能俊秀而用之,又推其法于天下,而郡县皆立学。”(《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儒学教官》)[4]
三、元朝中后期诸帝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崇礼与实践
元世祖之后的蒙古诸帝对儒家思想文化也是崇礼有加,仍以儒学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推进了儒学的发展。对此,元人欧阳玄赞曰:“成宗皇帝克绳祖武,锐意文治,诏曰夫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既而作新国学,增广学宫数百区,胄监教育之法始备。武宗皇帝煨兴制作,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祠以大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圣之规,尊五经,黜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于斯为盛。英宗皇帝,铺张钜丽,廓开弥文。明宗皇帝,凝情经史,爱礼儒士。文宗皇帝缉熙圣学,加号宣圣皇考为启圣王,皇妞为启圣王夫人,改衍圣三品印章……俾济宁路以修曲阜庙庭……今上皇帝入纂丕图,儒学之诏方颁,阙里之后鼎盛……于是内圣外王之道,君治师教之谊大备于今时,猗钦盛哉!”(《圭斋集》卷九《曲阜重修宣圣庙碑》)[16]元朝中后期的蒙古诸帝在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崇礼与实践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重视对孔庙的修缮和祭祀。史载,宣圣庙“太祖始置于燕京”[6]1892;如前所述,太宗时期就有敕修孔庙之举,宪宗、世祖时期也多次诏令修缮孔庙、宣圣庙。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诏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至元十年(1273),宫廷中举行大规模祭祀宣圣的活动;同年三月,“中书省命春秋释奠,执事官各衣其公服,陪位诸儒襕带唐巾行礼”[6]1892。成宗以后,修建、祭祀等活动更为频繁。“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元文类》卷一九《曲阜孔子庙碑》)[4],本此,成宗始命建宣圣庙于京师,大德十年(1306)建成。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诏加号于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崇之高超越了唐宋两代。仁宗“最能亲儒重道”[1],并认为“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6]549。仁宗即位不久,即命国子祭酒刘赓诣曲阜,以太牢祠孔子。皇庆二年(1313)以许衡从祀,又以宋代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从祀。罗贤佑指出,仁宗以“宋九儒从祀宣圣庙庭”之举,“对于确立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深具影响”[3]。延祐三年(1316),又下诏命设宣圣春秋释奠,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以汉儒董仲舒从祀,封爵给孟子、颜子、曾子、子思等人物,并对孔子、颜子的父母给予封谥[6]1893。元顺帝时期,对上都、曲阜孔庙的祭祀和修葺更显频繁:至元元年(1335),“遣使者诣曲阜孔子庙致祭”[6]827;次年,“敕赐上都孔子庙碑,载累朝尊崇之意”[6]835;至元四年,“诏修曲阜孔子庙”[6]843;至正八年(1348)“遣使祭曲阜孔子庙”[6]882;至正十六年,“命集贤直学士杨俊民致祭曲阜孔子庙,仍葺其庙宇”[6]930。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更加注重以不同时期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配享、从祀宣圣庙并加以爵封,其意在“以明斯道之所自传矣”(《圭斋集》卷九《元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赠正学垂宪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正许先生神道碑》)[16]。
第二,祭祀与教学相结合的庙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宋亡元兴,修道设教,天下学者复知尊信朱氏之学。学校修旧起废,至时无不轮奂一新”([元]刘岳申《南安路重修庙学记》)[9]。元代继承了两宋以来庙学合一的制度,庙学“即郡县学,它是以文庙(先圣庙、宣圣庙、孔子庙)为精神中枢,并依附于文庙而设置的儒学”[17]。时人则称:“自国都郡县皆建学,学必有庙,以祠先圣先师而学所以学其学也。”(《道园学古录》卷三六《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12]。元世祖以前庙学只是零星修建,世祖时期庙学在各地恢复和修建起来,成宗朝以后庙学则得以进一步发展。成宗即位,“诏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赡学土地及贡士庄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庙宇。自是天下郡邑庙学,无不完葺,释奠悉如旧仪。”[6]1908成宗元贞元年(1295),阎复上疏言:“京师宜首建宣圣庙学,定用释奠雅乐”,从之。大德二年,“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哈剌哈孙“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又集群议建南郊,为一代定制”[6]3293。大德四年,京师孔庙成,御史中丞何玮上言:“唐、虞、三代,国都、闾巷莫不有学,今孔庙既成,宜建国学于其侧”[6]3545,得到成宗的赞同。史载唐代“贞元间,天下郡国皆立庙以祠之。往往庙学混一,不能区异”[18],祭祀与教学相结合的制度在元代这一时期可谓得以完善。此后历朝均有数量可观的庙学修建,即使在顺帝后期,战乱频仍,庙学的修建也并未停止[19]。时人黄溍言:“盖古者惟有学而无庙,后世或有庙而无学,庙学之制莫备于今,诏书屡下,风厉作成,视昔有加,可谓盛焉。”[20]
元制:“每月朔望,郡县长吏率其参佐僚属,诣孔子庙拜谒礼毕,从学官升堂讲说”[6]2636,并规定对于诸郡县宣圣庙及书院,如“凡官员使臣军马,辄敢馆谷于内,有司辄敢听讼宴饮于内,工官辄敢营造于内,并行禁之”[6]2636。尽管元代的庙学存在着“重祭祀,轻教学”[21],“作为祭祀场所的功能远大于教化功能”[22]的情况,但正如时人所言:“夫庙无与于学也,然而道统之传在是矣,学于此者诵其诗,读其书,习礼明乐于其间,诚其道也。”(《道园学古录》卷八《新昌州重修儒学记》)[12]
第三,设科取士,推进儒学的传播和发展。蒙元科举之制“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于延祐”[23]二集,199。如前所述,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就有所谓“戊戌之选”,实行开科取士,但此后废止。元世祖至元初年,再议科举之事,朝官在议立科举程式时,提出“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庶几勋旧之家,人材辈出,以备超擢”[6]2017。史载世祖时期科举之制“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6]2018。武宗至大四年,又规定诸职官子孙承荫,须试一经一史,能通大义者免儤使,不通者发还习学,其中蒙古、色目人可自愿参加,如通过可进一阶[6]2061。元仁宗皇庆二年,重议科举,并决意开科取士:“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举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6]2018,中选者并将由皇帝亲试。规定科考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经义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这对于确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史载不同民族人士纷纷应试:“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23]初集,1729;时人马祖常亦称,“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送李公敏之官序》)[9]科举之施行,可谓对蒙古民族文化取向的改变起到了极大作用[24]。仁宗重开科举,体现了其“诚欲人人被服儒行,为天下国家用”(《元文类》卷一九《国子学先圣庙碑》)[4]的思想,仁宗曾感慨道:“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6]558
第四,翻译刊布儒家典籍,设奎章阁“讨论治道”。大德十一年,元武宗初即位,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呈以蒙古文所译《孝经》,武宗就此下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6]486元仁宗即位前,便“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人进《大学衍义》,仁宗命节译之,并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6]536。即位后,则将《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典籍译成蒙古文,颁赐臣下研读;延祐六年,又从太保曲出所言,以“唐陆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书,有益后学,请令江西行省锓梓,以广其传”[6]587。英宗为太子时,“于世祖所赐裕皇诸经及……受圣上所赐《尚书政要》等书,或三日或五日,讲说其义……知言行有法,鉴于先王成宪也”[25]。而史载文宗“稽古右文”,“文治灿然可观”[26]。天历二年(1329),文宗设奎章阁,“置学士员讨论治道”,并“日御奎章阁,听天下之政,盖所谓未明求衣,日旰忘食者也”(马祖常《恭题御书雪月二字》)[9]。元顺帝时改奎章阁为宣文阁,史称顺帝“崇儒重道,尊礼旧臣,万几之余,留心翰墨”[27],“诏选儒臣欧阳元、李好文、黄绪、许有壬等四人,五日一进讲,读四书五经,写大字,操琴弹古调,常御宣文阁,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焉”[28]。 奎章阁(宣文阁)不仅是皇帝与诸儒讲经论道之所,而且作为专门的文化机构,诸多珍贵书画、典籍赖其得以收藏和保存。元人周伯琦有《右咏宣文阁》诗云:“延阁图书取次陈,讲帷日月集儒臣。”萧启庆曾在《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一文中引用德国学者傅海波的观点说:“元朝诸帝之中虽然并无成就卓著的诗人与艺术家,但是假若元朝不速亡,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产生康熙、乾隆那样精通汉文化的帝王。”[3]
综上可见,早在太宗时期,蒙古统治者已开始尝试了解和接受儒学,元世祖时期确立了以儒治国的思想理念,并为此后的诸位皇帝所继承和发展。蒙元诸帝的汉化程度虽不及北魏,但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尊崇和认同则是一以贯之的。“元王朝尊崇程朱理学,也就是尊崇儒学传统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御众地位,实质上又是维护封建秩序。”[29]姜海军认为,蒙元政权尊崇程朱理学,不仅增进了汉儒对蒙元政权的政治认同感,且“使程朱理学超越了原有民族文化信仰,成为不同族群的共同文化价值体系,也成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融合与元朝大一统帝国稳定的基石与纽带”[3],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清]赵翼[M].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687.
[2] [日]羽田亨.元朝の漢文明に对する態度[C]//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 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57.
[3] [日]福田喜一郎.元の文宗の風流に就いて[C]//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东洋史学会,1995;[日]吉川幸次郎.元の诸帝の文学[C]//.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5卷.东京:筑摩书房,1984;Herbert Franke.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J].Asia Major,1952,(3);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J].民族研究.1987,(5);李则芬.元代诸帝的汉学修养[C]//李则芬.宋辽金元历史论文集.台北:黎明事业文化公司,1991;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C]//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陈得芝.从元代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5);姜海军.蒙元“用夏变夷”与汉儒的文化认同[J].北京大学学报,2012,(6);任红敏.忽必烈幕府文人与元代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3).
[4] [元]苏天爵.元文类[M]//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1919.
[5] 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86.
[6] 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C]//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余大钧.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J].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3).
[9] 李修生.全元文[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1998、2004.
[10]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姚景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250.
[11] [元]虞集.道园遗稿:卷四八(熊与可墓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M]//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1919.
[13] 柯劭忞.新元史[M].余大钧,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728.
[14]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2(中堂事记下)[M]//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1919.
[15]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8(皇元故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赠河南行省右丞相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M].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
[16] [元]欧阳玄.圭斋集[M]//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1919.
[17] [日]牧野修二.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J].赵刚,译.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8,(4).
[18] [元]郑奕夫.庆元路儒学重修棂星门记[C]//章国庆.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9] 胡仁.元代庙学的发展过程[J].文史杂志,1994,(5).
[20] [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9(义乌县学明伦堂记)[M]//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1919.
[21] 申万里.元代庙学考辨[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2).
[22] 蔡春娟.元代大都路儒学教育[J].中国史研究,2015,(3).
[23] [清]顾嗣立.元诗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 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C]//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南京大学学报专辑):6,1982.
[25] [元]同恕.榘庵集:卷4(上储君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6] [明]叶盛.水东日记:卷37(记瀛国公事)[M].魏忠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27]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8(大元),上海:上海书店,1984.
[28] [元]权衡.庚申外史[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8.
[29]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8.
2016-12-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
孙红梅(1978—),女,吉林桦甸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辽金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