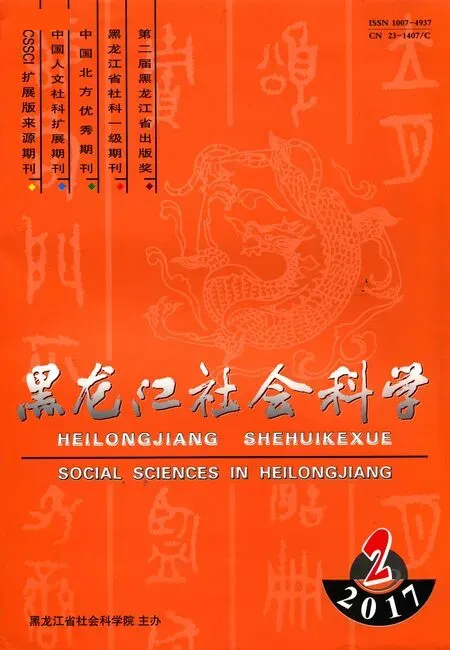“崇德”与“德治”
——清太宗“中国”认同观念管窥
李玉君,崔 健
(1.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2.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崇德”与“德治”
——清太宗“中国”认同观念管窥
李玉君1,2,崔 健2
(1.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2.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中国”一词在我国传统文化里具有多重含义。赵永春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五种:一国的中心,即“中央”“中央之城”“都城”“京师”“国中”“王畿”等;中原,引申为中原王朝,主要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华夏或汉族,引申为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是用民族作为划分“中国”的标准;在天下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的文化中心的含义;对政权的指称[1]。相对于地域、民族、政权等层面,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含义更为突出[2],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等观念[3]。由于这一观念被普遍接受,因此,即使改朝换代也未能破坏中华文明在典章文物、礼乐教化、语言风俗等方面的连续性,且改朝换代的过程又往往伴随着各民族“中国”认同观念的深化。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作为大一统政权能够享国268年,就与清代统治者的“中国”认同观念不无关系,而清太宗皇太极正是深化这一观念的关键人物。皇太极于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继承其父努尔哈赤的“恢弘大业”,并于次年改年号为“天聪”[4]25;十年后(1636)又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建立清朝,并改年号为“崇德”;在清军入关的前一年(崇德八年),皇太极去世。作为“积累者深而贻谋者远”[4]912的一位君主,清太宗的政治举措和制度建树对当时及后世均影响深远。探究其“中国”认同观念,对理解太宗朝政治运作的方式和内容、甚至清代政治史中的一些问题都至关重要。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还略显不足(如赵永春[1]及孙文良、李治亭[5]等人论著中的相关内容),因此本文拟从清太宗的“德治”实践角度来考察其“中国”认同观念,以此增进对清代统治者治国理念的了解。
一、“德治”与清太宗的“天命”观念
“德”,古义即“得”,指言行适宜,外无愧于人而内有得于心,是一种行为规范。西周初期,周公在“制礼作乐”的同时提出了“以德配天”说——《尚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便是“德治”思想的来源。“德治”学说宣称君主的道德行为是君主获得天命并进行统治的依据,因此统治者应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德治”学说本质上是商代“天命论”(即“君权神授”)的延续,具有迷信成分;同时“德治”学说也警告统治者,一旦失德,则其统治的合法性将遭到质疑,这又有积极的一面。
相映成趣的是,从清太祖到清太宗,其天命观念也经历了一个从“皇天眷佑后金”到“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转变过程[6]。皇太极“天命靡常”思想的形成,是他在后金与明朝对峙的外交、军事实践中,理解、探求天与人、天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结果,而这种实践最终促成了他的“天命”观念与中原王朝政治文化中“德治”思想的接轨。后金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正月,皇太极在致书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时说:“惟天不论国之大小,止论理之是非。……叶赫、哈达、乌喇、辉发与蒙古无故会兵侵我,尔国并未我援。幸蒙上天以我为是,师行克捷。后哈达复来侵我,尔国又不以一旅相助。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释还其人民。及释还,哈达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4]31在他向朝鲜国王提及此事时又说:“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我获哈达则胁令复还。我既还之哈达,为叶赫所侵掠,则又不出一言。明之偏私。”[4]235清太宗认为,既然大明王朝号称是承载了“天命”的“正统”(“尔既称为中国”),那么就应该以“天子”之德“恩养四夷”,处理事务时要“秉公持平”、不应“偏私”。
既然“天命靡常”,那么在清太宗看来,作为“天下”文化中心的“中国”当然也是可变的,是“有德者能居之”。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皇太极致书明朝崇祯皇帝曰:“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有未成而中废者,有既成而复败者,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者哉?”[4]632他认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可称为天子。……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天厌朕躬,更择有德之人君主是国,亦惟天是听而已。”(蒋良骐《东华录》,天聪九年五月。按:诸点校本皆未见该条,此处转引自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5]292故“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以此推之则享有天下惟有德之故,非世为君长之故也。自古邦国岂有常弱常强之理尔。”[4]371清太宗反复强调,德行才是天子的合法性依据。
清太宗为了一统“天下”,于是以“天子”之“德”要求自己。在建清称帝时,定年号为“崇德”,意思就是“崇高的才德”[7]。他曾对文馆诸臣说:“见(史籍中)史臣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称。今朕承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遂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爱乎?傥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天命靡常,宁足恃耶?”在这样的天命观念指导下,为了“克副天子之称”,皇太极“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鉴”[4]303,在个人修养、吏治管理和臣民教化上施行“德治”,体现了其“中国”认同的观念。
二、“德治”与清太宗的个人修养
《论语》云:“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可见,统治者要施行“德治”,首先要从自身做起,由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清太宗的“德治”实践,也确实是从“修身”开始的,以为天下臣民做出表率。
《孟子》云:“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皇太极自幼母亲病故,青年时即追随父亲戎马疆场,父子感情深厚。他即位后曾“因追忆太祖功德,念诸兄弟勤劳,怆然泪下。代善及诸贝勒群臣无不感泣”[4]29。天聪七年(1633)十月,皇太极谕文馆诸臣曰:“朕嗣大位,凡皇考行政用兵之大,不一一详载,后世子孙何由而知,岂朕所以尽孝道乎?”[8]43-44而“悌”则主要体现在其对兄长代善的关照上。如天聪六年,诸贝勒进茶给皇太极,他则说:“当先奉大贝勒”,代善饮后自己才饮[4]177。除了礼仪方面,在生活上,太宗对代善也关怀备至。崇德四年(1639),代善在射獐时伤了脚,皇太极亲自为他包裹伤口,心疼得潸然泪下;为照顾代善,“遂驻营其地,罢猎。还时,上令代善乘舆徐行。日行十五里或二十里。”[4]654
中原王朝的历代明君大都以节俭为美德,清太宗也崇尚节俭,反对铺张浪费。他曾告诫群臣说:“国家崇尚节俭,毋事华靡。凡鞍辔等物不许以金为饰;虽富家不少藏金,止许造盘盂匕箸。盖此等之类或至匮乏,尚可毁为他用;若以之涂饰,则零星耗折,岂能复取而用之。今后著永行禁止。至于阵获缎帛,用之亦当节俭;慎勿以获取之易,奢费无度,而忘其纺织之劳也。”[4]397皇太极也反对排场奢华,天聪十年四月,他以“仪仗止美观瞻,非于国有益,于兵有用”为由[4]369,对自己的仪仗队进行了裁减。皇太极还禁止给自己和后妃们送礼,就连过年节、生日也不例外:“元旦、万寿及中宫千秋,内外诸王贝勒等一切献物,俱著停止。”[4]679
进谏与纳谏历来为中原王朝所崇尚,如唐太宗纳谏于魏征就被传为美谈。皇太极深谙此理,指出:“忠告之言,虽逆于耳,实于治道有裨。”[4]705他多次鼓励进谏,曾要求臣下“见朕有过即当极谏,无有所讳”[4]125。他又下令都察院说:“朕或奢侈无度,误诛功臣;或畋猎逸乐,不理政事;或弃忠任奸,黜陟未当,尔其直陈无隐。”[8]56天聪八年,针对外廷对禁烟问题的议论,皇太极说:“若不当禁而禁,则彼时即当直谏。不然外廷私议设禁之非,是以臣谤君,以子谤父也。尔等思之,朕曾有因人谏诤而加谴责者乎?汝等如以进言为难,凡有所见,先启诸贝勒转奏可也。”[4]283可见皇太极对谏言的重视。他对范文程、宁完我等一批儒臣非常倚重,进谏、纳谏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清太宗虽有帝王之尊,在待人接物上却也能做到彬彬有礼,谦恭自守。天聪九年正月,几个蒙古贵族要离开盛京回科尔沁。“上欲亲送之。土谢图济农等辞曰:‘车驾亲送,臣等实切不安。’”皇太极则说:“岂今嗣大位,遂可遽忘旧礼乎?”[4]287坚持送别并饯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皇太极也反对阿谀奉承。天聪九年的一次宴席间,传来了捷报,于是一个蒙古大臣“举觞跪进”劝酒道:“主上圣明,皇天默佑……敢进一觞,虔申庆贺。”皇太极却说:“何至导以非义相劝以酒?傥朕政治有失,致民疾苦;或忿怒过当,违道而行尔,大臣即当直谏,无有顾忌。忠良之言,朕岂有不听者乎?”[4]305-306一席话说得劝酒的大臣羞惭不已。此外,皇太极也尊重传统及成法。当文馆史臣库尔缠针对“所修何书”回答“记注所行政事”时,他便根据帝王不干预史官修史的传统表示“朕不宜观”[4]110。
史家赞誉皇太极“以仁心爱万民,以仁政治宇内”[4]868,虽略嫌溢美,却也大致允当。皇太极对待百姓或士卒常有仁爱宽恕之德。他曾晓谕军中各级官员说:“勤加管束本旗人员,明白训饬,爱士卒如子弟。若能晓之以理,爱之如子弟,则旗人视尔等如父母,教训之言,铭记不忘。”[9]天聪四年十二月,大贝勒代善部下一个蒙古猛克射狍时“误中御衣”,代善等人坚持要将其射杀以正其罪。皇太极则不准,还把那个蒙古猛克保护起来。结果“诸贝勒皆怒,谓此人并未有功,不过阵获之人,获罪重大,岂宜宽宥?”皇太极解释说:“此人系误射,故赦之。所谓宥过无大也。”最后只打了其一百鞭子以示惩罚[4]107。
毋庸讳言,清太宗表现出孝悌、节俭、纳谏、谦恭、仁爱等德行,多是出于政治目的,不乏笼络人心的动机,此外他还有很多性格上的缺陷[10]。然而,考虑到他以帝王之尊还能努力“克己复礼”,也算难能可贵。如同后文将要谈到的,清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与他对“中国”的认同、对中原王朝为政经验的学习以及受到儒臣的影响有着紧密联系。
三、“德治”与清太宗的吏治管理
官员群体是君主维护其统治所要仰仗的中坚力量。《论语》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员们道德水平不高,“德治”也就无从谈起。清太宗深知“赞襄盛治,惟尔臣工是赖”[4]153,遂以前朝政治经验为鉴,在吏治管理中注重提升官员的道德修养。
清太宗大力反腐倡廉,并设置监察机构以限制官员的特权[11]。他告诫众大臣:“应洁己爱民,奉公守法,以副朕意。”[4]153他还要求都察院对大臣们进行严格监督:“诸贝勒或废职业,黩货偷安,尔其指参。六部或断事偏谬,番谳淹迟,尔其察奏。明国陋习,此衙门亦贿赂之府也,宜相防检。挟仇劾人,例当加罪。余所言是,即行;所言非,不问。”[8]56-57清太宗“禁止汉官进献岁礼”[4]30,也不准官员们向诸王或互相馈赠礼物。天聪七年(1633)十月,皇太极告诫归降的孔有德、耿仲明说:“卿等以礼物馈送诸贝勒大臣,此乃明人陋习,我国无此例也。此端一开,即成乱阶。自今以后,似此馈送,宜永行禁止。”[4]214清太宗还对狎妓、酗酒、赌博等官场不良风气进行了大力整顿[12]。
清太宗非常重视官员的儒学修养,大量提拔儒士,希望他们能对文化教育有所助益。天聪三年八月,皇太极下求贤诏曰:“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4]73九月,“考试儒生。先是,乙丑年十月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4]73。这二百生员遂从奴隶身份中被解放出来,补充到了教师队伍中。这样的考试此后又进行了数次,应该是对中原王朝科举制度的仿效。此外,清太宗还厚待、培养降附的汉儒生员。如天聪五年十月,“翟家堡降,获人百、牲畜五十、守台百总一员、生员一人。朝见毕,上擢百总为千总,赐狐裘貂帽,赐生员狐裘。”[4]138“天聪三年,太宗伐明,克遵化,选儒生俊秀者入文馆。”[8]9489他对“通汉书,习典故,为国宣力”的巴克什达海“注念不忘”,于天聪十年二月“召其三子至,赐馔及缎、布、食物,仍谕其次子陈德,勤习汉书”[4]350。
除了文臣的修养,清太宗也非常注重军中将领的品德,多次强调将帅应当爱护士卒。因为“君享康宁,臣居尊显,俱兵民是赖”,所以带兵的将帅应时刻关心“效力死战之士”[4]395。有一次,当军队还远在外地渡口的时候,将领们已经归家两天了。于是皇太极责备他们“不思效力死战之士,而先自还家,漠不相顾,于心奚忍耶?”他还讲了一个“忘人之劳者”的寓言来阐述这个道理,大臣们听后纷纷表示“愿亲自往迎”[4]395。
可见,清太宗以身作则践行“天子”之“德”的同时,又注重提高官员们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虽然其目的是让“效力死战之士”助他成就个人功业,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满族自身的发展和清朝社会的进步。
四、“德治”与清太宗的臣民教化
“德治”是与“礼治”相关联的一个政治概念。孔子主张对民众“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意即用道德礼仪之教化让百姓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历代中原王朝大都奉行这一理念。清太宗对此也非常认同,崇德元年(1636),“始创大业,即崇文重道,建孔子庙于盛京。”[13]同年八月,太宗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孔子曰:“惟至圣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4]387圣人“德配天地”,清太宗改年号为“崇德”,即意在昭告天下要实行“德治”。
“敦孝悌”是“礼治”的重要内容,《孝经》中有“移孝作忠”的说法。崇德二年三月,皇太极对诸王大臣说:“圣《经》有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尔等若谨好恶之施,审接物之道,御下以义,交友以信,如此则身修矣。孝其亲,悌其长,教训及其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身修家齐而国不治者,有是理乎?尔等当存忠直之心以为国,慎毋怠忽,有负朝廷。”[4]455他还曾对臣下说:“乃若虽具才能,而心怀离异,亦复何益?虽甚朴鲁,而为国效力,与朕一心,即为贤矣。尔等众大臣家中,皆各有一二奴仆。其与尔一心,及不与尔一心者,尔等以为何如?此其理一也。”[4]618可见太宗对“孝悌”之道的重视。
清太宗在与明朝的接触中体会到了读书明理的重要性。天聪五年(1631)八月, 皇太极亲率大军包围大凌河城, 对方“经四越月, 人皆相食,犹以死守”,他受到巨大的心理震撼, 认为这乃是读书明理的结果。回到沈阳后, 他立即对诸贝勒大臣进行了一番“忠君亲上”的训示:“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4]146这充分体现了太宗想通过文化教育来提高本民族素质的良苦用心。
清太宗也大力倡导“尊长敬老”等道德风尚和伦理观念。天聪三年二月,皇太极在海州听说当地一对年过百岁的夫妻带着73岁的儿子和全族一起持斋,于是召见其父子,之后谕令海州官员说:“此老人宜善视之。可令在寺庙中奉香火,以终余年,勿得扰累。”[4]70太宗还将儒家伦理道德融入法令之中。如天聪六年三月,太宗诏谕臣民:“若子告父、妻告夫及同胞兄弟相告,果系反叛逃亡,有异心于上及诸贝勒者,许告,其余不许。若有告者,被告照常审拟,原告罪亦同,不准离主。”而之“所以严禁者,以此乃古圣王之成法,故今仿而行之耳”[4]156-157,体现出太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此外,在太宗的倡导下,大量汉文典籍被翻译成满文,促进了中原文化在满族中的传播。
五、“德治”与清太宗的“中国”认同
清太宗皇太极能够施行“德治”,与其勤奋好学的性格、重用汉儒的政策以及善于进行实践总结是分不开的,而这都加深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清实录》说他“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性嗜典籍,披览弗倦”;《清史稿》也说他“性耽典籍,谘览弗倦”。皇太极也注重学习中原王朝的为政经验:“太祖制国书,因心肇造,备列轨范。上(太宗)躬秉圣明之资,复乐观古来典籍,故分命满汉儒臣繙译记注,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焉。”[4]70皇太极观看巴克什达海所译《武经》,读到“昔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时说:“观古史所载,将帅必体恤士卒。如我国额驸顾三台与敌交锋,士卒有战死者,尝以绳系其足曳归。主将之轻蔑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4]110
皇太极收纳的汉儒为其“德治”的施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总结说:“汉人之优遇,尤为太宗朝之特色。清国制度之规定,殆无一不出诸汉人之手……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14]为了得到汉臣的效忠,他不惜纡尊降贵:“朕于旧归新附之人,皆不惜衣服财帛马匹牲畜以养之,又每日三次赐宴,岂不惮烦?直欲使人心悦服,以图大事耳。”[4]293皇太极重用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石廷柱、马光远等汉儒,而对范文程尤其倚重。史载:“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上重文程,每议政,必曰:‘范章京知否?’脱有未当,曰:‘何不与范章京议之?’众曰:‘范亦云尔。’上辄署可。”[8]9351
善于对政治实践进行总结,是清太宗认同“中国”文化、进而形成“德治”思想的关键因素。努尔哈赤曾实行过偏激的民族政策,导致了辽东汉民的激烈反抗。太宗由此认识到“治国之要, 莫先安民”[4]26,即位后调整了民族政策,使得“汉人安堵,咸颂乐土”[4]27。他震惊于明大凌河城守军宁死不降的气节,返京后便训示子民以“忠君亲上”的理论[4]146;他见识到明军将领张春那有如史书中记载的文天祥般的气节后,便开始了对汉族文人的重用和对中原文化的重视[15]。在与明朝在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接触中,皇太极不断总结经验、调整策略,一步步深化了其“中国”认同理念。
清太宗皇太极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通过勤奋研读汉文典籍、重用汉儒,以及考量各种现实政治实践,在对人与天、人与政治的关系的探索中加深了其“中国”认同理念,形成了自己的“德治”思想。称帝后,为了“克副天子之称”,皇太极“内修政事,外勤讨伐”,“朝乾夕惕”;虽然最终“大勋未集”,但其“政治上之设施,亦颇足为清朝二百余年之基础”[14]。探讨清太宗的“中国”认同观念和“德治”思想实践,不仅有助于理解清王朝的治国理念,也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
[1] 赵永春,等.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1-6.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21.
[3] 许纪霖.多元脉络中的“中国”[C]//《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
[4] 清实录:第二册(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 成积春.从“皇天眷佑”到“天命靡常”——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天命思想的演变[J].史学集刊,2005,(1).
[7] 贾越.清朝皇帝年号考[J].北方文物,2012,(4).
[8] 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 满文老档[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954.
[10] 魏鉴勋.试论皇太极的个性——从修身谈起[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3).
[11] 高庆仁.试论皇太极的吏治管理[J].辽宁大学学报,1995,(6).
[12] 高庆仁.皇太极澄清吏治整饬陋习措施述略[J].满族研究,1991,(2).
[13] [清]嵇璜,刘墉,等.清朝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2309.
[14] 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8-219.
[15] 沈一民.皇太极的汉族文人政策评述[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5).
[责任编辑:王 昊]
2016-12-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儒学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治国理念研究”(2016T90113)
李玉君(1980—),女,吉林梅河口人,副院长,特聘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历史学博士,从事辽金史、北方民族史研究;崔健(1991—),男,黑龙江安达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辽金史、北方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