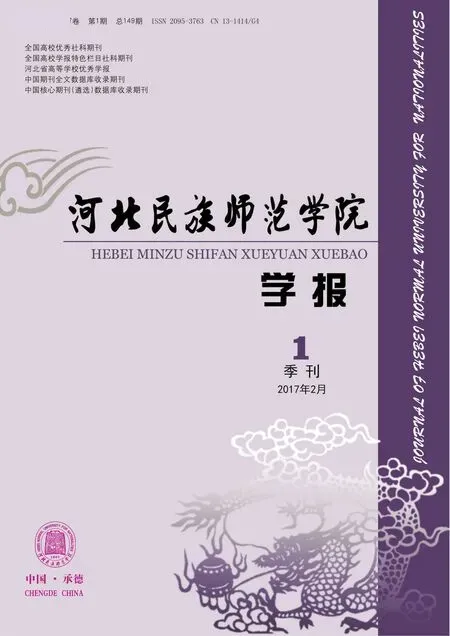梁启超对“文明”概念的转换及思想资源
全定旺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2)
梁启超对“文明”概念的转换及思想资源
全定旺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2)
“文明”的古义包含四种价值理想即尚柔不武、崇尚规则、中庸及群体本位下通过个人私德达到的群体和谐,而梁启超则对“文明”古义进行了四层转换,即分别转换为善武、尊重服从法律、进取冒险及个人本位下通过个人的公德承担国家责任。梁启超转换“文明”古义的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即以西方的“文明”为标准,通过转换“文明”古义中的非西方成分以实现“文明”概念的更新。第二,福泽谕吉“文明”概念中个人与国家的结构理论,即以个人为本位,以此独立地承担国家的责任。第三,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福泽谕吉;文明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度的文明转型的时期,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通过日文书籍了解了最新的西方理论,并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将这些思想引入国内。然而这些西方思想是通过以日本思想家为媒介而对梁启超产生影响的,这其中就包括许多新的西方概念通过日本思想家的翻译而被梁启超吸收,如“国家”、“国民”、“社会”、“文明”等概念,这些概念被引入中国之后,几乎重新规范了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的看法。当然这些概念基本上都并非是新创的,而是以古汉语所固有的词语而赋予其以西方概念的意义,所以通过对梁启超引入的这些概念的具体的考察,可以了解近代思想家在引入西方思想时所具有的特点。
本文以“文明”概念为核心,来梳理梁启超对古汉语“文明”的转换,并考察这种转换的思想资源。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曾撰《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一文,系统考察了梁启超“文明”概念所受到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梳理梁启超对古汉语“文明”概念的具体转换,也并没有对福泽谕吉“文明”概念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考察,同时没有足够重视中国传统的“文明”内涵在其中的延续。本文将在这三点上对石川的研究进行补充。
一、“文明”的古义及梁启超对“文明”的转换
“文明”最早见于《尚书》《周易》等先秦古籍,其义大致分三类:第一,谓文德辉耀。如《尚书·舜典》:“懶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1]第二,谓文采光明。如《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2]24第三,指与威武相对的概念,《易传》中以“文明”形容“离”卦阴爻得位而居中①“大有”、“贲”、“明夷”等卦中的“文明”概念与“同人”卦相近。“大有”的卦象为,即乾下离上,《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王弼注曰:“刚健不滞,文明不犯。”孔颖达疏曰:“‘刚健’谓乾也。‘文明’谓离也。”(《周易正义》)“贲”卦的卦象为,即离下艮上,《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王弼注曰:“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疏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周易正义》)“明夷”的卦象为,即离下坤上,《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文明”指“离”,而“柔顺”指“坤”。。如“同人”卦的卦象为,即“离”下“乾”上。《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柔得位居中”即指六二阴爻居阴位且居中,“文明以健”亦指六二居中得正。王弼注曰:“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也。”[2]86
“文明”概念除了三种古义之外,后来又衍生出文采、文治教化、文教昌明等意思。这些衍生义以及古义中的前两种意思都表示“文明”的状态,而古义中的第三种意思则反映出“文明”概念的价值基础。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最初的甲骨文纯粹使用图形来作为文字使用,而这些图形文字又与所表示的东西,在形状上很相像,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字所表示的意思与图形有很大的联系,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从图形上来理解“文明”,而“文明”的第三种古义为这种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易传》中“文明”出现6次,其中4次指“离”卦,我们可以从“离”卦所体现出的状态中理解“文明”概念的价值基础。
“同人”、“大有”、“贲”、“明夷”等卦中,都有“离”卦,且《易传》都以“文明”形容其状态,仍以“同人”卦为例,“离”主要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六二为阴爻;第二,阴爻居阴位;第三,居于中位。从这三层含义中可以引申出“文明”概念所具有的三种价值理想:第一,具有柔的特质,即不以威武;第二,重视规则,不僭越;第三,中庸。也就是说,在古代假如以“文明”形容某种状态或某个事物,那么这种状态或事物需基本满足这三种价值理想。
日本在近代以后开始以“文明”一词来翻译civilization,从而产生了“文明史观”,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接受了这种翻译,并将其引入国内,那么如果先从结果上来看,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大量带有“文明”一词的文章中,“文明”概念相对于其古义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可以从“文明”一词的三种价值理想入手来进行考察。
首先,就“文明”古义中崇尚柔而排斥武力来看,梁启超则主张尚武。1903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尚武》一文,认为柔弱的文明,不能抵抗野蛮的武力,如果没有尚武的国民,铁血的主义,那么即使具有文明,也必然不能立足于竞争剧烈的国际舞台。他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3]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似乎仍将武力理解为野蛮,只是将其视为维持文明的不得已的手段,但是实质上他是将尚武作为一种国民的高尚的精神,这点体现在一年后刊行的《中国之武士道》①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中。在其序例中,梁启超指出中华民族之尚武,是最初的天性,而中华民族之不武,实则是其第二天性。他认为中国自古并非统一之国,而是各族杂处,相互压迫、侵略,假使无尚武之精神,则无以图存,从而养成了中华民族尚武的原始天性。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专制政体,从而渐渐形成天下皆弱,而一人独强的局面,造成人民武德尽丧。在梁启超的文章中,“文明”的价值理想发生了第一层转换,即将尚武也纳入“文明”的价值之中。
其次,就“文明”古义中重视规则这点来看,梁启超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层含义。对近代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规则就是法律,梁启超在《新民说》②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③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服从释义》④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等文中认为,人群愈进于文明,则其法律愈严密,文明人之所以比野蛮人尊贵,就在于文明人能以法律自律,而野蛮人不能。他认为文明的自由,正是自由于法律之下,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就像机器的节奏,每个人的一进一退,就像军队的步伐。而自治与制裁则是维持文明的法律所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自治属于对个体的要求,即文明之人,皆须知其有服从法律之义务,并以此强自制裁,以使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内。而对于国家,则须有制裁力,以对僭越法律界限的国民进行制裁。可见,梁启超并没有彻底转换“文明”古义中重视规则的价值,而是赋予其现代意义,即从尊重法律来理解“文明”。
第三,“文明”古义崇尚中庸,而梁启超则鼓励进取冒险。他在《论进取冒险》一文中开篇便指出:“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4]他认为进取冒险精神是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的主要原因,如果人有此精神则生,无之则死,国家有此精神则存,无之则亡。他将进取冒险精神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四点,即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他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亦只是由于知明日而已。他不仅批判老氏之言只知不为物先、知白守黑、知足不辱,同时也批判后世儒者效法孔子者,往往遗其大体,只取其“狷”、“勿”、“坤”、“命”主义,而弃其“狂”、“为”、“乾”、“力”主义。由此可见,梁启超转换了“文明”古义中崇尚中庸的传统,而将进取冒险亦理解为“文明”的价值理想。
从“文明”古义的三个价值理想以及梁启超对其的转换中可以发现一个新的特点,即“文明”的古义是以群为本位的,而梁启超的“文明”概念是以个人为本位的。除了第二点两者具有连续性之外,从第一点与第三点来看,“文明”的古义崇尚柔、不武、中庸,强调的是群体的和谐性,再者《易传》本来就是以“文明”形容“离”卦的整体和谐状态。而梁启超则主张尚武、进取冒险,这些特点首先强调的不是群体间通过和谐的状态而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而是侧重于每个个体的独立承当。但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古义不重视个人,梁启超不看重群体,恰恰相反,古代的中国最看重个人道德的修养,而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则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最需要国家的强大,那么如何解释这种表面的矛盾?因为古代中国的“文明”价值是看重群体内部的和谐性,那么每个个体的私德就变得至关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依赖于每个个体的个人修养。而在梁启超的“文明”价值里,他看重个人尚武、冒险,同时他当时面临的首要课题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而个人尚武、冒险的特质均存在分离群体的趋向,因为仅依靠这两种德性不足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那么维护国家存在的德性就不能仅靠提倡个人的私德,所以梁启超这一时期十分强调合群等公德。由此得出了梁启超对“文明”古义价值的第四层转换,即不再是强调通过个体的善柔、中庸等私德而达到人际的和谐从而实现群体的和谐,而是重视个体的尚武、冒险等精神同时强调公德从而实现群体的竞争力的提升。
从梁启超对“文明”概念的四层转换中可以看出他受到了西方文明观的影响,而其中第一层和第三层转换带有进化论的色彩,第四层转换则具有国民国家论的特点,那么梁启超转换“文明”概念所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呢?“文明”一词作为civilization的译语而广为人知是由于福泽谕吉的文章,而梁启超亦首先是通过福泽谕吉而理解西方的文明理论,所以需要对福泽谕吉的文明理论进行考察。
二、福泽谕吉的“文明”的影响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一文中系统梳理了梁启超的“文明”概念所受到的来自日本思想界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梁启超1898年8月变法失败流亡日本至1899年11月暂离日本游檀香山的一年左右时间,第二个阶段为游檀香山及回日本之后的几年时间。石川认为第一个阶段梁启超热衷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福泽的“文明”概念对他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福泽的文明史观,福泽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即野蛮、半开化和文明,并认为人类社会是逐渐从野蛮不断进步到文明,同时文明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认为文明对半开化固然是文明,而半开化对野蛮,也不能不谓之为文明,以此为标准,福泽对当时世界各国的文明状况作了区分,他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5]17石川认为梁启超接受了福泽谕吉的文明阶段论,并以1899年刊于《清议报》的《文野三界之别》为例进行了说明,他指出civilization意义上的“文明”译语,并非中立地形容西洋社会的状况,而分明是以历史的“进步”为前提,并包含着对西洋为排头的一元性顺序和普遍公理的价值判断。他认为这样的“文明”,“实际上只不过是以近代西洋来认识自身和使自身正当化,从假象的亚洲社会状况中找到对比性根据而动员起来的工具之一。其自身在难以定位的自我,要表述它的惟一语词,就是把非西洋看做他者始能成立的‘文明’概念。”[6]那么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只要接受了“文明”观点,他们就只能以西洋的眼光表现自我,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洋文明国家中存在的东西。①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在分析福泽谕吉的文明观时认为在福泽那里,“文明”是相对而成的,它必然具备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即“野蛮”或“未开化”。因此,所谓的文明只有在与野蛮相对的关系之下才能成立,同样地,野蛮只有在遇到文明时才能被称为野蛮。他认为文明、野蛮均为相对的概念,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某个社会被视为文明社会,也必定有另一个社会自然地被视为未开化、野蛮的社会。此事表明,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不只是进度或程度上的相对关系,另外还有对立的关系。即文明这一概念的成立,势必连动地产生野蛮这一对立的观念。(参见:子安宣邦著,陈玮芬译,《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18-19页。)子安宣邦分析福泽谕吉的“文明”的方式与石川祯浩分析梁启超的“文明”的方式具有一致性,即认为“文明”概念具有反东方性。依照石川的分析,“文明”概念具有反东方性,即将东方固有的东西视为野蛮,从而使“文明”概念得以成立,那么引入“文明”也就意味着只有将东方原有的“文明”理念视为反动始才可能。这种分析基本上能解释梁启超对“文明”古义的转换,即梁是在修正“文明”古义的基础上对“文明”概念实现转换。但是仍存在缺陷,即梁启超对“文明”古义的第二层转换存在很强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传统的“文明”并没有全然被否弃为野蛮,而部分地在新的“文明”概念里得到的延续。
石川认为福泽谕吉的第二个影响是“国民国家”思想,福泽批判日本有政府而无国民,日本人知有家而不知有国,他宣扬“一人独立,则一国独立”的思想,致力于培养每个日本人独立承担国家责任的精神。石川认为当时梁启超的主题,就是确立把中国人改造成与西洋文明并肩的“文明”的“国民”的独立精神,而这体现在《国民十大元气论》②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一文中,该文受福泽谕吉重视“人民之风气”的独立精神的影响,致力于宣扬“国民之元气”,而该文的第一篇便是《独立论》,可见福泽思想的影响。但是该文没有完稿,石川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梁启超暂离日本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第二阶段他受了其他思想的影响。
石川认为梁启超在第二阶段受到了加藤弘之的“社会进化论”和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而开始认为“强权”、“竞争”等为更根本性的原理,而开始关注国权,并认为自由为团体之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石川认为这一阶段的梁启超开始疏远了《文明论概略》,而本应成为梁版《文明论概略》的《国民十大元气论》的续篇也终未发表。按照石川的分析,梁启超对个人与国家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第一阶段重视个人的独立精神,而在第二阶段则侧重于国家的权利。然而笔者上文论述梁启超对“文明”古义的转换时引用的《论尚武》《中国之武士道》《论进取冒险》等文章均发表于第二阶段,如果认为这一阶段梁启超完全完全偏向于国家的自由权利,那么难以说明梁启超对“文明”古义的第四层转换中以个人为本位的立场。在梁启超的“文明”思想中,实际上一直持续着以个人为出发点,并通过个人独立承担国家责任,以实现国家独立强大的结构。③台湾学者黄克武认为梁氏虽然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下的个人主义者,但也绝不是所谓的集体主义者或者权威主义者,他对个人自由与尊严有很根本的重视,可以说他所强调的是非穆勒主义式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仍是以保障个人为基础的,但同时以为个人与群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时强调以保障群体价值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参见:黄克武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新星出版社,2006年5月,第32页。)黄氏的观点强调的是梁启超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如果从梁启超对“文明”概念的转换中以个人为本位的观点来看,则与本文具有一致性。既然梁启超的“文明”概念是吸收自福泽谕吉,那么有必要对福泽谕吉的“文明”结构进行再考察。
通过对《文明论概略》的分析,笔者认为福泽谕吉的“文明”主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重视西洋文明的独立精神,重视个人的智。他认为半开化的国家在汲取外国文明的时候,必须要取舍适宜,而文明又包含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他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而内在的文明难求,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他将文明的精神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私德,即属于内心活动的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品质;第二种是公德,即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品质;第三种是私智,即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第四种是公智,即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轻缓的后办,重急的先办,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①参见: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114。而这四者中,福泽最看重的是第四种的公智,他认为如果没有公智,就不可能把私德私智发展为公德公智。福泽主张吸收西洋他在《文明论概略》序言中就指出“文明论”的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在于讨论广大群众的总的精神发展。所以,文明论也可称为群众精神发展论。可见,福泽关注的文明具有重视总体的特性。另外,福泽认为一国的文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风气,而国家的风气是全国人民智德的反映,但是这里他强调的智德不是个人的智德,他说:“这种智德,或者也可以不称为人的智德,而叫做国家的智德。所以称为国家的智德,是由于指全国人民的智德的总量而言。”[5]71从“文明”的第二个特点可以看出福泽的“文明”除了关注个人的智德外,还具有侧重于总体的国家智德的特点,也就是说的他的“文明”概念本身就具有国家主义的特性。但是,福泽谕吉在论述国与国之间的独立平等时指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日本国是日本人组成的;英国是英国人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国人同样是天地间的人,彼此就没有妨害权利的道理。一个人既没有加害于另一个人的道理;两个人也没有加害于另外两个人的道理;百万人、千万人也应该这样。事物的道理原不能由人数多少来变更的。”[7]从中可以看出在福泽看来,国家独立平等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个人之间的独立平等,即是说福泽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文明”的第一个特点可见归结为个人本位,而第二个特点可归结为具有国家主义的性质,而这两个特点又通过对第一个特点中个人的公智的强调而达到统合,即将国家主义的基础建立在每个人的理性判断之上,使每个个体能共同自觉地承担对国家的责任。梁启超吸收了福泽谕吉的“文明”中的这种个人与国家的结构,而这也能说明其对“文明”古义的第四层转换的思想来源。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文明”古义的第一层与第三层转换基本上是以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为思想背景的,而第二层转换除了具有西方文明的特点外,具有很强烈的延续传统的色彩,第四层转换则受到了福泽谕吉的“文明”中个人与国家结构的影响。可以说,梁启超转换“文明”基本上是以福泽谕吉的“文明”理论为其思想资源的主体的。然而在第四层转换中可以看出,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文明”具有显著的区别,虽然两者的结构基本相同,即以个人为本位,以此独立的个人承担国家的责任,然而梁启超在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时,侧重的是个人的公德,而福泽谕吉则侧重个人的公智,那么这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就需要对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文明”进行进一步的区分。
三、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文明”中对智德的不同偏重
在论述梁启超与福泽的“文明”中解决个人对国家的责任问题的方式的差异之前,有必要先略述西方的“文明”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欧洲近代描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代表性理论为社会契约论,如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是从自然状态出发的,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 没有一个人享有比别人多的权力,每个人又都是自由的, 都有权力处理他自己的人身或财产,同时个体之间是独立的,任何人不得侵害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但是,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对未来的事情没有统一的判定标准, 就会发生冲突,而如果个人之间发生冲突时没有共同的裁判, 冲突就会加大,就易于进入战争状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人们共同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力,订立契约,制定法律,进入政治社会。但是因为洛克把个人当作国家的前提和基础, 把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个人权利视为与生俱来的先于国家而存在的自然权利, 所以他认为人们订立契约时是保留了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而只转让给国家以惩罚罪犯和要求赔偿的权利,同时根据契约所建立的政府应该是有限制的政府,而且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是设立政府的唯一目的,如果政府违背契约侵害人民的自然权利,人民就有反抗和革命的权利。可见欧洲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理论关注的主要是个人作为独立自由的主体如何相互协商形成国家的问题,而不是关注国家作为整体一致对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福泽谕吉是一致的,即一方面吸收了西洋文明中以个人为本位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国家的独立与强大,所以个人对国家的责任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尤其重要。
福泽谕吉主要是依靠提高个人的公智水平以此使每个日本人独立承担对国家的责任,他主张吸收西洋文明智的精神,同时劝导大众学习实学以实际地提高每个人的智力水平,从而能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一个具有了公智的日本人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里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时,意识到的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导致人们进入战斗状态,而是每个人的权利都有可能因为外国的入侵而集体受到损害,这样他们每个人集中关注的焦点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独立平等是否能够实现,个人在这时候便能自觉地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
与福泽不同,梁启超则更强调公德在个人承担国家责任中的作用。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民说》中发表《论公德》,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最缺乏的就是公德,而公德是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基础,没有公德便无法组成一个国家。他对公德与私德进行了区分,所谓私德指人人独善其身者,而公德则是人人相善其群者。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的道德虽然发达,但是偏于私德,《论语》《孟子》等书,所教私德居十之九。他认为中国的旧伦理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重视的是一私人对于一私人的事,而西方伦理包括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所重视的是一私人对于一团体的事。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偏重私德而造成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故梁启超大倡公德,称其为诸德之源,视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他认为若国人知有公德,则新道德出焉,则新民出焉。
梁启超的“文明”中虽然是将公德视为约束个人承担国家责任的最重要的方式,但是并不意味着智力不被包含于其“文明”概念中。他在发表于《清议报》的《论强权》一文中指出动物至野蛮世界,强者全属体力之强;半开化的世界,强者体力与智力互相胜;而文明世界,强者全属智力之强。他将智力视为“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智力概念在他那里更多地表现为私人的,即不是像福泽谕吉一样鼓励每个人用智力思考自己对于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是将智力作为一种个人的权力的象征,以与统治者相抗衡。他说道:“彼野蛮与半开之国,统治者之知识,远优于被治者,其驾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权力势不得不猛大。至文明国则被治者之智识,不劣于统治者,于是伸张其权力以应统治者,两力相遇,殆将平均,于是各皆不得不出于温良,若是者谓之自由。”[8]也就是说,文明国家的国民因为每个人的智力而形成一种权力,而从统治者处获得更大的自由。梁启超在此所论述的智力存在分离国家的趋向,所以这样理解的智力必然依赖公德始能维护的国家稳定。
对每一个人来说,公德并非是可以独存的,难以想象一个不具有私德的人会具备完善的公德。梁启超在《论公德》发表一年后便又发表《论私德》一文以纠正其思想之偏,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1903年游美之后思想转变的影响,而公德完全是建立于私德基础之上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在此文中指出一私人而无私德,则如此的百千万亿的私人组成群体,也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因为公德者,为私德之推。由此他转变了之前的看法,认为欲铸就国民,必以培养个人的私德为第一义。并且他认为西方之新道德必待国民教育大兴之后,而当时对国民的德育,只能依赖于传统遗传的固有之旧道德,并提出三条纲领即正本、慎独、谨小。
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福泽谕吉强调个体对国家责任时的侧重是完全不同的,福泽谕吉较全面地接受了西方的智的观点,而梁启超则表现出很强的传统倾向。那么梁启超对“文明”概念的第四层转换中对公德的强调该从哪里寻找思想来源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德本位的传统。从“文明”古义的四种价值看,尚柔不武、重视规则、中庸、群体和谐全是属于德的范畴,而且包含这些价值的“文明”本身在古代便被视为一种德的概念。如孔颖达注疏《周易·革·彖》中“文明以说(悦)”时说:“能思文明之德,以悦于人。”[2]237正因为“文明”古义本身便是一个德的概念,所以固然梁启超通过福泽谕吉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史观,然而在通过西方的“文明”概念转换中国的“文明”古义时,他意识到的作为西方崇尚公德的“文明”反面的是中国崇尚私德的 “文明”,而并没有将“文明”概念本身的倾向作为反思的对象。也就是说,他在内容上不断意识到中国“文明”古义的非西洋成分,然而却并没有摆脱“文明”作为一种总体的道德倾向性,“文明”概念本身作为一种偏向道德的理念始终是稳固地扎根于梁启超思维的最底层。这也就能说明,为什么他发现公德概念不能单独存在便很快又重新转向私德。
四、结语:传统的延续
本文首先通过《周易》“离”卦的状态论述了“文明”古义的四种价值理想即尚柔不武、崇尚规则、中庸及群体本位下通过个人私德达到的群体和谐,而梁启超则对“文明”古义进行了四层转换,即分别转换为善武、尊重服从法律、进取冒险及个人本位下通过个人的公德承担国家责任。梁启超转换“文明”古义的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即以西方的“文明”为标准,通过转换“文明”古义中的非西方成分以实现“文明”概念的更新。第二,福泽谕吉“文明”概念中个人与国家的结构理论,即以个人为本位,以此独立地承担国家的责任。第三,传统思想的延续,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觉的延续,如第二层转换,另一方面是不自觉的延续如第四层转换中将私德转换为公德后又重新强调私德。
相比于梁启超的“文明”概念中较多的传统的痕迹,福泽谕吉则较为彻底地吸收了西方civilization意义上的“文明”概念,对于这种差别的原因或许可以用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对中日文明的差异的论述来进行说明。他认为日本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形成了天皇至尊未必至强,而将军至强未必至尊的社会结构,使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而中国古代基本是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必然趋向偏执。
总之,梁启超在吸收西方的“文明”概念以转换“文明”古义时所具有的特点给我们一种启示,也就是在考察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引入的西方概念时,必须要意识到这种概念的双重特点,即日本思想家的中介作用与中国传统因素的延续。
[1]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1.
[2]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梁启超.论尚武.收入: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615.
[4]梁启超.论进取冒险.收入: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562.
[5][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6][日]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收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17-118.
[7][日]福泽谕吉著,群力译,东尔校.劝学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4.
[8]梁启超.论强权.收入: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四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2269.
Liang Qichao 's Conversion of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and His Ideological Resources
QUAN Ding-w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ancient meaning of "civilization" contains four values: Not advocating force, Promoting adherence to the rule, Moderation, Through the individual private moral to achieve group harmony. Liang Qichao converted The ancient meaning of "civilization", The four values were converted to advocating force, Respect the law, Aggressive adventure, Through morality to bear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of Liang Qichao 's Conversion of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come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Fukuzawa Yukichi's civilization theory, which regarde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the standard, And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s renewed by transforming the non-western elements in the ancient meaning of "civilization". Secondly, Fukuzawa Yukichi's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which emphasized individuals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te independently. Third,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Liang Qichao; Fukuzawa Yukichi; Civilization
G125
A
2095-3763(2017)-0071-07
10.16729/j.cnki.jhnun.2017.01.012
2016-12-13
全定旺(1990- ),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日近现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