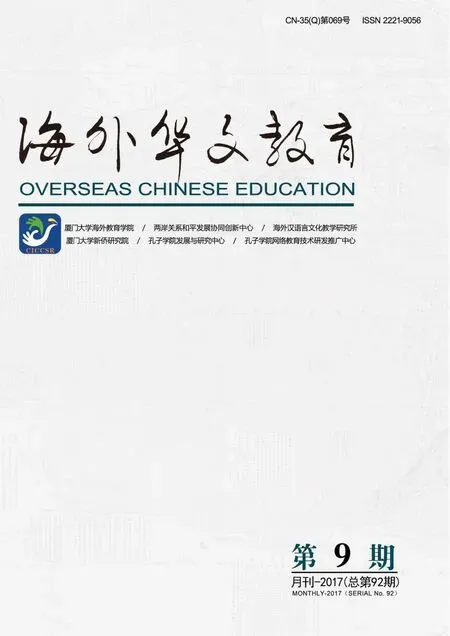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
刘振平
(广西师范学院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中国 南宁530001)
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
刘振平
(广西师范学院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中国 南宁530001)
新加坡华语作为现代汉语的一种区域变体,主要受南方方言和英语的影响,与普通话之间表现出一些差异,其语法特点及其来源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然而,直至目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均未明确确定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的内容,这就导致学者在确定语法特点时众说纷纭。确立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开展社会调查,搜集有代表性的语料,建立大规模的新加坡华语语料库是我们目前急需完成的工作。新加坡语言环境和语言政策的变化导致新加坡华语语法发生一定的演变,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
新加坡华语;语法;现状;问题
一、引 言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大陆开始了现代汉语的教学,同样受到该运动影响的新加坡创立了第一所新式华文学校——华侨中学,也开始了现代汉语的教学。由于当时新加坡的现代汉语教学“一切都是中国式的,教师和教科书都来自中国”(臧慕莲,1994),所以,应该可以说当时新加坡华文学校里所教授的现代汉语与中国大陆所教授的基本相同。然而,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与中国不同。又加上新加坡与中国自1949年以来又曾经隔绝了大约四十年,也就是说,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或者说很少接触,而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两地的现代汉语势必会出现差异(陆俭明,2002)。新加坡华人大多来自于南方方言区(闽粤地区),现代汉语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闽、粤、客家等这些南方方言的影响(陈重瑜,1986)。又加上长期以来,新加坡将英语作为行政语言,尤其是1986年以后,运用汉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华校消失,英语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汉语成为学校里的单科教学,“因此英语给予华语的压力与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周清海,2002)在这样的语言背景和教育政策的影响下,现代汉语在新加坡地区自然会发展出一些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从而形成一种区域变体——新加坡华语。新加坡华语作为现代汉语的一种区域变体,不同于普通话,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新加坡华语研究者陈重瑜(1986、1993)、萧国政(1999)、陆俭明(2001、2002)、周清海(2002、2007)、祝晓宏(2008)、刘振平(2016)等都对新加坡华语的区域变体地位给予了肯定。
既然新加坡华语不同于普通话,那么新加坡华语相对于普通话具有哪些特点,自然也就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截至目前,有关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对其进行梳理和评析,无疑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亮点,更加清晰地认识新加坡华语,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和顺利开展语法教学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受方言影响产生的语法特点研究
1956年新加坡出台了《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明确规定:各语文源流学校应当以英文、马来文、华文和泰米尔文这四种语言中的至少两种作为学校的教学媒介语(高茹、刘振平,2014)。在此之前,新加坡华校主要是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所以,从学校语言教育这个层面来看,英语对华语的影响有限。从华人的日常交际语言来看,新加坡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显示:1980年,华人家庭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口为81.4%,而以英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口仅为10%(吴英成,2010:59-60),“以方言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华语时,不免会把二者相混,形成富有浓厚本地色彩的语言特征。”(吴英成,1988)早期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新加坡华语受南方方言影响而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如余耕文(1984a、1984b)主要研究了新加坡华语的一些特殊语助词和结果补语的特殊形式。黄秀爱(1986)主要研究了新加坡华语助动词使用上的一些特点。陈重瑜(1986、1993)着重描述和讨论了新加坡华语“因南方方言影响而形成之特殊语法结构”。另外,吴英成(1985)、张楚浩(1986)、周小兵(1989)等也探讨新加坡华语所具有的汉语南方方言特点。
1956年后,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华校改为以华语和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英语对华语的影响逐渐增大。1979年,新加坡开始开展“讲华语运动”,要求华人家庭“多用华语,少用方言”。至1986年,新加坡华校教育体系彻底瓦解,所有学校变成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华语成为学校里的单科教学。与此相应的是,新加坡小学一年级入学新生的家庭主要用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数由1980年的64.4%到1989年锐减至7.2%;而以华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数由1980年的25.9%,增至1990年的最高峰,随后逐年递减,目前已经降至不足40%;以英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数则一直逐年增加,从1980年的9.3%增至目前的超过60%(吴英成,2010,刘振平,2014a)。由此可以看出,1979年以后方言的影响逐渐式微,而“英语给予华语的压力与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周清海,2002)
虽然随着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环境的变化,英语对新加坡华语的影响越来越大,方言的影响逐渐式微,然而,由于语法变异的速度较慢,方言影响而造成的特殊语法现象依然会在新加坡华语中长期存在一段时间。新加坡华语受方言影响而产生的语法特点,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仍是学者描写和分析的一个焦点。相关的学术论文有林万菁(1996、2006)、萧国政(1999)、邢福义(2005)、潘秋平(2009)等。林万菁(1996、2006)分别研究了新加坡华语中来源于南方方言的“有+动”句和“多”、“多多”的用法。萧国政(1999)指出,新加坡华语中“全”、“实在”的一些用法源于方言。邢福义(2005)对新加坡华语中“‘才’充‘再’”现象的来源做了详细的探讨,指出这一现象主要来源于闽方言。潘秋平(2009)分析了新加坡华语中“跟”所具有的一些特殊的介词用法,认为这些用法“是在和闽南语的接触下,由闽南语诱发而产生的一种复制式语法化现象。”另外,还有一些学位论文如朱淑美(1996)、傅丽君(2003)、何丽娴(2003)、黄淑盈(2006)等也都探讨了新加坡华语中所具有的南方方言特点。
三、受英语影响产生的语法特点研究
英语对新加坡华语的影响越来越大,自然使得新加坡华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英语的特点。吴英成(1988)指出:“由于英语是新加坡人的主要工作语言,举凡政府文告、工商业交往和科技的研究皆以英语为生,而且英语也是学校的第一语文和各种科目的教学媒介语,华英相混的现象也就司空见惯了”,“这种现象在小学阶段还不显著,因为88%以上的小学生以汉语方言和华语为主要家庭用语,英语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外国语,一切都感到陌生,完全处在萌芽阶段,加上他们的英语词汇有限,生活空间窄,对象简单,因此,他们对英语无法运用自如。到了中学阶段,基本英语能力已经稳固下来,加上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科目增加(例如英文文学、历史、地理、科学等),他们接触英语的机会很多,华语的课时又有限,他们在学习华语的过程中,常常出现英语式的华语句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很多的成果揭示了新加坡华语语法受英语语法影响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如萧国政(1999)指出,新加坡华语中“了”的一些用法和“副词+形容词”的状中短语并列时只用一个副词的现象可能是受英语的影响。周清海(2002)指出:“从新加坡华语的情况看来,因为没有共同的、成熟的口语为基础,却建立了共同的书面语,所以新加坡口语受外语(英语)的影响,远远超过书面语所受的影响。‘被’字句在口语里广泛应用,好像‘马路被修好了’等等频率很高的说法,都是新加坡华语口语受外来影响的现象。”
林素娥(2009)指出:“新加坡华语也深受顶层语言——英语的巨大影响,形成其主语优先的特征。英语和华语虽都为官方语言,但英语是新加坡各族人通用的语言,也是行政语言。长期以来,英语对华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触及新加坡华语的句法结构。英语是一种主语优先的语言,被动句广泛使用,形式主语成为强制性句法成分,它们也成为新加坡华语的句法特征。而这些句法特征与VO语序典型相互和谐,形成新加坡华语SVO语序典型的语序类型特征。”林素娥(2012)对新加坡华语口语中“懂”用作话语标记的现象做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懂’诸固定形式发展为话语标记也应是英语对应形式影响的结果,是语言接触长期作用的结果。”
江郁莹(2013)研究了新加坡华语中“给”字句式的典型用法,发现“新加坡的‘给’较接近英文中的‘give’及‘to’的概念”。
刘振平(2014b)指出,新加坡中学生的作文中“被”字句、“当……时/的时候”和存在句句首处所词语前用介词“在”等句法格式的使用频率很高,是新加坡华语的句法特征而不是偏误,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受英语影响的结果。
四、方言和英语影响某一语法范畴表达的研究
由于新加坡华语会受到南方方言和英语的双重影响,所以,某一语法范畴在表达上的一些特点,有可能部分来自方言的影响,部分来自英语的影响,如有关数的表达,尚国文(2012)发现:“新加坡华语中,‘万’可以说成‘十千’,如30,000常读成‘三十千’,120,000常读成‘一百二十千’。这种读法是受英语数字读法的影响。”而“新加坡华语中偏好用‘两’很可能是受闽粤方言的影响,另外用‘二’较少也可能跟当地人的发音习惯有关。由于er的读音包含卷舌音,以南方方言为母语的当地人读起来比较吃力,所以人们更倾向于使用‘两’来表达‘二’的数字概念。”
有关时间的表达,尚国文、赵守辉(2014)发现,新加坡华语中在表达“星期”这个时间概念时,除了用“星期×、礼拜×、周×”等形式来表达,还常用“拜×”来表达,“这种用法很可能来自闽语”。而“新加坡华语经常使用‘来临’做定语,表达未来的时点,意思是‘即将到来的’。‘来临’的这种用法很可能是直译自英语的‘upcoming’一词。”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着重对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的描写,而在对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分析上多是概括性地指出这些特点是由于新加坡复杂的语言环境造成的,既有来自南方方言的影响又有来自英语的影响,而对于哪些特点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产生的、哪些特点是受英语的影响产生的,则未加详细分析。这类研究成果有陆俭明、张楚浩、钱萍(1996)、陆俭明(2001、2002)、周清海(2002、2006)、祝晓宏(2008)等。
五、问题讨论与研究前瞻
(一)标准不立,众说纷纭
研究新加坡华语语法,首先应该明确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包括哪些内容。没有一个标准确定哪些是属于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内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谈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点也就没有基础、没有参照。比如说,新加坡人在口语表达中经常会用到“有+动词”的句式(林万菁,1996)、以“才”代“再”(邢福义,1995),那“有+动词”句式、以“才”代“再”是不是属于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内正确的、规范的语法现象呢?不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无法说清这是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点,还是新加坡人使用汉语表达时出现的错误。然而,吊诡的是,直至今日,关于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的具体内容,无论是新加坡官方还是学者都没能确定下来。正是因为目前尚未确立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系统,大多数研究新加坡学习者汉语语法偏误的成果中,往往就只能简单地依据普通话的标准来判断学习者的偏误,如崔娇阳(2012a、2012b)、高花、吴福焕(2014)等都是如此。
如果不承认新加坡华语是现代汉语在新加坡地区的一种区域变体,将新加坡华语等同于普通话,那么问题就很简单,所谓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就是普通话的语法系统,新加坡人在语法上表现出来的一些与普通话不同的“特点”,要么是偏误(普通话中没有的用法)、要么是使用特点(普通话中有的用法,但新加坡人在使用时更常用或较少使用),算不上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点,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新加坡华语”这一实体。然而,目前来看,不承认新加坡华语作为现代汉语的一种区域变体的定位,是大多数学者不能够认同的。毕竟新加坡人民在长期使用华语的过程中,“或则由于他种语言‘干扰’(interference),或则由于‘借用’(borrowing)”,而萌生了自己的特色(郭振羽,1985)。如若承认新加坡华语是汉语的一种区域变体,那么“判断某个语用法规范与否的标准来自新加坡华语本身,而不是其他华语”(徐杰,2007:46),这样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归纳整理出新加坡华语的语言规则系统”(徐杰,2007:282)。
虽然很多学者都有类似徐杰(2007)的观点,如周清海(1999)指出:“样样以人家的作为标准,没有自己的特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陆俭明(2002)指出:“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化,在我看来,也不一定要完全受中国普通话规范的限制。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由于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新加坡华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与中国不同,所以新加坡华语不可能跟中国普通话同步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考虑新加坡华语规范化问题时决不能感情用事,而需要面对现实,严肃对待,认真思考。对于那些虽然是从方言或外语来的,但很有表达力,而又不破坏汉民族共同语的规则,则可以接受,成为新加坡华语的组成部分。”但直到目前也未见有人做过归纳整理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的工作。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所说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是否真正属于特点,也就没有基本的判断依据。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开展必要的调查研究,及早确定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系统,方能为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的研究和华语语法教学提供基础。
(二)研究中所用语料的代表性值得探讨
确定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建立新加坡华语语料库。然而,到底哪些语料是真正代表新加坡华语的呢?这是一个需要细化研究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往往依据自己所搜集的语料来研究新加坡华语,其所占有的语料是否具有代表性,往往没有经过充足的调查和论证。如对于已有研究中指出的10个新加坡句法特点:“副词‘先’次序倒序”、“副词‘多’、‘少’倒序”、“‘来’、‘去’的及物用法”、“正反问句简化”、“特殊比较句”、“语尾助语‘来的’的插入”、“‘没有’作补语用”、“动词后状语的重叠”、“‘大’与‘小’的重叠”、“‘有没有’作为语尾助词”,吴英成(1990)在随机抽查的35名高中一年级学生和35名华文教师中做了调查,发现仅有24%的调查对象使用这些所谓具有新加坡华语特点的语法现象。由此可见,确定某个语法现象是否是新加坡华语特有的,必须首先确定哪些人所说的才是真正的新加坡华语,哪些语料才是纯正的新加坡华语语料,仅仅靠自己的语感或语料搜集不全面都会导致所得结论不够准确。
在搜集语料时,我们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必须在“老新加坡华人”中搜集语料。所谓“老新加坡华人”,是指其本人出生在新加坡且在新加坡至少受过完整的中小学华文教育(年长者要求是华校生),且其父母出生在新加坡以南方方言作为交际用语,或祖父母出生在新加坡以南方方言作为交际用语、父母以华语作为交际用语。二是,年龄和教育背景上既要有受过1979年前的华校教育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又要有1979年后在英语为主要教学用语背景下接受过完整的中小学华文单科教学的、以华语作为家庭用语的年轻人。通过这两个方面的限制,就将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排除在外了(第二语言学习者所说的华语,自然不能代表新加坡华语)。三是,既要有口语语料,又要有书面语语料。在综合考察口语语料和书面语语料的基础上,归纳出新加坡华语的基本语法系统,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口语语法系统和书面语语法系统。
(三)不同语体的语法特点研究不足
由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出,在1979年新加坡开展“讲华语运动”以前,大多数新加坡人的交际用语是方言,而课堂上、书面上接触的多是华语,“教育当局长久以来即在原则上决定华语和华文的标准全面向中国看齐。不但华语的读音以中国大陆发行的字典为标准,在文字改革方面也亦步亦趋,忠实仿效。”(郭振羽,1985)“新加坡在推行华语或中文教学、华语运动的时候涉及到语言标准的问题,我们也以中国的普通话作为我们的标准。”(周清海,1999)“新加坡的华文课本,语言方面向普通话靠拢。”(周清海,2009:62)也就是说,新加坡学校教育中教的是华语,然而,新加坡人在日常交际中说的却是方言。随着“讲华语运动”的开展,虽然大多数人改以华语作为口头交际用语,然而,相对于书面语,他们的口语表达势必有着更多的“不标准”的地方。如当下新加坡华人在口语交际中依然频繁地使用语气词“lah”、“leh”、“meh”、“hor”等,然而书面语中却很少见到这些。
研究当中如果依据口语则会看出新加坡华语有更多的与普通话不一致的地方,也就会得出更多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然而,学者在研究当中大多没有注意对口语和书面语进行区分,或单一依据一种语体研究得出所谓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或将来自两种语体的语料混杂在一起研究。
(四)缺乏对新加坡华语语法动态发展的研究和预测
新加坡华语由早期主要受方言的影响,变为目前主要受英语的影响,其所具有的语法特点势必发生一定的变化,这在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里再详细分析一下新加坡人使用“来得”的“比”字比较句的变化作为例证。陆俭明(2001)指出,新加坡华语中“比”字比较句中比较项与形容词之间往往用一个“来得”,做后面形容词的修饰语,普通话里没有这种用法,普通话里“他比谁都沉默、安静”,在新加坡华语中可以说成“他比谁都来得沉默、安静”。祝晓宏(2008)进而指出,新加坡华语中“‘来得’在比较句里用得非常普遍”,是“一种常规的比较结构”,“常常是用在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结构之前”,“也可以用在动词性结构之前”。然而,刘振平(2014b)的语料分析和抽样调查结果却表明,新加坡中学生和华文教师当下已经很少使用这种句式。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言环境的变化,新加坡华语语法是在不断发生变异的。就此而论,新加坡华语语法究竟会朝着什么方向发生变异,也就成为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然而,目前学界对新加坡华语语法现象的动态发展关注不够,缺乏系统探讨某一语法现象在新加坡华语中历时发展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六、结 语
新加坡华语作为现代汉语在新加坡地区的一种区域变体,早期主要受南方方言的影响,在语法上势必带有南方方言的特点,早期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将焦点主要集中在发掘和描述这些“南味”现象上。随着华文教学在新加坡变为单科教学,英语成为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和行政语言,新加坡华语更多地受到了英语的影响,新加坡华语语法受英语影响而形成的一些特点成为研究的焦点。然而,截止目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尚未确定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的内容,从而造成学者对哪些是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众说纷纭。这种情况下,选择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搜集有代表性的语料,建立新加坡华语语料库成为进一步深化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急需开展的工作。
新加坡华语口语长期以来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而“新加坡人接触的书面语,在新加坡建交以前,也不是中国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而是五四前后期的汉语书面语”(周清海,2002),所以,新加坡华语口语和书面语势必有着不同的特点,所以研究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必须注重所依据的语料的语体,至少应该将口语和书面语分开加以探讨。然而,目前的现状是学者对两种语体语法特点的差异缺乏必要的关注。
在新加坡华文教学成为学校里的单科教学、大多数学习者已经没有华语或方言基础的今天,新加坡华文教学已经逐渐蜕变为第二语言教学;由于英语是主要的教学媒介语、行政语言和大部分学习者日常交际语,当下的新加坡华语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英语的影响;又由于长期以来“新加坡的华文课本,语言方面向普通话靠拢。”(周清海,2009:62),普通话对新加坡华语也有较大的影响;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华语语法相对于之前主要受方言的影响,势必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然而,学界目前对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关注得不够,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
陈重瑜:《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特征》,刊于陈重瑜《华语研究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编印,1993年,第 328-391页。
陈重瑜:《新加坡华语语法特征》,《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崔娇阳:《新加坡小学生作文中的虚词特点》,刊于徐为民、何文潮《国际汉语教材的理念与教学实践研究——第十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6-431页。
崔娇阳:《新加坡小学生作文中方位结构的使用特点及偏误分析》,刊于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5-183页。
傅丽君:《新加坡华语与普通话常用名量词的对比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论文,2003年。
高 花、吴福焕:《新加坡小一学生华语语法偏误分析》,刊于谢育芬《华语作为二语与外语的教学——探索与实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9-311页。
高 茹、刘振平:《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中因材施教理念的注入与发展——新加坡教育政策报告书解读》,《外国教育研究》,2014年第3期。
郭振羽:《语言政策和语言计划》,刊于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第103-121页。
何丽娴:《新加坡华语中语气词的功能》,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论文,2003年。
黄淑盈:《新加坡华语中语气词leh之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论文,2006年。
黄秀爱:《新加坡华语助动词的语法特点》,《中国语文通讯》,1986年第3期。
江郁莹:《“给”字句探索:以台湾华语与新加坡华语的口语语料为例》,《国际汉语学报》,2013年第1期。
林素娥:《新加坡华语“懂”格式的华语特征》,《语言研究》,2012年第1期。
林素娥:《新加坡华语的句法特征及成因》,刊于陈晓锦、张双庆《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3-191页。
林万菁:《“多”与“多多”的用法及其变异问题》,刊于林万菁《汉语研究与华文教学论》,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第 154-163页。
林万菁:《从修辞的观点看非规范的“有”字句》,刊于林万菁《语言文字论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编印,1996年,第79-82页。
刘振平:《汉语语法在新加坡的变异及教学语法研究》,《汉语学习》,2016年第3期。
刘振平:《新加坡华文教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刘振平:《新加坡中学生使用汉语常用介词的特点与偏误》,《华文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陆俭明、张楚浩、钱 萍:《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南大中华语言文化学报》,1996年创刊号。
陆俭明:《新加坡华语句法特点及其规范问题(上)》,《海外华文教育》,2001年第4期。
陆俭明:《新加坡华语句法特点及其规范问题(下)》,《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1期。
潘秋平:《从方言接触和语法化看新加坡华语里的“跟”》,刊于吴福祥、崔希亮《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 247-283页。
尚国文、赵守辉:《新加坡华语的时间表达与规范》,《南开语言学刊》,2014年第1期。
尚国文:《新加坡华语中的数词及其相关表达》,《华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
吴英成:《从新加坡华语句法实况调查讨论华语句法规范化问题》,刊于新加坡华文研究会《新加坡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印,1990年,第118-123页。
吴英成:《关于华语语法教学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3期。
吴英成:《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吴英成:《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台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1985年。
萧国政:《新加坡华语虚词使用说异》,刊于深圳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深港澳语言研究所《双语双方言(六)》,香港:汉学出版社,1999年,第377-394页。
邢福义:《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方言》,2005年第2期。
徐 杰:《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
余耕文:《本地华语中的一些语尾助词》,《联合早报》,1984年8月25日。
余耕文:《本地华语中结果补语的特殊现象》,《联合早报》,1984年12月1日。
臧慕莲:《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八桂侨史》,1994年第3期。
张楚浩:《华语语法里的两个问题》,刊于新加坡文化研究会《普通话与方言》,新加坡:新加坡文化研究会编印,1985年,第 83-85页。
周清海:《变动中的语言》,新加坡:玲子传媒有限公司,2009年。
周清海:《论全球化环境下华语的规范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周清海:《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
周清海:《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与处理差异的对策》,《联合早报》,2006年3月21、23日。
周清海:《语言规划、语言教学与语言研究》,《联合早报》,1999年12月5日。
周小兵:《新加坡华语小说的语法特点》,刊于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双语双方言》,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9-230页。
朱淑美:《新加坡华语语法、词汇中的方言成分》,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论文,1996年。
祝晓宏:《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Analysis of Singapore Chinese Grammar Research
LIU Zhenp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Education,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Nanning 530001 China)
As a regional variantofmodern Chinese,Singapore Chinesewasmainly affected by the dialect of southern China and English.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darin and Singapore Chinese,whose features and sources are always the focus of the academic field.Anyway,both the official circle and academic field have not clearly defined the contents of Singapore Chinese grammar system even by now.So,it is difficult for the scholars to confirm the grammar’s features.It is the very work for us at present tomake a social investigation among representative people,collect typical linguistic data,and then establish amassive corpus of Singapore Chinese.The changes of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 led to the evolution of Singapore Chinese grammar.However,the research on that is stillweak.
Singapore Chinese;grammar;present situation;problems
H04
A
2221-9056(2017)09-1180-08
10.14095/j.cnki.oce.2017.09.002
2017-05-26
刘振平,广西师范学院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语音与国际汉语教学。Email:liuzhenping79@sina.com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语竞争中的中国语言形象建构研究”(14XYY020);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面向东盟的对外汉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2JGZ122)。本文写作过程中曾蒙杨绪明教授指教,谨致谢忱,文中不妥之处概由本人负责。感谢《海外华文教育》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中不妥之处概由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