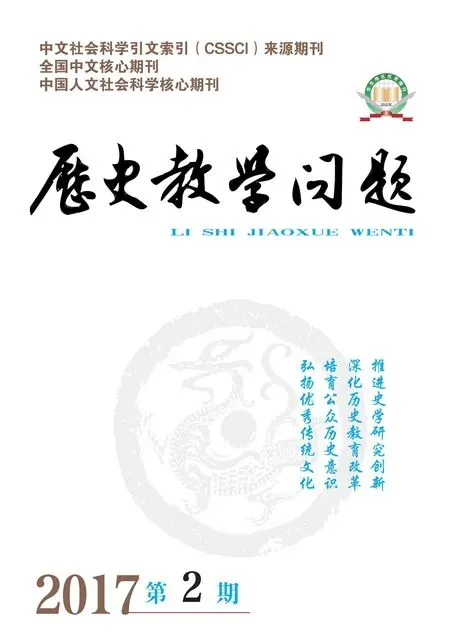元代朱熹《家礼》论略
刘舫
元代朱熹《家礼》论略
刘舫
朱熹《家礼》在中国礼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相比于《家礼》在宋代和明代的清晰轨迹,元代的《家礼》传播和影响并不为学者重视。但细究起来,如果没有经过元代特殊社会环境的发酵,《家礼》无法由私家之礼演变为国家之礼。本文试图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考察《家礼》的传播和汉人士庶的服膺情况,勾勒宋明之间《家礼》流传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家礼》逐渐成为“国礼”的深层原因。
朱熹;家礼;元代;礼制;汉文化
朱熹《家礼》在中国礼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持续至今,而且对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意义也非同一般,此点已被反复提及。①杨志刚:《论“朱子家礼”及其影响》,《朱子学刊》1994年第1辑;汤勤福:《朱熹〈家礼〉的真伪及对社会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11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美华:《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相比于《家礼》在宋代和明代的清晰轨迹,元代的《家礼》传播和影响并不为学者重视,这似乎也无碍于其由南宋的一家之言突然擢升为明初颁行全国的《性理大全》中的重要文本。但细究起来,如果没有经过元代特殊社会环境的发酵,《家礼》无法由私家之礼演变为国家之礼,而以“礼下庶人”的大势所趋来理解这一段历史似乎并不充分。在蒙古人统治的元代,未借助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家礼》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获得众多汉人士庶的服膺,是元代社会中汉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侧面,因此,宋明之间《家礼》的发展非常值得深入探讨。
一、元初《家礼》的北传
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于乾道六年(1190)居母丧期间,参酌古今仪制,撰成《家礼》。②杨复《家礼序》云:“故冠礼则多取司马氏;昏礼则参诸司马氏、程氏;丧礼本之司马氏,后又以高氏为最善;及论祔、迁,则取横渠遗命;治丧,则以《书仪》疏略而用《仪礼》;祭礼兼用司马氏、程氏,而先后所见又有不同。节祠则以韩魏公所行者为法。”(胡庚等:《性理大全》,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1301页)其中“高氏”指宋高闶,字抑崇,号息斋,浙江鄞县人。绍兴元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高闶……集《厚终礼》一编行于世,朱文公《家礼》多用之”。(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四《人物考》,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320页)《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作“高闶,《送终礼》一卷”。(中华书局,1977年,第5134页)现存《家礼》最早的宋刻本是淳祐五年(1245)杨复注附录本,并附诸图。杨复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师从朱熹弟子、女婿黄榦,黄榦在《家礼》跋文中指出,《家礼》所述“无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当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见之明,信之笃,守之固,礼教之行,庶乎有望矣”。③黄榦:《书晦庵先生〈家礼〉后》,《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50页。《家礼》共五卷,第一卷通礼,包括祠堂、深衣制度、司马氏居家杂仪;第二至第五卷,分别为冠、昏、丧、祭礼。继杨复之后,又有刘垓孙增注,刘璋补注,元代将三人注合为《文公家礼集注》一并刊行,增加附图,多次翻刻。而元代流传的《家礼》影响更大的或是黄瑞节《朱子成书》中的一种。①《朱子成书》共10卷,汇集了不包括《四书》在内的朱熹和蔡元定对历代典籍的注本共10种。其中的《家礼》刊刻于至正元年(1341),全称《纂图集注文公家礼》,不分卷,前有庐陵刘将孙于大德乙巳(1305年)序文,书中大字为朱熹本文,附小字为黄瑞节解说。首列由黄瑞节编定的礼图19幅,内容为家庙、祠堂、深衣、冠礼、昏礼亲迎、丧礼、丧服、丧仪、祭祀、大小宗等。明代《性理大全》直接采用黄瑞节本为《家礼》蓝本。
《家礼》由宋入元,就目前已知最早的《家礼》刊刻时间到该书被明代官方收入《性理大全》的百多年间,②“赵君师恕之宰余杭也,乃取是书锓诸木,以广其传”。(黄榦:《书晦庵先生〈家礼〉后》,《朱子全书》第7册,第949-950页)是年为南宋嘉定九年(1216)。主要时间是中原被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如果说南宋的士大夫们已经从实践层面为士庶礼仪准备好了行动指南的话,那么真正的推广和流行,尤其是在北方的普及,可以说是在元代完成的,而这一段历史常常在“宋明”这一框架下被悬置,有待进一步挖掘。
宋金对峙时期,金朝的汉人在长期的异族统治之下,风俗胡化显著,南宋人甚至视之非我族类,南宋人叶顒曾感叹“国仇未复,陵寝未还,中原士民,日夜企鸾舆之返。顾乃尚胡服,习夷乐,非孟子用夏变夷之意”。③杨万里:《宋故尚书左仆射赠少保叶公行状》,《诚斋集》卷一一九,《四部丛刊》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然而,南方汉人的习俗同样不胫而走,影响北方。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正式颁令:“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④《金史》卷八《世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页。又如,宋辽金时代,无论是北方民族统辖的辽、金,还是汉人的宋,火葬的习俗都非常普遍。⑤参见马强才、姚永辉《近六十年宋辽西夏金火葬研究综述与反思》,《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火葬的习俗最早见于中原以外的偏远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墨子》中就有“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⑥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六《节葬下》,中华书局,1993年,第268页。《周书》载,突厥人死后,“取亡者所乘马及经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⑦《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中华书局,1971年,第910页。《北史》载,契丹人死后,“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及收其骨而焚之”。⑧《北史》卷九四《契丹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8页。这与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与风俗习惯有关,而到了北宋时,“河东人众而地狭,民家有丧事,虽至亲,悉燔爇取骨烬,寄僧舍,以至积久弃捐乃已,习以为俗”。⑨江少虞:《禁焚尸》,《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13页。南宋时,“火葬之惨日炽,事关风化,理宜禁止。望申严法禁,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⑩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2933页。为此宋廷下令严禁火葬,并载入刑典,但从实际情况来说,人们选择火葬的习惯似乎并没有改观。直到元代,仍有士大夫指出:“切惟送终,人子之大事,今见中都风俗薄恶,于丧祭之礼有亟当纠正者,如父母之丧,例皆焚烧,以为当然,习既成风,恬不知痛……其在汉民,断不可训。”⑪王恽:《论中都丧祭礼薄事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乌台笔补》,《四部丛刊》影印本。至元十五年(1279)朝廷还明令“禁约焚尸”。⑫陈高华、张帆、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062页。以上情况说明,在士庶的层面,人们不自觉地从众好尚,风俗的浸染不受夷夏或敌国观念的影响,而这正是礼仪规范缺位的表现。俗因自然而成,而礼则伴随着教化,寓观念于中,以仪践履。
蒙古人南下,姚枢(1201-1278)在随军南征时救出被誉为理学北传始祖的南宋耆儒赵复,“尽出程、朱二子性理之书付公”。⑬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中华书局,1996年,第156页。其实,金人并非完全不知程朱之学,金代进士王遵古“潜心伊洛之学”,⑭元好问:《王黄华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影印本。王若虚遍读宋儒著述,撰《论语辩惑》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进行逐条辩驳。只能说在赵复之前,程朱之学没有在北方遇到强而有力的知音而已。姚枢不仅深为其学说倾倒,更致力于普及其中的“日常工夫”。他因不满于燕京行台花剌子牙鲁瓦赤惟事货赂,一度辞去燕京行台郎中,携家眷归隐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自板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还于“城中置私庙,奉祠四世”,⑮《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第156-157页。并作别室奉孔子及周敦颐等人之像,⑯《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711页。身体力行《家礼》仪范,在当时北方的汉族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像他这样自觉以《家礼》行事的元代汉人士大夫并不少。陕西高陵人杨恭懿(1224-1294),“书无不读,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父没,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居丧尽礼”。①《元史》卷一六四《杨恭懿传》,第3841页。受到他的影响,关中地区的丧葬大多符合礼仪。②“盖关中土厚俗敦,太史杨文康公恭家世为儒,冠昏丧祭,一遵礼书……公(吕端善曾孙)之治丧,稽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及杨文康公已行故实,使古人送终之正复见于世。故关中丧葬多合乎礼者,由公等一二儒家为之倡也”。(苏天爵:《元故翰林侍读学士赠陕西行省参政知事吕文穆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七,中华书局,1997年,第95-96页)这里的“礼仪”应该就是朱熹《家礼》中的丧礼仪制。又如,忽必烈朝曾受诏“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并担任过“礼部侍郎兼侍仪司事”的重臣赵秉温(1222-1293),③《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5页。其后人多在朝中为官,赵氏家族十分兴盛,至其孙赵时勉主持家业的时候,“岁时伏腊昏丧,君承之皆有法”,但他仍然感叹“近世之士贵为公卿而享祀其祖礼同庶人”,于是“乃稽司马氏、朱氏《祭仪》《家礼》,为祠堂于正寝之侧,凡丧祭昏冠议而行之,乡郡闻家或从而化”。④苏天爵:《故曹州定陶县尹赵君墓碣铭》,《滋溪文稿》卷一八,第290页。赵秉温之后人如此行为,不能不说受到赵秉温的影响。以上三位元朝汉臣在接触程朱理学后即遵行《家礼》,认可宋人损益过的礼仪规范,并导化乡人,可见蒙古人统治下的北方汉人社会需要符合儒家思想的礼仪规范。
当然,朱熹《家礼》在元代并非独树一帜,坊间还可以找到多种家礼,如元代实用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说到墓祭时称:“按季氏《居家必用》初卷略载文公《家礼》,其意甚善。又按秦氏本不载,别载孙氏《荐飨仪范》,今观文公《家礼》,非可妄损益。近世士大夫家能行之者,详见本书全帙,于祭礼一条,孙氏《家仪》亦可参择用之,故并存于后。”⑤《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乙集《祭礼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7页。显然,当时可以见到的家礼类书籍除文公《家礼》外,至少还有季氏《居家必用》、秦氏家仪、孙氏《荐飨仪范》等等。⑥元代与朱熹《家礼》有相似内容者,常见于族规、家训、家范、家谱等著作。因此,也有士大夫对《家礼》的仪制提出疑议,金末元初名士杨奂(1186-1255)在写给姚枢的信中说:“朱文公,后宋人也,建炎南渡,庙社之礼一荡,就有故老或郁郁下僚无所见于世,此说在《中庸或问》中略见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于神主于石室皆不及也。《家礼》所载神主样式亦非。奂三十时入汴梁,得宫室庙社法度于一故老处……夫礼者,制度名数之所寓也,不有所据必有所见,文公所述未见其所据,当以奂之所目睹者为庙之定制。”⑦杨奂:《与姚公茂书》,《元文类》卷三七,中华书局,1958年,第490-491页。显然,杨奂评价仪制的标准是亲眼所见的前朝故遗,不同意朱熹存礼义用时宜的观念,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对古礼旧制有所研究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其实是对朱熹所代表的南宋之学的革新风格存有质疑。
综上,《家礼》作为程朱理学的一部分,其影响已经逸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元初的汉人士大夫阶层从了解、质疑、信服、遵行,逐渐开始思考和实践《家礼》中各项礼仪。
二、元中期《家礼》的“上升”
元中期之后,随着程朱理学地位的上升,自然朱熹所著各种著述也广受重视,《家礼》当然也被看重,更为流行。大致说来,元仁宗皇庆三年(1313),元朝中书省奏准科举“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⑧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五《科举》“皇庆二年十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页。至延祐二年(1315)正式开科取士,基本确立了程朱理学为官学的地位。《家礼》的流行还被认为是始于宋代的“礼下庶人”的重要表征。有学者指出:“将社会成员区分为皇帝和宗室、品官、庶人三大等级。这一等级结构至少在(宋)仁宗朝即已显露……由宋代下迄近代,‘庶人’‘庶民’‘士庶’‘民庶’这几个概念大抵相通,表示不居官位的平民百姓。”⑨杨志刚:《“礼下庶人”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官方颁布《政和五礼新仪》,“许士庶就问新仪”,设有庶人婚、冠、丧,首次针对士庶阶层而制礼。为明朝继承,《明集礼》有“士庶冠礼”“庶人婚礼”“庶人丧礼”。
另一方面,自唐代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礼记》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中“礼”的元典,北宋科举虽经过多次改革,但《仪礼》式微,习者寥寥,专治《仪礼》者更少。宋元期间,《仪礼》研究撰著极少,屈指可数的只有李如圭《仪礼集释》、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吴澄《仪礼考证》、敖继公《仪礼集说》、汪克宽《经礼补逸》等。《仪礼》所载士礼多已佶聱难懂,而《礼记》所论“礼义”却令人心向往之,《家礼》的兴起恰在此时填补了这一空白。在科举道断、仕宦路绝的元代,绝大多数汉人已几无到达较高品官阶层的可能,能做的也大多只是地方儒学的教员之类的小官,于是他们转而研讨礼经,服膺《家礼》更是为了上绍圣贤,取得汉文化的身份认同。其实,“礼为有知制”,①《白虎通》卷四《五刑》,中华书局,1985年,第245页。《家礼》的受众不是“庶人”,而是包括了朝廷重臣在内的汉族读书人,他们并未过分强调礼所讲究的等差,也不在意礼在官民施行中的差异,而是将礼的核心问题从“辨上下”,变成“别夷夏”。就这个意义上说,《家礼》受众的知识水平是上升的,许多元代著名儒士遵行《家礼》仪制,并积极向民间推广。如吴澄(1249-1333)为避兵乱,奉亲隐居布水谷,父亲去世后,“居丧治葬率循古制,参以《书仪》、《家礼》之行,乡党姻戚亦多依效,不用浮屠,里俗或讥之,则以为解”。②危素:《临川吴文正公年谱》“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条,《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0页。湖州路学正潘著(1308-1358),才华名闻京师,因秉性耿直不愿被罗致大臣馆下,考铜陵教谕,教子弟数年,因丁忧去职,“居丧悉遵朱子《家礼》,屏浮屠不用,郡人贤之”。③贡师泰:《湖州路儒学正潘君墓志铭》,《玩斋集》卷一○,明嘉靖刻本。于此可见元代学者的治礼风格。
当然,丧葬礼中使用佛道教仪在当时非常普遍,《家礼》还担当着辟二氏的角色。时人指出“近世焚楮帛及下里伪物,唐以前无之,盖出于元(玄)宗时王屿辈,牵合寓马之义。数百年间,俚俗相师习以为常。至于祀上帝亦有用之者,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愚众。天固不可欺,乃自欺耳。士大夫从而欺其先是,以祖考为无知也……及吾祭祀时,一遵《家礼》,凡冥钱寓马皆斥去”。④孔齐:《楮帛伪物》,《静斋至正直记》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元末参与负责宋、辽、金三史撰述的危素(1303-1372)为邵阳县丞陈颐孙题写家堂记时,称赞陈家“祭祀用朱文公《家礼》,参之以司马文正公《书仪》……不奉神鬼、浮屠,不用巫觋”。⑤危素:《陈氏尚德堂记》,《危学士全集》卷七,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在遵行《家礼》的记载中,常以丧礼仪制不用佛老来显示《家礼》丧仪的与众不同,表明使用《家礼》仪制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新的做法,显示出遵礼者试图以礼变俗的用心,希望唤醒“日用而不知”的士庶民众重新回归到儒家伦常的礼仪规范中去。
这里,再从一些宋元交替时期隐居不仕者来看他们对《家礼》的态度。与许衡齐名的西蜀名士王西轩先生(1219-1292),终身不仕,“丁母忧,水浆不入口者七日,柴毁骨立,父有嘻其甚矣之叹,作诗劝之。及丁父忧,年几五十矣,其哀毁有过,自初丧至葬祭,一遵文公《家礼》,虽期功之丧,亦必自尽而不苟,亲党及乡里有丧者,必就正而取法焉”。⑥蒲道源:《青渠王先生墓志铭》,《闲居丛稿》卷二四,元至正刻本。南宋宝章阁大学士冷应徵之子冷正叔(1254-1322),元初以服父丧去官隐居,“居丧校杨氏附注《家礼》,可传于世事”。⑦刘岳申:《有元隐君子冷正叔桐乡阡碣》,《申斋集》卷九,《四库全书》本。元代文学家陆文圭(1256-1340)隐居江阴东乡,他为父亲陆垕立传中写道:“称事丧祭,一用朱子《家礼》,不谄鬼神,不佞老佛。”⑧陆文圭:《陆庄简公家传》,《墙东类稿》卷一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609页。元代的隐士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养,在元初宽松的文化气氛中,宋代禅宗和金元道教迭兴,汉族知识分子隐逸山林,却表现出异常敏感的文化收缩趋向,对他们来说已无“国”可言,只有“家”仍存在,以“治家”曲折表达“平天下”的政治意愿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心态。元人欧阳玄说:“惟大姓其祖必有德,非德无以蕃,无以著,无以久,久则我后人念之,宜也,念之念之,奉其烝尝云乎哉,行其揖让云乎哉。思其人必绳其武,食其德必笃其庆,父诏其子,兄诏其弟,以诗书礼乐为教,以孝弟忠信为行,达则泽其民,穷则善其身,使国人称愿之曰,幸哉。”⑨欧阳玄:《秀川罗氏祠堂记》,《圭斋文集》卷五,《四部丛刊》影印本。儒家《大学》的“三纲八目”和朱熹《家礼》的日常礼仪恰好配成了本末俱足的教义和戒律,俨然成为可与释道鼎足的汉地“教门”,将异族统治下的汉族知识分子摄归其中,而他们的做法与元廷为巩固政权而推行尊儒的大政相一致,在客观上促进了《家礼》的深入民心。
与知识分子强烈的自觉意识形成对比的是真正的庶民,他们随俗而生,没有与异族区隔的诉求,经济上也有所拮据,所以相当一部分人也就不会严格执行《家礼》的礼制,为此吴澄感叹:“古之卿大夫、士,祭不设主。庶士之庙一,適士之庙二,卿大夫亦止一昭一穆,与太祖而三。今也下达于庶人,通享四代,又有神主。斯二者与古诸侯无异,其礼不为不隆,既简且便,而流俗犹莫之行也。”①吴澄:《豫章甘氏祠堂后记》,《吴文正集》卷二五,《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440-441页。可见,《家礼》在元中期真正赢得了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可,在这个意义上说,《家礼》的影响力或说地位是大为“上升”的。
三、元季:国制家礼的呼之欲出
朱熹《家礼》在元初仅被作为“汉儿人旧来体例”来看待,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如早在至元初年,婚礼礼制基本确定,《通制条格》载:“至元八年(1271)九月,尚书省礼部呈:契勘人伦之道,婚姻为大。即今聘财筵会,已有定例外,据拜门一节,系女真风俗,遍行合属革去外,据汉儿人旧来体例,照得朱文公《家礼》内婚礼,酌古准今,拟到各项事理,都省议得:登车乘马设次之礼,贫家不能办者,从其所欲外,据其余事理,依准所拟。”②《通制条格》,第36页。到了元代后期,受惠于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家礼》在民间迅速普及开来。清人曾指出:“今世宗祠,合族数十百主咸在,似起于元之季世。”③张履:《答陈仲虎杂论祭礼书》,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〇,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536页。这里所说“宗祠”之制,正是朱熹絜矩众礼家之长首创的祠堂,置于《家礼》卷首。④按照《周礼·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随着世族门阀社会结构的瓦解,家庙之制到五代时已荡然无存,北宋司马光《书仪》的影堂即是为恢复家庙而设计的,朱熹在影堂的基础上创制祠堂,不仅行使祭祀祖先的职能,还使之成为整个家族活动的中心,冠婚丧祭中的“告庙”环节要在祠堂里进行,主人和主妇出入必告、正朔参拜、俗节献食物,并置祭田以给祭用。祠堂之制并非要恢复周礼,所以名称不著“庙”字。朱熹在《家礼》自注中明确表示:“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⑤《家礼》卷一《通礼》,《朱子全书》第7册,第875页,第875页。士庶虽贱,但只要略懂得儒家伦常,在精神上都需要安放自己与先人的关系,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人伦之一,在民间流行的释道教仪无法取得他们认同的时候,祠堂之制既不泥古,所采用的都是时宜之礼,又能体现“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⑥《家礼》卷一《通礼》,《朱子全书》第7册,第875页,第875页。真正地体现了得“义”起“仪”的制礼精髓,因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事亲祭祖的依据。传刘因之学的离石人(今山西吕梁)安熙(1268-1311)出自河北真定安氏大族,于“至大三年(1310),考《家礼》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⑦袁桷:《安先生墓表》,《元文类》卷五六,第817页。诗人戴良(1317-1383)出自世居浙江鄞县的戴氏大族,“乃营祠堂正之东……中设四龕,以奉宗子之四世……四时祭飨,略如朱文公著仪式,而参诸世守之旧”。⑧戴良:《戴氏祠堂记》,《九灵山房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页。南宋大儒谢上蔡后人谢理,元顺帝时官至枢密院都事,总制余姚,其兄弟共五人,合家人百余口共居,“凡冠昏丧祭悉遵紫阳《家礼》”。⑨贡师泰:《谢氏家训序》,《玩斋集》卷六,明嘉靖刻本。
面对这样的形势,当政者越来越清楚礼制的重要性,朝廷已经意识到颁定系统的符合汉人礼俗的礼规是十分必要的,是有利于维护元朝统治的不断深入。元代后期首次以法令形式规定五服令,⑩“五服著令,见于《通制》、《国朝典章》、《至元新格》”。(吴黻:《丹墀独对策科大成》卷一五《刑书》。转引自《〈元典章·礼部〉校定和译注(三)》,京都《东方学报》2008年第83册,第239页)“至治以来,《通制》成书,乃着五服于令”。(《经世大典·宪典·名例》“五服”条,《元文类》卷四二,第606页)并刊布五服图,⑪《元典章》卷三〇《丧礼》载《本宗五服之图》等6幅丧服图,前4幅与朱熹《家礼》所附家礼图一致,后2幅也是《家礼》相关内容的表格化。以图表明示丧礼中的五服关系,五服图始创于《家礼注》的作者杨复,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杨复《仪礼图》:“尚皆依《经》绘象,约举大端,可粗见古礼之梗概,于学者不为无裨。一二舛漏,谅其创始之难工可也。”(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中华书局,1965年,第160页)与朱熹的礼学传承明显有着直接的关系。撰成于至顺元年(1330)的《经世大典》云:“昔者先王因亲立教,以道民厚,由是服制兴焉。法家者用之以定轻重,其来尚矣。然有以服论而从重者,诸杀伤奸私是也。有以服论而从轻者,诸盗同属财是也。大要不越于礼与情而已。服重则礼严,故悖礼之至,从重典。服近则情亲,故原情之至,从恕法。知斯二者,则知以服制刑之意矣。”①《经世大典·宪典·名例》“五服”条,第606页。五服不仅是丧葬礼仪的依据,更是经国序民的根本原则,维护服制对治国来说无疑可以起到持领振裘的效果。于是有民间人士顺势而为,希望通过元廷的认定来进一步推广儒家礼仪。嘉兴学者龚端礼继承家学,撰成《五服图解》一卷后自费付梓,至治三年(1323)嘉兴路儒学耆宿叶知本为之作序,嘉其民彝世教之功,次年泰定元年(1324)由嘉兴路呈浙江省移咨中书省,称“庶使人民慎于孝礼,尽其诚厚之道,实非小补”。为此,龚氏对该书进行润色修改并重印,希望得到朝廷重视。龚氏在《图原》一节中说:“愚思此集乃当今官民必用之文,复虑世人不克周晓,故尽心穷礼,按古增划《易晓之图》,重别印造成集,具解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进呈朝廷裁择。”②龚端礼:《五服图解》,《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金元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877-878页。正如龚氏增制礼图的命名,他认为“易晓”是决定五服之礼能否取得官方认可的关键所在。
而朝廷对朱熹《家礼》又有另一番考量。至正年间执掌国子学的吴师道(1283-1344),在《国学策问》说:“近世司马公《书仪》,朱子《家礼》,号为适古今之宜,好礼之家或所遵用,然不免于讪笑。非出朝廷著令,使通习之,殆于不可然。《家礼》后出,颇采《书仪》,《书仪》所有或《家礼》所无,又窃闻《家礼》乃未定之本,为人所窃去,未及修补,今所行者是也。然则二书当考而损益之欤,或止用其一欤,《家礼》之外尚有可议者欤。谓宜定为式程,颁之天下,使民习于耳目而不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其不在兹欤。”③吴师道:《国学策问十四首》之三十五,《礼部集》卷一九,《吴师道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01页。民间士庶自发遵用朱熹《家礼》等儒家日常礼规在官方看来“不免于讪笑”,原因在于此礼“非出朝廷著令”,官方并不打算承认任何来自南宋学者所制定的民间礼仪,质疑是否出自朱熹亲定可以看作是一个借口。又如,顺帝时拜集贤侍读学士的同恕指出:“详考晦庵《家礼》,亦只以温公《书仪》为据。小祥条内注云:‘礼既虞卒哭,则有受服。’今人无受服及练服,故《家礼》亦不言练服制度。今士大夫家,一遵《家礼》,小祥但以稍细熟布改为一冠、去首绖,衰服则去负版、辟领衰,如此而已。首绖一除无服再用,盖去古已远,岂能一一尽如礼经。”④同恕:《答王茂先经历论丧服书》,《榘庵集》卷四,《四库全书》本。作为朝廷经筵侍读官,同样对朱熹《家礼》有所保留。可见,像吴师道、同恕这样身居高位的汉臣提出应该由官方来担当择从众家之说的角色,而不是简单地独尊一家。
正如有学者指出:“朱熹的《家礼》经历了许多的变化。几乎在它刚问世的时候,那些将《家礼》作为自我修养指南的学者就认为补充是非常必要的。他们写下评语解释礼仪实践的初衷和朱熹损益的原因。相较而言,朱熹编撰《家礼》的意图更应该被看作为鼓励庶人行礼提供实用指导,而不仅仅是对古礼的简化和删削。”⑤Patricia Buckley Ebrey,Chu Hsi's Family Rituals: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Weddings,Funerals,and Ancestral Ri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1,pp.xiii.以《家礼》为蓝本的各种家规、家范、家仪等等被元代的众多士庶家族演习和传承,如元武宗旌表居于浙江浦江感德乡郑氏家族为“义门”,从南宋初年开始同族人开始共爨。元顺帝时,六世孙郑文嗣从弟郑文融继主家事,“冠婚丧葬,必稽朱熹《家礼》而行执”,⑥《元史》卷一九七《郑文嗣传》,第4452页。定立族规五十八条,是为郑氏《家范》,后增补为一百六十八条,在明代刊行于世。⑦《明史》卷二九六《郑濂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585页。《义门郑氏家仪》为元末明初郑氏八世孙郑泳等根据《周礼》、朱熹《家礼》和郑氏传统家仪,顺应浦江地方风俗编制而成。从体例上看,与《家礼》一样分为五部分。可见,尽管朱熹《家礼》在元代并未获得政府认同而成为“国礼”,它传播的意义也并不在于士庶家族能严遵谨循其中的每一项礼仪,但是人们普遍地意识到议定详细的家规礼范是凝聚族人和彰显家风的重要手段,并且因时因地以制宜的做法也是被肯定的,显然,《家礼》可以说是没有获得元政府颁布的但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为人们普遍遵从的“国礼”。其实,由官方来颁定一部士庶礼规呼之欲出,只是时间问题,这一过程到明朝初年便水到渠成了。
综上所述,南宋朱熹《家礼》在元代经历了北传,为众多汉族知识分子接受和服膺,最终推动明廷于“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⑧《明史》卷四七《礼一》,第1224页。说明《家礼》在元代的普及已经逸出了传统经学的范畴,无论是基于《仪礼》还是朱熹《仪礼经传通释》的对《家礼》的批评,还是对其是否出自朱熹所作的质疑都不足以揭示《家礼》的意义所在。在元代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它充当了儒学的“戒律”,一定程度上成为元代汉族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寄托,是外族统治下汉文化自我保护的凭依,这种自觉性在儒学史或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家礼》虽脱胎于上古礼经,但它最终是经由宋元明三代所有遵礼者共同参酌时宜完成的,元代知识分子在朱熹《家礼》前贵贱同仪,在政治的边缘自觉地维护和创造汉文化的价值。因此《家礼》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本,而是一段体现着礼以时变的历史。
(责任编辑:李孝迁)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2&ZD134)阶段性成果。
刘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邮编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