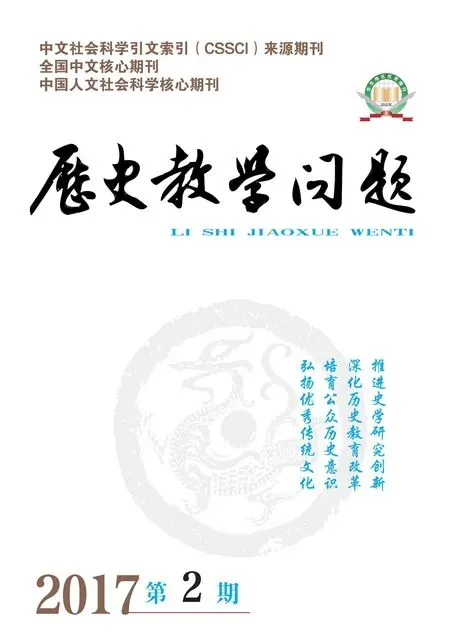二十年宿怨:孙诒让与陈虬
——从温州戊戌府试打人案谈起
邱林
二十年宿怨:孙诒让与陈虬
——从温州戊戌府试打人案谈起
邱林
1898年7月温州府试开考之际,因妹夫黄泽中应试一事陈黻宸在考棚外殴打廪生彭某,事件后来扩大为持续半年多的诉讼案,黄体芳、孙诒让、陈虬等也受到牵连。为此孙诒让对非直接当事人陈虬大加斥责,不过这与其说是针对打人案,不如说是孙、陈之间近二十年宿怨的总爆发。同在瑞安小城的孙诒让与陈虬,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几乎都保持着不相往来的敌对状态。孙诒让对陈虬颇有偏见,陈虬也因狂傲不羁的个性饱受挫折,悲愤一生。
温州戊戌府试;孙诒让;陈虬;陈黻宸;宋恕
晚清时候温州瑞安的孙衣言、孙锵鸣及黄体立、黄体芳兄弟接连进士及第,风气波及,温州地区开始呈现人才荟萃的局面。除了三孙(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五黄(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之外,陈虬、宋恕、陈黻宸还并称为“东瓯三杰”。近年来,随着温州地方文史资料和“温州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有关温州地区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其中有关温州学人孙诒让与陈虬之间近二十年的宿怨也有人论及,比如俞雄《孙诒让传论》一书提及孙诒让、黄体芳与陈虬、陈黻宸的矛盾,但是他低估了温州维新人物之间存在的对立情况,因而作出孙诒让是当地维新人物群中“理所当然的领军人物”这一与事实不符的结论。①俞雄:《孙诒让传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一书的第五章展现“布衣士绅”与地方大族的对立,其中温州戊戌府试打人案就是其中表现之一。②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不过,在具体史实的叙述和孙诒让、陈虬的关系论述上,有些地方值得推敲。徐佳贵在硕士论文中对甲午之后孙诒让与陈虬在文教事业方面的对立和竞争也有所提及。③徐佳贵:《地方士人与晚清地方教育转型——以浙江瑞安为个案的考察》,复旦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32页。不过,总体来说温州戊戌府试打人案的史实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本文即从这一事件入手,进而梳理孙诒让与陈虬近二十年的恩怨,最后试图分析影响两人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对陈虬的治学和个性进行简单评价。
一、温州戊戌府试打人案
1898年温州府试开考在即,送考的陈黻宸却在考棚外与人发生肢体冲突,此事后来不断发酵并扩大成诉讼案,受到牵连的人还包括黄体芳、孙诒让、陈虬等,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和解。对此,当年9月15日孙诒让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做了详细叙述,随后又在另外两封信中告知此事的最新进展。此外,10月27日叶瀚向宋恕“面询陈介石孝廉与孙仲颂主事结讼情形”,④叶瀚(1861-1936),字浩吾,余杭人,1895年曾在上海与汪康年创办《蒙学报》。为此,宋恕遵照嘱托分条详述,写成《陈事节略》,并于11月初二日交给他。①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941页。
不过,孙诒让和宋恕两人在事件的起因、直接后果、扩大化的原因等方面歧异甚多。对于打人事件的起因和直接后果,孙诒让说:“介石妹婿黄姓者祖父县役,例不得考,介石志三为求温守王琛违例收考,众廪与阖邑童生阻之,介石率利济医院友直入考棚,拉廪生赵姓痛殴之几死。”②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四》(1898年10月29日),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庼遗文》,中华书局,2013年,第360页,第360-361页,第362页,第360页。宋恕则这样讲:“介石妹夫黄姓文童本年应府试时,挨、认均已画押。廪生彭姓向之强借不遂,乃指称其祖曾充县役,临场抢卷殴童。介石送考目睹,与之互殴,多人劝散,两无稍伤。”③宋恕:《致叶浩吾书》(1898年12月13日),《宋恕集》,第595页,第595页,第595页。暂且不论冲突的真实起因,孙、宋两人在基本事实的叙述上就有明显出入,是痛殴几死还是两无稍伤,被打者为赵姓还是彭姓,两人的说法大相径庭。孙诒让的叙述时间是9月份,宋恕的陈述在11月,两人应当都不是事件的目击者,对打人事件的了解也只能是来自他人转述。
幸好当日同样送考的张棡,在7月初六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目睹到的情形:“是晚三更送本邑诸生进场。时在城有库房黄寿浩之侄名泽中应试,童试中人均谓其伊祖充县役,身家不清,不容应试,而泽中之妻兄则陈孝廉介石也。介石恃势力,且谓人攻讦无据,临场时身自送考,不料府尊点名时,泽中卷已为廪生彭镜淮抽去不给,而泽中胆敢在府尊前不服稽查,与介石诸人公然用武,竟将彭某拖出凶殴,幸提调永嘉县饬人救护,未获重伤。”④《张棡日记》(1898年8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5-46页,第45-46页。张棡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诸生参加府试的时间为7月初;陈黻宸妹夫“黄姓”名为黄泽中,为黄寿浩之侄,被打者为彭镜淮而非“赵姓”;彭姓“未获重伤”,而非“痛殴几死”。作为在场目击者且没有利害关系,张棡的叙述应该基本可信。
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黄体芳、孙诒让、陈虬等多人又先后卷入这一事件。对于事件的演变,孙诒让和宋恕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孙诒让说:“黄漱兰丈与赵略有姻连,颇斥其非,而志三为介石作书致黄丈,语极狂妄,以是士论不平,阖邑廪、童同攻之,弟为执矛焉。”⑤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四》(1898年10月29日),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庼遗文》,中华书局,2013年,第360页,第360-361页,第362页,第360页。宋恕则说:“而彭姓知介石与通政及仲容有憾,遂激怒仲容出面呈控介石,又妄称黄姓之钱多以涎通政。通政谴人连召黄姓之伯父至,授意献贿,而渠伯父不能领略微言,通政疑为介石所阻,则大怒,遂致函藩、学诸宪请革介石……”⑥宋恕:《致叶浩吾书》(1898年12月13日),《宋恕集》,第595页,第595页,第595页。孙诒让提及黄体芳与被打方的姻亲关系,宋恕则认为是旧怨和借机谋利未遂促使黄体芳把事件扩大。总之,黄体芳是打人事件升级的关键人物。黄体芳为同治二年(1863)进士,曾任江苏学政、兵部左侍郎、通政使等职,儿子黄绍箕为张之洞侄女婿。因此,在瑞安小城黄家颇有势力。此案还牵扯到黄体芳对陈黻宸和陈虬的旧怨,⑦“介石与通政结怨缘由”详见宋恕:《致叶浩吾书》(1898年12月13日),《宋恕集》,第594页。事情比孙诒让想象的错综复杂得多。后来孙诒让在致信汪康年时也说:“敝里讼事未已……至于事变离奇,不可喻度,他日溃决,未能知其所止。”⑧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四》(1898年10月29日),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庼遗文》,中华书局,2013年,第360页,第360-361页,第362页,第360页。
下面我们回头来探究黄泽中应考是否违规,这正是打人事件发生的导火索。对此孙诒让说:“黄姓祖父县役,例不得考,温守王琛违例收考”;⑨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四》(1898年10月29日),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庼遗文》,中华书局,2013年,第360页,第360-361页,第362页,第360页。宋恕说:“廪生彭姓向之强借不遂,乃指称其祖曾充县役”;⑩宋恕:《致叶浩吾书》(1898年12月13日),《宋恕集》,第595页,第595页,第595页。张棡的说法是:“童试中人均谓其伊祖充县役,身家不清,不容应试……”⑪《张棡日记》(1898年8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5-46页,第45-46页。黄姓祖父是否曾充县役,黄泽中是否身家不清,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三年后陈黻宸为了让黄泽中再次应试而写给弟弟和知府王琛的信,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和想象。
尽管妹夫戊戌之年应试引发了冲突和诉讼,陈黻宸并没有善罢甘休。1901年他又积极策划和暗中布置,试图让黄泽中再次应考。当时陈黻宸正在杭州养正书塾担任教习,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他与弟弟陈醉石通信十多次,细密交待黄泽中应试的各项事宜。在其中一封信中他还详细交待了具体操作方法,并强调“此信极密极紧要,万万不可令人得知,即家亦不可人人得”。⑫陈黻宸:《致醉石弟书第七》(1901年5月),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1048页。在信中他一再交待要十分谨慎、细细斟酌、严密布置,避免又生枝节。除此之外,陈黻宸还一直密切关注新任学宪莅临温州和出棚的时间,并对其背景、主张、结交和读书偏好都了如指掌。当然,暗中策划和搜集情报之外,打通各个关节还离不开“孔方兄”的帮忙,教书为生的陈黻宸并没有如此财力。不管是一再邀“期颐老人”(一百元)作引线,还是需要《毛诗》一部(三百元),一切还得靠黄泽中伯父“鹤公”之力。①“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举万不可错,而惜小费尤为第一误事。想九仞之劳,鹤亦备尝(其)味,必不为一篑争矣!”陈黻宸:《致醉石弟书第四》(1901年3月),《陈黻宸集》,第1044页。
新任学宪张公莅瓯之际,陈黻宸专门致信知府王琛,提及“舍亲黄泽中久处覆盂之下,得年伯拨而出之”,②陈黻宸:《致王雪庐书第一》(1901年5月11日),《陈黻宸集》,第1016页,第1016页,第1015-1017页,第1017页。由此我们得知戊戌府试打人案得以和解,有知府在居间调处。信中陈黻宸一再保证三年前的案子无需过虑,“铁案如山,虽大力必不能移”,“积案盈尺,终成铸铁”。③陈黻宸:《致王雪庐书第一》(1901年5月11日),《陈黻宸集》,第1016页,第1016页,第1015-1017页,第1017页。接着,对于此次应考陈黻宸预想了可能出现意外之事的三种情况:“一、耸人联名具呈,二、挨保不画押,三、场前揭匿名帖,临场买人阻挠以作恫吓之势”,并一一提出应对方法。④陈黻宸:《致王雪庐书第一》(1901年5月11日),《陈黻宸集》,第1016页,第1016页,第1015-1017页,第1017页。为了让黄泽中安静进场,陈黻宸还恳请王琛帮忙,“以免场中无赖辈无端指耸”。⑤陈黻宸:《致王雪庐书第一》(1901年5月11日),《陈黻宸集》,第1016页,第1016页,第1015-1017页,第1017页。为了再次应考顺利,陈黻宸处心积虑、精密策划,黄寿浩慷慨解囊,知府暗中帮助,所有这些都表明,黄泽中应试确实如孙诒让所说“温守王琛违例收考”。⑥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四》(1898年10月29日),《籀庼遗文》,第360页。
戊戌打人事件发生十年之后,围绕瑞安中学存废问题,陈黻宸与项崧等人意见不一。⑦项崧(1865-1909),字申甫,瑞安人,时任浙江省教育会长。1909年2月20日项崧以“温州留杭同乡”的名义在《浙江日报》上登《陈介石先生鉴》启事,又重提陈黻宸“因令妹倩黄某送考”之事。为此,陈黻宸也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予以反驳:“黄君世袭武职,家藏封诰,以伯父经营钱业,彭镜淮有索未遂,耸众捏诬,经讼数年,黄君得伸,有学署卷宗可稽。黄君现为学界办事人,然亦曾入院试二次,乡试一次,入京取入国子监南学肄业……”⑧陈黻宸:《致项申甫公开信》(1909年4月6日),《陈黻宸集》,第1027页。另外,这一年清廷实行预备立宪,诏令各省设立咨议局,陈黻宸、贾燊和项崧之兄项湘藻等六人当选温州议员,随后陈黻宸当选咨议局正议长。⑨陈谧:《陈黻宸年谱》,见《陈黻宸集》,第1201-1203页。项、贾二人于咨议局正式开幕日又提出“揭发议长资格异议案”,第一条即黄泽中应试一事:“光绪戊戌年,黻宸妹夫黄泽中冒考,经廪生彭镜淮查出,黄泽中以系县役黄奎之孙,照律面禀府宪扣考。黄即奔告黻宸,率党闯入考棚,扭该廪生倒地朋殴,有地方官详文及绅士孙诒让等六十余人公禀、抚藩各宪批示为证。其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一也。”⑩林损:《〈项湘藻贾燊揭发浙江咨议局议长资格异议〉驳正》,陈肖粟,陈镇波编校:《林损集》,黄山书社,2010年,第1024-1025页。对此,陈黻宸外甥林损撰文驳正,说法大致与陈黻宸反驳项崧时相同。
十年前的旧事一再被重提,由此也透露了更多关于戊戌打人案和黄泽中的情况。陈黻宸、林损抓住“彭镜淮有索未遂”这一点,矢口否认冒考一事,坚持说是彭某“耸众捏诬”,“有学署卷宗可稽”。1901年,陈黻宸为了黄泽中再次应考,花费半年多的时间周密策划、暗中布置。知道这样的事实后,陈黻宸公开信的辩驳当然难以让我们信服。此外,看来陈黻宸的策划非常成功,后来黄泽中“入院试二次,乡试一次”。因为黄泽中参加科举一事,陈黻宸殚精竭虑并一再遭人指摘。对此,黄泽中万分感激,1917年陈黻宸去世时黄泽中的挽联中不忘提及此事。⑪“忆昔棘荆满地,薏苡遭诬,沈海太茫茫,仗义有公冤独雪”。见胡珠生编:《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67页。黄泽中,后改名公起。
如上文陈黻宸写给知府王琛的信中所言,戊戌打人案最终和解得力于王琛居间调处。1899年2月17日的《张棡日记》以“赴王小木表兄家议黄泽中求和事”为提要,⑫王岳崧(1850-1924),号筱牧,俗称小木,瑞安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记载了事情和解的具体参与人员和方案:“近因黄泽中扣考事到伊家议和……下午许竹友师、郭梅笛、陈式卿、周仲龙均来,周幼仙亦来会议此事。盖黄约出英洋二千五百元,以作捐免之例:一千二百元作宾兴之款;一千元为学堂创办;三百元为童场县府道场卷费。诸廪保来者均照议而去……”⑬《张棡日记》(1899年3月28日),第50-51页。原来,最后是黄泽中出钱和解,这笔钱即陈黻宸所说用以“填案”的花费。①陈黻宸:《致醉石弟书第七》(1901年5月),《陈黻宸集》,第1047-1048页。至此,戊戌7月初六的打人案,经过前后半年多的时间,于1899年2月得以和解。
综合以上围绕温州戊戌打人案的私人信件、日记和报纸公开信,事件的大致经过简单说来如下:陈黻宸通过严密布置使妹夫黄泽中得以违例参加温州戊戌府试,廪生彭镜淮抓住把柄借机强借但未能得逞,于是宣扬黄姓祖父曾充县役之事,送考的陈黻宸便与之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黄泽中被扣考。之后因为姻亲、世交或朋友关系黄体芳、孙诒让、陈虬等人卷入事件,黄、孙与二陈的旧怨又使得事件升级为诉讼案。半年多后,在知府王琛居间调和、众士绅商议下,黄泽中出钱求和,事情才最终和解。
了解事实真相后,回头再看宋恕和孙诒让对此事的转述,可以发现两人的个人倾向。作为陈黻宸的好友,宋恕在叙述此事时对于众人指出的身家不清一事只字不提,显然有回避事实、为朋友遮掩之嫌。宋恕把矛头更多指向了黄体芳,信中对其平日行为多有抨击。孙诒让在陈述此事时却对黄体芳的所作所为只字未提,矛头直指陈虬,他毫不掩饰对陈的厌恶之情:“其人在乡,鄙恶狂谬,不可殚述,其假维新为职志,而肆其植党牟利,无所不至……弟于志三,十年前即痛斥为小人。”②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四》(1898年10月29日),《籀庼遗文》,第360页。孙诒让一再痛斥陈虬,且言语之激烈完全不是他宽厚谦和的一贯风格,那么孙诒让与陈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呢?
二、孙诒让与陈虬的恩怨
虽然自称“乐清陈虬”,但陈氏迁居瑞安已十一世,所以陈虬算是孙诒让的瑞安同乡。不过孙诒让大部分时间都随仕父亲孙衣言,先后辗转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两人的初次见面应该是在1878年春,当年7月15日孙诒让在写给陈虬的信中这样说:“里居三月,匆匆□□[就道],□□[阁下]宏辩,冠绝时贤。乃知孟公惊座,名固不虚也。”③孙诒让:《答陈子珊书二通·一》(1878年8月13日),《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页。也就是说,孙诒让早已听闻陈虬孟子般的雄辩之名,这年春末因侍奉母亲回乡居住三个月,才得以见到他。孙诒让重返江宁官署后,两人有书信往来。针对孙诒让的《征访温州遗书约》,陈虬提供了一些线索和建议,孙诒让也一一作出回馈和解释。在另一封信中,针对陈虬论述的“吾乡学派大略”,孙诒让也详述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商榷意见。两人年龄相仿,通过见面和书信往来,孙诒让对陈虬的个性和学问高下应该有了大致了解。
1879年底之后,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回到家乡瑞安,不复外出,因而与同居瑞安的陈虬等当地士人有了更多接触。早在1875年,孙衣言就在瑞安城北营建新居并设立“诒善祠塾”。回乡后的第二年,孙衣言重订诒善祠塾课约,在此后的十五年左右广聚温州各地英才而教之,先后受业的弟子达数十人。然而正是这个时候,陈虬与孙氏的关系走向恶化,双方的对抗关系直接反映在求志社与诒善祠塾的竞争关系,以及“布衣党”与官宦之家的针锋相对上。宋恕提到:“当是时,孙太仆归田,提倡乡哲薛郑陈叶之学,设诒善祠塾,以馆英少。其后瑞人才所出,苟非诒善祠塾则必求志社,求志社闻天下。”④宋恕:《介石先生行年五十生日寿诗有序》,见《陈黻宸集》,第1220页。宋恕提到的求志社是在孙氏父子回乡后才开始活动的,光绪七年(1881)前后,在许拙学的提议下陈虬等人结成求志社,“当时东瓯布衣有天下人物之名”。⑤池志澂:《陈蛰庐先生五十寿序》,见《陈虬集》,第391-392页。陈虬对此也颇为得意:“故好事之徒倡有布衣党之目,名虽不雅,意颇甘之。”⑥陈虬:《致宋燕生书(二通)·一》(1889年9月20日),《陈虬集》,第342页。
1882年,陈虬在撰写《瑞安何氏旌节坊记》时对孙家拜佛颇有讥讽:“高明之家妇女喜与觋妪、斋尼往还,而妖妄之婢因挟以自重。……呜呼!夫若辈之足以乱入闺阃也,学士大夫有身受其毒而尚不自知者!”⑦陈虬:《瑞安何氏旌节坊记》,《陈虬集》,第171页。看来此时陈虬并不介意把与孙家关系恶化的事实公开化。求志社主要成员金鸣昌看完此文后予以回信,全文言语刻薄,对孙家嫉恨之情溢于言表。⑧“且今之学士、大夫,其所自为者诚得矣!彼其日暮图远,自唯生平行事不获罪于天也,又见佛家有祸福忏悔之说,妄谓罪之可免而福之可邀也,乃以老悖垂死之年,乞灵于朽质淫腐之鬼。……故常以其所自为者假托先哲,诱其后进,陷溺聪明英隽少年之士,使皆嗜利无耻而出其门下。故其坏风俗、丧廉耻,为世道人心之害,祸盖甚于洪水猛兽……”金鸣昌:《答陈志三书》(1882年),见《陈虬集》,第172页。何氏旌节坊记和这封私人信件反映出当时陈虬与孙家的矛盾已经相当深刻了。此外,1888年春孙衣言于瑞安城东虞池金带桥北别营新居,并建玉海藏书楼五楹于宅旁,①张宪文:《孙仲容先生年谱简编》,见《孙诒让遗文辑存》,第506页。而陈虬于1885年设立的利济医院也在城东虞池河边。同在瑞安小城,陈虬与孙家之间难免发生一些不愉快,双方的矛盾日积月累。孙诒让1898年给汪康年的信中这样说:“弟于志三,十年前即痛斥为小人。”②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四》(1898年10月29日),《籀庼遗文》,第360页。
甲午战败举国哗然之际,陈虬和孙诒让也都有所行动。1895年秋,陈虬在温州设立利济分院;1896年创《利济学堂报》,并为《经世报》撰文;1898年进京会试时结交康、梁并参加保国会。此时,孙诒让也悕念时艰,更加关注世事,拟组织“兴儒会”,大力倡导兴儒救国之论。孙诒让还从此走上了兴学救国之路,先后开办了瑞安学计馆(1896年)、蚕桑学堂(1897年)、瑞平化学堂(1899年)等,希望培养“以应时需”的实用人才。虽然孙、陈二人都热情支持和积极投身维新事业,但是两人对立依旧。甚至有人说:“当时孙治让等人创办的学计馆与陈虬等人主持的利济医院、学堂之间便存在着明显的对立……甲午戊戌年间瑞安及温州在文教领域的维新史,就是一段以孙、陈二派为中心的、自发形成的内部竞争史。”③徐佳贵:《地方士人与晚晴地方教育转型——以浙江瑞安为个案的考察》,第24-25页。
孙、陈之间的多年积怨,使得两人在不少场合都保持界限或者回避,《利济学堂报》和瑞安务农支会就是典型的例子。1896年大寒日(1897.1.20),陈虬主办的《利济学堂报》正式出版。据孙诒让对汪康年称:“顷闻报馆颇引贱名以募资,弟不得已至申浦,后刊告白以自明,(去年十二月杪)甚可笑也。”④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一》(1897年),《籀庼遗文》,第356页。孙诒让的《申报》告白曰:“温州利济医院新开报馆,本宅毫不与闻,刻外间忽传本宅捐有洋五百元,实属不敢受此虚誉,理合声明,以免招摇。”⑤《申报》光绪丙申十二月廿八日(1897年1月30日)。告白刊载的时间是《利济学堂报》第一册出版后的第十天,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与陈虬撇开关系,孙诒让不惜亲赴上海,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1897年春,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设务农会,瑞安人士黄绍箕、黄绍第和陈虬等人先后加入该会为会员。⑥孙延钊:《孙延钊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农学报》第三册、第九册还刊有陈虬的《拟务农会章程》,⑦陈虬:《〈务农会试办章程〉拟稿》附胡珠生按语,见《陈虬集》,第254-258页。看来陈虬是上海务农会的积极参与者。1898年2月务农会瑞安支会正式成立,黄绍箕、黄绍第为正副会长,孙诒让任研究部长,而“瑞安务农支会会友题名”三十九人中竟然没有陈虬。⑧孙延钊:《孙延钊集》,第290-291页。不管是陈虬主动回避还是被动离开,在瑞安务农支会这一地方组织中孙、陈没有共事确是事实。
行文至此回头再看1898年7月温州府试打人案,大概可以理解为何孙诒让矛头直指陈虬了。与其说孙诒让的痛斥是针对案件本身,不如说这是孙、陈两人近二十年积怨的总爆发。如果将漫漫历史比作沉沉黑夜,那突发事件就像天空划过的闪电一下子将漆黑的夜晚照亮,使得黑暗中的景观暴露无遗。或许温州戊戌府试打人案也是一道闪电,透过此事孙、陈两人的宿怨更清晰地展露在我们面前。
至1903年底陈虬去世,孙、陈二人的关系是否有所缓和呢?作为孙诒让的妹夫、陈虬的好友,宋恕一直尝试调解孙、陈关系。尽管因此而“得罪仲容,又被诮志三”,⑨宋恕:《致杨定甫书》(1895年3月19日),《宋恕集》,第525页。宋恕并没有放弃努力。1902年9月,宋恕因母亡寓居瑞安仍不忘调解两人的关系,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十四日,出门谢吊,调和孙、陈,先陈后孙,皆允。十五日,再走白陈,订乐清来面和。”⑩宋恕:《壬寅日记》(1902年10月15日),《宋恕集》,第960页。“调和孙、陈”的“陈”指陈黻宸,“乐清”才是陈虬。陈虬与孙诒让是否和解,宋恕日记没有后续记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打破坚冰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1903年11月14日,陈虬悲愤离世,不管最终是否和解,孙、陈关系都画上了句号。
三、陈虬的学术与心术
相比孙诒让服膺乾嘉家法,陈虬治学则相当驳杂。他二十岁之后留心经世之学,后又专心医书,兼涉历、相、星命诸学,宋恕说:“蛰庐先生少好名、兵、纵横、词赋家言。渐进儒家……”①宋恕:《书陈蛰庐〈治平通议〉后》,《宋恕集》,第239页。治学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二人“愈趋愈远,愈不可合”。②宋恕:《致杨定甫书》(1895年3月19日),《宋恕集》,第525页。况且陈虬还有争胜之心,宋恕还因此把孙、陈关系比作北宋的苏、程之争:“仲容经学湛深,郡人莫不仰若山斗。独陈志三起,而以经济之说与之争雄,温州学子遂分二党,积不相能,日寻舌锋以相攻击,于是彼此丑诋,略似北宋之苏、程。”③宋恕:《致叶浩吾书》(1898年12月13日),《宋恕集》,第594页。
陈虬最重要的著作是1893年汇刻的《治平通议》八卷,其中包括《治平三议》、《经世博议》、《救时要议》、《东游条议》和《蛰庐文略》,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他还在近代中国最早提出了“创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宋恕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道:“志以《治平通议》已抄就者二本见示,多不刊之论,文章尤雄深雅健,直逼西汉,真天下奇才也。”④宋恕:《辛卯日记摘要》(1891年11月9日),《宋恕集》,第927页。在与友人通信中也说:“其宗旨与礼不合,考证亦或欠核,然才雄学博,亭林、默深之亚……”⑤宋恕:《致王浣生书》(1895年3月15日),《宋恕集》,第523页。据说张之洞对此也很赞赏,⑥“昨姚颐仲来言:‘闻金陵帅幕说,香帅见陈氏《通义》而大悦,渴欲接谈,屡向幕员询踪,而皆以不知对。’”见宋恕:《致陈志三书》(1895年10月3日),《宋恕集》,第537-538页。梁启超也把此书列入《西学书目表》。谭献在1898年的日记中也记下了看过陈虬《治平通义》附《报国录》的想法:“匡时之论,凿凿可见施行”“深切著明,必有宏验”,还发出“安得风尘相见作竟日谈?”的感叹。⑦《复堂日记》(1898年3月30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4页。相比之下,1898年孙诒让却用“其所论绝浅陋”来形容陈虬的论著。⑧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五》(1899年1月6日),《籀庼遗文》,第361-362页,第361-362页。当然,相比学力深厚、著作等身的孙诒让,陈虬的高谈阔论略显浮浅,但是陈虬的变革主张确实回应了当时的时代命题和士人的普遍关怀,以“绝浅陋”来完全否认其价值显然有失偏颇。
相比学术上的分歧,孙诒让最看不惯的还是陈虬的狂傲个性。刘久安在《陈蛰庐先生行述》中这样描述陈虬的相貌和举止:“生有异禀,龙颜隆准,面瘦削,颐无肉,胸骨直竖,腰窄若束,而精神十倍于常人,辩有口,喜谈兵,发声若雷,目光炯炯射人,当者魄丧。”⑨刘久安:《陈蛰庐先生行述》,见《陈虬集》,第394页,第394页,第395页。陈虬的母亲还曾告诫他:“汝目有杀气,恐不得其死!”⑩刘久安:《陈蛰庐先生行述》,见《陈虬集》,第394页,第394页,第395页。陈虬年少之时,塾师即恶其顽梗不群,“稍长尤不羁,使酒负气,习拳棒,善泅水,见不平,叱咤用武,虽不敌不计。……遇老师宿儒,往往摘经史以难先生,于是得狂名”。⑪池志澂:《陈蛰庐先生五十寿序》,见《陈虬集》,第391-392页。
陈虬还相当自命不凡,甚至有当教主之心。他认为自己“一切聪明才识,自问不让古人。惟德性不及程、朱诸公”。⑫刘久安:《陈蛰庐先生行述》,见《陈虬集》,第394页,第394页,第395页。好友陈黻宸在挽联中说他:“生平以神农、黄帝、孔子、释迦、基督、摩西、穆罕默德自名。”⑬陈黻宸:《挽陈志三虬》,见胡珠生编:《东瓯三先生集补编》,2004年版,第436页。甚至只是稍微读了一点《利济学堂报》的谭嗣同也很快觉察到陈虬“欲为教主”的想法,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这样说:“《利济学堂报》乃缘《时务报》已登告白,故买阅之,今寄到。不意中多荒谬迂陋之谈,直欲自创一教……”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1897年7月23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258页。这样个性的陈虬,在“平生雅不喜虚骄之论”的孙诒让眼中就是一个“鄙俗诡险”“鄙恶狂谬”的小人。⑮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1897年),《籀庼述林》,第384页。孙诒让认为:“大凡论人必以朴诚为本,喋喋利口之辈图窃利禄者,万不可用。”⑯孙诒让:《兴儒会略例并叙》,《籀庼遗文》,第328页。
不仅看不惯陈虬的狂傲,孙诒让还怀疑他维新活动的动机:“渠扺掌谈时务,只为屠门大嚼计耳,岂有强中国拯黄种之心哉!”⑰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五》(1899年1月6日),《籀庼遗文》,第361-362页,第361-362页。还说他“以洋务为竿牍求利”,⑱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一》(1897年),《籀庼遗文》,第356页。“假维新为职志,而肆其植党牟利,无所不至”。⑲孙诒让:《与汪穰卿书十一通·四》(1898年10月29日),《籀庼遗文》,第360页。陈虬家贫,祖父三代无知书者,1890年他对山东巡抚张曜说:“……手创利济医院,猝难毕工,家门二十余口,岁需五百余金,倚虬以活。”①陈虬:《上东抚张宫保书》(1890年6月),《陈虬集》,第331页。出身底层的陈虬借创办医院和学堂养家糊口,本无可厚非,在孙诒让看来却可能是“牟利”之举。通过办学、行医,陈虬在学生和百姓中有一定的认可。另外,陈虬重义气,“厚骨肉,笃朋友”,②宋恕:《致王浣生书》(1895年3月15日),《宋恕集》,第523页。“情谊所系,虽从井不辞”,③池志澂:《陈蛰庐先生五十寿序》,《陈虬集》,第391-392页,第392页。因而也结交了宋恕、陈黻宸等好友。宋恕这样回忆两人的交往:“戊子、己丑间始获密接,纵谈政教每连宵昼。然恕自信甚,不合即面折,声色俱厉,先生不罪,反益扬许。”④宋恕:《书陈蛰庐〈治平通议〉后》,《宋恕集》,第239页。陈黻宸则这样评价他:“先生古貌古心,于时流少所投合,顾独辱与宸交甚契,夜庐风雨,一灯相对,纵谈古今,悲愤所激,令人不知哀感之何从,固性情中人也。”⑤陈黻宸:《陈蛰庐孝廉〈报国录〉序》,《陈黻宸集》,第511页。陈虬在戊戌府试打人案发生后为朋友陈黻宸出手,也正体现了其重义气、笃朋友的一面。通过求志社、利济医院和学堂,陈虬身边围绕了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学生,这也许就是孙诒让所说的“植党”。
严辨君子小人无可厚非,但是完全从个性推断一个人的心术也难免失当。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虬是个卑鄙、险恶的小人,或许孙诒让与陈虬间的旧怨使他颇有偏见,因而也影响到对陈虬心术及其维新思想和活动的评价。在温州戊戌府试打人案中,孙诒让激于意气挺身而出,在这件事上宋恕这样评价他:“仲容本是光明磊落者流……惟涉世太浅,知人不明,意气太不平,遂至始则常受小人之愚,轻率出面,继则将错就错,反于本来面目有伤耳。”⑥宋恕:《致叶浩吾书》(1898年12月13日),《宋恕集》,第593页,第595页。他还曾说:“籀庼经子之学欲过德清先生,品行亦殊高洁,惜乏知人之明,听言太轻,忠厚有余,聪察不足。”⑦宋恕:《己酉日记》(1908年12月27日),《宋恕集》,第1004-1005页。
狂傲不羁的陈虬不仅遭到孙诒让的厌恶,更因此饱受坎坷和痛苦。因为对黄体芳表现出的轻视和狂妄,陈虬在戊戌打人案中受到牵连。依照宋恕的说法,“通政且怒且恐不胜乡里之公愤,会八月大变,通政喜有美机可乘,乃挟‘康党’二字以图置志三、介石于死地,且以禁制乡人之为志三、介石鸣冤”。⑧宋恕:《致叶浩吾书》(1898年12月13日),《宋恕集》,第593页,第595页。于是,戊戌政变风声鹤唳之时,参加过保国会的陈虬不得不背井逃难,辗转上海、杭州等地。直到第二年初案件和解,陈虬才得以还乡。
除了逃难他乡外,戊戌政变对陈虬多年经营的事业也带来冲击,池志澂回忆说,“不意戊戌变政,风潮反对,罢学堂,闭报馆,云散二百徒,累败八千金”。⑨池志澂:《陈蛰庐先生五十寿序》,《陈虬集》,第391-392页,第392页。深受挫折却又自命不凡的陈虬,只能以“天妒英才”来自我宽慰,直至临死前不久写给弟子的信中,他都在感叹:“苍苍者天,何祸我之甚也!虽然,抑亦我有以自取之也。……天何不祚,命也如斯!”⑩陈虬:《致杨伯畴书(四通)·四》(1903年),《陈虬集》,第353页。虽有才华但狂傲不羁,并因此与世家为敌,本来鲜有凭借的他又给自己增加了外在阻力,使得经世学问难有施展空间。自命不凡的陈虬又没有安贫乐道、独善其身的洒脱,最后悲愤离世。大概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这样,对此只能同情又无奈,可怜又可叹了。
(责任编辑:李孝迁)
邱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邮编2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