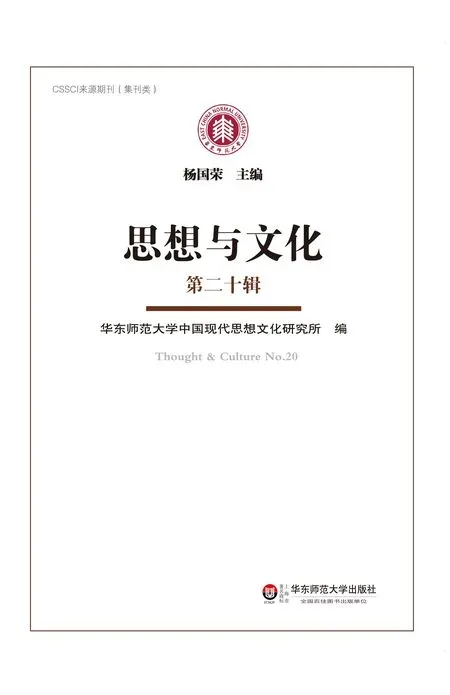《老子》之“有”、“无”再探
——基于比较哲学的视角
●
玄冥之无
西方形而上学自始强调在(Being)而否定无(Nonbeing),存在又以各种方式与光联系起来。而在神学中上帝本身变成了光。形而上学和神学因此要求人从现世的黑暗转向光明。相比之下,道家则要人从万有之光色转向玄冥之无,即本源的道。那么说万物之母的本源是玄冥之无,其意义何在呢?
首先,这一“无”绝非形而上学中的nothingness。西方哲学把nothingness理解为有或者在(Being)的对立面和否定,或者是缺失,nothingness因此成了no-thing,即无物存在。道家的无超越所有肯定和否定,并由此肯定一切。但无论如何,既然是无,我们对之又如何感知,如何言说,如何思呢?对此,老子曰:
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此三者不可致诘,故而为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随之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第14章)*本文《老子》引文是综合河上公本、傅奕本、王弼本、帛书本、北大汉简本等版本而成,并不固定于某个版本,相对更重视帛书本。
此处老子所言,并非如常识所理解的那样,是说道不可被感知。恰恰相反,老子正是在描述道之经历。因为他明白地告诉我们,他在视、听、触摸道,他在追问道,他在追随、迎接道——实际上他在紧紧持守(“执”)道。道不可见,所见莫非道也;道不可闻,所闻莫非道也;道不可触,所触莫非道也。“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无物者,无所不在也。需要注意的是,与形而上学只能通过理性而非感性被言说和思想的存在不同,老子的道之“无”不可以通过抽象的概念或者理念被把捉。它是在人类语言之外的“无名”,但却可以被经验。当然这并不是说道是感性的,因此是非理性的。这一观点并不少见,实际上道之经验常常被误解为理性对立面的“直觉”。此种观点实际上以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为标准,一切理性自身难以企及的、异质的思想都被当做神秘或者非理性匆匆打发了。但是道之经验超乎形而上学感性/理性的二元区分之上,它先于此种区分。
那么,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一玄冥之无呢?我们又当如何避免理性之光的遮蔽,使得玄冥之无向我们展开呢?从何处找到通往无的道路?或者,如果最终这是一片无路之地,虚无的道本身可以引导我们吗?
首先,“无”向我们展示出的是道并非一物。并非有某种实体叫做“道”。正如庄子所言,“物物者非物。”(《知北游》)道不是与感知世界相分离的原则或者概念。它也并非一种形而上学的物的全体。它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言的todeti。(todeti是亚里士多德用来指称实体的用语,意为“这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理念形式和上帝都是beings,存在者。尽管他追问了存在之为存在本身。我以为因此他的形而上学落入了物的层面。)
这说的是为早期中国哲学各个流派所强调的道物区分。《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在此指的是物的层面,因为万物包括人都是相互关联,因此是相互为用的。“器用”常常并举正是这个意思。这里的“用”只是指关联性而言,并非具有道德色彩的“利用”。器物之用或者关联性却是来源于道的,而道是超乎关联性之用的“无用”。所谓的“无用”当然不是说道是useless。相反,它说的是“有”之以为利皆必以“无”为用,万有之用皆本于无。故而曰“形而上者谓之道”,道之本源义喻于其中。
但道物区分对人来说却是最难的。才说“道”,便有被把持为一物的危险了。这说的是,遗忘大道乃是人的天命,它是归属于道之天命的。当道不能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之时,它总是被把捉为一物并于此落入物的层面了。这就是为什么当道在现代生活中不能被经验之时,它被贴上了种种标签: 我们说道是“最高的原则”,或者是“普遍的法则”,或者是“宇宙的终极依据”,如此等等。这一切的标签恰恰是道不再被经验的明证。因此,随着人的异化一道,道被物化了。这就是现代生活方式之下道的遗忘。
道物区分绝不意味着道物的隔离。西方哲学中恰恰是因为存在(Being)与在者(beings)的隔离造成了存在被把捉为一种在者,于此二者的区分被遗忘了。*比如柏拉图的存在世界和生成世界的分离。理念被把捉为beings,亚里士多德正是基于这一点来批判他挚爱的老师柏拉图的:“对那些提出理念是原因的人来说,首先,在寻求我们周围事物的原因之时,他们介绍了其他数目相等的东西,就好像一个人要数东西,却认为数目太少不能数清,于是把事物的数目扩大再来计算一样。”Aristotle, Metaphysics,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Edited by 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990a35—990b5.翻译出自本文作者。道物区分却是要求道物不二的。
恰因为道是无,它才能遍在诸有。因此老子说,“无有入于无间”。(第43章)“无间”指的是物的限定性(determinacy)和固着性。一切物都是限定的,被固定在一定的形态当中,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地点之中。惟“无”可以超越所有对反的限定性。它亦大亦小: 因是无,可谓至小,但万有出乎其中;可谓至大,但却隐藏自身于无有。“道汎呵,其可左右也。”(第34章)它超越也因此包涵了所有的开端和结束,道自身却无始无终。故道被称作天地之始。它超乎高低、冷暖、动静、善恶、死生、有无,它因此和万有之光色而一入于玄冥。自隐于玄无,道是使得所有差异之光开启的“一”。
老子说: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是谓玄德。(第51章)
道德之尊贵并不依赖于人之名言的估价。它超乎人类的语言并最终超越人类的一切价值。它在恒常的自然中隐藏自身。因此万物之生、畜、长、遂、亭、毒、养、覆皆是道之自然。道自隐于无,因此叫做“玄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德”同时指道物为言。它既指道生养万物之德,又指万物得道以存乎己之“德”,此义后来发展成物之“性”。但“性”字失却了老子的“德”同时贯穿道物的意思。
道之隐藏和自然显现不二。它们是同一的,是隐藏者在显现。此即道之自我展开。
因此,无绝非是一无所有之意。无和有也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过程。相反,有乃是无的展开。在此意义上,无与有处于永恒的动变交流之中,这种动变交流中涵具着有无的同一性。但此种同一性并非逻辑的同一律,A=A,一种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有无的同一性与道物区分并非矛盾,二者乃是同一事件。正是在有无的此种动变交流中无的本源意义才得以彰显。(关于有无的关系详见下文。)

“虚”首先意味着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涵具着丰富性之义在其中。虚若谷,而万物聚焉,万化育焉。因此老子称谷为天地根。(第6章)在虚无中物之真实才能被展开。
“虚”隐含了动之理。“虚”常常与“静”相连,谓之“虚静”。惟虚静方能生物之动。惟虚而不屈方能动而愈出。(第5章)因此曰,“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6章)“绵”从“糸”从“帛”,谓系取细丝,积丝成帛。(《说文解字》)因此“绵”有连续不断义。“绵绵”是说道之连续性。但这不是一种由纯粹的存在(pure being)构建的连续性,如同巴门尼德的存在之球(the ball of Being)一样。相反,这种连续性恰恰是由虚无(nonbeing)构成,万物之有(being)由之而来。万物之兴作乃是在虚无中展开。因此道之虚静不是万物之兴作的对立面,它本身包含了物之生成和消逝,并和之于道之玄冥。
老子常用“沖”来表示道之虚无。沖兼具动与虚之义。沖最初意为水之涌摇,“涌,上涌也。摇,旁摇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因此沖又有混、和之义。因此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沖气以为和。”(第42章)这句话向我们展示出道之动以和物。第4章曰:
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渊呵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也,象帝之先。(第4章)
在此,老子通过“冲”、“和”向我们呈现的“同一”并非如同质性的存在一样的自身的等同*Parmenides, Fr. 8, 32-49. 见G.S.Kirk, J.E. Raven and M. Schofield,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p.252.,而是涵具了所有差异之光。
这种动态意义上的“虚无”暗示出有限性的消解。道之虚无与物之实在相对。实在之域(the realm of the concrete)在时间上有限,空间上固定。这一点前文已有涉及,下面我再从人的感知的角度进一步阐明。这里的“实在”不仅是感官的对象,它同时包含了人的认知对象。由感知(sensitivity and cognition)所呈现的必须在一定的界限之内。实际上我们的感知本身不断划分界限,它因此建构着界限。当我经验世界之时,哪些可以被感知,哪些不能被感知,以及世界如何被感知,这是一个先天与历史性交相建构的过程。世界如何被感知就构建了我也同时构建了我的世界。
关于感知的界限,《则阳》曰:“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而道作为虚无穿透一切界限,故庄子曰:“道通为一。”(《齐物论》)但这不意味着道是外在于有限的物之世界的实体,或者道物分离。动态的虚无显示这些界限和局限是可以被打破的,而虚无本身就是打破之的途径。在虚无之中我们的感知成为通向自由的凭藉。“虚”、“无”和“沖”因此包含了“无知”的意思在其中,即,无其知以通乎道之玄冥无碍,唯此,物之笃实才可能向我们展现。《老子》第16章曰:
致虚恒也,守冲笃也。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第16章)
是虚而恒,虚而笃。惟有在冲虚之中恒常才能被呼唤,才可前来与人照面。由此笃实唯有在虚无之中被保存。在此“归根”并非如同常识所理解的物之消逝。万物之兴作与归根不二,它们并非两个不同的过程。这即是说,万物的兴作与消逝构成了它们的“归根”,这其中涵具着动静不二之理。归根之静包含了万物的兴作、消逝之动。因此老子所说的与“静”密切相关的“命”就绝不是一种外在于物并强加于物之上的命令。对老子来说命甚至不仅是关乎人的,它关乎万物。“复命”说的是万物兴作消逝的生命展开。而最重要的是,命是关乎道的。老子曰:“复命曰常。”“常”向我们指示出在万物的兴作、消逝之展开中一以贯之的道。知玄无之常而明生焉。知因此与虚无相关,它最终是无知。
有无的游戏
有无这一重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首发于老子。从世界哲学的进程来看,如果说西方哲学注重有(存在,Being)而印度佛教注重空无的话,那么,比较而言,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有无的相互彰显,我把它叫做“有无的游戏”。那么在道家哲学中的有无又是什么意义呢?在现代性的存在中又如何才能避免对有无的曲解呢?

接下来看“无”和“無”,我将借用庞朴先生的考证。*参看庞朴: 《谈玄说无》。此是庞朴先生于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演讲。整理的文稿请参看http: //www.gmw.cn/01gmrb/2006-05/09/content_413816.htm。先看“无”字。“无”字从字形上看乃是“元”通上去一点,故《说文解字》曰:“通与元者,虚无道也。”《说文》又说,无(無)从大,丰也。这初看的确令人费解,既然是无,又怎能说丰呢?但汉语之无的确就是此一意思。实际上这种解释保留在许多汉字之中。比如“芜”,“草”字下面一个“无”,意思并非没有草,而是很多草;又如“炁”字,是“无”加“气”而成,这当然不是说没有气,而是表示气之丰沛。

有与无皆自先民之祭祀以求佑护而来。惟有在此意义上,道才能一统有无。亦惟有在此意义上,道的本源意义向我们彰显出来。因此老子才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所道出的,乃是对万物之所从来的眷恋。
需要注意的是,“有”、“无”在日常语言中主要是指存有与否,即使在老子的时代也是如此。而老子的哲学实际上保存了有无最源初的意义。他对于道之自然的思考是围绕“有”、“无”的这种源初意义展开的。那么我们今天应当从何处获得通向有无之思的道路呢?
气的思想是中国哲学不同流派共通的背景。以下我将通过气的思想展开对有无的探索,以期这一新的思考路径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解,并希望“有”、“无”之新义可以由此向我们展现。但这并不是说有无便只是气,与道分离;或者道(之有无)竟只是气,道物区分由此被消解了。前文已经指出,道物区分并非是道物隔离。恰恰因为隔离这一区分才被消解,如此道便未免被把持为一物了。而我们在此要做的是通过气的思想来探索有无的道路。
首先,气分阴分阳,阴阳相须相待。无无阴之阳,亦无无阳之阴。因此有无互为彰显,相互诠释,此即有无的游戏。老子总是有无并举,从不离有谈无,亦不曾离无谈有。如第十一章: 当其无而有其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第11章)第十四章: 视之听之捪之者,皆似有也,故谓之“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然复归于无物,是谓惚恍;而“迎之”、“随之”又是恍惚有物矣。执古道之无以御今之有,复知古始之无。此是有之无之,无之有之,动乎不已。第二十一章: 恍惚窈冥者,道之无也。“恍惚”、“窈冥”皆有视之不清之意。*关于道家著作中的视觉性语词的精彩分析,请参看郑开: 《道家著作中的“视觉语词”例释》,《思想与文化》第十八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恍惚者,不定也;窈冥者,深远也。然必后之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恍唯惚。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恍呵忽呵,中有物呵。窈呵冥呵,其中有精呵;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也?以此。”(《道德经》第21章)《老子》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皆是有无亲密游戏,一如阴阳往来。老子用“恍惚”来描述道之在:“道之物,唯恍唯忽。”恍者心之光,似有也,在有非有;忽者心之无,似无也,在无非无。故谓之“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如此有而不有无而不无。有无交相辉映,皦昧恍惚不定,光影追逐徘徊,阴阳变化莫测,此是老子中有无的相互游戏。
其二,阴阳的视角是不定的,随时转换的。如人有男女,此一阴阳;一身之中,气又分阴分阳,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而五脏之气(如肾)又分阴阳,等等。故而有无或以道言,或以物言,或以人言,也是游移不定的。析而言之,我们可以说道之有无,或者物之有无,或者人之功夫的恒有恒无。又无知、无为、无欲方能有众物之用,以明白四达,爱国治民等等,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无之者,无其知、为、欲等等。又或者以道为无,以物为有。这些不同的层面在《老子》中同时存在,有时一句话涵盖了不同的意思,很难用现代汉语的主谓宾结构将其析离。绝非说道不及物,说物不及道。相反,说道便已经在物了,说物便是道了。故而我并不认为说道之有无处便不是物之有无,或者反之。接下来我将进一步阐明此点。
其三,以气言,有无并非静态的、抽象的辩证法概念,而是动乎不已的大化流行。《系辞》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者,阴阳也。有无乃是阴阳往来的动态过程。故而我认为我们必须打破一种现代性的,把有无作为抽象概念的做法。有无应当从动词的意义上得到理解。这一点在其词源学的意义上已经得到阐发。如第二章曰:“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恒也”,是“有”、“无”与“恒”相联系。有无相生的过程即是阴阳相推而生变化,“恒”即是此变化恒久不已之谓也。第十章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则是明显的“有”用作动词。不有之,故无之,故而继之以“为而不恃”。为而不恃者,无为也。玄德者,有而无(不有)也。第十一章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之”、“无之”也是必须从动词的意义上理解。即使在现代汉语的语法看来“有”、“无”用作名词的地方,我认为也应当从动名词的意义上理解。阴阳有无并非实体之物。汉语中的“物”却是必须从阴阳流变,有之无之的自然流行中才能得到理解。
这种从阴阳交流来理解的有无决定了它们不是指道、物或者人的单方面而为言,却常常是贯穿道、物、人不同层面的。这一点在许多汉字中体现出来,比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虚”,“无”,以及此处的“有无”等。这也是诗性思维的一个特点,一字,一词或者一段诗句暗含了多层次的意义在其中。由阴阳流变的思想背景所展开的对世界的动态把握乃是体用一如的根本原因所在。阴阳视角的游移不定,有无动态的贯穿,决定了老子从不把体用或者道物隔离开来的事实。
如此我们再来看第二章:“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恒也。”此处的“有无”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指现象界之物而言,它同时指本体之恒有恒无,故而帛书《老子》曰“恒也”。盖体用原本一如,即用即体,本体之永恒与现象之变化不一不异。第十一章曰:“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因为我们惯常从名词的意义上理解“有”、“无”,此处的“有”、“无”一般被理解为仅指现象界,而非本体层次的。但从动名词来理解的“有”、“无”贯穿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物。此处的“有”、“无”绝非仅仅是用的层面的,老子是借用以显体,同时直指人心体道功夫。即,借物之有以喻万有之有,借物之无以喻道之无,故而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之”、“无之”更涵具了体道以致用的过程,即抱一不离(“无之”)方能有物之利用。因此道体之究竟,物性之实然,与人之体道治世一并贯穿。
最后,阴阳一气,有无一体。非有一气曰阳,有一气曰阴,阴阳者指变化而为言也。故阴阳者变化之道也。非有一物曰有,有一物曰无,有无者以观变化之妙也。故第一章曰恒有恒无以观眇观皦。以动态的视角来看,阴消即是阳长,非是阴尽了有个阳气生出来(如《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湘云所言)。有无乃是道之动。阴阳无始,变化无端,纵横捭阖,皆以言道之动而已。
接下来我们看《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恒无欲以观其眇,恒有欲以观其所皦。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
首句开道与言关系的先河。在点明恒道不可道不可名之后,老子开始了他对道的五千言叙述。“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恒无欲以观其眇,恒有欲以观其所皦。”此处断句历来有两种。对前两句我采用“有”、“无”的断句方法,即,“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原因有二。其一,以往断句种种争论,皆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有”同“无名/有名”的区分到底何在。“有名”必是人的世界,而决不能以此泛言天地万物之生成。“有名”乃是人之历史之展开,有人则必有名,裁度天地以为法令制度,此亦名言之危险,即人之为人的危险所在。老子对此是十分警醒的。故曰,“道恒无名”而“始制有名”,“始制有名”者,就人而言也。故绝不能以“有名”为“万物之母”,明矣。其二,当然,老子也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但老子未尝用“有名”来指谓道。即使断以“有名”“无名”也必须从“有”“无”才能得到理解。蒋锡昌更一语点明,“无即无名,无名即道”。但这话套用“有”则显然不可。《庄子·天下》论关尹老聃之学曰:“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回避“有”“无”的断句,此种断句也未必一定是宋代以后的事情。*对此断句的具体讨论请参看刘静: 《道之思: 〈老子〉第一章疏解》,《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第2期。“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是说无与有同为道之一体两面,有无说出的乃是本源。
“故恒无欲以观其眇,恒有欲以观其所皦。”这两句唯独帛书本在“无欲”“有欲”后有“也”字。倘若我们遵循帛书的断句,作“恒无欲”、“恒有欲”的话,这里的“欲”显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非理性的感官欲望。我主张解释为“恒无之”、“恒有之”。眇者,窈冥也,谓视之不清;皦者,明也。*参见郑开: 《道家著作中的“视觉语词”例释》,《思想与文化》第十八辑。这里的“恒无”、“恒有”也并非仅仅指人的功夫而言,“恒”字向我们展露出本源之道的所在。此处的有无也是如上所述,乃是通贯道、物、人的。因其有而一归于无,以观众有之杳渺;因其无而开其有,以观玄无之光明。“两者”指有无,同出于道,虽名不同然指谓则一也,道也,故“两者同出,异名同谓”。
作为道之展开的有无的游戏老子在此用“玄”字来表示。首先它是指玄色,道敛万有之光一入于玄无之初。根据庞朴先生的考证,“玄”字来自水之旋流*见庞朴: 《谈玄说无》,http: //www.guoxue.com/xzcq/ddxz/pangpu/txsw.htm。,其字又象丝之旋转,《说文》谓“玄,幽远也”。水之漩涡,或丝之相缠之象,以有无言,则是指二者相绞、相合、相成、相生而相通,以观道物幽远无止境之妙也。故谓“玄之又玄”而承之以“众眇之门”。此处的“眇”既是指物,同时又指道为言。眇以言无,“众”字则暗示其有之展开。门者,开阖谓也。开而众有皆出,阖而一归于无。故“玄”同“有”“无”一样,是动态的生成。(汉简本作“玄之又玄之”,动态义更鲜明。)恒无之恒有之,即是玄之又玄之。如此则有无之游戏绵绵不断,涌摇冲荡,至于浩浩混混,远无际涯,皆一也。
从无声无形之道乃是万物本源的意义上看,一切有皆是无之有,而非有则无之本源义无从得见。道恒隐而恒显,恒无而恒有。在此意义上,当其有便是其无,当其无便是其有,此是有无不二义。如同海浪不曾离开大海,万有自无而来又一归于无。又,万有生灭如风云,风起云涌,云聚生云,云推动云,云掀起云,云遮蔽云,云覆灭云,云聚为彩,风吹云散复入于天空之玄冥静谧。然而毕竟有云无云?毕竟有风浪也无?故而庄子曰:“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知北游》)而风又从何而起,云又缘何生灭乎?皆是无中生有,万有俱无。故而大程曰:“亦无始亦无终,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处有,亦无无处无。”*程颢、程颐: 《二程遗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自物观之,云云相生,是一个变化无穷的关联的、动态的过程;自道观之,万物起灭的历史性进程却一入于玄无之初。因此道家不只是如同佛教一般地讲因缘或者关联性,它更强调这一关联性的解构和超越。众缘起灭无常,寻其因,终不可得,所道说出的却正是恒常。这并非否定关联性,而是涵具并超越之。道家也绝不只是关注历史性的生成而已,历史性本身有其本源,它最终乃是无中生有的。它因此解构并超越历史性和时间性,令其一入于永恒之无。这一超越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上升至一个最普遍的概念。反之,它乃是一种下降的姿态,到最卑下的,最柔软的所在——道是万物的本根。
综上,我把《老子》中的有无概括为:“以无无有而眇有,以有有无而明无。”
有生于无
《老子》第四十章曰:“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两段话成为后世无数由无生有之思想的源头。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这种道生万物的过程又被解释为一种“宇宙论”了。这种理论在今天已经陷入了各种困境,于是我们开始争论: 宇宙究竟有没有一个开端的“无”生出万物?既然是无,又怎么说“有无”?无则无矣,又如何生出万物?这一作为“无”的开端又该如何去想象呢?作为无难道它不是已经否定自身吗?
先来看《老子》第四十章。此处的“反”至少涵具了两层意思在其中。其一,它指关联性之中的有无相生;其二,它指的是,万有之起灭过程即是归根之静,这是从“复归”的意义上理解的“反”。因此曰:“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指示出本源的所在。(也正因此我不取“生于有,生于无”的读法。)一切有本无,又本于无,而反于无。于无有处观万有变化不息,反覆无常,所谓道之动也。是以静观动,守本而顺应。
这里的关键是,老子所说的“无”绝非仅仅是某个时间段中的空无一物。无彰显的是道之本源义。从无的本源义出发来理解“有生于无”没有任何问题。这些前文已经详述。只有当离开本源义谈论“无”之时,无才被理解为空无一物,在此它却恰恰被把持为一物了。因此难免陷入了自相矛盾: 或者有物,但此物却是“无”;或者无物,既然如此无又如何生出有?此正《庄子》所言“或使”、“莫为”之属。而庄子亦明察其执物之弊:
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远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为,疑之所假。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其有极。(《则阳》)
此段文字中《庄子》详细分析了“或使”、“莫为”如何执物的。大致人于死生之间,未免随时间之展开(庄子所谓“假”者)以逐物。谓物之往来无穷无止,此只是言语上的“无”而已;谓之有物使然(“或使”),或者无物使然(“莫为”)者,如此寻求的“本”亦只是言语上的。实则二者皆未尝离乎物以臆测道。故而曰:“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乎大方?”这里涉及到语言与道的问题,在此不便深入探讨,但有两方面值得注意。其一,道本身有言的意思在内,语言总已经把我们送上大道了;其二,道不可言。但言并非绝不可以尽道。故庄子言:“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那么何谓足言,何谓不足之言,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总之庄子还是承接老子,注重道之经验。足言乃是属于道之经验的。而不足之言远离道之经验,未免逐物。
执无以为物之弊,庄子叫做“有无”。这一说法一看就自相矛盾,但又很无奈。为说本源非一物,老子名之曰“无”,但人总难免忘却道而沉沦于物了,因此便以为有一物曰“无”。庄子因此主张“无无”。(详细见《知北游》“光耀问无”,以及《齐物论》“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等相关段落,此处不再展开。)但“无无”绝非忘却、取消道之本源义,这是现代性存在中在一种失道状态下对庄子的错误解读。庄子谓“无无”是反对将道把持为一物。恰恰是人失道之时,道才被把持为一物了。
《老子》第四十二章与此类似。它说的并非实证式的宇宙生成论或者宇宙论,即,老子并不是说有一物曰道,在时间中生出了天地万物,康德已经详言此种思维之不可能。*参看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454-B461。这种理论基于一种对时间的线性的理解,是受西学影响的结果,并不存在于中国古代思想之中。在道家思想中,时间之海就是玄冥之无本身。它是无始无终的。万物之生以道生,因此道生一、二、三、万物,无时无刻不然,在在皆是也,此即道之流行。一生二、三、万物者,亦道生万物。
实际上我以为我们必须避免对道生万物的一种宇宙论式的解读。中国思想中没有理性标准之下的ontology/epistemology/cosmology等等之类的划分。而是体用不二,这些不同层面都是圆融为一的。说“道生”就是说心性,实际上所有“道生万物”的版本都必须与人的体道状态融合才可以被理解。舍道之经验,则道隐不可见矣,又如何能见“道生万物”呢?如《齐物论》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有无并非是简单的科学实证问题,而是人之“知”中呈现的道物状态。“道之所以亏”也并非是道生成万物之后就撤离了,而是起源于人心之是非。这当然不是什么唯心论,其中万物的存在都被取消了,而归之于人之主体性。道之体验发生在任何主观/客观的二元区分之前。它意在守护道之本源。
由此我们来看一下《亘先》中的相关文本。从一种常识的角度,《亘先》似乎给我们两种相互矛盾的“宇宙论”模式。它在一开始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熟悉的由无生有的画面:
恒先无有,朴、静、虚。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自厌不自忍,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未有天地,未(第1简)有作行。出生虚静,为一若寂,梦梦静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
这似乎类似于庄子所言的“或使”。但接下来它又推翻这种观点,主张气是自生。
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恒气之(第2简)生,不独有与也。或,恒焉,生或者同焉。
如此,问题就是,倘若气是自生,恒莫生气,那么恒的位置如何来理解呢?气之自生自作是无始无终的,这似乎推翻了“恒先无有”的观点,类似于“莫为”之论。如此“恒先无有”的状态又如何理解呢?
倘若我们不把它当做纯粹的宇宙论,那么我认为它并非相互矛盾的。“恒莫生气”是说非有一物曰“恒”。“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或恒焉生或者同焉。”这句话有各种不同的断句方式。但我认为它讲的都是恒,或气之生乃是同一过程。前半句的意思,我解读为:“恒,气之生;气之生,不独有与也。”所谓的恒,就是气自生自作,它不是外在于这一过程的某物。我认为即使读作“恒气”,它要表达的意思也是如此。而开始所讲的朴、静、虚的状态并非只是宇宙论的问题,而是借此以喻体道过程。后文“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作”更体现了这一点。朴、静、虚说的是道之恒无的究竟。
- 思想与文化的其它文章
-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所见刘氏一族之义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