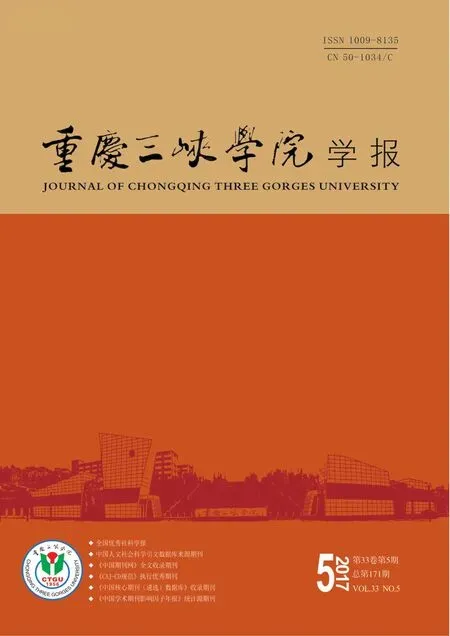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中的“尊生”实践与精神
曾婷婷
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中的“尊生”实践与精神
曾婷婷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广州 510665)
晚明“尊生”观念渐趋成熟,晚明文人注重生命内外宇宙的和谐,以审美的形式实现个体与自然的融合。晚明文人的尊生既与自然万物相互协调,表现在敬天、顺时,又始终追求审美境界。晚明旅游高度发展,文人在自然山水中安顿身心,在精巧的游具、精美的游记中彰显独特的品味,实现与自然的融合。生命个体与宇宙万物的和谐,有助于消解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深刻体现了晚明的“尊生”精神,以人性自由为指归。
晚明;尊生;审美;个体;自然;人性自由
尊生与审美是晚明生活美学文化极具特色之处,二者内在统一。晚明文化以重视现世感官享受为特征,其内在的意旨是对生命尤其是感性生命的尊视。但又不仅仅是对感性欲望的放任,更多的是对感性欲望的升华与自制,使身心处于和谐的理想状态。这不仅体现在自我生命载体的养护上,还突出体现为重视生命个体内外宇宙的协调、安适,即个体与自然的融合。本文将重点探讨后者,研究晚明文人在尊生实践中如何以审美的形式实现个体与自然的和谐。
一、晚明文人的“尊生”及其审美精神
(一)敬天、顺时的尊生实践
自我生命体无时无刻不处于自然时空之中,与自然时空发生这样那样的关联。古人谈尊生,是将自我生命体放在自然时空的框架下进行观照。人体是内宇宙,自然万物则是外宇宙,内外宇宙同一“气”。古代养生家们深谙内外宇宙同步生息之理,“是以一身之中,阴阳运用,五行相生”[1]卷十一《饮馔服食笺上》,将自我生命体的养护与宇宙阴阳四时的运作结合起来,以达到内外宇宙之间的和谐。
古代养生尤为注重不同年月、季节、时辰的自然流变对自我生命体养护的影响,对使宇宙万象发生流动变化的“时间”给予了极为细密的关注。据陈秀芬的研究,依季节进行调摄的思想早在《黄帝内经》和张家山《引书》的时代即有[2]55,这种思维后来为“师法自然”的道教所吸收,主张人的生命变化与自然变化之间有相通之处,个人修养须依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有所调整,这种四时调摄法有时也与民间的岁时宜忌观念相互结合,强调摄养行为要顺应十二个月令甚至三百六十五天的顺序而有所不同[3]294-297。一般而言,道教四时摄养法的特点乃是按照阴阳五行气运规律,将脏腑机理与四时节气排列对应,再一一纳入饮食、吐纳、导引、禁忌、房室等要求[3]296。历代均有此类养生书籍,如宋代周守忠的《养生月览》、姚称的《摄生月令》、元代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元明之交冷谦的《修龄要旨》等等。晚明的尊生书籍正是沿袭了这一传统,又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充与衍伸。尤其是高濂的《遵生八笺》,更是养生思想的集大成者,且于其中增添了可贵的审美元素,极富时代特色。明代审美化的生存从文人崇陶尊陶,不断地庚和陶渊明诗文也可见一斑[4]。
高濂《四时调摄笺》开宗明义:“时之义大矣,天下之事未有外时以成者也,故圣人与四时合其序,而《月令》一书尤养生家之不可少者。”[1]卷三《四时调摄笺·春》如春季是万物生发的时节,应“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1]卷三《四时调摄笺·春》,又需“生而勿杀,与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季之应,养生之道也”[1]卷三《四时调摄笺·春》,春季主肝脏,逆此则伤肝;夏季属火,“心气火旺,味属苦”[1]卷四《四时调摄笺·夏》,故“当夏饮食之味,宜减苦增辛以养肺。心气当呵以疏之,嘘以顺之”[1]卷四《四时调摄笺·夏》。正像高濂所说:“余录四时阴阳运用之机,而配以五脏寒温顺逆之义,因时系以方药导引之功,该日载以合宜合忌之事。”[1]卷三《四时调摄笺·春》这一点显然不脱道教四时调摄的思维,养生必须顺应四季节气变化而有所调整,即是说,内宇宙应该自觉地与外宇宙协调一致,方是养生之真谛。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虽一再强调儒家养生之理与道释养生之术的区别,但仍是以四季更迭来展开颐养,分别有春季行乐之法、夏季行乐之法、秋季行乐之法和冬季行乐之法。在各季养生法之中,也体现了依照节气特点蓄精养神的尊生精神,如“春之为令,即天地交欢之候,阴阳肆乐之时也”[5],“然当春行乐,每易过情,必留一线之余春,以度将来之酷夏”[5];夏季则“神耗气索,力难支体,如其不乐,则劳神役形,如火益热,是以性命为仇矣”[5],夏天更应注重养生,“人身之气当令闭藏于夏”[5]。
高濂与李渔可视为晚明两种不同尊生观念的代表,前者注重从五脏六腑与阴阳五行的关联去探究养生之术,通过服药、导引、按摩等方法得以实践;后者则从四季不同特点去探究养生之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更为紧密。然而,二者均极为关注节气时间的细微变化对养生的影响,其中除了有尊重自然规律的因素外,还体现出深刻的敬天思想。儒家和道家同要追求天人合一,加上道释二教在民间信仰的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人敬天畏地、泛神论的普世宗教观,人对于宇宙万象抱着一种崇敬乃至信仰的心态,从而发展出一套与万物保持顺应关系的养生方法。晚明文人喜用“尊生”,其中就包涵有尊重宇宙万象之意涵。文人的养生,是建立在对宇宙万象的顺服与敬仰之上的。因此,文人还以四时作为趋吉避凶的时间主轴,在《遵生八笺》的《四时调摄笺》中,高濂列出了各月的宜忌事项,这些宜忌事项甚至精确到了某日某时,如“正月,日、时不宜用寅,犯月建,百事不利”[1]卷三《四时调摄笺·春》,“清明日三更,以稻草缚花树上,不生刺毛虫”[1]卷三《四时调摄笺·春》,带有神秘的宗教泛神论色彩,这种天地四时月令各项宜忌的出发点是尊生和农植,即为了保护生命的安康,使其顺应有利之条件,而避开不利之天时。并且,《起居安乐笺》的“三才避忌”条,更具体地显现出泛神论色彩,对天象自然表现出一种敬畏之情,如天时诸忌:“人当勿指天为证,勿怒视日月星辰。行住坐卧莫裸体,以亵三光。勿对三光濡溺,勿月下欢淫,勿唾流星,勿久视云汉”[1]卷八《起居安乐笺下》;地道诸忌:“勿以刀杖怒掷地,勿轻掘地,深三尺即有土气,伤人。勿裸卧地上”[1]卷八《起居安乐笺下》等等,自我生命体对于宇宙万象必须怀着万分之敬畏,不怨天不怨地,并抱着感恩天地之心与其交流,方可称为“尊生”。
(二)尊生实践与审美的内在融合
晚明“四时调摄”思想最有特色的还是尊生与审美的结合,顺应四时的节气更迭,“随时叙以逸事幽赏之条,和其性灵,悦其心志”[1]卷六《四时调摄笺·冬》,以美学的方式与万物相交融。高濂《四时调摄笺》每一季都附有“逸事”和“幽赏”条;李渔撰有四季行乐之法,具体描绘四时可资游赏之景与境;程羽文《清闲供》依春夏秋冬四时,详述当季起居赏乐细节;卫泳《枕中秘》之《闲赏》篇,记录了春夏秋冬四时之风俗与自然景象。
仍以高濂《四时调摄笺》为例,在春夏秋冬每一时节的颐养法则之后,都附有“逸事”和“幽赏”条,足见高濂已正式将审美生活纳入尊生范畴,虽说“四时调摄”以生命体的养护为指归,但在养护生命的过程中却不能缺少风雅,自然情境之美能令人心旷神怡,陶情养性。尊生在晚明文人的眼里,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身体调摄,而升华为一项综合了养生、审美、宗教等面向的高级情感活动。我们看“冬时逸事”,腊八日粥、灶中点灯、馈岁别岁、守岁分岁[1]卷六《四时调摄笺·冬》等等,均是应节之风俗,每一则都有着美妙的传说与渊源,带有浓郁的人文美;而砚炉暖盒、辟寒香、却寒帘、捏凤炭、炷暖香、煮建茗、暖寒会[1]卷六《四时调摄笺·冬》等等,则是在冬日的御寒活动中寻求风雅与韵味,是顺应自然景致之尊生审美活动。毛文芳曾研究文震亨“悬画月令”条,文氏“随时悬挂,以见岁时节序”[6],依据文氏所论之悬画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趋吉避凶的目的,如岁朝宜悬挂宋画福神及古名贤相,立春宜东皇太乙图,祈雨宜古画风雨神龙春雷起蛰图等;另一类是符合节令典故人文趣味者,如元宵前后宜看灯傀儡,三月三日宜宋画真武像,移家宜葛仙移居图等,使居家生活充满典故情境之美好想象;还有一类则是顺应自然之景者,如正二月宜春游士女、梅杏山茶玉兰桃李之属,清明前后宜牡丹芍药等等,以使屋里屋外之景致和谐[7]316-318。这一研究极有新意,可见晚明将人文风俗之美与趋吉避凶的养生观相结合之时代特色。
而更有特色的,是体现于“四时幽赏”之中的尊生精神。还是以冬时为例,“高子冬时幽赏”:湖冻初晴远泛,雪霁策蹇寻梅,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山头玩赏茗花,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听雪敲竹等共12条[1]卷六《四时调摄笺·冬》。虽是严冬,万籁俱寂,寒风逼人,生命主体却不畏严寒,走向自然,用审美的眼睛追寻静寂寒冬之中的每一线生机。在晚明人的尊生观念里,自我生命体要顺应自然,但在自然面前又绝不是被动的,故能于初晴结冰的湖面“时操小舟,敲冰浪游,观冰开水路,俨若舟引长蛇,晶莹片片堆叠。家僮善击冰爿,举手铿然,声溜百步,恍若星流,或冲激破碎,状飞玉屑,大快寒眼,幽然此兴,恐人所未同”[1]卷六《四时调摄笺·冬》,主体在破冰之旅中感受到了一种人生豪情,“扣舷长歌,把酒豪举,觉我阳春满抱,白雪知音,忘却冰湖雪岸之为寒也”[1]卷六《四时调摄笺·冬》。这是一种与自然生机融合而一的豪情,在寒冬中感受到了融融春意。又有冬日寻梅、赏花、玩雪等幽趣,“踏雪溪山,寻梅林壑,忽得梅花数株,便欲傍梅席地,浮觞剧饮,沉醉酣然,梅香扑袂,不知身为花中之我,亦忘花为目中景也”[1]卷六《四时调摄笺·冬》。梅花数株,却足以让“我”沉醉,梅花顽强的生命力令人叹服。又有“山窗听雪敲竹”:“淅沥萧萧,连翩瑟瑟,声韵悠然,逸我清听”[1]卷六《四时调摄笺·冬》,雪在“我”眼里也是有生命的,声韵雅逸;然“忽尔回风交急,折竹一声,使我寒毡增冷”[1]卷六《四时调摄笺·冬》,主体重生、惜生之情于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情感细腻若此,为“竹”之折枝而伤感扼腕,与自然的惺惺相惜便是文人对“尊生”的最佳注脚。值得一提的还有晚明文人对物候与俗尚的细腻感知,春时看菜花、试新茶、啖煨笋、望桑麦、观柳、玩落花、看雨;夏时看新绿、玩蚕山、谈月、避暑、采莼、听轻雷断雨、剖莲雪藕;秋时醉红树、赏桂花、听落雁、听泉、看石笋、观海云、访菊、听芦、夜玩风潮等,极为敏锐地捕捉到了每一时节的物候与俗尚,包括花季、物产、雨季、潮涨等自然流变,并用玩味的眼光看待四时之更迭,一年四季都充满了由物候与俗尚而生之无穷趣味。可见,晚明文人的“四时幽赏”,是融尊生精神于审美雅兴之中,主体尽情感受自然万物的蓬勃生机,从而激发起生命的豪情逸兴,最终达到内外宇宙和谐一致,尊生精神的极致恰恰回归了中国儒道文化所尊崇的天人合一境界。
二、晚明文人的尊生与旅游美学
(一)晚明文人的山水游历及其特点
晚明旅游风气极其兴盛,就连平民百姓、妇女等也加入到了出游的队伍之中。游有俗游与雅游之别,文人士大夫无疑是雅游的引领者。晚明文人游风之盛可从明人游记小品中得到印证。罗筠筠认为:“对自然山水的痴情与热爱,可以说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士大夫的‘通病’。几乎每一位明代知名的文人雅士,都有记录下了他们在从自然山水中所得到的审美享受,通过他们对所游之景所进行的细致入微、栩栩如生的描绘,通过对于游览过程中的奇闻趣事的记载,不仅明代的江山美景如同呈现眼前,且能够对明人因何如此醉心于游历名山大川有深刻的理解。”[8]211晚明游记众多,从徐渭的《游五泄记》《纪游》、屠隆的《海览》、汤显祖的《青莲阁记》、张大复的《登惠山》、李日华的《礼白岳纪序》、陈继儒的《游桃花记》、袁宗道的《上方山》、袁宏道的《天目》、袁中道的《西山》、朱国桢的《山游》、王思任的《游敬亭山记》、钟惺的《中岩记》、谭元春的《三游乌龙潭》、李流芳的《游石湖小记》等单篇游记,到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谢肇淛的《百粤风土记》、王士性的《五岳游草》、袁中道的《游居柿录》等记游著作,明人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华夏大地[8]211-212。那么,自然山水游历与尊生有何关联呢?
高濂《遵生八笺》的《起居安乐笺》有言:“闲溪山逸游者,为得安乐欢”[1]卷七《起居安乐笺上》,“四时游冶,一岁韶华,毋令过眼成空,当自偷闲寻乐,已矣乎!吾生几何?胡为哉每怀不足?达者悟言,于斯有感”[1]卷八《起居安乐笺下》。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高濂明确将自然山水游历当作尊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二是自我生命在山水游历中可以获得身心舒展的快乐,当珍惜光阴,及时行乐。单就此而言,已与晚明之前的文人有所不同。魏晋以后,文人雅士多喜登临胜景,吟诗作赋,正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唐代以后,山水游记更是数不胜数。但他们游历山水,写作游记,不过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借山水游记发牢骚,抒发人生感慨,正如奚又溥在《徐霞客游记》的序中说:“夫司马柳州以游为文者也,然子厚永州记游诸作,不过借一丘一壑,以自写其胸中块垒奇崛之思,非游之大观也。”[9]卷十下,附录相对于此,晚明文人的山水游历与游记则更多是审美与尊生的面向,游历的心态也增添了逸乐的成分。简单地说,晚明文人的山水游历是要玩赏、寻乐,在自然山水中怡情养性,安顿自我生命。
李渔在《颐养部》“夏季行乐之法”中写道:“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夏不谒客,亦无客至,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可谓极人间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5]回忆起这段与自然相伴、无拘无束的生活,李渔的眷恋之情无以言表,“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5]。后李渔为生活所迫,迁居城市,“酬应日纷,虽无利欲熏人,亦觉浮名致累”[5],由此生发无尽感慨:“人非铁石,奚堪磨杵作针?寿岂泥沙,不禁委尘入土。”[5]隐居山水之时的李渔,正遭遇了科举的接连失利与国破家亡的动乱,然而这不幸的际遇却给了他一个回归自我生命的机会,与自然山水的交流是平等的、无拘无束又充满闲情逸致的,主体与自然完全融合而一,抛却了世俗的是非纷扰,直面一个本真自在的自我。李渔对于这段生活颇有因祸得福的感受,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富贵荣华,更多与安乐、惬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与自然的交融,令人真正回归了自我,这也正是“尊生”的意义所在。
晚明文人热爱游历山水,热爱与自然融合而一,一方面是结交四方好友,开拓视野,更重要的则是看重自然山水给予他们都市生活所追寻不到的东西。袁中道的游记中就颇多这类感叹:“家累逼迫,外缘应酬,熟客嬲扰,了无一息之闲,以此欲远游。一者,名山胜水,可以涤浣俗肠;二者,吴越间多精舍,可以安坐读书;三者,学问虽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见境生情,触途成滞处尚多;或遇名师胜友,借其雨露之润,胎骨所带习气,易于融化;比之降伏禁制,其功百倍,此予之所以不敢怀安也。”[10]外集卷一《游居柿录》袁中道深惧世事的纷扰,官场的束缚、家事的烦恼、生活的琐事、人心的虚伪等等都让他感到疲惫、无聊甚至厌烦,“了无一息之闲”,自然的清新却能令人涤浣俗肠,寻回真实的自我,身心得到完全的释放。袁中道受兄长袁宏道的影响很深,崇尚个性自由,性格豪放不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无拘无束的名士脾气,但比起袁宏道,袁中道的仕途颇为坎坷,科场屡败,故其性格又多了几分感慨与放荡。正如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所说:“盖弟既不得意于时,多感慨;又性喜繁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11]卷一袁中道纵情声色,又为血疾所困,时常处于“骨刚”与“情腻”的矛盾之中①,他坦言爱好舟居生活的重要原因在于借此断绝色欲,延长寿命。可见,在人欲横流的晚明社会,回归自然也是一种自觉调控欲望、尊生养生的手段,晚明文人将声色欲望转移至自然山水的赏玩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命智慧。
(二)晚明文人的“游具”及其精神旨归
晚明文人精致的山水游历生活,从他们对游具的精心选择上可见一斑。屠隆的《考槃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以及文震亨的《长物志》都专门提到游具。游具,即“济胜之具”,是文人出游时必备事具的总和。譬如高濂的“游具”就包括:竹冠、披云巾、道服、文履、道扇、拂尘、云舄、竹杖、瘿杯、瘿瓢、斗笠、葫芦、药篮、棋篮、诗筒葵笺、韵牌、叶笺、坐毡、衣匣、便轿、轻舟、叠桌、提盒、提炉、备具匣、酒樽等等[1]卷八《起居安乐笺下》。舟船是文人重要的出行工具,故他们对游具的叙述中均有提及,由于本章谈“尊生”,故仍以高濂《遵生八笺》的描述为讨论重点。高濂对“轻舟”的描述是:“长可二丈有余,头阔四尺,内容宾主六人,僮仆四人。中仓四柱结顶,幔以篷簟,更用布幕走檐罩之。两旁朱栏,栏内以布绢作帐,用蔽东西日色,无日则悬钩高卷。中置桌凳。后仓以蓝布作一长幔,两边走檐,前缚中仓柱头,后缚船尾钉两圈处,以蔽僮仆风日,更着茶炉,烟起惚若图画中一孤航也。”[1]卷八《起居安乐笺下》高濂笔下的“轻舟”虽简朴,却很素雅,他特别提到中仓朱栏内要有布绢作帐,后仓要有蓝布作长幔,以蔽风日;当轻舟航行于湖河之上时,起灶煮茶,又能享受一种“烟起惚若图画中一孤航”的萧索之情。从“轻舟”的设计,可知高濂所强调的既有舟船的舒适以及感官的享乐,又有借此游具融于自然的精神追求。高濂的“游具”种类繁多,细致周全,“竹冠、披云巾、道服、文履、道扇、拂尘、云舄、竹杖、瘿杯、瘿瓢、斗笠、葫芦、药篮”将游乐中的文人装扮成一个野逸、超然的山人形象;“坐毡、衣匣、便轿、轻舟、叠桌、提盒、提炉、备具匣、酒樽”将家居生活的日用必需品均准备周全,使文人在旅途中也能享受到安逸舒适的生活;而更有意思的是文人在游历途中仍不忘带上“棋篮、诗筒葵笺、韵牌、叶笺”等“长物”,以备随时随地的逸兴勃发。如“叶笺”:“余作叶笺三种,以蜡板砑肖叶纹,用剪裁成,红色者肖红叶,绿色者肖蕉叶,黄色者肖贝叶,皆取闽中罗纹长笺为之,此亦山人寄兴岑寂所为。若山游偶得绝句,书叶投空,随风飞扬,泛舟付之中流,逐水浮沉,自有许多幽趣。”[1]卷八《起居安乐笺下》三种颜色的叶笺,分别酷肖红叶、蕉叶、贝叶,游历途中逸兴忽来,则将好词佳句书于叶笺之上,令其随风飞扬,或逐水浮沉。晚明人玩得如此清雅、尽兴和投入!
高濂种类齐全的“游具”,为的正是令游冶文人更舒适、雅致、超然地融入自然,这从侧面深刻反映出晚明文人对自由与尊生的炽热追求,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对社会政治价值的回避与对个体自我价值的重新体认。张维昭指出,晚明文人内心渴求的人性自由大致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机能,认为心是自由的,无拘无束,可上天入地;其二则是人的生理内驱力,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肯定男女之间热烈的感情,极力讴歌世俗生活的享乐。虽然说晚明心学的兴起解除了理学的桎梏,但晚明文人的放诞任真只能摆脱自身内在的拘泥,却无法解除外在的束缚。皇帝的长期怠政、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争、朝臣间的彼此倾轧与黍离麦秀的苍凉、流离失所的惨痛交织在一起,严重威胁着晚明文人的生存。晚明文人急需重构新的生命意识与价值以远离晚明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对生命的戕害与扼杀[12]33-34。于是,文人选择了回归自然,在自然山水中娱情养志,安顿自我,他们尽情投入于游具的选择、游记的创作之中,令外逐的心灵得以回归并观照自我。性好山水的袁宏道说:“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借山水之奇观,发耳目之昏聩;假河海之渺论,驱肠胃之尘土。”[11]卷二十一对政治和社会失去热情与希望的文人转而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精神慰藉与寄托,自然山水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更启人以精神高洁。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晚明文人的“尊生”,极为重视个体与自然的和谐,追求生命内外宇宙之间的高度融合。他们的尊生实践顺应自然,又始终贯穿着审美精神。自然山水是晚明文人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尊生”成为晚明旅游美学的精神主旨。而晚明文人的“尊生”,包含了肉体与心灵两个层面,而当以人性自由为旨归。容身自然山水之中有助于消解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主体自我身心的和谐以及自我生命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共同塑就了晚明的尊生精神。
[1] 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M].明万历刻本.
[2] 陈秀芬.养生与修身[M].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
[3] 郝勤,杨光文.道在养生:道教长寿术[M].台北: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4] 邓富华.明代“和陶集”考略[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2):58-61.
[5] 李渔.闲情偶寄:卷十五·颐养部[M].清康熙刻本.
[6] 文震亨.长物志:卷六·几榻[M].清粤雅堂丛书本.
[7] 毛文芳.晚明闲赏美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
[8] 罗筠筠.灵与趣的意境——晚明小品文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9]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袁中道.珂雪斋集[M].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11]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M].明崇祯刊本.
[12] 张维昭.悖离与回归——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现代观照[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郑宗荣)
①“骨刚情腻”的矛盾,语出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三《东游记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骨刚则恒欲逃世,而情腻则又不能无求于世”,之不能终归于隐,并非“不肯高举”,而是“为腻情所牵,故复与世相逐”,说到底还是不能耐寂寞:既需声色之娱,又求口腹之乐,尤不能忘情世间的清誉令名。
The Practice and Spirit of “Living” in Literati’s Daily Aesthetic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ZENG Tingting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concept of “living”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The literati paid attention to the harmony of inner and outer universe, and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and nature in the form of aesthetic. It was then that the “living” practice of literati is in harmony with all things in nature, and is manifested in respect of heaven and time and pursues the aesthetic realm always. Tourism was highly develop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literati put themselves into the natural landscape in order to settle the body and mind, and they highlight the unique taste in the exquisite tourist equipment and travels, in order to achieve integration with nature. The harmony of life and universe always helps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hysical body and soul, matter and spirit, profoundly embodies the “living” spiri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aims at human freed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ving” concept; aesthetic; individual; nature; human freedom
I262
A
1009-8135(2017)05-0064-06
2017-06-03
曾婷婷(1980—),女,广东梅州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文艺美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文论与‘去黑格尔化’研究”(13BZW0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