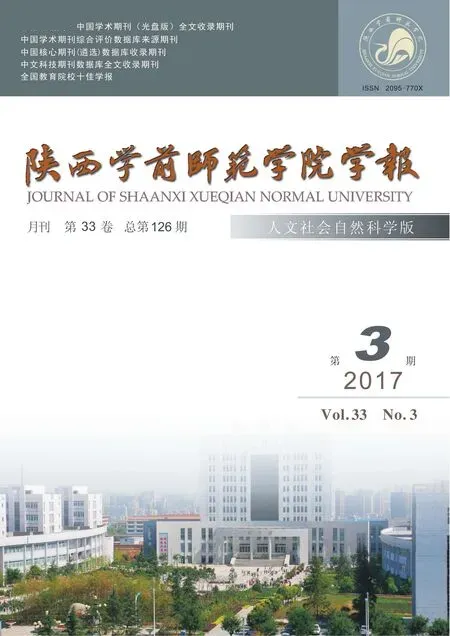“红色经典”文学现代性扩张的美学审视
张 静,陈芳清歌,赵伯飞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文学艺术研究

“红色经典”文学现代性扩张的美学审视
张 静,陈芳清歌,赵伯飞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现代性是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实践,有助于推进民族国家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红色经典”文学建构式、重构式改编获得成功的原因即尊重原著精神,而解构式的改编则基本不被大众所认可。因为解构式的改编往往采用过分扩大英雄人物七情六欲,甚至瓦解人物信仰等方式迎合大众。事实上,“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应该既要把握住原作所表现的核心精神,又要体现出现代人的审美追求、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红色经典”的生命力,将“红色经典”文学不断传承下去。
“红色经典”文学;现代性扩张;改编
现代性是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实践,有助于推进民族国家的发展。英国文化之父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我们用‘现代’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导向某些独特性或社会特征出现的单一过程,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性’的定义。”[1]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包括“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的衰微,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展现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个人主义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冲动。”[1]而现代性扩张指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原本的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从而产生向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挣脱和断裂。
正是因为“现代性”涵盖了哲学、经济、政治、审美、文学等多种领域,从而使现代性扩张有了较为宽泛的含义。“红色经典文学现代性扩张是指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对传统“红色经典”文学进行的体裁的变更及其内容的扩展,其主要表现在对其文本改编的重构和建构上,并对文本植入更多现代化的气息。
一、文学的现代性扩张分析
1992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加快了中国商业化进程,我国开始步入消费型社会。“消费社会却是一个抵抗‘思想’的时代,它打破了人们关于经典的种种幻象,消费文化的颠覆性在于依靠大众并且借助媒体的力量不断散播着当世的情绪、即兴意识,于是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消费时代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法则更是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了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2]在大众消费的影响下,文学生产变得功利化、消费化,更加注重市场回报。“红色经典”文学是消费时代下文学生产的好文本,它塑造的典型人物和紧凑情节已深深刻在国人心中,具有巨大的市场号召力,符合中国的审美接受心理。不论是重构、建构改编“红色经典”文学,其中都增添了不少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元素,比如爱情戏份、武打场面、离奇情节等等。所以,许多现代电影、电视剧编剧都乐于对“红色经典”文本进行改编。他们期望自己生产的文艺作品在拥有低制作成本和低市场风险率的同时,收获中老年怀旧人群和新一代年轻人两类不同观众,从而达到最佳的市场利益。
(一) “红色经典”文学的重构
当一部文学经典被社会普遍接受,是不可以被随意重构、建构的,因为历史不能被随意消费,不能用现代代替整个历史过程。事实上,读者阅读文学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再创作,他们在内心产生的不同理解与感悟,是一种对作品的重构行为。不同时期的人们阅读经典时,都会用自己所处环境形成的特定思想来进行解读和阐释,这个过程必然会对文本加入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元素,忽略认为掉难以理解的部分。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对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3]具体体现为对小说人物的人性化思考,增添更多人性叙事和文化叙事,通过丰富原作实现充分深化改编的意义。“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一方面受到了消费时代的影响,另一方面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全球化社会的迅速发展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慢慢失去“红色”信仰的人们出现信仰危机,这时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来让民众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人在本体论的维度上,始终存在着偶像崇拜的内在需求。”[4]重构“红色经典”文学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红色记忆,重回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岁月,其所蕴含的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奉献牺牲精神是现代社会文化建设所需要的。
“关注人的生活境遇、内心困惑和人性深度,从中探寻主流价值在当代的实际意义,这种重构方式具有现代性想象的审美特征。”[5]电视剧《红旗谱》,相比于原作人物更鲜活,主线更突出,是“红色经典”文学重构改变的成功之作。改变剧导演胡春桐曾说:“原著的‘红色精神是绝对不能动的我们牢牢把握‘志士慷慨洒热血,只为百姓谋稻粱’的主题精神,让该剧具有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他的成功在于很好地保留了原著的红色精神,并合理地拓展了人物,故事性更强,人物性格更为鲜明。电视剧中朱老忠的扮演者吴京安,表演真实可信,注重挖掘人物内心世界,没有过分戏剧夸张。新加的“比武”、“大闹冯兰池寿宴”几场戏,更加突出朱老忠作为农民革命先行者的英雄形象。而通过新加人物儿媳桂仙,更加衬托出了冯老兰人性中的恶毒荒淫。重构改编的《红旗谱》电视剧用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释忠诚、信仰、情感等社会主流价值形态的意义,增强了小说人物的历史厚重感,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
(二)“红色经典”文学的建构
“建构式的影视改编是最能尊重原作的改变方式。所谓建构,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尊重原作的主要情节、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二是重视原作所体现出来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内涵。”[6]这样的改编方式只是为了对其包含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效宣传,意味着对原作最大程度的尊重。基于革命理想主义建构的“红色经典”电视剧,是对当今社会人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建构的良好资源,有助于巩固民族红色文化,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红色经典”文学是当时那段革命历史和英雄感恩情绪建构的产物,是革命文化建构的重要部分。现代社会虽然不需要革命,但革命历史小说中蕴含的深刻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信仰是我们这个时代严重缺失的。此时,对原作还原度极高的“红色经典”电视剧,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行为,实现了对消费时代人们建构信仰的目的。
电影《青春之歌》是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上映之后获得了来自各界的赞誉,并多次在国外展映,产生了巨大影响。导演崔嵬是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他带着过来人的真实感受拍这部影片,所以对原作还原度极高。演员们的出色表演,都能恰如其分的诠释角色内涵,增添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感。主演谢芳通过自己细致、生动、准确的表演,不负众望,实现了与小说林道静形象的完美重合。小说中描述林道静的眼睛又大又黑,而扮演者谢芳眼睛明亮、眼神犀利,加上导演使用蜡烛灯光对人物眼眸刻画,使得电影中的林道静眼睛更为灵性,能够表达出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青春之歌》电影情节生动,表现真实感人,很好的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通过电影,我们看到和余永泽的爱情并没有让林道静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于是热爱自由、不甘平庸的她在受到共产党人启蒙和引导后,毅然选择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相结合,最终实现了由冲动的小资产阶级向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事实上,该影片在改编过程中也进行了一定处理,针对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问题,导演特意加重了主人公在走上革命道路后“与工农相结合”的情节表现。这部分改编更突出了原作表现的核心思想,也满足了观众对于林道静成长之后生活的幻想。尽管现代社会处于和平时期,但在今天信仰有所缺失的社会里,更需要我们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精神。而通过学习“红色经典”文学中人物的革命热情、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可以指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现代性扩张中的审美异化
在当今社会文艺“大众化”发展的驱动下,“红色经典”文学改编作品中表现出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和过去相比已明显不同,趋于泛人性化、平民化。而原作中所蕴含的审美观念在现代性扩张中也逐渐发生了异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红色经典”文学在现代性扩张中的审美异化并不是一种发展,因为“所谓‘真正的发展’是以‘真实的自我’(即所谓‘全部的过去’)为前提的,只有建立在自我全部的真实基础上的创造,才是实质性的创造。异化了的艺术是建立在异化了的人格——即被毁坏的‘过去’或支离破碎的‘过去’和异化了的对象基础上的,因此,它既便就是与以往的艺术风格有什么不同,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发展。”[7]
(一)“非人化”到“泛人性化”
20世纪80年代,“红色经典”文学因为其题材的固定化,人物脸谱化,逐渐被广大人民所冷落。但是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红色经典”改编剧又将大众的眼光吸引了回来。然而,“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人物缺乏丰富人性,是“高大全”的理想英雄,他们的基本人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受到作家压制,被塑造成了一个个“非人”的人。所以,还原人性真实成为了“红色经典”文学的改编趋势,改编者着重挖掘英雄人物平凡的一面。开始忽视他们身上的真善人性,在再创作过程中加入了很多世俗的、情欲的描写。比如杨子荣被改编成了一个语言浮夸、极具痞气的人,他甚至多了一个初恋情人;江姐同叛徒甫志高产生了暧昧情愫……改编剧将英雄人物“平民化”,面对死亡会产生害怕、见到美女会觉得心动,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奉献精神变成了调侃对象,身上被赋予了各种坏毛病。在此类改编剧中,“人性化”过度扩大成了“泛人性化”,以所谓人的自然性否定人的社会性,严重误导了社会道德价值观。“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后的“泛人性化”和“滥情化”,颠覆了作品原本昂扬的革命激情,借“人性化”之名解构了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使“红色经典”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
(二)“阶级文化”到“共享文化”
“红色经典”文学原本是面对广大工农兵群体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影视作品大都也是以革命历史事件为主题的。那时的“红色经典”文学是社会主流文化——“红色”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时代,艺术商品化使得“红色经典”文学改编走上了“平民化”、“大众化”的道路。上至中老年下至青少年人成为了改编者的目标人群而在此时,“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反映出的是一种共享文化。改编后的《红色娘子军》被观众认为战争味不足,其增加了7位年轻美丽的女主角,使它像一部青春偶像剧。这部电视剧除了沿用小说主要人物的姓名之外,还增添了许多故事情节,比如黎妹洗澡、南洋妹与军医在刑场相拥热吻等情节。对于原作中潜在的一条爱情线索——吴琼花与洪长青的感情,改编剧却将这条个人私情变成了故事情节的主线。事实上,两人在原作中始终保持着同志关系,谈论的更多是革命话题,并没有过多的感情纠葛。因此,改编后的“红色经典”从阶级文化变为共享文化,原本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作品变成了主动亲近更多人的市民作品。
(三)“革命主线”到“突出情感”
“红色经典”文学等一系列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史实是故事的主线。通过表现英雄人物在战争中的勇猛形象,突出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色经典”改编剧的“人性化”淡化了作品的革命色彩和政治说教味,使得故事在内容上更注重人物情感的表达,英雄人物的人性更加丰富,故事中也没有了脸谱化的正反面人物。“红色经典”改编更加注重人们对自我的认知,用大量描写人的情感世界的变化,体现再创作者对原作人物情感的扩张,从而折射出现代社会的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这种改编思路下,《红色娘子军》从一部反映旧社会妇女在反抗和斗争中成长的故事变成了众多漂亮女主角的青春偶像剧,她们的情感成为了电视剧情节发展的主线;《林海雪原》改编剧对杨子荣叙述从英雄视角转向了平民视角,他因为自己救初恋情人儿子的私情中弹身亡,变成了一个有着基本生理情欲的普通人。这种注重突出情感的“红色经典”改编剧,内容上表现为对原作的背景时代不够尊重,手法上对历史真实的处理也很随意。这种对“红色经典”文学的任意“创新”,不但使经典变味,而且伤害了民族情感。
三、恶搞“红色经典”文学
自“恶搞文化”在中国兴起,恶搞对象从名人照片、古典诗词到经典著作,一步步冲击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和文化底线。随着恶搞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有些人开始用讽刺、戏谑、调侃、无厘头的语言肆意亵渎“红色经典”文学和其中的英雄人物,从编造和炒作雷锋的初恋女友到创作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这股恶搞之风已不仅仅是带给生活轻松和幽默的“调味剂”,事实上完全超越了新娱乐的范畴。这种解构“红色经典”的行为充分反映了现代人精神信仰的缺失,印证着人们走向欲望化、肤浅化、娱乐化。
(一)“红色经典”恶搞现象
“红色经典”文学改编中,建构式、重构式的改编因为尊重原著精神往往能获得成功,而解构式的改编则基本不被大众认可。解构式改编是站在淡化原作所要表现的主流意识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解、重组,拼合成改编者期望展现的形态。它往往采用过分扩大英雄人物七情六欲,甚至瓦解人物信仰等方式迎合大众,通常意味着被解构作品所代表的社会主流文化的衰落。
“恶搞”是解构的一种表现形式,“恶搞”来源于日本游戏界,后逐渐演变为一种互联网文化,成为一种颠覆和批判的思维方式。恶搞的题材可以是生活中的任何实体,人们可以用游戏、Flash、电影短片等形式在现有的图片、文艺作品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将各种搞笑元素融入原作,进行诙谐、讽刺、夸张、恶作剧的解构。恶搞反映了人们对快乐的追求,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恶搞“红色经典”文学,以“去教化”主义和去精英主义为解构策略来戏说英雄人物,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种解构,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否定。在我国,《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可谓恶搞鼻祖,胡戈对电影《无极》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栏目《中国法治报道》进行了重新剪辑,重新赋予电影人物不同的身份,如模特、城管等,颠覆原作情节,演绎了一场无厘头的杀人案件侦破过程。这一部20分钟长的网络恶搞短片,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胡戈之后,更多年轻人开始了对各类文艺作品的恶搞。胡倒戈就是其中一员,他制作的视频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社会风波。
短片中,革命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个做着明星梦、发财梦的青年,他的父亲是地产商潘石屹,母亲的梦中情人是李咏。潘冬子想参加第12届青年歌手大赛,并意图通过报名“民族唱法”上“春晚”。在得到了亲朋好友的支持后,他通过送礼、摆平评委等手段,一步步走上星光大道。对此,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人表示,《潘冬子参赛记》的恶搞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不同,后者调侃的对象是商业娱乐片,暂且可以容忍。但《闪闪的红星》是公认的红色经典,其内容与青年歌手大赛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改编是对传统的颠覆和反叛,只能是网络垃圾。随后,胡倒戈对八一厂进行了道歉,也表示认同“红色经典”不容恶搞。
(二)人性化过度扩大
“红色经典”文学在改编的过程中,每一个再创作者在处理上都会对小说人物人性进行扩大。像《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优秀的改编影视剧能将人物的“人性化”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度,让观众觉得人物形象更为饱满、鲜活。但是在恶搞“红色经典”作品中,英雄人物往往因蓄意迎合大众趣味而被歪曲。原作中的英雄人物是没有七情六欲的,他们的革命信仰能战胜个人世俗情感,而在恶搞剧中,“红色经典”文学所蕴含的革命理想被去人性化。英雄变得世俗、利益,失去了原本的革命信仰和英雄主义精神,原本理想人性变成了有限的人性。
《林海雪原》改编电视剧将一部革命历史文学作品变成了浪漫言情剧“林海情缘”,小说中原本隐晦的爱情描写,在电视剧中被扩大强化。英雄人物除了人的本性被丰富之外,伦理情欲更是被无限扩大。如苏军少校萨沙、白茹、少剑波混乱的“三角恋”关系;杨子荣多了一个“旧情人”槐花,而槐花的现任丈夫是老土匪,槐花的儿子是座山雕的养子,槐花本人曾被栾平强奸过。可以说,杨子荣几乎与所有敌人一起因一个女人卷入了情天恨海之中。电视剧中,智取威虎山成为主体框架,原著中的线性结构被抛弃,其他片段中的人物出场顺序被打乱,改编剧根据原作的线索加入自己创造的人物,重新编织起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杨子荣在威虎山上一方面要经受住蝴蝶迷的情色考验,另一方面,要想尽办法解救情人的儿子,结果自己不幸在这次行动中牺牲。这部《林海雪原》电视剧由于涉及过多感情纠葛,从播出起便受到广大观众的反感,最终被停播。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提到了“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创作者在改编过程中,没有体会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作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坏境,没有尊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的作品认知,片面追求市场利益和商业价值,过度扩大人物的人性化。“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爱情戏;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同时,随意的扩大作品内容,淡化原作情节,都严重影响了“红色经典”文学的严肃性和经典性。
(三)恶搞“红色经典”是对历史的亵渎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力决定传播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红色经典”文学若想被脱离了当时历史环境的现代社会人广为接受,电影、电视剧改编是最便捷有效的一条道路。“红色经典”文学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蕴含中国民族的英雄情结,它可以被改编,但不能成为恶搞剧的题材。恶搞“红色经典”首先是对历史的亵渎行为,歪曲历史、消解英雄人物信仰,会严重伤害人民感情;其次它有可能毒害青少年,青少年没有经历过那段真实历史,很多人也没有阅读过原作,如果他们认可新编、恶搞的作品,并进行盲目模仿,可能会造成他们漠视中国革命历史,严重者会给一生带来消极影响。最后,恶搞“红色经典”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践踏,对英雄人物的亵渎,更是对红色文化的颠覆,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反叛。在改编剧作者眼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道德理性、革命信仰早已消失殆尽,只剩下金钱和利益。
“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严肃的,经过长期历史考验、洗刷留下来的经典,这些经典的东西我们是不允许随意的娱乐化,几千年灿烂文明留来的遗存,我们也不允许庸俗化。”胡戈恶搞《无极》被原片导演陈凯歌怒告侵权、胡倒戈《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被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求道歉、《林海雪原》电视剧被广电总局勒令停播,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接受恶搞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破坏,不允许冲击社会道德体系的恶意改编存在。事实上,“红色经典”文学是可以被改编的,《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为改编的非常成功,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得到了主流文化和观众的双重认可。
改编是一种创新,创作者在改编过程中应当坚持三大原则:尊重历史、尊重原著、尊重英雄。若想成功的改编“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剧作者应带着感情和理性阅读原作,在改编时时刻谨记自己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在“尊重历史、尊重原著、尊重英雄”的同时,考虑时代变迁的影响,融入“审美现代性”以适应观众的娱乐化需求。在改编时坚持三个“尊重”确保改编剧能勾起老一辈观众的红色记忆,融入“审美现代性”是为了在注重教育功能的同时兼顾娱乐功能。总而言之,“红色经典”文学改编既要把握住原作所表现的核心精神,又要体现出现代人的审美追求、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红色经典”的生命力,将“红色经典”文学不断传承下去。
[1] Stuart Hall&Bram Gieben,eds.Formation of Modernity[M].Cambridge:Polity,1992.
[2] 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J].文学评论,2006(5).
[3] 聂珍钊.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J].文艺研究,2013(5).
[4] 王妮娜.“红色经典”热与当代时代语境下的信仰焦虑[J].理论导刊,2005(4).
[5] 丁亚平,董茜.“红色题材”电视剧的现代审美趋向[J].中国艺术报,2010(8).
[6] 任志明,黄淑敏.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再审视[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6(6).
[7] 刘星:现代性与审美异化[J].美术,2003(12).
[责任编辑 李兆平]
The Modernity Extension of Red Classics Literary
ZHANGIing,CHENFang-qing-ge,ZHAOBo-fei
(Xi’anPeihuaUniversity,Xi’an710100,China)
Modernity is a practice after people's self-consciousness acknowledgement. It help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ta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Red Classics Literary success. The paper thought it is because of respect of the original works spirit. While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works were not successful,which is excessively used in exaggerating the hero desires,and even disintegrating their faithful characters to cater to the public. In fact,the Red Classics Literature adaptations should not only respect the original spirit,but also reflects the modern people's aesthetic pursuit and value judgment.
Red Classics Literature;Modernity;Adaptation
2016-10-25;
2016-11-08
张静,女,陕西长安人,西安培华学院中文系系主任,讲师;陈芳清歌,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赵伯飞,男,广东新会人,西安培华学院教授。
G206.4
A
2095-770X(2017)03-0065-05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3.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