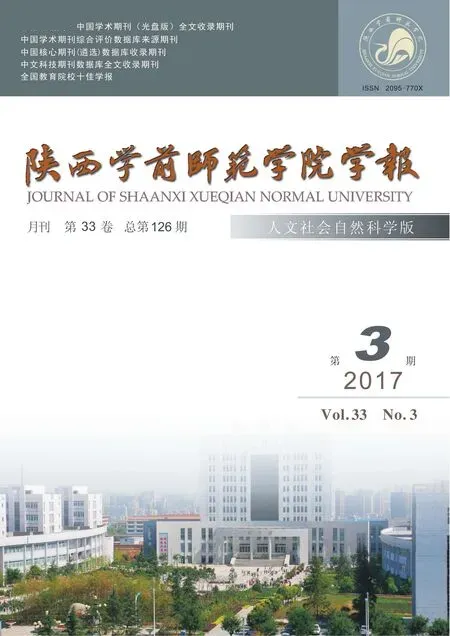《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
刘茸茸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文学艺术研究

《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
刘茸茸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野草》作为鲁迅内涵最复杂、丰富的作品,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大都以相当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解读。1930年代以来各时期的大陆学者对《野草》的解读凸显出不同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个时代的文学史塑造出的鲁迅形象;而海外学者以其新颖的解读视角为文学史叙述带来了世界性的宏大视角。通过梳理各个时代和不同语境下《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能够揭示文学史叙述模式和解读视角的某些内在规律,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现代文学史;《野草》;鲁迅;叙述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自胡适《白话文学五十年》问世以来,几乎每一本文学史都给予鲁迅崇高的地位和相当的篇幅,《呐喊》、《彷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已是几代学人普遍的共识。《野草》作为鲁迅创作于1924年至1926年彷徨期的一部散文诗集,是反映鲁迅矛盾、苦闷、复杂心理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是“鲁迅最特异、最深邃也最复杂的作品”[1],在鲁迅个人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1925年,章依萍提到,鲁迅明确说过“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2]13,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野草》以独具一格的体裁、深邃复杂的内涵堪称现代散文诗的经典之作,自问世以来,引起了研究者异常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因此,考察《野草》在不同时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正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个时代的文学史塑造出的鲁迅形象,从而凸显出文学史叙述的某些内在规律,为今后的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一
最早在文学史著作中提及《野草》的是1932年4月出版的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在论述鲁迅的小品文时提到“他的《野草》则是含有哲理的诗的散文”[3]208,虽然只有简单的一句,但作者的态度比较中肯,并未流露出明显的褒贬倾向。真正使《野草》获得比较清晰呈现的,是1933出版的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和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较早的新文学史专论,深受30年代左翼文学的影响,将新文学定义为“大多数人所能享受的很普遍的作品”,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肯定社会变革对文学流变起着主导作用,“当着一个社会快要临着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压迫阶级凌虐的快要铤而走险,素来是一种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快要成为具体的表现的时候,在一般人尚未感受得十分迫切,而在神经质的文艺家却已预先感受着。先把民众的痛苦抖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先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由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4]13因此王哲甫的一些观点难免烙上左翼思潮的印记,具有文学的大众化倾向,对普罗文学、大众文学持推崇的态度。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试图建设较为开放的文学观,在具体介绍和评论作家作品时,能够给予大致相当的篇幅,不求经典化,尽量避免倾向性。即便如此,王哲甫将鲁迅列为新文学第一人,给予了鲁迅较为高的评价,并且将鲁迅的作品定位在“国民性”批判这一角度,认为他“把‘老大中国’的沉疴很详细的珍视出来”。但是他没能给予《野草》单独的叙述,只是在叙述鲁迅散文的文字风格时提及,用“巧譬善喻的方法,精切有力的成语”[4]176来评价《野草》的文字风格,对其思想内涵则忽略而过。王哲甫避而不谈《野草》,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野草》不符合王所推崇的普罗文学和大众文学而被忽视,一方面可能是评价《野草》将不可避免地使叙述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至少可以看出王哲甫对《野草》是不甚重视的。
如果说王哲甫在文学史叙述中,有意或无意忽略了《野草》在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那么,贺凯则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对《野草》作了正面解读。他比王哲甫更加凸显了“革命性”,对《阿Q正传》的定论从王哲甫强调的“国民性”转移到“反封建”的视角上,“阿Q代表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他是被封建势力的豪绅所压迫”,“阿Q正传是含泪的讥讽封建势力”[5]297-298。正是在阶级观的制约下,贺凯将《野草》解读为鲁迅“彷徨”、“朦胧”时期产生的悲观人生的反映,“鲁迅虽然‘呐喊’‘彷徨’,依然感到人间的阴森黑暗,找不到出路,这是他没有认识了社会,没有握着时代的轮轴,因此在‘五卅’以后的革命高潮期中,而我们的鲁迅还是‘朦胧’着,感到生命的空虚,寂寞,渺茫,灰暗,于是产生了他的悲观人生——《野草》”[5]301。将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作为叙述的落脚点,这一观念在左翼话语叙述模式中具有代表性,是“悲观人生反映”此类叙述模式的滥觞。在贺凯设定的文学史视角中,“反封建”成为鲁迅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而与此不甚相符的《野草》,则是鲁迅“没有握着时代轮轴”的“朦胧”、悲观的产物。因此,在《新文学运动史》中较为多维、丰富的鲁迅形象,在贺凯的《纲要》中逐渐删减和统一在单一的“反封建”的革命话语中,这是鲁迅形象在文学史中被神化和政治化的一个信号。
二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呈现出向主流意识形态紧密靠拢的特点,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瑶195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刘绶松195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国新文学史稿》于1951已初具规模,作者在1951年撰写的《初版自序》中提到:“本书是著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程的讲稿”。由此可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实有49年以后新文学史开创之功,对此后的新文学史书写具有深远的影响。与这一时期大多数新文学史著作一样,《史稿》和《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文学史的叙述更像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阐释和论证。王瑶在《绪论》里写道 :“新文学是‘五四’开始的新文化革命的主要旗帜”,“新文化是在新的物质力量的基础上,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新的觉醒,是思想领域的革命”[6]5。《绪论》多次引用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其文学史写作的基点不言而喻。刘绶松则在《绪论》开头旗帜鲜明的表明:“在任何时代被写下来的历史书籍,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都是为某一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的”[7]绪论。
但是,《史稿》并没有用大量的篇幅叙述《野草》,其第五章《收获丰富的散文》中,第一节用“匕首与投枪”作为标题来形容鲁迅散文的风格,王瑶占用了大部分篇幅来叙述鲁迅的杂文,而称《野草》“是诗的结晶,在悲凉之感中仍透露着坚韧的战斗性,文字用了象征,用了重叠,来凝结和强调着悲愤的声音”[6]145。只用了短短几行从“战斗性”这一角度作了简要叙述,未做进一步阐释,值得注意的是,王瑶与王哲甫等人一样,都选择了《这样的战士》来作为其叙事的例证,而避免选择难以从“战斗性”角度来阐释的篇什,从而规避了正面叙述《野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野草》蕴含的哲理性、矛盾性则整体处于被遗忘被遮蔽的状态,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叙述本身就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阐释,文学史对鲁迅形象的阐释必须努力向“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靠拢,尽量符合毛泽东称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一定位[8]698。无疑,《野草》是最能够表露鲁迅思想世界复杂、矛盾的作品,王瑶对《野草》叙述的一带而过,正体现了这一代学者在政治话语藩篱下的尴尬抉择。
相比《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更凸显了新文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对《野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正面的定位。一方面,他坚持称《野草》“不只流露了鲁迅本时期彷徨、寂寞、苦闷的心情,但更重要的,也表现了鲁迅本时请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并由此对许多作品作了相当牵强的分析,如《过客》体现了“鲁迅对于封建地主阶级所统治的社会,是多么深恶痛绝”等,这样的阐释与鲁迅创作的初衷相去甚远,完全是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过度解读。另一方面,对《野草》流露出来的苦闷和寂寞做了如下的解释:“我们读出了鲁迅当时的寂寞和苦痛……也看出了他对于具有强大革命威力的集体斗争生活的渴切想望与要求”。《初稿》在分析《野草》时延续了贺凯的观点,将《野草》解读为鲁迅“悲观人生”的产物,是知识分子没有找到前进道路的“彷徨”反映,并在进一步解析中,凸显了鲁迅对“强大革命”和“集体斗争”的向往,将《野草》的悲剧性内涵和鲁迅的苦闷心情尽量往政治性阐释的方向靠拢。尽管如此,刘绶松能够在195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以较多的篇幅来论述《野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毕竟囿于时代背景的制约,在阶级论的话语模式下,未能更深刻地解读《野草》丰富复杂的艺术世界。
三
20世纪80年代初,应着“文革”的结束和解禁思潮的涌动,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开始松动。文学史叙述逐渐摆脱政治桎梏的束缚,呈现出努力到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姿态。
1981年集体编写、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谓这一转变的先声,其在《绪论》里对现代文学作了新的定义,“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应,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9]7-8。在此,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阶级论和反映论的影响,但已经剔除了“革命”、“阶级”这类政治意识形态浓厚的表述方式,突出文学的本体性和复杂性。唐弢对《野草》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其“以内心抒发为主,交织着严肃的自剖和不倦的战斗,感受非常深切,探索非常艰苦”[9]140,“体现了存在于作者自己思想里的同样的冲突”,主要从作者思想的角度入手来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对《这样的战士》、《过客》、《秋夜》等篇章的分析能够大体切合鲁迅创作的实际情况,较之以前的文学史强调“战斗性”和“革命性”来说,意味着文学史叙述的重心悄然转移,表露出叙述焦点从作家作品的“外部”向“内部”转变的痕迹。当然,唐弢并没有彻底放弃对宏大的政治命题的叙述,如对《野草》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如下表述:“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鲁迅一方面和封建势力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现代评论派’作韧性的鏖战,另一方面由于《新青年》团体的散伙,在文化战线上一时还看不到作为核心的领导力量,他的思想在苦闷中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将鲁迅精神苦闷的原因仍然归结于进步的知识分子“没有认清前进的方向”[9]140,这表明,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嬗变”将是一个艰难的渐变的过程。但唐弢这一代学者毕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政治话语”的制约,文学史叙述中尽量避免长期以来政治唯一的衡量标准,从而突出文学的主体性和复杂性。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野草》进行了高度的关注,以往遭到冷遇的《野草》研究全面复苏,深刻影响了同时代的文学史书写,对文学史叙述形成了有益的补充。许杰的《〈野草〉诠释》和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前者以矛盾论来分析鲁迅的世界观和思想世界,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解读《野草》,鉴于长期以来《野草》研究中弊端,“不是强调作品的阴暗、消极的一面,就是强调作品战斗性与革命意义,而且有时还作了任意的曲解”[10]1,许杰对以往“内容决定形式”、“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论调提出挑战,纠正了以往片面夸大鲁迅思想的阴暗、消极面,以及片面拔高鲁迅对所谓光明、希望的追求的倾向,并且给予《野草》的艺术特色以高度的重视,强调“《野草》的艺术成就的重要性和它的高度艺术造诣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10]65,这是以往的文学史叙述和《野草》研究长期忽视的方面。但是,矛盾论的二元对立分析法阐释性强,其优点很明显,能够将复杂的问题整合、归纳在一个主题之下,其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野草》矛盾、丰富、多样的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展现,鲁迅思想世界的复杂性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也有没有得到更深的开拓。与许杰不同,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野草》,“《野草》中反应的对现实社会和精神生活这种寂寞的感情,并不是他个人特有的心境,这里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内容”[11]8。从“历史”角度出发对《野草》作出的新的阐释,纠正了许多长期以来的过度阐释和主观“索隐”,如对《野草》的“战斗精神”往往从“革命性”、“阶级性”等政治性较强的角度进行解读,而孙玉石则更加重视“人”的战斗精神。不可否认,上述的专题研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野草〉研究》中将“夜游的恶鸟”解读为“依附于黑暗势力”[11]22的象征就值得商榷,但对《野草》新的解读方式极大地扩宽了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
四
经过1980年代的转折期,文学史写作进入了全新的“重写文学史”阶段,现代文学史书写经过长时间酝酿、反拨,最终在质的方面实现了全面地突破,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格局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首先,最明显的转变是《野草》和《朝花夕拾》在文学史中从鲁迅杂文的附属地位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章,我们可以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修订过程中清晰的看到这种转变,在1987年的版本中,涉及到《野草》的小节以“鲁迅早期杂文和《野草》和《朝花夕拾》”[12]为标题,修订版中则以“《野草》与《朝花夕拾》”为小节标题[13]。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试图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用“纯文学”的眼光来审视《野草》,这一文学史著作从“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野草》是“从‘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中升华出来的鲁迅哲学”,“构成哲学的基本单位(元素),并不是抽象的逻辑范畴,而是一些客观形象与主观意趣统一的意象”,这些“意象”有的暗示着“人的某种生存困境与选择”,有的象征着“个人与他者的紧张关系”或“自我的命运”。[13]41钱理群等学者完全放弃了以往文学史中时代背景、思想背景的叙述模式,而是深入文本,将《野草》上升到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来进行全新的解读。与之相似的是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和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这两部专著,它们与文学史的叙述共同将《野草》的研究推上新的高峰。上述著作颇具个性化的叙述方式带来了独特的解读视角,“纯文学”的视角以及上升到哲学高度的解读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一部与众不同的《野草》,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完全隐匿,社会背景论的传统解读模式有所突破,这是现代文学史叙述方式上的一种有益尝试,并且成绩斐然。但是,《三十年》有意识地规避政治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鲁迅与时代和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有可能造成了新的遮蔽。
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野草》的解读则显示出某种新的“回归”,重拾“国民性”的文化批判精神,不仅就《野草》的“自我解剖、自我审视”[14]187的性质对其进行了解析,而且对作品展现出来的思想意义给予相当的重视,本书将《野草》包含的23篇作品分为四类,分别是“诗化的心灵独白”(《影的告别》、《墓志铭》等),“不屈不饶、顽强战斗的精神”(《这样的战士》、《过客》等),“童年生活和故乡美好景物的热情憧憬与真挚向往”(《雪》、《风筝》等),以及“针砭国民性、揭露世态相”(《死后》、《狗的驳诘》等)。现代文学史经过一段具有“先锋性”的叙述历程后,重新回归传统,在“坚守传统中自觉追求创新”[15]。严家炎等学者不仅对《野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论述,并且广泛吸收了《野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了许多精彩的创见,如指出《野草》“形式虽是荒诞怪异的,精神则深深植根于现实之中”[14]190,这样的解析可能比以往的文学史叙述更加切近鲁迅的本意,再如对《野草》的艺术渊源的叙述,能够在“传统”的表述和“中庸”的立场下有所创新,与《三十年》的个性化叙述相比,显得更为“冷静”,使表达更具学理性。
表面上看来,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逐渐减弱,学者对文学史的定位更加贴近文学本体论,文学史写作的独立性得到了强化,但是在深层面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依然存在,以更加潜在的方式影响着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和叙述话语。
五
海外的现代文学史则从不同的语境和视角来阐述鲁迅的《野草》。1978年出版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由于对“左翼”和“政治”话语的反感,在叙述鲁迅时流露出鲜明的倾向,认为鲁迅的散文“既没有徐志摩的天马行空,周作人的舒卷自如,也没有郁达夫的幽幽而说”,《野草》具有“凝练的美”,但也有“显出凝滞,不开展”的特征[16]184-185。由此可见,司马长风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考察作家和作品,对作家的时代背景则较为忽略,海外现代文学史保持了这种与“政治”绝缘的写作立场,但此后的德国汉学家顾彬、美国汉学家李欧梵等学者一致给予《野草》较高的文学史地位和评价。
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将《野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散文诗这一题材的唯一代表作,“鲁迅也许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在散文诗上获得成功的中国作家”,而得出这个结论是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他对《野草》的描述首先从语言方面入手,认为“悖论和重复是《野草》最根本的标志”,这就形成了一个系统,将鲁迅全部作品整合进“悖论”这一西方新批评术语中,“悖论是鲁迅生平和作品的根本性标志”。另一方面,顾彬又将《野草》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阐释,对其艺术形式进行了追溯和比较,将《野草》与法国象征诗人、拜伦、雪莱、尼采以及犹太人传统中的流浪汉形象联系起来。由此可见,顾彬完全把《野草》代入西方语境下进行描述和解析,以西方新的理论成果(悖论)作为其支撑点,这是大陆文学史中没有的新颖视角[17]2,79,但鲁迅毕竟是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作家,用西方的文化视角来审视《野草》,解读起来难免会造成某些隔阂。
李欧梵虽然不治文学史,但其对《野草》的阐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铁屋的呐喊》对《野草》作了精彩、独到的分析。“现代性”是李欧梵解读鲁迅的核心概念,散文诗《野草》尤其能够体现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象征主义的结构,再加上许多小说和戏剧的手法,似乎是在讲述一个梦或寓言领域内的虚构的‘故事’”[18]95。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李欧梵赞赏《野草》“阴郁”、“黑暗”的一面,这能够充分表现鲁迅隐喻的艺术才华和存在主义的哲学沉思,在对《过客》的分析中,他将其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相比,认为“也如贝克特一样,鲁迅想引发一种人的存在的荒诞感”,而对过客“走”的意象的分析中,认为其中也许蕴含着“积极的人文主义的内涵,”那也是以“用存在主义的方式提出的”。李欧梵注意到了鲁迅提到自己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但他认为“个性主义”的方面“几乎是存在主义的”,《野草》就是鲁迅“陷在一系列难于解决的矛盾的绝路上,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18]102-108。李欧梵几乎完全是从存在主义的哲学层面解读《野草》,这也是以“现代性”为潜在语境的必然结果,与此相似的是王德威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解读,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仍然能够看出其潜在的“现代性”话语,在王德威笔下,《野草》“充满着超现实的情景、噩梦般的遭遇和飘荡的幽灵暗影”[19]575。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野草》在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历时性变迁和共时性差异,我们能够看到,文学史的叙述深受时代背景和语境差异的制约。一方面,大陆现代文学史对《野草》的解读经历了30年代左翼思潮的影响,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图解,和新时期以来思想解禁潮流的冲击,文学史叙述走过了一个受政治制约到“纯文学”再到重新关注社会、时代的过程,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另一方面,海外的现代文学史对政治表现出天然的疏离和排斥,不同的语境下孕育了不同的叙述视角,与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有益的互补。但是,无论是新时期以来大陆文学史对《野草》的“纯文学”审视,还是海外的西方语境和“现代性”话语,无疑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偏离和遮蔽。当然,也各有所长,史料的丰富性和文化的认同感是大陆现代文学史的优长之处,而世界性的宏大视角则是大多数大陆现代文学史所缺乏的。梳理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野草》在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或许能够揭示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和解读视角的某些内在规律,从而为今后的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1]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2] 章依萍.古庙杂谈.古庙杂谈《五》[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3] 胡云翼.胡云翼重写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2004.
[4]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M].北平:成杰印书局,1933.
[5]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M].新兴文学研究会版,1933.
[6]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1979.
[7] 刘绶松.中国文学史初稿[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0] 许杰.《野草》诠释[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
[11] 孙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2]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3]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5] 钱理群.守正出新——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9).
[16]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
[17]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8]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尹慧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9]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M].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学术编辑 胡世强]
[责任编辑 熊 伟]
The Weeds in the Narra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LIURong-rong
(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Lu Xun was the most famous writer who cannot be forgotte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arration. As the most complex and rich connotation in Lu Xun's works,The Weeds gained considerable interpretation in the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s Since the 1930 s’,domestic scholars g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eeds. These reflect the understanding of each era of Lu Xun's image. However,the overseas scholars gives us the worldwide grand perspective of Lu Xun for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modern literature;The Weeds;Lu Xun;narration
2016-09-03;
2016-12-31
刘茸茸,女,陕西子洲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
I210
A
2095-770X(2017)03-0076-05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3.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