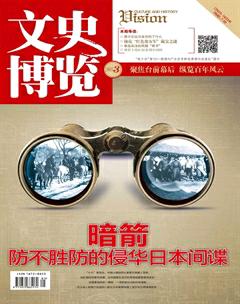“改造地球”的知青岁月
肖江华
弹指间,我从1975年3月下乡到湖南娄底涟源蓝田镇当知青至今已40年,记得当时为表达到广阔天地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决心,我唯一一次将满头乌发剃成光头……
离城那天,领导为我们百多名知青戴上大红花,每人还送了一个斗笠,并组织人员敲锣打鼓送我们出城,许多知青家长、朋友也来送行,场面颇为热闹,我们内心似有点“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感。出城不远遇上一场雨,带队领导率我们分赴各个大队,我与另外两个男知青被安置在涟钢附近的一个大队茶场。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场长便来叫我们出早工,我们扛上锄头跟场长等人爬到后山山顶上挖土,准备种西瓜。我们虽有十七八岁,但力气不够大,劳动一天手上便磨起了泡。在山上种西瓜,需要到两三里远的河边挑潮土做底肥,西瓜才能长得又大又甜。三个知青中只有我的力气最小,开始时我只能挑七八十斤,特别是上山那段羊肠小道比较陡,几天下来,肩膀磨得又红又肿。但我暗自坚信“坚持就是胜利”,几个月后,我也能挑上百多斤了。
西瓜地经过我们施肥、除草,苗子长得很快,到夏天时层层梯土都结满了圆圆滚滚的大小西瓜,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种出的丰收果实,我们内心充满了喜悦。
还有一次是深秋时到20里外的煤矿挑煤,吃完早饭挑起箩筐与场长出发,赶到煤矿时快11点了,场长他们挑了百多斤,我考虑到路途较远还翻山越岭,只挑了80多斤,开始我还能跟在他们后面,慢慢地我们几个知青便落伍了。走了一半的路程时,我们几个又渴又饿,见路旁一块被挖过红薯的土里还剩几个泥巴根根红薯,便捡起来找口山塘洗一下充饥,然后又互相鼓励继续慢慢往回趕。
下午四五点钟,我们终于将煤挑到了茶场。顾不上洗脸,我们端上饭便狼吞虎咽般吃完了。吃完感觉还不解饿,又煮了两斤多米,3人风卷残云似的消灭了。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也是最多的一餐饭。
冬天在山上顶风冒雪开荒挖橘树坑的艰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树坑的要求是一米见方,好像是五分工一个。那座山火石子多,严冬时节,北风呼啸,锄头挖下去,火星四溅,手掌震得发麻,虎口开裂,我们脱去棉衣与风雪搏斗,弄得满身泥雪,每天也能挖三四个。
后来茶场陆续来了几批知青。为了便于照看山上的茶叶、黄花、豆子、花生等作物,场长带我们在山腰上用土石加竹条筑了几间土
屋,我们将家从祠堂搬到了山上。那时候知青招工和推荐上大学,需要劳动两年后才有资格。开始的两年,大家都颇有“改造地球”的激情,劳动较积极,个个都想表现自己,思想比较单纯。但两年后有点家庭背景和关系的知青陆续远走高飞,知青们的思想开始复杂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只有把思绪沉入到中外名著中去寻求解脱,一直坚持到1979年6月返城。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上海见过一家“知青酒家”,感觉既亲切又陌生,五味杂陈,思绪万千。涟水河畔那不紧不慢、日夜转动的大筒车,见证着我们那充满困惑和艰难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每当想起那张月落乌啼的“知青旧船票”,都会情不自禁地勾起我对那段早已成为尘封历史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