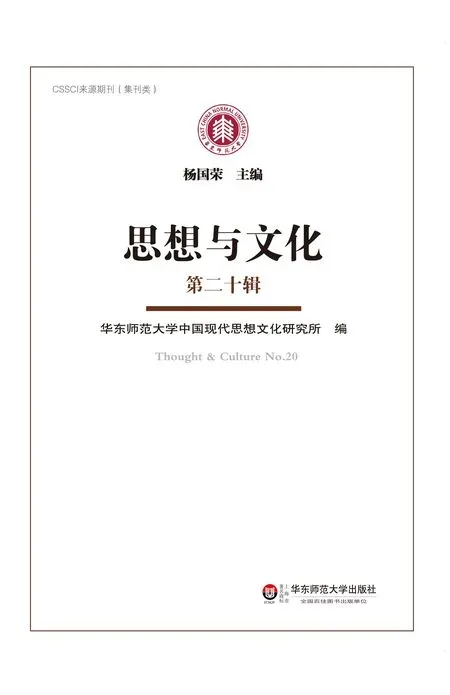儒学政治与普遍主义
——就孟子政治哲学与赵教授商榷*
●
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注之一,是普遍的正义秩序与具体的价值之善的关系问题。中国自身现实政治问题的思考,有着多样性的资源,比如西方世界行之较为有效的政治模式及其观念支撑、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及其观念传统以及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及其理论等等。尽管不同的历史时代与不同的民族国家,其具体的政治结构模式都有着内容上的差别,但就历史与现实政治实践的例示而言,人类社会的政治设计,其趋势不断指向着普遍政治秩序与具体道德价值的适度分离。然而,当下中国政治哲学思考中,有一些声音,展示出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 拒斥西方的政治模式,以之为某种西方中心的特殊价值而非普遍性的东西;代之以中国“儒家”自身固有的、真正普遍性的东西。如此有些矛盾的论述,实质上是以道德价值的特殊主义拒斥政治的普遍秩序,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从儒学立场而言,道德与政治及基于儒学的普遍主义,其具体的内涵,必须得到更为清晰的阐释与澄清。对此两个问题,赵教授以孟子为中心提出自己的一些主张。这些主张,赵教授以《孟子: 儒学普遍主义的可能与基础》为题,发表在2017年1月20日《文汇学人》。*下面引用的原文,都出自该文。另外,赵教授以《古今自由: 道德与权利的分野》为题,有一部分观点摘录发表在2016年12月8日《南方周末》,但因为篇幅太小,其具体论点和论证都没有得到清晰展示。
总体上看,赵教授的宏文,在几个基本的方面,我都高度赞同且受益良多,即: 坚持自由的基本立场,不以特殊主义苟合强权专制的伪说为然,对于自圣倾向的政治儒学加以拒斥,而且对于政治必须使得社会成为可能、使得每个人能自我完善之论等等。但是,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赵教授认为,道德(儒家道德)与政治是本质一致的、政治必须以道德之善为根基并指向道德之善;对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看到道德与政治的本质相异性,二者必须彼此适度分离,道德之善与政治秩序二者各自面对不同问题、有不同界域。同时,对于孟子儒学的普遍主义问题,赵教授认为孟子哲学以一个人例示了普遍之人的存在,但没有注意到孟子所谓“心之所同然”命题,其实蕴涵着道德上个体生存的内容差异性与形式普遍性的划分。从而,赵教授所谓孟子的儒学普遍主义,也就成为某种特殊主义的言说。
一、 道德与政治——孟子哲学所彰显的领域究竟何在
(1) 历史上,孟子被视为迂腐而不切实际的道德主义;
(2) 时下以政治儒学反对心性儒学,从而就否定了孟子,否定孟子也就是用政治否定道德;
(3) 赵教授认为,否定了孟子哲学的所谓政治儒学,是反道德的(将政治视为武力和强制的领域);
(4) 赵教授反对政治与道德的截然划分(尽管二者之间有一定分际),孟子要求政治必须合于道德是一种很自然的古典观念;
(5) 孟子的“道德”哲学强调政治的起点是仁心的恢复,而非完满的道德——“或者说,自由意志的觉醒与自由实践之要求,这完全是政治的,这是一个更强的论点”;
(6) 赵教授借用柏林的话来说,正确的政治观,是认为“政治论不过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
(7) 以宋代社会政治为早期现代性,以孟子思想为宋代社会政治制度与具体做法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奠基;
(8) 孟子对孔子的阐释,使得教化成为政治的最高实现,实现了“天下化成”与“个人典范”的统一。
显然,这就是将孟子哲学视为“真正的政治哲学”——“以政治作为人的完善与发展之道,亦以人之完善和发展作为政治的目标”。
撇开以孟子道德哲学与宋代政治之间关系论证的不严谨,也不论宋代社会政治究竟是不是现代性的,在赵教授如此明确的“政治哲学”理解中,不那么明确的问题是: 政治究竟是人的目的还是人是政治的目的?我想赵教授肯定要强调人自身的存在、发展与完善才是政治的目的。当然,赵教授会说,一个自我完善的人,如果是有道德的,就必然要担当政治责任,督促政治之合于道德——这是“合情合理”的想法。但是,过此以往,赵教授的说法里面,还会显示出一些更强的“政治色彩”——道德只有进入政治并使政治得以完善,才是道德自身的最终完善。这后一层的意义,则是以政治为道德的目的,而非道德是政治的目的了。
这种对“政治责任”之担当的极端强化所带来的扭曲,恰好是我极为警惕的。
我一向对政治哲学比较疏远。在潜意识里,我一直觉得有些政治哲学的论调在真正的问题上错失太过于深远。尽管政治哲学与权力政治并非同一回事,但是,政治哲学对于权力本身的理解与诠释,却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哲学立场。
面对政治权力,如果持有道德理想主义,就只有一种可能: 即这种道德一定内在含蕴着自相矛盾之处。我坚信,道德不可能成为政治的基础,也不可能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根基。*这一论点,在同时参加邹城会议的赵广明教授那里,得到明确的突出强调,参见其《从现代视野看血缘道德与公共秩序》,《南方周末》2017年1月12日。赵广明教授强调自由是道德与政治二者共同的根基,比较突出普遍道德法则的内在自律与政治秩序之外在强制二者相对立的一面,注意到个体道德与公共政治秩序的界限,但似乎没有注意到政治秩序本身的道德属性,比如正义秩序本身可以促进个体公共道德观的养成,并有助于社会风尚的教化,以及具体政治人物个体之道德对于其践行、遵循政治秩序具有关联性等等。当然,赵教授可能会就此申言说: 政治必须是合于道德的,必须是道德的实现,政治才是合理的。尽管政治与道德具有各种复杂的关联,但直接将政治与道德的本质等而齐之,则是典型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观,忽视了政治与道德二者不可弥合的本质差异——政治以利益和权力为核心关切,而道德则是以道和义为中心。传统儒者的王霸义利之辩突出了二者的对峙,但大多儒者却始终陷于道德理想主义乌托邦,幻想以道德来驾驭、驯服以及转化政治。赵教授之意,似乎多少仍有着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政治场域,是一个利益与力量纷争之所,其目标是形成一个最为透明而普遍的秩序。只有不同的多元利益和力量之间,能够相互制衡并彼此妥协,那样一个政治上的普遍秩序才能产生。如此秩序,使得多元利益与力量的邪恶争斗,不至于让人之自足自成的生存可能性丧失殆尽(各得其合于相互制约意义下的基本利益满足涵摄于此)。赵教授在论述孟子的普遍主义意义时,特别地说明,不是北宋社会的现实需要促进了孟子学的兴起,而是孟子哲学自身的内在理路蕴含着后来者思考的基础。这种论调,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北宋儒学的兴起,与北宋社会现实整体的发展,至少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参见卢国龙: 《宋儒微言》,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撇开具体历史的考察不论,单纯从社会政治秩序生成的基础来看,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的真正基础,什么时候是由抽象观念产生的?社会的政治秩序,本质上基于社会内部多元利益的相互制衡、彼此妥协,而非单纯从抽象的观念来建构出来。政治领域中利益与力量的多元性,是多元思想绽放的土壤;多元思想的绽放,反过来促进政治秩序保障社会的多元自由。就此而言,具体历史与现实中,政治与思想之间其实共有一个当下社会生活的根基,并相互投射与相互渗透。但单纯诉诸一个抽象的哲学传统或是天命、天道观念来作为政治秩序的根源,则不但不合于历史事实,也把思想对于历史事实的事后诠释颠倒为事先奠基。
思想可以秉持着对于权力政治的批判性警惕,但是,思想不能僭越地以为可以由自己生成或决定政治。道德作为思想与个体生存相结合之物,尤其在自身持守对于权力的思想警觉与在自身切己践行中体现自己的本质。
就传统思想而言,简单地看,道家在其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中,秉持批判、拒斥、远离而求自然自足的态度,根本上具有弱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色调的“小国寡民”取向,但并没有完全否决有限性社会性秩序的制约问题。
法家则完全拥抱权力,强调以力量控制社会及他人,以谋最大利益作为政治的基本内容,主宰者与被主宰者同时认可并分享着这同一个观念——所以,这就是普遍性力量宰制的无所谓精神性与自性的强权政治。
儒者可能会强调区别于政治的道德-教化生存,但是,由于众多儒者的论调强调了某种普遍道德性精神及其外推实现,这在底子里应和于法家的强权政治之普遍力量;而且,一些儒者常常会倾向于与强权媾和而生,将道德和思想视为为之背书粉饰的伎俩;如此,这使得儒者本真的非政治性道德-教化生活(特指区别于以权力和律法为中心之政治场域的道德-教化领域),亦即那种介于道家与法家之间的道德-教化场域被湮没了。
这个道德-教化的领域,在孔子与孟子的最为核心的论述中得以绽现,在赵教授的文章里,也若隐若现——比如宋代相对独立于权力政治控制的士人在野、教民养民、书院勃兴之民间社会的兴起,但赵教授又笼统称之为“政治社会”,将道德-教化之域与政治场域混为一处,而没有彻底领悟孔子和孟子念兹在兹的修德-教化之域独立于权力政治的深意。
从本质上说,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关切的政治,与道德本质相异。政治的道德性不是因为它基于道德而建立,或者说道德能将政治转化为道德-政治,从而二者具有本质一致性,使政治秩序合于道德性地建立;而是说,政治能被限制于不侵越道德与自然生存的界限之内,当政治以限制自身的方式使得每个人的道德得以可能,不干预或妨碍个人的自我道德完善,使得个体道德保持其自由独立,这样的政治是符合道德的——这种符合道德的政治,本质上是以道德与政治相分,不让政治凌越道德的意思。就历史与现实而言,如果二者有某种所谓的本质一致的结合,现实和历史表明的恰好不是政治合于道德,而是道德本身被政治所扭曲和毒化,成为非道德的伪道德说教或意识形态欺骗。将一个具有完全否定性意义的政治生活转换为人的本质性生活,或者视为道德生活的更高状态,我一向很难接受。我拒绝政治是人的生命本性和必然内容的说法。赵教授或许会强调,一个不担当社会-政治责任的思考者是一个犬儒主义者,但是,这个批评本身是错误的——真正的思考者批判的是政治对人的戕害,一个真正的思考者不可能认可“扭曲的现实政治安排”。面对更为邪恶的政治现实,一个哲思者可能具有的最好命运,有时候就是安静而无恶地死去(柏拉图语)。
在当代,权力政治、金钱与技术形成的“在精神上的空虚无实”之物,成为所有人的“普遍而共同的生命内容”,这是无法忍受的。人类生活应当走向一个更为深邃的、本质的目标——经由浅浮政治、宰制技术而走向每个人的自身。政治应当限制自身对于人的生命内容与本质的侵蚀。尽管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本己的生命内容,但政治不能成为所有人、每个人的生命之本质的内容。政治不是目的,不是本质。人,每一个人,才是目的,才是本质。
政治的关切,应该是简单透明的,是人所共知的,因为它不涉及什么深邃的、精神性的东西。其基本的方面,即是否定性的限制性秩序而已。
当然,追求自我实现而参与政治的方式,可以有多样性。但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和致思者,除了持续不断的批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本质的方式。让独立于权力政治与技术专制之域敞现出来,这是一个思者的本职所在。让政治开出、让与每个人走向自身的通道,而非堵塞各成其己之道而完全使得所有人引归政治的唯一广场,这才是一个儒者应该的思考,或者才是一个思考着的儒者。*现在,儒学、儒家、儒教、儒者等等概念用得很杂乱,具体涵义都没法确定。在极为狭义的立场上,我自己大概只接受“儒者”的概念——即,基于自由的学思修德而“学不倦诲不厌”是儒者的基本生存样式。
因为蔽于这个道德与政治的“本质相悖”,赵教授此文在孟子哲学一个基本点上就只能避重就轻,并且难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孟子讨论过王道仁政,通常以为王道仁政的基础是治国者或当政者(掌有权力者)的仁心(不忍人之心或良知)——一个治国者有善心,以善心行事施政,岂不就是王道仁政么?孟子也说,一个有如此善心之人实现王道仁政,易如反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很多人会忘记,整个《孟子》文本的开篇,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的基础——治国者关注的是政治权力与利益,而孟子劝导的是道义,二者以冲突的方式彰显出来。在《孟子》开篇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实质上,孟子针对的现实前提是“利欲追求及其悖谬”——即利欲追求带来利欲自身的不能满足,由此凸显与之本质相异的道德之义。
在孟子的性善论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之间,当大多数人仅仅片面地关注孟子认为君王(掌权者)由其善性或善心而行善政(王道仁政)之际,其实湮没了孟子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取向——即,政治制度本身的善,是人性善的前提。这本身就是孟子的追问: 人性善(普遍的人性善),那么社会之恶来自哪里?显然,孟子提到了这样的答案——每个人都会循其自身而实现其自身而为善,那么,一个人之为恶,“其势则然也”(《孟子·告子上》)。很多人会以为这个看法是荀子的观点,这是有些浮浅的。对于任何个体而言,那个能扭转、扭曲其自身之善而为恶的外在之“势”,主要指向权力政治本身。这就是孟子政治哲学中,之所以蕴含深沉的对于权力之恶的批判与反抗的根由。荀子的立场是,普通人之本能不能自我节制而善,而易于引向社会整体的恶,所以强调圣人神道设教、立法以教化民众、约束民众——也就是说,在荀子这里才是圣人(君王)以善性/善心而实行善政,荀子赞扬、高举了君王,但贬抑、压低了普通人;在孟子那里,所有人、每个人都是善的,他的话头却是不断批评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侯,批评他们不能由善性/善心以行仁政;反而对百姓的衣食住行之欲进行合理性辩护,并进而指出,恰好是梁惠王、齐宣王等如此现实的恶政,使得天下之民不能“依据其本性而完善自身”——使得所有人(尤其普通百姓)不能成其为善,就是治国者施政的不善。因此,在孟子政治哲学中,政治的恶,恰好成为道德之善不能实现自身的现实阻碍或障碍。简言之,在孟子,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是——政治之恶,妨碍了每一个体道德之善的自我实现。赵教授宏文可能接受了常识性的意见,以为孟子以道德之善来论证政治合理性或合理性政治(王道仁政),这太过于直观而失之肤浅了。孟子哲学中的政治思想,其更为深刻之处,需要看到现实政治对于性善加以扭曲和遮蔽的恶。换句话说,性善首先不是政治建构原则,而是政治批判原则。从而,道德之从政治权力退却之处获得自身场域,便是一个极为合理的推论。
由于赵教授没有看到性善本身的批判性意义,反而片面地关注其在君王那里的建构性意义,从而就走向了他主张的自由哲学的反面——一般人需要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恒产需要外在的“给予”和“担保”,这恒心也就需要外在的“建立”与“强加”。因此,赵教授便不仅舍不得扔掉“圣人”这个多余而累赘的概念,还得反过来强调孔子之非王而圣,强调圣人让百姓“恢复仁心”。只要是在道德与政治本质一致性的意义上来理解道德与政治,那么,道德之自化自成,便会转变成权力政治对道德的非道德性外在强加。
孟子哲学中的道德与政治相悖之主张,可以有一个可能的现代解读——就是普遍而良善的政治安排,必须以所有人、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并完善其本性为目的;由于现实政治总是易于以其恶而障碍个体道德之善的实现,因此,政治哲学的核心之点,不是对于道德善的实现,而是对于自身之恶的限制或克服。从而,经由孟子所揭示的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背离”,才可能找到现代自由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共同纽节。
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司马迁说:“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本是一个历史性与事实性的启示,与孔子晚年之回归一样,昭示了一个“区别并独立于权力政治的诗思修德之域”。*“孔子晚年返鲁”与“孟子之退而著述”,本质上是孔孟二人的学思修德与现实践行的必然结果,昭示的恰好是儒者那个修德-教化必然从政治之域独立出来的本质道路。但由于孟子本人的器宇轩昂,他对于杨朱、墨子及其后学(比如夷之)以及农家(如许行)的夸张批评,使得思想自身相濡以沫的、独立于权力的共存未能彰显。在《论语》中,孔子对泰伯、殷之三贤以及所遇众多隐者的态度及言说,在在表明,孔子对道家或隐者之流的那个“领域”充满着敬意,这个敬意,恰好是因为孔子的志业所在,就是在隐者所生活的领域与权力政治宰制的领域之间,造就一个友爱的自觉修德、共同学习、教学相长的“教-学-思-修”一体的“人文”世界。赵教授自然不会从教化与政治的独立来理解,因此,他就认为教就是政治的内容。以教为政治的内容,这个观点一出来,赵教授一开始表达的“自由立场”便大打折扣了——权力专断下的政治,对于教育的扭曲,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教化之应当独立于政治?
德-教的人文世界,当然需要坚韧的担当才能捍卫,但那不是因为权力政治的鄙弃而然,而是因为自身的自珍而得。以道德、教化和思想作为政治的内容,忽视或掩盖其利益与权力争斗之本质,最后就是扼杀道德以及人本身。这与所谓政治儒学,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二、 普遍性与个体性——孟子的普遍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赵文有些含糊地说:“我们认为,孟子以对‘道德与政治’的分/合为起点,基于个体自由、权利与文明秩序的政治见地与制度设计,方堪称之为政治的儒学。它不仅不是特殊主义的历史陈迹,而且预留着对未来的启示和奠基,我们因而称之为‘儒学普遍主义的可能和基础’。”在如此模糊叙述中,普遍主义之与孟子哲学的关系和意涵,隐晦不明。
(1) 一方面,赵教授说“普遍主义乃儒学的根本义理所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孟子对儒学普遍主义之未来的奠基”。如此论断蕴含着模糊之处: 究竟孟子哲学本身就“已经”是普遍主义的呢?还是说能从孟子哲学中发现儒学在“未来(但尚未)”具有普遍主义的某些根基?
(2) 一方面,“我们没有必要完全依靠孟子来证立儒学普遍主义”;另一方面,用孟子来证成普遍主义是针对“否认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在儒学的存在,是目前的普遍现象,一些人甚至公开为‘特殊主义’张目”。这个意思是说,孟子哲学中只是勉强拿出“普遍主义”特征来应对特殊主义么?而这个勉强的“普遍主义”,其内涵即是具有自由、民主之类普遍观念么?如前所述,赵教授以宋代为早期现代性,宋明儒者在宋代已经广泛地建设各种职业的平等性、乡村自治等的社会之域。大概赵教授是说这种走向社会的现代性是普遍的,而孟子的思想是宋代儒者建构社会的思想根基,这就是孟子儒学普遍性的涵义。但是,这个论证本身的力度还欠充分。这不免让人觉得,孟子之普遍主义与自由民主观念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乃至于只是毫无证明力的外在牵合。
(3) 赵教授的文章有删节,但在刊印出来的行文之间,已经有些敏锐地看到,孟子一方面强调“圣人与我同类”、“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的普遍主义取向;另一方面,又以愿学孔子为例,突出了“堂堂正正做个人”的个体性之一面。可能由于篇幅限制,也由于前面政治角度的过分强化,这里,赵文并没有完全勾勒出普遍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合理“界限”及其相应“内涵”,最后以为孟子继承孔子而“化成天下”,并将自身成就为“一个‘人’的典范”。我猜测,最后这个说法,是故意为之——孔子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典范”?这并不好回答。因为这与自由、权利的“未来普遍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厘定。
就关于普遍主义与个体存在的关系而言,我们借用康德与孟子的比较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在认识论范围之内,康德认为,理智与理性具有层次的不同。理智是范畴的能力,理性是理念的能力。理性的理念是理智的认识所不能抵达的,是使得理智的概念认识得以“统一为”知识整体的基础(而实际上的知识不可能抵达彻底的整体)。
在康德,对象世界与自我主体都是不可知的物自体。但不可知并不等于不存在。康德划分可知世界与物自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人的道德存在找出根据(当然,其中也还有科学认知的普遍必然性根据,以及信仰的可能根据)。
就自我作为物自体而言,它意味着,“由自身开启一个自我决定的行动及其结果”,亦即自由才是道德的基础,而非认识论领域之内的因果律所决定。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实践的客观性/实在性”以区别于“认识的客观性/实在性”。本来,在康德,所谓客观实在性,实质的意义是指“普遍有效性”。这一点对知识来说,很好理解,但对于道德来说,则存在着困境。自由的存在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而是一个道德哲学的问题。在认识论领域,是人为自然立法,这个普遍一致性可以在主体之间达成;但在道德领域,人是为自己立法,这个普遍性如何可能呢?因此,在康德这里,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自由的个体性道德存在如何得到知识论上的普遍性表达问题。
以“普遍立法原则”为例,康德的意思是一个道德行动主体,他在某种具体境遇中行动,要引用一条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条规则需要具有一种“普遍性质”——即,别人,所有其他人在如此情境下,能而且必须采用这条规则,一个人才能“依据这条规则而行动”。规则一旦是可以普遍化的,就是法则。所以,简单说,普遍立法原则的意思,就是一个具体主体,使用普遍法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行为出自对普遍法则的遵守,才能是道德的。在理解的时候,我们可能片面注意到法则的“普遍性”,而忽略此一普遍法则的“自我立法的个体主体性”。
实质上,自我立法而成普遍法则,这是在道德之域对于知识性表达的一个接纳与限制。作为道德生存的主体,是不可知的物自体,因此,自由及其丰韵的内容本身就不是普遍化的知识所能表达的。但一个人呈现在他人眼里,他人又只能从知识性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这就需要一个最低程度的、但无内容的、空的形式意义上的普遍法则——比如今天的宪法原则,这个法则可以得到知识性的理解,但它只是让或使得每一个体去自由存在得以可能,而并不构成每一个体自由存在的主要内容或其本质内容(这一点结合自律和意志自由就更能理解了)。
如果我们在推论的时候,将普遍法则理解为每一个体的生命内容及其本质,就会出现问题(比如不同语境、不同个体的生命内容完全迥异,究竟如何采用同一条普遍法则);如果仅仅理解为最低限度的知识论上的普遍性,即空无内容的形式原则——有点类似今天所说的程序性原则,使得自由个体的生命内容充盈而殊化为非知识论的个体性得以可能,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得到消解(它只意味着一个规则或秩序的形式要求,具体内容则完全属己的、不可普遍化为知识的自为自觉之物)。
在孔子哲学的主题中,仁的实现问题,也可以做如此理解。比如孔子回答颜回问仁,强调仁是“克己复礼为仁”与“为仁由己而不由人”统一。其基本的意蕴就是以普遍的社会礼仪(道德规范)约束自身行为,进而打开每个人自己成就自己的通道并走向自我实现,而不陷自身于为他人普遍认可的知识之域(能动的自我实现与摈弃求为人知,这是孔子道德哲学的突出之点)。
在孟子,问题得到更为深入地理解。一方面,孟子批评了在认知主义的视野中,那种普遍主义视角对于个体差异性的湮没。在与告子“生之谓性”的辩论中,告子以“一切白物都是白色的”的这种认识论上的普遍主义立场,来理解人之生与犬牛之生,也就是用某种认知主义立场上的“普遍生物学特性”来湮没了犬牛与人的差别(甚至犬与牛的区别,乃至白雪、白羽与白玉之白对于雪、羽、玉差异的湮没)。人性不能是认知主义那种定义式的某种普遍之物,而是否定了普遍之后的那个非知识性的内在丰盈。但是,一个人成为不可以知识方式把握的“个体自身”,他必须是在最低限度的理智认识的普遍性基础上才得以可能,个体是在作为类之分子基础上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而不能是从“人之类本质上”的倒退为禽兽的那种与众不同。所以,孟子强调,有理智之思的个体主体,在眼、耳、口的一般欲望追求上有普遍的相似性,在心思自身的追求上有普遍的一致性(即有所谓“心所同然之理义”)。但是,这个理义,是形式上的优先,它本身只是空无内容的,真正的内容,是遵循这一原则而自由自主地去创造自身之所得(成为出类拔萃之自我)。*实际上,戴震对孟子“心之所同然”的普遍主义,有一个表现面上肯定而实质上否定的解释,由此,我分析出孟子“心之所同然”具有空形式的普遍性与内容的个体性双重涵义。关于对孟子“心之所同然”的普遍主义内涵的分析,可以参见拙文《一本与性善——戴震对孟子道德本体论的圆融与展开》,《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
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普遍律令,与孔子和孟子的道德哲学是可以相联系并相通的。不过,康德似乎更为强调了普遍道德律令的超越性,往往使得个体道德生命的真内容成为一个僵死教条的表现工具而已。就此而言,孔孟道德哲学,更多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要求切己践行与修养,把自己造就为一个充满德行的鲜活的个体。
而且,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孟子“心之所同然”的普遍主义,有两个重要的体现: 一是具体普遍性,一是器用普遍性。两者使得克服和走出认知主义普遍性得以可能,并促成政治的普遍性秩序担保道德的个体性。
所谓具体普遍性,在《孟子》中,主要体现为典型事件例示,即在两个具体个体彼此完全差异的行事活动对彰中彰显普遍性义理,比如,《离娄上》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讨论。一个故事说,禹治洪水而救天下溺者、稷救天下饥饿者,两个人三过家门而不入,颜回“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三个人具体行事完全不同。另一个故事说,曾子居武城,有寇盗来了,他自己逃走了,让人看好他的东西,寇盗离开了他就返回;子思居卫,寇盗来了并不是自己走,而是一起抗击,两个人行事完全相反,甚至有学生提出质疑。而对于这两个故事,孟子都得出结论说“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上》)。这就是突出基于差异性的具体情境性,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就是具体普遍性——它突出的是将原则涵融于每一个体切于自身独特环境的自我实现。
对于器用普遍性,孟子有很多说法,这主要与规矩有关: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孟子·梁惠王上》)
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上》)
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
规矩,方圆之至也。(《孟子·离娄上》)
规是作圆形的工具或器具,矩是画方形的工具或器具,它们都是具体性器物,它们本身,规并不圆,矩并不方。在古希腊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智思辨哲学中,作为方和圆之极致或最完美体现者,不是某种具体的制方画圆的工具或器具(规或矩),而是纯粹的理念(或本相),方的理念就是绝对的方,圆的理念就是绝对的圆。在现实的具体方圆之物以外,去构造绝对纯粹的方圆理念,这在孟子看来,就是“凿”,就是自私用智,孟子对此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孟子·离娄下》)孟子强调由规矩以成方圆,有一个本质性的环节就是要每一个体自己切实去“做”或“行事”——不使用规矩进行具体制作,就没有方圆之物;不去切己权衡度量,便没有事物的轻重长短,心的实现活动尤其如此。以具体的器具之使用为基础来理解普遍性,这就是器用普遍性。器用普遍性避免了一个绝对独立的抽象观念世界,突出了基于切己行动的个体生命存在本身,这对于今天的技术专制对于个体生命的剥夺而言,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启迪。
无论具体普遍性还是器用普遍性,两者都是对于孟子心之所同然之普遍性的体现,而其实质性的意蕴就在于将空的普遍性形式作为内容的个体性生存的前提或担保。
当然,我们不是苛求赵教授对《孟子》文本所内蕴的普遍性论述,有详细而深入的专题化探讨,但在政治作为“形式或法则的普遍性”,与道德作为“实质或内容的个体性”之间,如果没有做出分疏,那么,其所说自由与道德,两者就都落空了。
赵文反对特殊主义,但没有看到他自己所谓普遍主义的有限性与适用界域。实质上,如果不能分开内容的个体主义与法则的普遍主义,所谓的特殊主义,只是一种变态的普遍主义;相应地,所谓的普遍主义,也只能是一种扭曲的特殊主义。
孟子哲学当然具有多元解读的空间和可能性,但仅就赵教授《孟子: 儒学普遍主义的可能与基础》一文所涉及的道德与政治及孟子儒学的普遍主义问题而言,以上的分歧,实际上折射了政治哲学本身的复杂性。然而,不管如何,政治要建构普遍的政治秩序,就必须与具体的道德善保持一定的疏离;否则,以特定的道德价值之善作为政治秩序的本质内容,那么,此一政治秩序就不可能是普遍而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