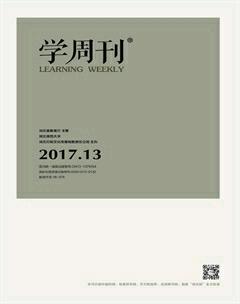试论理雅各1871年《诗经》翻译的经典性
武琳丽
摘 要:理雅各1871年《诗经》英译本是一部文学翻译的经典译本。分析理氏1871年《诗经》英译本的结构要素,揭示其经典性,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省思和借鉴。
关键词:《诗经》;结构要素;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7)13-0233-03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7.13.145
一、理雅各1871《诗经》翻译的经典地位
“经典”一语大约从汉魏时期就开始使用了,主要用来指儒家典籍,与英语对应的词是“canon”和“classic”。由于“canon”这一概念原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所以就文学经典而言,“classic”似乎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字。“经典(classic)”是“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语,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1]本文所关注的是文学翻译的经典著作理雅各1871《诗经》英译本。
理雅各(1815-1897)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他率先系统地译介中国经书。1871年《诗经》英译本属其译著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系列(共有5卷,计8本书,所译中国文化典籍依次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春秋》和《左传》),由香港伦敦传道会印刷所印刷出版。译本推出后,得到了具有经典地位的中西方学者或批评家的一致推崇,使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在诗歌界声誉鹊起。譬如,译本一经推出,1875年理雅各成为由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捐资设立的西方汉学研究的最高荣誉儒莲奖的第一个获奖者,以表彰他的《中国经典》。清代学者王韬说:“西儒见之,咸叹其详明该洽,奉为南针。”[2]在英国颇具影响力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1872-1901)的主持编辑欧德理赞扬理雅各对自己的《诗经》英译工作“几乎到了挑剔的地步”[3]。英国著名汉学家与传教士艾约瑟(Dr. Edkins)认为:“对于一个渴望了解中国文献的人来说,接触理雅各的译本是最实在的事,学成了就是荣耀。”[4]近半个世纪后,著名汉学家小翟理思,翟林奈(Lionel Giles)赞美理雅各说:“50余年,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5]一个多世纪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勒亥大学(Lehigh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USA)的诺曼·吉拉多特(Norman Girardot)教授充分肯定了理雅各的翻译成就,认为理雅各的翻译是他的“东方朝圣之旅”,指出“对于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所面临的生活之互相理解学习来说理雅各的经验,依然为一典范”[3]。
译本出版后对西方影响甚广,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诗经》标准译本。仅1893年通过英国牛津Clarendon Press、英国牛津Oxford Reprint和美国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三家出版社再版。至20世纪,在美、英、中国台湾、香港以及内地等地出现翻印和再版,包括英国牛津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美国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1900)、香港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1970,1982)、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SMC Publishing Inc.(1983,1991)等出版社数次印刷。从2000年至2016年,不过十数年,翻印近20次。译本里面的一些译文被广为引用,如由当代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和中国学者刘绍铭编辑而成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译文集》(第一卷)(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1, 2002)这部被誉为“里程碑”似的巨著就收入了理雅各翻译的《关雎》《柏舟》《君子陽陽》《女曰鸡鸣》《素冠》《君子于役》及《大雅·绵》译文;吕叔湘编著的《中英诗比录》中辑录的理氏《诗经》译文更多,不能一一列举。在他之后,许多译者大多选择在他的译文基础上进行重译,如詹宁斯译本、阿连壁译本、庞德译本等。可见理雅各的1871年《诗经》译本在翻译界名声大噪,享有经典的声誉。
不过,这些无非是说明其经典身份的外在因素,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有其自身内在的更为重要的内在本质特征,即经典性。如此,本文通过分析译本的结构要素来探讨其经典性。
二、理氏《诗经》译本的经典性
刘象愚概括出经典的内在本质性特征,即经典性有:(1)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2)经典应该具有实质上的创造性;(3)经典应该具有时空的跨越性;(4)经典应该具有无限的可读性。毫无疑问,要想成为经典,这几点是不能少的。
理氏1871年《诗经》译本体例包括学术绪论、正文和评述注释,是其译本的结构要素。那么其译本的经典性是如何在这三部分体现的呢?
(一)译本内涵的丰富性
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所谓丰富性,是指经典应该包含关于人类社会、文化、人生、自然、宇宙中那些重大的思想和观念,……并极大地丰富和有益于人类生活”[1]。理氏1871年《诗经》译本的绪论有182页,共计五章,内涵丰富,包含了政治、历史、宗教、家庭、婚姻等许多方面。理雅各颇为推崇孟子说《诗》之法:以意逆志。依循这一思路引诗解诗,就会将《诗》纳入历史的序列中。理雅各认为“诗的采集和保存是为了表彰德政和善行。诗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为我们展现出国家政治和社会风俗之盛衰兴亡的真实图景”[6],即《诗经》中保留着中国先人生活和思想信息,拥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在理雅各的头脑中“一直保持着一种清醒认识,即学者们对于其他的‘伟大历史,同样怀有神圣使命”。[6]理雅各在绪论中查考了《诗经》时代的国家疆域、政治、宗教信仰、社會风俗,甚至涉及了妇女低下的地位及一夫多妻制,他“努力以体验的方式重构《诗经》产生的历史语境,把握其原初功用”[7]。再者,理氏《诗经》译本的注释有1928条,篇幅宏大,长度远远超过译文,为译文提供了详尽的解释、背景知识和研究资料。理雅各的关注是文献学式的和学术式的,他所提供的长篇的绪论和注释,可谓是“百科全书似的知识”[4],其译本内涵的丰富性从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二)译本翻译的创造性
经典应该具有实质上的创造性,“必须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不仅仅是重复前人或他人已经说明的东西”[1]。翻译是译者有目的的活动。理雅各十九世纪翻译《诗经》等中国经典的初衷是为了掌握中国的古典典籍,挖掘中国人“某种最伟大的德性和力量而成就的道德和社会原则”,打开中国思想的大门,成功传播基督教思想。因此他的翻译绝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复杂的文化信息的传递。《诗经》属于四言古诗,诗句简短精练,但信息含量大。为了成功揭示儒家道德思想,理雅各创造性地运用了直译加注翻译法,理氏“译经以忠实存真为第一要义,一以贯之的方法是直译加注,传达原文信息丝丝入扣,保存原作形式不遗余力”[8]。这就形成了理氏1871年《诗经》英译——这个《诗经》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与其他《诗经》译本不同的重大特点之一,即长度大大长于原文的学术绪论和详尽注释,也成为人们研究经典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三)译本的时空跨越性
经典应该具有时空的跨越性,也就是说,经典作家或作品应该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且属于所有的时代,并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参考资料首要的两个即为《毛诗注疏》和《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皆以朱子之说为宗”,是有关《诗集传》集大成性的权威资料。《毛诗注疏》又名《毛诗正义》,该书全部保留《毛传》《郑笺》的注文,并给这些注文做有疏解。理氏译本以汉宋两代的《诗经》学研究——朱熹的《诗集传》和汉代的《毛传》《郑笺》为主要参考依据,有力地保证了其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中国思想,忠实再现《诗经》“经典”品质。正因为如此,理氏译本具有跨越时空的内在本质性特征。
《诗经》“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在周代宗法社会发展而来的长期封建社会,被应用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9],譬如《国风》虽为歌诗,富有生活情趣,但是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政教的外衣。敬畏于儒学典籍的崇高文化地位,理雅各选作忠实型的译者,充分尊重权威诠释《诗集传》及《毛诗正义》,翻译时忠实再现了它们的道德礼教特点。我们以《周南·关雎》为例:
原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译文:“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
《关雎》原是一首民间歌诗。现代派诗经学者程俊英女士认为《关雎》是表达“一个青年热恋采集荇菜女子的诗”。《诗集传》解为“见其有悠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而理雅各完全接受了朱熹的观点。“窈窕”一词,许慎在《说文》中释:“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指心灵仪表兼美的女子。程俊英女士对“窈窕”的解释为:纯洁漂亮。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中指出“窈窕,美好貌”。从古至今,“窈窕”的释义中没有显著的道德色彩,理雅各则把“窈窕”译成了“modest, retiring”。理雅各在《邶风·静女》的注释中对“retiring”的释义是“the idea which it conveys is of one who is modest and correct”。“modest”和“correct”都是道德教化意味浓厚的词汇。再看“淑”一字,其释义多为“善”,就是“好”。理雅各自始至终都把“淑”译为“virtuous”“virtuously”或“virtue”,偏重于道德含义,如在《邶风·燕燕》:“淑慎其身”、《墉風·君子偕老》:“子之不淑”、《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曹风·鸤鸠》:“淑人君子”等诗篇中“淑”字的翻译。另如,《豳风·狼跋》:“公孙硕膚”,理雅各的译文是:“The duke was humble, and greatly admirable”。虽然朱熹的释义是:“硕,大。膚,美也”,《毛诗传》亦同。程俊英认为:硕膚就是肥胖的意思,余冠英持同一见解。可是,理雅各却把“硕”译为了“humble”,经这一改写,刻画的人物不再体态肥大,而是成了一位谦谦君子,蕴含于其中的道德意味油然而生。此外,理雅各把“膚”,即“美”,译成了“admirable”。其他如《郑风·叔于田》:“洵美且仁”、《郑风·有女同车》:“洵美且都”、《齐风·卢令》:“其人美且仁”、《唐风·葛生》:“予美亡此”、《陈风·防有鹊巢》:“谁侜予美”等篇章中的“美”皆译作“admirable”,充满了道德评判的味道。再者,理雅各通过对诗篇原文信息添加语言元素,以强化原诗所隐含的道德礼教内容。例如《桧风·匪风》:
原文:“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译文:“Who will loyally go to the west?
I will cheer him with good words.”
如果按照理雅各忠实直译的翻译策略,“谁将西归”的应当译为“who will go to the west”,实际的译文添加了“loyally”一词,强调对国家的忠诚,渲染了原诗尚不鲜明的政教色彩。另如,《秦风·小戎》:“五楘梁輈”,理雅各译之为:“With the ridge-like end of its pole, elegantly bound in five places”。朱熹《诗集传》中说:“五,五束也。楘,历录然文章之貌也。梁輈,从前轸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则向下鉤之,衡横于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处束之,其文章历录然也。”《毛诗传》云:“五,五束也。楘,历录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历录。”程俊英认为:“楘,有花纹的皮条。梁輈,车辕。古时马车一根辕,形状有些弯曲,像房屋上的横梁,又像船,所以叫做梁輈。因为太长,怕它折裂,所以五处用由花纹的皮条箍牢。”对比旧说或新解,我们不难发现理雅各的译文添加“elegantly”一词,这样译诗就直露了原诗原本含蓄的道德礼教内容。理雅各在原诗道德色彩不浓烈或者含蓄的地方,通过使用一连串的道德词汇对诗篇进行了道德礼教化阐释,使译诗比原诗具有了似乎更加鲜明的道德说教意味,再现了《诗经》的“经典”品质。
(四)译本的无限可读性
经典应该具有无限的可读性,是说一部经典应该经得起一读再读。理氏《诗经》译本的长篇绪论和注释是一种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的学术型翻译,[10]目的在于“促进目的语文化对他者文化给予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11]。理雅各在翻译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注释对译文进行二度翻译,重构文化语境,烘托历史氛围,为不了解原文文化的目的语读者提供了理解原文的可能,能够使读者读起来启蒙益智,让读者总想复读而每一次的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从而真正地完成了文化翻译的过程。译本出版后的一百四十多年来,超过30多次的翻印与再版,有力体现着这一经典性。
三、结语
理雅各1871年《诗经》英译本是文学翻译的经典译本,其经典性在译本的结构要素绪论、正文和注释三部分中得到有力呈现。理雅各翻译成功再现了《诗经》在中国文化意义上的经典地位,译本出版后在世界影响深远,为中国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发挥了独特作用。可是,也正是由于理氏的远远超过原文的长篇注释及过于忠实的翻译,使他的译文“不如原文简朴”[12],显得僵硬。因此当下在进行文化典籍的翻译时,我们应该随附精悍的注释,采用更为灵活、自由的译文形式,以求在保证艺术品质的情况下,“原汁原味”地传播中国思想。
参考文献:
[1] 刘象愚. 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2).
[2] (清)王韬.近代文献丛刊 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
[3] 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著,段怀清,周俐玲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4] 岳峰.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A]. 福建师范大学,2003(3).
[5] 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3[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10).
[6]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The She King.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7] 左岩. 诠释的策略与立场:理雅各《诗经》1871年译本研究[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8):85.
[8] 王辉. 理雅各与《中国经典》[J]. 中国翻译,2003(3):37.
[9] 夏传才. 诗经讲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10] Kwame Anthology Appiah. Thick Translation[J]. Callaloo, Vol.16, N.4, 1993:808.
[11] 王雪明,扬子. 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J]. 中国翻译, 2012(3):103.
[12] 许渊冲 诗经:汉英对照[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9(9).
[ 责任编辑 张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