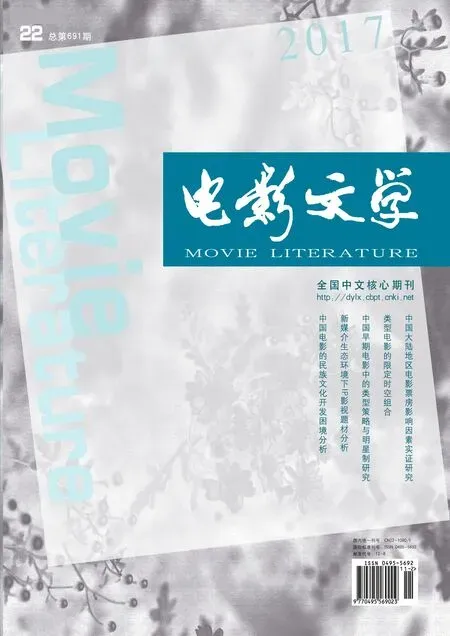叙事逻辑的转换
唐 莹
(长春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卡罗尔》曾经在2015年金球奖上斩获五项重要奖项的提名,并且饰演女主角之一的鲁妮·玛拉也因此斩获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最佳女主角奖。虽然在票房上《卡罗尔》的收获可能并不理想,但从另一层面来看,《卡罗尔》在艺术上成为《断背山》同性爱情叙事的继承者。和近些年概念炒作较为火热的同题材电影《平常心》《丹麦女孩》以及《小姐》不同,《卡罗尔》中既没有奇情诡谲的性别认同问题,也没有基于人权作为剧情构筑基础的“政治正确”,更没有超越了正常叙事视野范围之内的颠覆传统。事实上,《卡罗尔》的内核并不集中在女性恋爱层面,反而更加倾向于表现主角之间情感的细微变化,而正是这样一种非刻意的常态化塑造了《卡罗尔》一种生活化和艺术化的独特气质氛围,也使得《卡罗尔》成为近几年奥斯卡获奖提名大热影片中关注叙事节奏与叙事策略的重要作品。影片《卡罗尔》和文本《盐的代价》的精神融合,也给眼下部分原作改编系列影片提供了借鉴的基础和重要的参考样本。
一、色彩的语言——文本气质的影像化建构
《卡罗尔》的原作小说写于1952年,当时英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开始崛起,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女性意识则因为资本的繁荣初露峥嵘,但同性之间的恋爱依旧是非正常和非合法的。麦肯锡主义盛行之下的美国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氛围,女性被呼吁要求回归家庭。特别是在中产阶级人群中,离异、同性恋爱、女性成为工作妇女往往被看成是不体面的事情。然而在当时美国社会同样也存在女同性恋的人群,但其表现形式往往依旧是男性主义的模拟态,她们生活在社会基层,一方往往表现出极强的男子气概,穿背带裤、男士牛津鞋,打领带,从而意图向世界宣告其与男性拥有同等的权利与功能。但从另一层面上,这同样是对女性自我认知的一种拒绝和否定。和底层工人阶级不同,《卡罗尔》中所描述的富裕中产阶级的女性之间的恋爱交往有很大差异,她们常常已婚、暗地里拥有自己的伙伴和朋友,拥有秘密的朋友圈子,与此同时她们并不拒绝认同自我的女性气质,善于打扮,并且教养良好。这种背景差异导致的文本气质差异也相当大,因此并不能从文本内容上,将《盐的代价》简单等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同性恋文学代表作品。同理,《卡罗尔》也并不应该被简单看成是表现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同性恋的生活状态的影片,联系文本,似乎更应该将《卡罗尔》划归为时代风情气质展现的影片。
为了模拟过去的黄金时代,《卡罗尔》影片的布景色彩搭配、影片整体尝试模仿冲印胶片的偏黄绿色调色,以及角色的穿衣色彩都尝试在重新塑造文本气质。在卡罗尔和特芮丝第一次见面的一节中,镜头中几乎层层叠叠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时代典型人物:穿着风衣和毛线袜、戴着呆板的黑框眼镜的中年妇女,穿黑色呢子大衣、戴黑色礼帽的中产阶级绅士,穿着深灰色套装裙的青春期少女,清一色地盘在后脑的女性卷发。几乎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毫无特点。镜头在取景上有意识地模糊了非中心人物的脸,让每个作为布景的群众演员看起来像毫无个性的复制品。然而在观众的关注逐渐失焦时,卡罗尔出现了。这时的卡罗尔头戴正红色的贝雷帽、穿着金色的狐皮大衣,金色的短发有点散乱。卡罗尔在镜头中几乎成为一个身份形象上的“异类”。这也是卡罗尔的第一次“亮相”。
在其后的镜头叙事中,红色几乎成了卡罗尔的代表色。在随后的情节中,卡罗尔因感谢特芮丝送还手套,而邀约吃饭,坐在敞篷跑车上时,她和好友艾比戴着颜色鲜亮的亮红色与苔藓绿的头巾,甚至为了提醒观众,卡罗尔还自嘲:“我可真不敢想我婆婆看见我穿成这样会说什么。”红色同时也构造了一种视觉亮点,一种对观众群体的潜在暗示,卡罗尔既是特芮丝改变沉闷生活的出口,同样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危险因素。在卡罗尔第二次对特芮丝邀约去城外时,穿着全身鲜红的套装裙,并且由于镜头选择和剧情因素,穿着红衣的卡罗尔和特芮丝在夜色中长谈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氛围调性,让卡罗尔这一形象多了更多的情欲暗示。她并不只是一个优雅、成熟的女性客体形象,她同样暗示着一种征服者和挑逗者。这也是影片和文本分歧最大的地方。在小说中,卡罗尔美丽并且成熟坚定;在影片中,观众同样可以看到美丽和坚定的卡罗尔,但在气质认识上,却很难设身处地地返回当时那个麦肯锡主义盛行的时代——从性别气质上,卡罗尔的扮演者凯特·布兰切特不论如何看上去都是一个不输男性的女王。
因此,红色的用色同样可以看成是对演员表演的一种补充,在影片中可以看到色彩被刻意地强调。例如,在圣诞夜卡罗尔的丈夫哈奇大闹一节中,卡罗尔就换上了浅蓝色套裙与圣诞绿的开襟毛衣,在丈夫酒醉、无理取闹之后,她伤心、愤怒却无可奈何的处境被刻画得让人信服,此时她退回了普通的中产阶级妇人身份,让观众对其长达十年的婚姻生涯有了短暂的一瞥。这种有趣的依靠服装色彩对人物的映照一直在影片中持续不断,在卡罗尔和特芮丝度假的第二日,发现隔壁的私家侦探时,身穿金色狐皮大衣、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卡罗尔从手提包中拿出手枪,对准侦探,镜头从角色的左下方切入,卡罗尔的表情和气质与费·唐娜薇在《邦妮与克莱德》中的抢劫银行的场面如出一辙,这种非女性的特点也依靠服装和色彩传达,有效地模拟了文本气质,近乎还原地为观众呈现了卡罗尔与特芮丝的时代。
二、非台词的与太台词的——影片音乐对文本的取舍与重建
语言是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旁白则是观众直接了解人物内心的重要窗口。写作《盐的代价》的灵感,来自于作者帕特丽夏·海史密斯的自我经历,当时还仅仅是一个商店柜台售货员的帕特丽夏,在圣诞节也遇到了一位身穿狐皮大衣、一头金色短发的妇人,只是没有后来的故事。从帕特丽夏对《盐的代价》的叙事和写作经历来看,《盐的代价》也并不同于她的其他小说,《盐的代价》更像是作者的个人私语,一种对未竟情感的非公开表达。因此,虽然《盐的代价》是一本第三人称小说,但内容上却出现了大量夫子自道式的独白与抒情。影片在处理这些情感叙事时,处于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既没有办法通过角色的个人描述表达个中感情,也没有办法从非人物口中实现旁白。影片用了一个相对折中的办法实现了文本的心声吐露。
影片中的重要情节几乎都是有音乐相伴的。甚至音乐本身也参与到影片叙事中,成为剧情和人物情绪表达的一部分。例如,在卡罗尔邀请特芮丝到她家中度过圣诞节的夜晚,两人驱车穿过隧道时,背景音乐You
Belong
To
Me
响起,镜头剪辑得相当梦幻,以一种奇异的视角扫过卡罗尔的狐皮大衣衣角、沾了雨水的车窗玻璃、卡罗尔的金发,音乐成了该段的重点,随着女声唱道:“You belong to me,I’d be so alone without you,Without you...Oh my daring till you're home again,You belong to me.”(你属于我,没有你的我是如此孤单……)这种借助音乐来代替主体叙事的存在,两人前往芝加哥的行车过程中,和第一次驱车的情节相比,这一次的镜头不再迷幻,镜头简单地给卡罗尔几个特写和定焦,替代了特芮丝的眼光,告诉观众,主角正在关心的焦点,车离城区越来越远,音乐也逐渐开始越来越欢快。此时响起的是One
Mint
Julep
,歌曲颇为调侃地叙述了一个男人因为多喝了两杯薄荷朱丽,搭讪了一位女人,从而拖家带口、养家糊口却反过来埋怨薄荷酒的故事。歌曲的节奏轻快、音乐自由畅达,同时也暗示了特芮丝和卡罗尔芝加哥之旅的愉快心情,而歌曲开头的“I met a woman we started talkin...I don’t remember just how it started.”(我遇到了一个女人,我们开始聊天……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开始的……)也正是卡罗尔和特芮丝在商店一瞥后,莫名开展两人关系的始末。在人物塑造上,音乐同样功不可没,特芮丝在卡罗尔家中度过争吵的圣诞夜后,独自去唱片店挑选给卡罗尔的礼物。这时唱片店背景音乐中播放着Kiss
Of
Fire
,这一段中镜头没有给特芮丝特写,但用音乐描写了这种即将看到卡罗尔的狂喜心情。通过音乐,特芮丝表面上纹丝不动、内心却暗流涌动的状态被明确展示,代替了传统电影的冗长独白,别具一格地调动了影片的氛围情绪。三、温柔的倡议与疏导——基于背景的女性主题重现
虽然《卡罗尔》的文本气质突出,并且影片也将叙事的焦点放置于卡罗尔和特芮丝两人的感情上,但《卡罗尔》依旧承担了时代表现功能,从细节入手,尝试向观众展现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的社会处境与内心世界,这种基于人本主义的照拂,同样也使得影片在主题展示上更加完满。
男女地位的对照是《卡罗尔》中女性地位最为明显和集中的展示。通过人物对话可以得知,卡罗尔的丈夫隐秘地了解到卡罗尔与艾比和特芮丝的关系,面对他复合的要求被拒绝,哈奇愤怒地对卡罗尔提起了“道德条款”,从而阻止卡罗尔探望女儿;并且雇用私人侦探跟踪卡罗尔和特芮丝,不计后果地找到证据来让卡罗尔失去女儿的监护权。并且通过艾比和哈奇的对话得知,在卡罗尔和哈奇的十年婚姻中,哈奇对卡罗尔拥有强大的控制力,在社会的要求和中产阶级的审慎自我意识中,卡罗尔无时无刻不被要求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存在。卡罗尔和哈奇参加舞会时,卡罗尔婆婆对卡罗尔的鄙夷以及哈奇圣诞夜大闹时,一进门,卡罗尔就习惯性地整理衣服、穿上高跟鞋,无一不是卡罗尔的附庸地位的显示。而卡罗尔对哈奇无可奈何的曲意逢迎,让哈奇重新燃起两人复合的希望,也是一次有趣的反讽,卡罗尔因为两人关系的疏离性与正在离婚当下的敏感性,不得不答应哈奇共赴舞会的要求,哈奇却出人意料地将这种接近于畏惧的尊重看成了一种欲拒还迎的复合暗示,有趣的男女地位倒置,也反映出卡罗尔本质上的“非女性”特质。
此外,影片也给予了当时作为工人阶级的女同性恋者们一种审视。在特芮丝为卡罗尔购买唱片作为圣诞礼物时,镜头给予了两个正在唱片店门口吸烟的女人特写,她们穿着男式西装,手抵着墙,抽着烟,以一种困惑和鄙夷的姿态看向特芮丝。同时镜头也报之以特芮丝的困惑表情,背景音乐的Kiss
Of
Fire
是特芮丝即将和卡罗尔约会时兴奋心情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困惑,两个西装女子的打扮是当时工人阶级女同性恋人群的标准打扮,她们强调性别的认知,强调女人和男人拥有同等权利,她们选择伴侣的重点就集中在对方是不是一个和自己有同等价值观念的女人,但是这种评判标准却忽视了两人之间感情因素。特芮丝在看到这两个女人时的困惑,既是对自我性别意识的困惑,也是对自己和卡罗尔之间的感情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延续到影片结尾,特芮丝遇见了一个长相酷似卡罗尔的女演员,那个女演员在派对上对特芮丝示好,但特芮丝却感觉毫无波澜,也正是这一点让特芮丝确定了自己并非是只喜欢女人的人,她只是恰好喜欢上了卡罗尔而已,对她来说,那个人也只可能是卡罗尔。这种细节铺垫也给影片以更深层次的升华,让《卡罗尔》从一部噱头十足的“女版《断背山》”,变成了真正的女性主题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