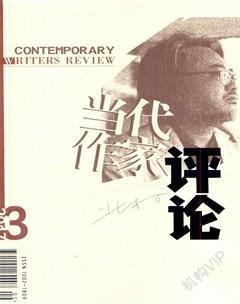新乡土情境下的“差序格局”
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自问世以来,一直被作为语言学及小说叙事研究的经典文本。众多学者围绕作品的“词典体”叙事结构以及小说中起索引作用的马桥词汇做出了诸多精彩的论述。但笔者认为,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试图寻找湘西地域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根源所在。而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来源。正因为如此,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选择了与其另外一部作品《爸爸爸》相似的乡土情境。但不同于《爸爸爸》中落后、封闭、愚昧的原始小山村,《马桥词典》的故事发生在一座处于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马桥。此时的马桥村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正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性文明洗礼的地方情境。《马桥词典》为我们展现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使我们从“对当代社会中所存在的旧文化因素的挖掘与批判”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这一“文化寻根”的意义上更进一步,在微观的个体实践层面上探究传统文化初遇现代性时所产生的冲突与融合。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旧文化因素”的面目更加清晰,而融合则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留存在于当代社会,而这正是“文化寻根”的基本动因之一。
为了更好地探究乡土传统与现代性在马桥这一地方情境中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更好地明晰与概括传统文化的意义内涵,在此我们引入社会学中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认知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将其作为分析《马桥词典》文本的索引。透过差序格局的视角,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原本传统封闭的乡村在面对外来政治权力及现代性文化时所发生的变化。
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自提出以来就被认为是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对中国的社会所做的最重要诠释之一,尤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被学者们广泛地应用在有关中国文化的模式、中国人行为的研究中。这一概念扩展了本土社会学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去探究异于西方学术语境下的中国社会。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有关差序格局的表述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個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也就是说,差序格局是以“己”(石头)为中心经由各种关系(同心圆波纹)推及出去所构成的社会格局。这其中的关系可以是亲属关系,也可以是地缘关系,而且这些关系像同心圆一样有明显的亲疏之别。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对于差序格局概念的阐述是以近似散文式的比喻给出的,而此后他也并未对此概念做进一步的扩展。近些年来,众多学者尝试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对“差序格局”进行补充与延展。阎云翔将焦点集中于差序格局的纵向等级。阎云翔认为,差序格局不止是社会关系的结构,更是由伦常纲纪所建构的尊卑等级秩序。这一秩序由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诸方面来维持。个体会通过一些制度化的社会途径改变自己的等级,从而实现在差序格局中的流动。个体会根据所处的不同情境而重新界定自己的位置,从而形成一种弹性的“差序人格”。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翟学伟则认为,差序格局比喻式的阐述并不是一个问题,反而能够引发更多的洞见和启示。差序格局的缺憾是无法直接体现中国社会的立体结构,但其中蕴涵着一种动态视角,能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这一概念。这一动态视角实际上包括了一种纵向等级变化,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入仕实现社会流动,而个人的成功又与家庭有着莫大的联系。所以差序格局更适用于从己走向天下的个体,但顾及到更为普适性的解释力,费孝通最终还是回到了“推”字上来,使差序格局的概念停留在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解读上。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但无论是费孝通,还是后续阎云翔、翟学伟等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一个既定的血缘秩序基础上来对差序格局进行讨论的。这种既定的血缘秩序决定了差序格局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明晰的等级性,它往往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形成波纹状的有规则的亲疏远近关系。这也意味着个体想要在差序格局中实现向上流动是十分困难的,往往只能依靠读书入仕这样的正式制度途径。但建国后社会主义农村改造的开始,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所生长的土壤——乡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原有的血缘关系和礼俗尊卑的视角去探讨差序格局中的秩序与流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差序格局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即一种以个体亲疏关系建构而成的社会秩序与运行机制。其中,血缘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亲亲、尊尊”等级秩序更是中心性的规则。同时,这种以个体出发的社会传统也为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那就是对于差序格局的探究,必须放在充满个体互动的日常生活中,这也正是笔者选择《马桥词典》的重要原因。不同于充满暴力革命意味的早期“农村题材”,也不似《白鹿原》《秦腔》等以时代变迁的史诗基调作为写作特色的作品,《马桥词典》所选取的,是一个时代的横截面,是集體记忆的一个断片,更是日常生活的剪影。当我们重新审视《马桥词典》的“词典体”结构时,会发现诸多的词条都来源于马桥人的生活,而其中许多词条更是以人物命名,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从个体的角度探究马桥村中的差序格局。
马桥村中的传统秩序
“格”是《马桥词典》故事发生地马桥村的方言,是马桥人对他人的基本评价尺度。一个人的资历、学历、出身、地位、信誉、威望、胆识、才干、财产、善行或者劣迹,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会使当事人的格发生变化。韩少功:《马桥词典》,第1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有格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会有“话份”,他所说的话会更有分量,更容易被人追随。在马桥人看来,诸如女人、年轻人、贫困户这样的人是没有话份的。这表明马桥村的社会首先基于传统的差序格局结构,即由亲属血缘关系(男性)而发展出的长幼之序。作为一个单姓村(马姓),几乎所有的马桥村民都有亲属关系,年龄大辈分高的人说话会更高的格,而年轻人则少有话份。相对地,马桥村的外来人几乎没有什么格,他们无法进入到马桥的血缘关系网络之中,继而很难融入到这种靠血缘维系的差序格局中。这一点在希大杆子的故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希大杆子是一个读了新学的外乡人,略懂西医且接生有术,按理说即使不受村民爱戴,也应该相安无事,但他却一直受到马桥村民的敌视。究其原因,除了他经常做一些异于马桥常理的出格之事(如吃蛇、把上好的吃食喂鸟等)以外,目无尊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面对村里的长辈,他从不让座,更不敬烟敬茶,态度也是爱答不理,这是马桥传统所不允许的。
但当我们进入到马桥的血缘体系时,却发现了些许迥异于传统差序格局的地方。按理说,在传统血缘的差序格局中,应该有一位或几位长辈(长老)拥有较高的格,居于差序格局的中心,并由此发散出亲疏关系的波纹状网络。然而在马桥,这样的中心始终是缺失的,除了在希大杆子的故事中出现了笼统的“长辈”称谓外,小说着重描写的十几位人物没有一个是这样的长辈。我们无法在小说的文本中窥见人与人之间基于传统差序格局尊卑秩序的互动,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作为马桥共同体一员的村民对于既有秩序的遵守及维护。换句话来说,马桥的血缘秩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內外团体的区隔,而在马桥村内部,血缘秩序实际上并不严整。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桥村中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如果说非要在马桥挑出一个类似于“长辈”的人,那无疑就是马本义了。只不过,马本义的格并不来源于他的辈分,而是来源于他的身份——他是马桥村的支部书记,村里行政机构的一把手。此时,我们看到原本作为建构差序格局主体的血缘关系和长幼秩序,让位于了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的介入——传统差序格局与现代性的冲突
实际上,类似共产党政权这样的势力在马桥地区一直是存在的。比如日本侵华时期的维持会,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地区军阀、土匪武装等等。对于马桥人来说,这些带有武装色彩的势力无疑是极具震慑力的,毕竟真枪实炮不是闹着玩的。然而这些势力并未对马桥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实质影响,在动荡时局中,像马桥这样不起眼的村庄很难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但新时期的共产党政权却不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对农村进行改造,促进农业生产。于是,在解决掉周边地区的武装力量之后,国家权力开始了对马桥的渗透,建立了以马本义为首的基层党政机构。人民公社的体制和上级领导的视察使村民们真切地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存在。国家权力对于马桥村的差序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在国家权力与马桥传统文化的斗争中产生的。
解放前,马桥的贫困户是没有话份的,财富是衡量格的一个标准。但共产党政权建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马桥村有位地主叫茂公,有很多田地,还当过日伪的维持会长,是位于马桥差序格局上层的人物,但新政权建立后,茂公成为了典型的地主汉奸,地位一落千丈。在书记马本义带领下,村民们捣毁了茂公的田地,逼得茂公放火烧掉了自己所有的禾苗,之后便断了气。共产党政权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出身成分的划分使得穷人的阶级地位一跃而升,而地主富农则成了被改造的对象。
同样被改變的还有马桥人对于知识的态度。之前马桥人对诸如知识、科学这类事物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它们完全超出了村民的认知。尤其是与知识相关联的人是诸如希大杆子这样完全没有格的人,即使知识再有益处也会被当作巫术而让人敬而远之。
新政权建立后,知识作为现代性文明的代表开始逐渐被马桥人所接受。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马桥人开始接受教育,这些原处于马桥传统差序格局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赋予知识更多的安全性,另一方面,知识有了国家权力这一强大的后盾,同时国家权力也借知识试图对马桥的传统社会进行改造。
在“下(以及穿山镜)”的章节中,来自县城公社的吴部长为了纠正马桥懒散下流的风气,在村民全体大会上出示了两个长长的镜筒,并告诉村民们说这是穿山镜,有了它不管村民们做什么事情都能被远在县城的自己看见。尽管这个“穿山镜”只是一个双筒望远镜而已,它也不能让吴部长在遥远的县城监视马桥村民,但马桥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自此不敢乱说乱动。
与希大杆子的医术一样,“穿山镜”的威力自然是超脱于多数马桥人常识之外的,但两者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导致结局不同的最重要因素是掌握知识的人以及其背后的力量。希大杆子是一个被排除在马桥亲缘关系之外的边缘人,完全没有格,而吴部长背后则是强有力的新政权,这个新政权已经在向马桥渗透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与其说马桥村民害怕的是象征知识的“穿山镜”,不如说他们更惧怕“穿山镜”后面的国家权力,惧怕因越轨行为而遭受到惩罚。
当然这不是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就不值钱,正如前面所说,读书参加科举走入仕途是传统差序格局中的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主要途径,入仕做官的人当然拥有较高的地位。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同样能够对乡村的传统差序格局造成影响。但以前的读书人在向上流动过程中会离开原属的乡村社会而向城镇流动,知识与国家权力的联结不会出现在乡村情境中,留下来的只有像希大杆子这样毫无话份的人,此时的知识当然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新政权对于马桥差序格局的改变无疑是制度化的,也是立竿见影的。如茂公这样以前拥有较高格的人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与过去那种寒窗苦读多年而入仕的流动显然大不相同。茂公的遭遇同时也说明,个体在差序格局中的力量是有限的,随时会因为手中资源,尤其是由政治权力所带来的资源的变化而导致地位的升降,此时个体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变化。
在《马桥词典》的文本中,我们看到,当国家干部可以拥有地位,有财有田会失去地位,读书学习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说,在国家权力进入马桥后,影响差序格局中格的因素愈加繁多,个体在马桥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会随着临时被建构起来的运作逻辑而变动。
新差序格局中的个体流动
每一个马桥人在村中所居的地位是有多个层面的,围绕着这些层面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资源场域。随着各个场域中的资源流动,个体在其中的位置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影响还会侵入到其他场域中。不同层面之间在某些时候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马桥日常生活的行为实践中,个体地位的某一层面的变化会被换算到另一个层面中,从而影响其在整个马桥村差序格局中的地位。
仲琪是马桥村一位普通村民,他既不是干部,也没什么辈分,但他出人头地的渴望十分强烈,千方百计地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一次,仲琪用一只山鸡同一位知青换来一瓶龙牌酱油。这龙牌酱油是当地名牌,年年都要送到北京为毛主席做红烧肉的,地方上起码要县级干部才沾得上边。消息传开,求酱油的人蜂拥而至,仲琪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说话也有底气了。然而,随着酱油一天天的减少,仲琪的格也水落船低,最终又恢复了原先的水准。
酱油此时成为了仲琪获得地位所凭借的资源。全村独一份的高档调味品使仲琪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而村民们的渴望则使酱油的作用向外扩展开来。我们可以想象,尽管仲琪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村民们为了能够借到酱油,平日里对待仲琪自然要恭敬一些。在这种颇为实用主义的日常交往中,龙牌酱油在居家生活中的价值被换算成了人际交往中的资源。而当酱油越借越少时,仲琪就不能来者不拒了,他需要考虑借给谁更为合适。借不到酱油的村民自然会改变对于仲琪的态度,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当酱油没了之后,仲琪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
相比于仲琪,另一位普通村民明啟则通过自己的手艺让其他人另眼相看。明启刚开始被村民称作“明启叔”,勉强算是个长辈。后来因为他馒头蒸得好而常常被公社叫去做馒头,这给了他很大的资本。每当他做完馒头后回村,都会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指指点点。明启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地参与大队干部会议,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意见,即使耽误了干部们的正事也没人敢对他下逐客令。然而一桩桃色事件毁掉了明启的前程。他与县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勾搭在一起,昏头昏脑地把一整袋特批给县领导的高级面粉扛到了李家,顺手还捎去一个猪脑壳。东窗事发后明启再也没有去给干部们做过馒头,地位一落千丈,别说是干部开会,就连全体社员大会也轮不到他发言。他常常被派去干最苦的活,工分也比别人低。
明启偶然获得的机遇使得他被全村人所尊敬,人们对于明启的称謂由“明启叔”变成了“明启爹”。明启的辈分当然没有这么高,但他与国家权力的勾联使得马桥村民在日常互动中提高了他的辈分。这一称谓的变化再次印证了血缘关系所建构的秩序在马桥并不是稳定的,它可以随时被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只有明启被召到公社做馒头时人们才会唤他“明启爹”,这一换算而来的辈分也是在不断确认着明启的资本留存,后来当他失去资本时,便立刻跌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村大队书记马本义作为马桥的一把手,居于极高的地位,但在家庭生活中他却一直被妻子铁香所压制。铁香出身不好,通过与马本义的婚姻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仗着自己年龄小,长得漂亮,铁香在家里家外完全不顾忌马本义的面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马本义有所反抗,铁香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直到丈夫赔礼道歉才作罢。
后来,铁香的行为愈发出格,最终发展成了偷人。马本义对于妻子前两次外遇的态度比较暧昧,因为两个姘头都是县里的人,一位是文化馆馆长,另一位是照相馆的伙计。但铁香的第三个姘头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这位叫三耳朵的人从小吃里爬外,忤逆不孝,被赶出家门,寄居在村里一幢无人居住的破宅子里,马桥人几乎不把他当人看。这次马本义终于不再沉默,先是揍了铁香一顿,接着设局把三耳朵吊在树上毒打了一顿。值得注意的是,三耳朵是被扣上强奸铁香的罪名而受到惩罚的,这说明马本义想要掩盖铁香与三耳朵勾搭上的事实从而保全自己的面子。但本义的面子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年春,铁香与三耳朵私奔了。本义顿觉没脸见人,一连几天紧闭大门,不理公事。
马本义的故事直观地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乡土传统的斗争。在马本义看来,铁香的两次偷情并没有给自己的地位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毕竟那两个人都是来自权力中心的县城,而且其中一位还是比自己级别高的干部,这位馆长还因此批给了马桥村不少图书、化肥和救济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两个姘头在国家权力上的格抵消掉了家庭层面上的耻辱。但铁香与三耳朵的偷情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铁香抛下了两个还在念书的娃崽,抛弃了作为干部夫人的格,与三耳朵这样的一个边缘人私奔,彻底摧毁了马本义作为一个丈夫的尊严。这同时也影响了马本义对于国家权力的行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大队书记的身份,闭门谢客以躲过风头。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在村民们看来,堂堂一村之长不但看不住自己的媳妇,还让三耳朵这样的人作威作福实在是有失体统。马本义无法阻止自己的家庭丑事成为马桥人饭后的谈资,而这对于自己的政治权威的打击是致命的。直到铁香与三耳朵客死异乡后,马本义才算是缓了过来,毕竟惹出大麻烦的两个人还是没落得个好下场,本义也算挽回了些面子。在重拾作为一个丈夫的尊严后,本义可以继续当他的书记了。
在仲琪、明启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即使当不上国家干部,普通人依然可以凭借偶然的机会获得临时的资本,从而获得地位。马本义与铁香的故事则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地位不仅仅与自身所获得的资源有关,还跟个体之间的互动有关。一旦关系亲密的人出了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层面上的资源获得,就如妻子的丑事让马本义的村支书权威一扫而空。此外,铁香偷人对于马本义的打击实际上也是村庄习性对于个体的影响,不守妇道(而且是跟三耳朵那样的人偷情)的铁香有悖马桥村的伦理,自然会被马桥村民所唾弃,连带着窝囊的丈夫马本义也被指指点点。此时,背靠国家权力的马本义也不得不在村庄的伦理秩序前低下头。
结语:“寻根”之“寻”
借由差序格局的概念索引,我们看到,《马桥词典》中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更是追寻传统之根的过程,也是重述一段历史的过程。《马桥词典》虽然是一部以人民公社运动为背景的作品,但小说中却没有对这场改造运动的正面描写,而是将其作为马桥日常生活以及普通村民互动的一个注脚,崇高的革命叙事在这里已不见踪影。《马桥词典》中没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甚至村中没有一位绝对权威的首领存在。在这里我们所体会到的,是韩少功对于寻根的理解——“文化之根”必须从更为日常更为惯习的个体生活中去找寻。除此之外,《马桥词典》更多着墨于传统的文化在面对国家权力、现代性文明的入侵与改造时所发生的变化,换句话说,《马桥词典》更注重的是“寻”。当然“寻”的过程与“根”的内容并不是矛盾的,正是人民公社时期马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长久以来存在于马桥的传统伦理、乡土共识。《马桥词典》所解答的,是一个潜藏于“寻根”下的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得以寻根的根本可能性,来源于民族性的传统依然存在并影响着当下的社会,正是这种影响让我们意识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一个区域的文化的重要性,才促使我们循着蛛丝马迹进行历史与文化的追溯。但“寻根文学”的着眼点依然是现实的,他们并没有一味地溯源而将写作的题材聚焦于久远的历史神话,而是试图从接近于现时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在解放前,马桥村的社会基于一个既定的血缘秩序,其差序格局本身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次序性,它会严格按照一个亲亲尊尊的秩序,以个体为中心向外推及,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但在《马桥词典》中,这一秩序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尤其是国家权力作为一种资源的进入,马桥人对于差序格局的实践逐渐变得实用主义了。在小说汇总,血缘辈分的秩序完全不如现实利益来得重要,所以明启的辈分可以随意变换,书记本义可以获得他原本享受不到的长辈待遇。而真正应该居于差序格局高位的“家长”在《马桥词典》的文本中始终是缺失的。
这是国家权力抑或现代化进程对于乡土传统的一种冲击,那就是人们发现自己的地位高低可以不再由血缘辈分来进行划分了。在传统的差序格局中,血缘辈分秩序是固定的,由此而发散出的关系网也是固定的,个体无法改变自己在差序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但是,当外来的国家权力凭借强硬的手段进入到乡土情境中时,人们发现,依靠国家权力所带来的资源可以改变自己由亲缘秩序所固定的地位,而这种情况是传统中国在“皇权不下县”的局面下从未出现过的。《马桥词典》中个体在差序格局中的地位高低处于一种时常变动的状态,这显然有悖于传统差序格局秩序稳定的特性。马桥人的格基本上与血缘辈分无关,跟亲亲尊尊的伦理也搭不上边。实际上,决定马桥人地位的可以是国家权力赋予的政治身份,可以是一门做馒头的手艺,可以是见不得人的家务事,甚至可以是一瓶酱油。在马桥的日常实践中,差序格局具有高度的随机性和偶然性,通过各种资源的流动与资本的建构,每个人得以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
同时,我们不可忽视地方共同体在差序格局的具体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偶然的机遇和稀缺的资源对于马桥人在差序格局中地位的影响往往基于马桥村的集体共识。正因为如此,希大杆子才始终无法获得格,马桥通过对他的拒绝而维护了村中既有的秩序。而马桥人的共识也使明启成了马桥的门面,明启的荣耀成了马桥的荣耀,每个马桥人都因此有了脸面。当村民们对龙牌酱油趋之若鹜时,仲琪成了村中的红人,而当酱油被用尽时,仲琪就被人们抛弃掉了。在《马桥词典》中,差序格局不仅是基于个体利益与价值诉求的亲疏关系网络,它更受到作为地方共同体的马桥村的建构。无论个体有着怎样的资本,都需要得到马桥这一共同体的承认。从这一点来讲,个体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地方共同体对于格的给予或剥夺。
而在马本义的故事中,我们更应该看到面对外来国家权力的入侵时,乡土的传统所做的化解。马本义除了支部书记之外仍有自己的私生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权力的任何痕迹,党支部书记的丈夫经常被作为乞丐富农女儿的妻子压制。同时我们还看到,马本义的家庭私生活还影响到了他作为党支部書记的形象。所以,笔者认为,国家权力的资源仅仅是众多影响马桥人地位的因素之一,也许会有更大的权重,但显然对于马本义来说,其他因素仍然会影响到其作为村支部书记的威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乡村传统伦理的顽强生命力,国家权力与乡土传统在新差序格局的个体流动情境下达成了妥协。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无论是国家权力对于乡土传统的冲击抑或现代性知识的进入都没有改变差序格局以个体为中心的结构运行。虽然共产党政权试图用集体主义对农村成员进行改造,但在《马桥词典》中,个体在面对各种资源的流动与获取时仍采取了极具实用主义的行动策略。表面上,个体在差序格局的位置变动变得更加随机与偶然,但总体来讲,由国家权力与现代性文明所带来的变动是逐渐趋于稳定的,诸如仲琪故事中的酱油这样暂时的资源无法长久改变一个人在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话句话说,《马桥词典》中的馬桥依然是一个稳定的高低有序的差序格局,只不过决定地位高低的资源不单是血缘辈分,还有更多的外来因素。一旦这些外来资源融入马桥社会中,其运作的模式仍然遵循着传统差序格局的逻辑,所以马本义的妻子铁香虽然是个低成分的富农后代,但仍不能阻挡其作为书记夫人而在差序格局中处于较高的地位。马本义与铁香之间的联系,仍然是传统的亲缘纽带,依然是是以同心圆的方式决定了个体间的远近亲疏。
在某种意义上,《马桥词典》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寻根”历程。它揭示了当代社会与“文化之根”之间的因果链条,同时也彰示了“寻根”之意义所在。当差序格局被作为索引来对马桥村的日常生活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新的外部情境在一开始对原有的乡村传统产生了影响,但最终还是被差序格局所容纳,从而延续到了当代社会。当我们试图通过“寻根”来探讨存在于当下社会中的旧式文化时,文化传统的变迁与纳入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只有通过这种变化的过程,文学的“寻根”才能真正把握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才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得真正的线索所在。
【作者简介】孙绍文,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