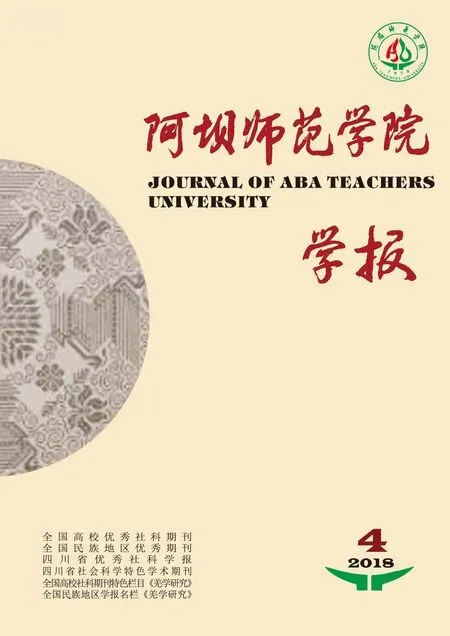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文化振兴:松潘小姓乡“毕曼”歌节的人类学研究
刘 超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四川省2017年7月实施了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2018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乡村文化振兴首次被提及。这表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将是未来各项相关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2018年7月20日,农历六月十五,松潘县小姓乡埃期村举行了以羌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民歌”为核心的毕曼歌节。该举措一方面是在遵循当地传统的基础上,以更为现代化的方式让人们在节庆狂欢中感受到仪式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也借此引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为当地文化旅游作宣传,带动地方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民歌
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松潘县小姓乡的羌族群众都要跟随亲朋好友,带着丰盛的食物,聚集到一起,举行祭祀仪式,唱起祖辈们传唱下来的古老的歌曲。这种歌曲在当地人中被称作“妮莎”,其中最古老的一首酒歌叫做“毕曼”,而这些歌曲以一种复音形式演唱的歌曲被称作“多声部民歌”,羌族多声部民歌于2008年被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多声部民歌是一对或一组歌手同时唱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声部的民歌,又称为“二声部民歌”或“复音民歌”。目前,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分布在松潘县小姓乡、镇坪乡,茂县太平乡、松坪沟乡以及黑水县知木林等相邻地区,因此这些区域又被称作“复音孤岛”[1]。此外,有学者指出:近百年来,茂县西路的赤不苏、渭门、沟口,汶川的羌锋、龙溪,理县的增头、桃坪、蒲溪等地,曾经也是羌族多声部分布的地区之一[2]。1984年,四川省文化厅汪静泉老师偶然发现了羌族地区的多声部唱法,2006年羌族多声部“毕曼组合”获得央视青歌赛原生态组铜奖,2008年羌族多声部被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由羌族学者毛明军整理出版的《羌族妮莎诗经》,收录了102首多声部民歌。羌族多声部已经名扬海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外学术界均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存在多声部的演唱形式[3],进而认为羌族也不可能有多声部民歌的存在,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羌族多声部首次被发现才填补了学术界的这一空白。1985年,四川省文化厅汪静泉老师跟随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赴马尔康采风,在参加民歌集成的记谱工作时,偶然在录音带中听到几首羌族多声部民歌,随后汪老师走遍了黑水、松潘、茂县等地,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对羌族多声部进行了大量的收集与整理工作[4],系列工作为羌族多声部民歌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由于羌族历史上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文字,羌族多声部民歌一直以来都是依靠口传心授,一代一代传唱下来,而汉文典籍里也少有相关文献记载。因此,关于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历史很难从学术意义上加以定论,只能从其传统的唱法及其古老的歌词中推断,羌族多声部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以及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社会各界均加强了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关注,学术界对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研究逐渐增强。最早对羌族多声部歌曲进行分类的是樊祖荫,他认为羌族多声部民歌可分为山歌、劳动歌、酒歌、舞歌和祈祷歌等五类[5]。此后,刘洋、朱婷、龙有成等人均沿用此类分法进行相关研究。有研究者认为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社会功能主要有民族团结、道德规范、认识与教育、审美、娱乐等[6]。而金艺风的研究则认为羌族多声部民歌不同于其它任何民族的多声部民歌,因为它以两名男声不分上下高低声部,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演唱[7]。除此之外,学者们均从羌族多声部民歌的演唱风格与方法、结构特征、艺术价值、学术研究价值等方面展开讨论,但是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对羌族多声部民歌进行研究的较少。
2015年,由羌族学者毛明军整理出版的《羌族妮莎诗经》[8],收录了102首多声部民歌,它是首部用文字记录的多声部民歌集成。据当地人介绍,羌族多声部其实还有更多歌曲,如今已经无人再会唱全所有歌曲。“毕曼”是羌语的音译,是松潘小姓乡一带众多多声部歌曲中的一种,它在当地人中被称作是酒歌的父母,是最古老的一首酒歌,所有的酒歌都源自于这首歌,又被称作“酒歌之祖”。由羌族多声部民歌歌手仁青和格洛组成的组合取名为“毕曼组合”。2018年农历六月十五小姓乡举办的“毕曼歌节”的“毕曼”二字即是由此而来。
妮莎也是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羌语名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民歌在当地被称作妮莎。它是由一人起调,随之有人和音补音,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或千人。因此有学者指出妮莎是羌族二声部或者多声部唱说,羌语北部方言称为妮莎[2]。
无论是当地人所称的“唱妮莎”还是“毕曼歌节”,亦或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羌族多声部民歌”,这种古老的演唱形式一方面充分表明羌族这一古老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也表明,它是羌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集体欢腾:“毕曼”歌节的仪式过程
传统节日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祭祀、宗教和崇拜活动密不可分,而这一系列的传统节日活动中总会涉及一项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看来是一种最能够表达神圣性的民间节庆狂欢——集体欢腾。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是涂尔干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进行宗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涂尔干主要通过在对澳洲原初社会各种宗教仪式的研究中,认为原初社会的人们在宗教仪式中通过集体的狂欢进行社会神圣性的表达。集体欢腾作为涂尔干对初民社会生活场景的再现,不仅是对那种原始宗教的仪式场景再现,更是隐喻现代社会中人们仍然通过某些集体狂欢的方式表达社会的神圣性。因此,从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的诸如彝族火把节狂欢、藏族雪顿节朝圣、新年烧头香的寺庙集会、NBA球队夺冠的街头游行等集体欢腾现象来看,这些现象是现代社会中社会神圣性依然存在的体现。松潘小姓乡举行的毕曼歌节上,人们通过各种活动的表演达到集体欢腾,仪式之后就地分享食物以达到与神共餐,不仅是对祖辈传唱下来的古老的歌曲的传承,更是通过集体欢腾的仪式表达维持已有的社会秩序以及获得新的社会结构。
在松潘县小姓乡埃期村举行的毕曼歌节上,当地人表演了释比开坛、数十首多声部民歌,2006年央视青歌赛原生态组铜奖获得者毕曼组合以及当地出生的著名羌族歌手邓巴也分别登台献唱。这既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盛典,又是当地的一场文化盛宴。此次歌节由当地政府部门出面,邀请了省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以及其他羌族聚居地政府的相关部门参与本次活动。毕曼歌节举行期间,由于雨季导致山洪泥石流爆发,多处道路中断或阻塞,当地政府专门派出车辆接送专家学者,节日当天下午所有专家学者又到县城与相关部门进行座谈,由此可见当地对歌节的重视。
举行毕曼歌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便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活动流程的策划、专家的邀请与接待、生活住宿、通信设备、电力设备、清扫路障、搭建舞台以及必要的节目排练等。前一天全体村民便在空地搭建了简易帐篷,摆放了桌椅板凳,进行了节目的彩排,晚上还精心准备了篝火晚会,跳锅庄,烤全羊等体现羌族民俗风情的活动。
活动当天,首先进行的是嘉宾的欢迎仪式,两列嘉宾依次进入仪式场地,当地村民依次为嘉宾献上表示祝福的羌红。演出正式开始之前,村里的男子前往祭祀塔举行了祭祀仪式,通过念经、抛撒“龙达”、点燃柏树枝等方式,以告知神灵祈求平安吉祥。所有的男性成员身着传统服饰,腰间别着短刀,由当地富有威望的老人带队,唱着妮莎,跳着古老的舞步,围绕祭祀塔转圈然后回到活动现场准备接下来的演出。从众多民族志材料来看,仪式之前的请神祭祀是大多数民族举行仪式的必要过程,通过请神赋予仪式神圣性,神灵在场的仪式在地方社会中更具一种地方性意义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进而体现社会的神圣性。
演出中,除了当地普通民众演唱的多首原生态妮莎歌曲之外,活动的高潮主要出现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郎加木、见车牙等人带领的男女两队进行《祭祀歌》、《若喏》等原生态妮莎歌曲的合唱环节,还有龙波他主持的释比开坛仪式,由郎木加与见车牙合唱的酒歌之父母的“格林毕曼”以及原生态妮莎卡若,口弦等表演,当地出生的羌族歌手邓巴亦亲自登台演唱了其新歌《挂羌红》,2006年央视青歌赛原生态组铜奖获得者毕曼组合也登台表演。这些环节将仪式推向高潮,当地人完全沉浸在节庆仪式的狂欢之中。这些登场表演的人都是当地颇具威望的人士,正如在人类学研究里的“大人物”(bigman),他们不是地区政治组织的管理者,但却是当地各项社会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例如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注的拉美尼西亚社会里的“大人物”,他们不拥有权力,但拥有权威、信任、资源及协调能力,在当地人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9]。这种地区性的“大人物”拥有的是权力之外的权威,除了日常参与地区性社会事务之外,还体现在仪式之上的神圣性。祭祀仪式上能够优先获得食物或者分享更多的祭品,但是他们带来的通常是仪式神圣性的抬升。在小姓乡当地颇有影响力的郎木加、见车牙、毕曼组合等“大人物”参与该仪式,无疑增加该仪式的神圣性,体现了该活动的级别之高。像这样的演出,在以前叫做“耍坝子”,不需要任何舞台、音响设备与主持人,几家亲戚或者关系要好的邻里朋友聚成一群唱妮莎。如今虽然舞台化,却因地方性“大人物”的参与同样兼具仪式的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的体现则是当他们登台表演,台下的村民热烈鼓掌与口哨声以及新闻媒体记者疯狂聚焦的闪光灯下展现的节庆狂欢。
涂尔干认为,在现代社会,史诗、英雄与宗教的影响虽已减弱,但人类对神圣性的体验仍将继续存在[10]。据当地人介绍,以前前往祭祀塔举行的祭祀才是当天仪式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仪式的核心,现在虽然该环节得以保留,但是已然被缩减。仪式的主体被舞台上的多声部民歌表演所取代,以前那种随意围坐在草坪上随意对唱妮莎的形式被规范化的舞台表演与排列整齐的观众坐席所取代。虽然仪式的形式和名称有所变化,但仪式的核心却没有变化。放到当地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舞台化表演中流变的只是仪式表现形式,而从当地人集体的节庆狂欢中依然展现的是仪式的神圣性以及地方社会对神圣性的认同。
因此,无论是妮莎还是毕曼歌节,亦或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羌族多声部民歌,仪式的变迁只是表征的文化现象的流变,而核心文化则仍然体现了当地人通过集体欢腾的神圣表达。遵照传统时间节律举办节庆,仪式核心的祭祀环节,仪式高潮的集体欢腾以及仪式之后的与神共餐,赋予了这场活动更加丰富的地方性文化意义体系与文化认知逻辑。
三、与神共餐:仪式之后社会秩序的重建
涂尔干认为,与神共餐是所有仪式的关键部分,表达一种与神灵的平等沟通以及友好的表现形式。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指出共餐制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与神灵进行交流的方式。据众多人类学资料显示,从澳洲到斐济群岛,从拉美尼西亚到波利尼西亚,从夏威夷到北美印第安等土著部落当中均有与神共餐的习俗。
小姓乡的村民在举行完仪式,进行文娱活动之后通常会就地摆开携带的食物,与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分享美食。在仪式靠近祭祀塔的空地上,村民头一天便在此搭建了简易帐篷,准备了桌椅,有的甚至直接在地上铺开地毯,将准备的丰盛的食物依次摆开放在桌子或地毯上。因是当地一年一度的集会盛宴,每家每户都会精心准备,食物形式最多的便是以现杀现煮的羊肉汤锅所呈现;其次是大盆装的大块牦牛肉;还有颇具当地风格的“土火锅”,里面煮着烟熏了一年的腊肉与香肠、新鲜鸡肉以及各种蔬菜,色香味俱全还营养丰富;当然啤酒更是少不了,有的家庭还准备了可乐、雪碧之类的饮料,加上各种面类做的主食,可谓相当丰富,可以说每家每户都集聚齐了一整年的劳动成果在此。一方面是有神灵的节庆总不能怠慢,难得的与神共餐的机会赋予了仪式神圣性;另一方面从世俗社会来看这也是一家人难得的聚集在一起享受节庆的欢乐时光。
当地人聚餐以血缘与地缘两种社会关系进行聚合。最常见的是以姓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戚聚集在一起,携带食物放在一顶帐篷或一张桌子或一张地毯上,亲戚们围坐在一起分享食物,话语间闲谈的都是家长里短,或者是从外地回乡的人讲外面世界中的趣闻。另外一种便是超出血缘关系之外的聚餐,邻里乡亲熟人之间都可以参与,这种聚餐的参与更多的是出现在发生过社会矛盾的人之间。羌族聚居地区大多在高山峡谷之中,一直以来草场、林场与药场等资源竞争相对激烈,邻里或寨子之间难免发生争执或不愉快的事情。通常都是由寨子里的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出面调解暂时平息事情,但是要真正缓解矛盾或者解开心结,则需要双方当事人自己心照不宣地进行沟通与交流。“耍坝子”的聚餐则提供了非常恰当的契机,平日里难得闲下来坐在一起喝酒谈心事,尤其在过去一年有过不愉快的双方,在当地具有威望的人召集之下坐在一起敞开心扉将心结解开。聚餐除了调节世俗方面的事务,还有更重要的是对神的神圣性的尊重。仪式之前将神请到人间,聚餐则提供一个平等的与神交流与互惠的机会。人们利用这个机会为神灵分享人间的食物,神灵则为人间提供保护与帮助。
在大部分民间信仰中,灵神通常都被看作曾经是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人,因为他们生前都是对现实社会有功的,当他去世以后,人们希望通过供奉的形式让他们继续对现实社会有作用。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曾指出,现实社会对神或祖先的供奉通常都要在桌子上摆放碗筷,是希望通过共同食用同一类食物达到与祖先或神之间的沟通[11]147-136。仪式之后的与神共餐是难得的能够与神灵一起享用同一类食物的机会,人们向神灵供奉精美的食物,同时也向神灵提出互惠的条件,通常要求神灵在来年要保佑村寨平安,风调雨顺。这在涂尔干、莫斯等人对澳洲与斐济土著人的研究中多有呈现,因此仪式后的聚餐被称作与神共餐。神灵的在场赋予聚餐神圣性,之前关系友好的亲朋好友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稳固的情感联系,与此同时,曾经发生过矛盾与纠纷的人之间通过神灵在场的聚餐化解矛盾,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罗马尼亚著名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以一种二元结构性的思维探讨了神圣与世俗在本质上来说是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存在形式,他指出神圣的时间与空间代表着秩序与道德,世俗就是从起点到终点再到起点无限的轮回。仪式上通过神灵的回归赋予仪式及地方社会神圣性,仪式后在与神共餐中通过神灵在场赋予的神圣性进一步建立起社会的新秩序。因此,小姓乡毕曼歌节仪式后的与神共餐进一步赋予仪式神圣性,正如伊利亚德所讲的那样,神圣代表秩序,仪式背后的神圣表达维持了既有的社会关系又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
四、结语
松潘县小姓乡毕曼歌节中,祭祀塔的仪式是请神,通过传统的祭祀仪式通告神灵,将神灵邀请至人间,毕曼歌节上的各种狂欢代表了与神共欢的集体欢腾,仪式之后的与神共餐则是人神之间的谈判与互惠,更是神灵在场的社会关系维护与重建。从人类学视野来看,整个仪式虽然极具现代化的舞台展演,但仪式的神圣性却仍然得以体现,既尊重了传统又有了现代性的表演,既不失文化的本真性又能够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这或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当前系列困境的一种路径探索,也是对那些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结合便是解构传统的质疑声的一种有力回应,同时也印证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是能够相结合却又并不失文化的本真性。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传承。大多数地方均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造一乡一文化品牌甚至一村一品的文化复兴。汶川县雁门乡月里村农历十月初一的“褂卧”节(大还愿)、茂县太平乡牛尾寨农历正月初六的“哟咪”节(跳铠甲舞)、茂县赤不苏地区九龙村正月十五的“厷戊”节(送龙灯)、理县蒲溪乡蒲溪村农历二月初二的“夬儒”节(祭山会)、北川县青片乡尚午村5月份的“情歌节”以及本次松潘小姓乡举办的毕曼歌节,均是对传统节日在现代化语境中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在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国家政策与方针的感召之下进行的乡村文化振兴。
——为混声四声部合唱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