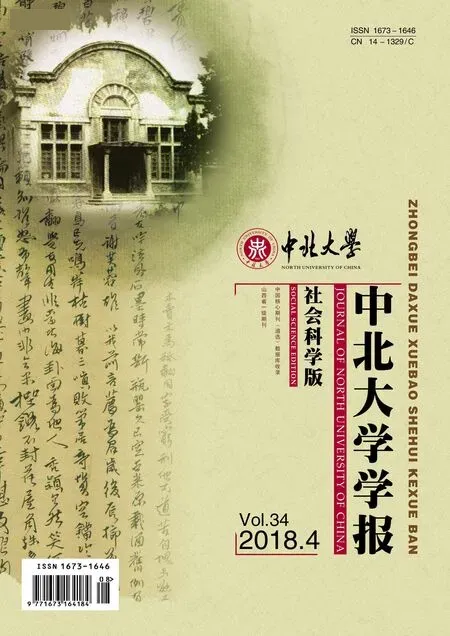大众文化对“民间文化”的继承与改造
徐国源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大众文化通常自认为“草根文化” “庶民文化”或“民间文化”,似乎与精英文化“道不同,不相谋”。 这种“谱系”划分中外皆然,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区隔”不仅相当模糊,而且各种文化之间也经常妥协、互融,可以“混”(mixed)得很美。
从“发生学”角度看,“大众文化”其实与“民间文化”也相去甚远,两者处于全然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是在不同历史场域中生成的文化形态。 可以认为,当代大众文化以“民间”为标榜,借“民间”做广告,其实是简化了“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复杂背景,因而也就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 这种文化思维,也许可以看作是我国由来已久的一种“托古”传统,即我们固有的文化思维惯于从历史传统中寻找话语资源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这种思维带来的问题是古今不分,以古同今。 大众文化正是借助“同化”(而不是“差异化”)思维,一方面建构出“自有来头”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也希冀从文化母体中汲取营养,并按照“当下”原则重构“民间性”。
1 “民间”意识的历史溯源
关于作为文化概念的“民间”和“民间性”,在此有必要稍作梳理。 尽管“民间”作为一个标明社会阶层、文化身份序列的“群体”早就存在,但真正把它看作独立的范畴,并明确提出这一文学概念,则晚至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 在《序山歌》这篇短文中,冯梦龙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同殿堂文学、文人写作相分野的“民间”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 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惟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1]425在这个表述中,冯梦龙很鲜明地指出,以述唱“民间性情”为特色的歌谣,是早就存在的;同时他还指明,这个“并称风雅”的文学源头,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学空间、一种美学格调,是由于遭到历代以来“正统”文学的冷漠和排挤,乃变成了不列诗坛的“山野之歌”。 可贵的是,冯梦龙与“荐绅学士”所持的文学立场不同,他特别推崇这种抒发着“民间性情之响” “不屑假”的歌谣,以为“歌之权轻”的民间文学看上去“浅”,但浅则浅矣,却“情真而不可废也”,因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 正是基于对“非正统”(文学意识) “非主流”(风格和文体)文学审美趣味的认同和赞赏,他便另辟蹊径,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白话小说和山歌民谣,以文学实践张扬了中国文学的一脉,同时也在理论上彰显了一种“民间”的文学价值观念。
冯梦龙所持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趣味,其实也是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学“市民化”的投影。 自明代以还,传统诗文虽无衰落,但更为大众化的白话小说却从“街谈巷语”蜕变为普泛媒介,日趋成熟就是明证。 在市民文学的滥觞期,不只出现了《三言》 《二拍》等整理自民间的话本与拟话本小说,而且还诞生了成熟的长篇小说(即《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和《金瓶梅》“四大奇书”),中国的几大传统小说——历史、游侠、世情、神魔,都因之发展成熟。 这些长篇小说虽属文人创作,但无疑融入了大量来自民间的文化与艺术元素,反映出浓厚的民间意识与民间审美价值取向。
从文学的角度看,明、清以还市民文学勃兴的意义在于:它以切实的文学形象“再现”了一个通俗而生动的“民间”语义场,建立了一种可真实触摸的“民间想像”,并由此影响了后来“民间意识”的积淀和建构。 具体而言,明清通俗小说对文学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侧面:①描绘了一批从权力体制和宗法礼俗中游离出来的江湖游民,彰显了在现实层面被抑制的自由精神文化;②通过描摹市井生活图景,赋予“民间”人性、人情的色彩,大力张扬“民间化”的道德伦常,把从庙堂等级制下恪守道德的“忠”,转为具有民间“江湖”意味的“义”。 人们在文学中领悟的忠奸对立、善恶报应、富贵忘旧、见利忘义、富贵无常、祸福轮回等等,后来成为了中国民间社会最常见和最典范的道德评判模式;③推崇文学(话本)的故事性和传奇性,满足大众观赏性、娱乐性和刺激性的需要,“好看”原则也演变成了小说美学观念最重要的因素等等。[2]
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尽管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旧文化进行了“洗心革面”的改造,如在文学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平民的文学”以抵制“旧文学”;又如1930年以后,革命文学提倡“为工农兵服务” “向民歌学习”等等,但不能忽视的是,即使文学回归理性和“常态”,由“水浒” “三国”和其他通俗文学培育的“民间”意识和伦理,却仍然是我国社会文化结构中较为稳定的层面。 人们还是认同由“传统”积淀形成的观念:“民间”作为一个社会象征系统,它所承载的始终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3],其渊源既包括来自中国传统乡村的村落文化,也包括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 1980年以后,“现代”与“传统”及“革新”与“寻根”等理论话语互为镜像,交替浮出,“民间”问题也在新的语境中再次凸显。 在这次有关“民间”的讨论中,学者们不仅从“民俗学”的知识视野还原它本真的内涵,而且还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民间”乃是一个与“庙堂”相对应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空间,是个性与自由的载体,本源和理想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是在“民间意识”回归文学的同时,“民间”这个社会文化场本身却开始裂变与分化。 回顾1980年前后,一部分作家带着温情描写乡间民俗和市井生活场景,着意于勾画一幅幅古老的中国式城市、乡村民间社会的风俗画卷,如汪曾祺的《受戒》 《大淖记事》、邓友梅的《那五》 《烟壶》、陆文夫的《小贩世家》 《美食家》和冯骥才的《神鞭》 《三寸金莲》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个新名词——大众文化,则直接以“新大众” “新民间”文化自居,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炫目登场了。
2 “民间”作为想像力资源
以邓丽君歌曲的流行和不久以后纷纷登陆的港台影视为标志,它们以不同于作家文学的大众文本形态宣示了“民间”将以自我言说,而不是“作家”的文学想像直接呈现出来。 人们注意到,这些不久后被称为“大众文化”的文本,不仅表达的媒介不同,前者主要以传统的小说、散文形式出现,后者则主要以通俗歌曲、武侠和言情小说、舞台小品、影视剧、新媒体文化等新媒介涌现,而且它的表现内容也不同,如故事、俚语、野史、传说、段子、民歌、神怪故事、“还乡体”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但他们却“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承托着地壳,渗透到规范性文化。[4]这是一个为精英文学陌生的江湖怪客,鲜有“规范”,却生机勃勃,且赢得了巨大的读者群和商业市场。
需要追问的是,长期以来“民间”就一直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存在,但它除了被掠夺以外,一直处在差序化的权力和文化格局中的次等地位,历来被污名化为“下里巴人”,且在文化价值评判中,它的“杭育杭育”歌与文化精英们创造的歌赋雅乐何止相距千里?大众文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何以将“民间”作为想像力资本,并对这个文化符号倾注如此巨大的热情?在我看来,这只能从社会文化的“典范转移”及人们的精神境遇中寻找答案。
2.1 民间是哺育人类的“血缘”之地
真正的民间建立在“身体”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 它较为远离权力体系,保持着自身与土地、植物、动物的天然联系;它既不像政治巫师那样关心宇宙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也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关注自然与社会主体的对应关系。 “民间想像建立在‘身体’与自然的恒久关系之上。 他们想像着自己像谷子一样永远循环往复地孕育、生长、死亡。 他们作为欲望(身体)主体,既是‘人’,又像‘植物’;‘欲望化’是对外部世界的占有,‘植物化’是向外部世界支出。 这种收支平衡状态,使民间想像力既刺激又消解‘身体’欲望。”[5]23因此,与其他承载过多功能的精英文化相比,真正的民间想像保持着“食色性也”的天然状态,就如同一个童话、一曲牧歌,是最为大众化的遥远而亲切的文化记忆。
2.2 从对立视角看“民间”
“民间”看起来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语词,实际却隐含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看待社会政治的传统思维——这就是“民间对体制” “民间对精英” “民间对现代”等这样一种二分式基本视角。 对此,学者甘阳认为,“民间”概念的含混性与“对抗性”的态度取向有关,因而,人们使用“民间”时,云集着各种话语势力,放大了某种“对立性”。 “民间社会这个词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毋宁是一个可以唤起一大堆非常感性的历史记忆的符号。”[6]236因此,“民间”与其说是带有“共时性”的想像建构,不如说是由中国代代相传的无数历史记忆和文学形象所构成的。
2.3 民间想像在大众文化层面的巨大释放某种程度上暗含了人们对现代文明范式的“反动”
且不说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现代文明远未像它标榜的那样尽善尽美,即便科技高度发达如西方世界也并不能真正做到物畅其流,人遂其愿,何况人的精神追求还有许多“非技术因素”必须考虑在内。 著名文学家J·乔伊斯曾以感性的笔触写道:与文艺复兴运动一脉相承的物质主义,摧毁了人的精神功能,使人们无法进一步完善。 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中化为一滴泪水。 当下的“民间想像”,其实就包含了一种“回归”意识,即从商业物流、都市红尘中自拔出来,返回到人之为人的置身之地。 因此,所谓“原乡感” “怀乡症”等情结,莫不包含一种深刻的“时空差异”,涉及了今昔之比和异国他乡与故里老家之比等等。
尽管今天的都市大众远非“乡土中国”的大众原型,但在大众文化策略家的视野里,“民间”作为对应于自然、身体、原乡与历史记忆的多重性“意义符号”,却意外成了最具“卖点”的文化想像。 于是在莫衷一是的状态下,“民间”便作为一个最有力的符号、手段和最终落脚点,成为当代文化最热衷的宏大叙事以及最具有召唤性的文化想像。
3 “民间”的想像性重构与呈现
与作家文学的民间叙事不同,大众文化的民间表述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自足意义的存在。 如果说作家文学所持的民间立场与民间理想,多少还只是由于“在启蒙话语受挫,并同时受到市场语境的挤压之时”,那么作家们鉴于“重返庙堂的理想”已被终结,开始对当代文学精神价值进行一种新的寻找和定位,但深入分析,他们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只是一种由“体制”转向“民间”的视角转换。 而大众文化创作者则不同,他们的民间立场基本立足于本位,无需调整姿态,他们的身份和传统中的三教九流市井人物之间具有某种微妙的血缘联系,所以被“正统”称为城市的边缘人、游走者、文化闲人或“精神痞子”。 随着1990年以后“大众”主体身份建构的完成,其民间立场更为鲜明,它们既与主流保持距离,又与知识精英互不来往,而只是一味地迎合市场和读者,形象一点说,“他们(她们)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成了一种角色定位和商业包装的需要,成了一种对市场份额的谋算”[2]。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化立场和视角的差异,作家文学与大众文化各自的“民间”审美趣味也是迥然不同的。 作家文学提出的“重返民间”,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一种“外视角”,是艺术的想像和“表演”而已,是“为文化而文化”;而大众文化就来自于民间,是“内视角”的真实书写,是民间的自我表现。 用来自城市民间的大众文化的创作者的话说,他们与精英文学艺术的差异在于:大众文化的“根源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就真实地生活在这火热的土地上,我们的出路就在当下现实的改造中,所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就变得很踏实,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 这种直接面对现实的态度,必然会形成不同于主流精英的民间美学:
我知道当我们感受到现实的疼痛时,就会喊出来,正如一个工友说的,我们不可能把这种疼痛写成多么深沉而朦胧的东西。 我觉得民众文艺有着自己的美学,这种美学肯定是区别于主流的、精英的,是大众的,是来自我们劳动第一线的,是要让大家能够来表达的。 而表现形式也是鲜活生动的,让大众能接受的,它当然要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做连接,充分吸取其养分,但肯定不是像一些艺术家那样有洁癖,不是那样唯艺术论。 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7]
这里,大众文化的“宣言者”明确划清了与主流精英的分界线,自觉指认出自己的艺术来自民间生活,具有为民众服务的本质,而且其表达形式和语言也是大众的,它们与“为文化而文化”的唯艺术论观念显然不同。
不过,仍需厘清的是,即便大众文化的理论家和实践者高喊“民间”,指认其为精神故乡,但这个“民间”的语义场毕竟与中国传统乡村的村落文化的状态,或者与来自工业化早期的城镇市井文化的生态已经有了质的差异。 1990年以后,大众文化文本所大致呈现的三种形态,即“乡村民间” “城市民间”和“大地民间”,从根本上讲是新的文化范式的产物,是传媒消费文化的体现,而与自在、本然状态的“乡土的民间”相去甚远。 例如,传统的民间节庆活动——中秋节,原本是一个祭祀节日,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已有“秋分夕月(拜月)”活动。 到了唐代,中秋已成为官方和民间都相当重视的节日。 北宋时,农历八月十五被定为中秋节,并出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节令食品。 众所周知,中秋节最核心的文化内涵是祝愿社会和谐进步和家庭团圆幸福,所以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重视。 但时至今日,中秋节原有的文化内涵逐渐消失,已演变为假日经济和消费文化,中秋成为“月饼节”。 节日被商家包办,沦为美食节、购物节、旅游节,失去了它原来的味道。 过去,中秋节吃的月饼包装很简单、朴素,但负载的美好愿望和生活理想很珍贵,现在的月饼虽然被包装得精美、豪华,却渐渐变成了纯礼品,这些礼品又被负载了另外的内容,比如利益、交换等。 这些当代消费社会的因素融入月饼中,就把节日那种朴素的美好东西冲淡了。
4 结 语
大众文化对“民间”的吸纳与改造,自有其积极意义。 巴赫金等从“狂欢”理论的视角指出,大众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民间欲望的再生产,人们在集体的狂喜之中,一方面预演了一种“天下大同”的乌托邦,一方面从权威真理和既定秩序中解放出来,将阶层等级、性别歧视、文化区隔、经典教义等悉数抛诸脑后。 大众文化所隐藏的正面意义,在于它消除差序、颠覆威权,以反叛、戏谑和讽刺等形式,构成对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冲击,实现了寄托着自由精神的民间文化对传统范式、思维和语言等方面的全面渗透,并以鲜活生命力建构起自身的文化实体,从而有可能跻身于文化的殿堂,实现各种差异性文化的重组。
[1]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张清华.民间理念的流变与当代文学中的三种民间美学形态[J].文艺研究,2002(2):53-64.
[3] 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J].文艺争鸣,1994(1):53-61.
[4] 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5] 张柠.想像力考古[C]∥朱大力.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甘阳.“民间社会”概念批判[C]∥张静.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7] 林生祥,崔卫平,老羊,等.歌唱与民众[J].读书,2008(10):5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