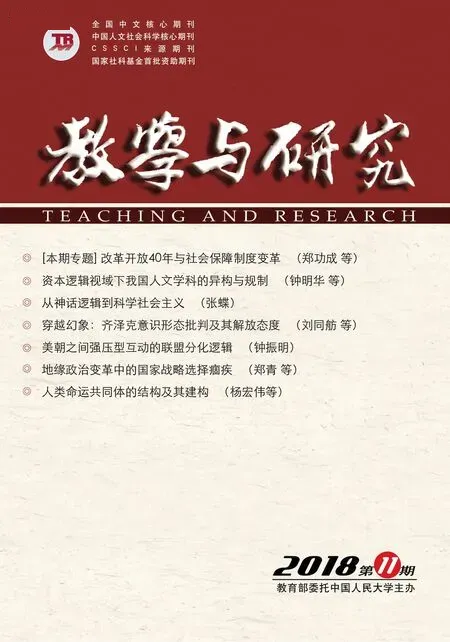穿越幻象: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及其解放态度
,
20世纪90年代活跃于西方学术界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 )否定只要打破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谎言就可以让人获得真实和解放的传统观点,从存在论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及犬儒主义展开了细致的分析与尖锐的批判。他以意识形态为切入点,借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类获取自我主体身份的生命历程进行考察,将意识形态和生命中的本能欲望相关联,睿智地向我们揭示了意识形态背后的心灵隐秘。齐泽克研究意识形态的最终旨趣是关切生活在由意识形态“编织”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命运与解放问题。虽然齐泽克较少在其著作中使用“解放”一词,也没有系统、详尽地论述过人的解放问题,但他从心灵和生命本体层面展开洞悉的意识形态理论蕴含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意识形态及后意识形态时代背景下人类解放面临的新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一、意识形态幻象的指认
齐泽克认为,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意识形态常常与“蒙蔽”“扭曲”和“颠倒”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主要被视为一种为统治阶级利益合法化而辩护的“虚假意识”。马克思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种情形:由于没有意识到运作于社会现实和个人行为中的虚假意识的支配,人们长年累月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忍辱负重、辛勤劳作以维持生存之需,即“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1](P24)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深知自己的处境,他们完全明白事情的本来面目如何,却依旧顺着意识形态规则来行事。换言之,即使人们在理论上已经识破意识形态骗局,明白商品、货币与资本等如何作用于自身,却依然不会与之断绝关系。针对这种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问题,齐泽克根据当前意识形态变化的新情况对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质疑:“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即质朴意识)是否还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这样的意识形态现在还在运行吗?”[1](P25)
在齐泽克看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传统意识形态家对当下意识形态状况的解释是无力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局限于“知”的层面,具有非常明显的启蒙性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培根,从培根开始,人们就把意识形态当作阻碍正确认识获得的假象和偏见。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最为盛行的是一种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它已不再只是简单的谎言,而是走向了启蒙理性的反面,即它使人们知晓官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真实状况间的巨大鸿沟,却依旧能够继续保留这张意识形态面具。“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概念依然是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这样的概念中,意识形态处于‘知’的一边),那么今天的社会必定是后意识形态性的”。犬儒主义(cynicism)使“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有任何真实性可言;人们不再严肃对待意识形态命题”。[1](P30)古典意识形态的逻辑前提是人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意义,需要被启蒙,当今的犬儒主义则是已经被启蒙的意识形态,然而即便如此,它不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式嘲讽,相反,它是对现实的屈从,是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响应。由此,我们毫无防备地坠入一个新的后意识形态时代,相应地,合法化已经取代真理,成为判定意识形态的法则。
齐泽克深受拉康的影响,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精神分析学式的改造,指出当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关系不大,反而和“无意识”相连甚密,即是说意识形态不止作用于人的大脑,更多地直接作用于人的欲望,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无意识。按照拉康的观点,人的生存状况可分为“三界”:想象界、象征界或现实界、实在界(“三界”并不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而是一种交错介入的拓扑结构)。想象性自我是自己最为满意的理想意象,却不具备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人只有经过文化符号秩序建构才能走出想象界被文明所认可,获得“象征界”中的主体身份,而这种主体身份的获得还意味“实在界”中的本真自我的缺失。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缺失,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真相,而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因为人要想认识自我、获得独立行动能力并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以积极的方式接受他者质询,与自己原初状态中的真实自我进行分离,向幻象和误认沉沦,否则就会成为被社会所排斥和挤压的边缘人员。因此,“成长”的过程必然伴随人被阉割的“创伤性的损失”,造成的结果就是,丧失本原性和真实性的主体从内心深处渴望一个掩盖其创伤的客体对应物,以幻想的方式找回自己的损失。拉康通过幻想公式$◇a对此进行了说明:$表示的是短缺的、被撕裂的主体;◇是一道屏障;a是主体欲望趋向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即幻象客体。短缺主体对本原性真实的追逐和欲求是一个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的过程,这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生存之困。
齐泽克在承继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将拉康的欲望概念引入意识形态研究中。他认为,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的人们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而总是被象征秩序打磨和塑造着,但并不是所有的自然本性都会接受这种塑造,因而产生对抗性的裂缝和缺口,未被塑造的“硬核”就需要意识形态的缝合。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在于此,它不仅是掩饰社会冲突的虚假表象,还迎合人的欲望,提供一个让人憧憬和希冀的幻想对象,又称崇高客体。生活于由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所建构的非物质性幻觉中,人们感受到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不会质疑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真理性,总是对其不打折扣地全盘接受。“意识形态真正重要的,是它的形式,即下列事实:向着一个方向,尽可能地沿着一条直线,不停地走下去;一旦下定了决心,即使最可怀疑的意见也要听从……他们必须相信,他们的理由绝对充足,他们的决定会使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1](P99)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奴役和剥削并未真正消失,反而比之前更为隐秘和残暴,成为一种“隐性暴力”,可是被象征秩序所限定的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们依然坚信平等这一幻象客体。因此,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与其说和政治、经济挂钩,倒不如说它和欲望、快感等心理因素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和直接。面对纷繁复杂、层次交错的大千世界,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观念的权威,头脑中向往着也充斥着崇高的观念。因为意识形态唤醒了弥补“真实的缺失”的原始冲动和回归完整自我的内心渴望,只有意识形态能够克服现代人在自我身份确立过程中由真实的虚无所造成的焦虑感,满足返回未经分裂和异化的本原性真实世界的欲望,使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的必需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认为,在“后意识形态社会”中,意识形态已经冲破“社会意识”的界限,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存在”。他对意识形态和人之生存境遇关系的深度思考超越了意识形态真假、对错、是非的争论,将其定位为一个生存论概念,即意识形态像幽灵一样既可以幻化为观念的存在,也可以幻化为物质的存在,更以“无意识”或“非意识”的方式,渗透于现代人所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实存在本身。意识形态作为对现实的幻觉性再现,存在于无意识主体的欲望活动中,镶嵌在文化传统、语言、市场、媒体等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各种规则之中,积极创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本身,是一种人们无法逃遁的、客观的社会存在。
二、意识形态幻象穿越与解放症候
社会现实不可能是一个肯定的、完整的和自我封闭的实体,而总是充满对抗、矛盾和冲突。面对这种“不幸”,谋求人类解放主要呈现三种态度:一是积极行动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二是悲观地认为无法谋求改变人类命运实现彻底解放的法兰克福学派态度;三是坦然承认、与之妥协,这正是齐泽克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面对现实现状,人唯一能做的是“将其视为自己无可避免的命运接纳下来,然后投身其中,接受它的观点,同时回溯性地置身于过去(未来的过去)的有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可能性之中(‘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的灾难就不会发生’),我们现在就要按照这种可能性采取行动”。[2](P10)
齐泽克坦然接受种种对抗与苦难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意义,但绝不意味着他就此放弃对当代社会的质疑和批判。相反,他以一种源自生命关怀的情怀,找到了激发人类不懈追问自身命运的基点,通过对意识形态幻象的不断穿越来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批判的首要目标不是去揭露,而是去体验、去穿越,即透过社会的象征体系“直抵作为快感内核的根本幻象(fundamental fantasy)”,然后“穿越幻象,与幻象保持距离,注意幻象构成(fantasy-formation)是如何遮蔽、填补大对体中的空隙、匮乏和空洞位置的”。[1](P87)他在这里实际上想要表明的是,意识形态幻象通过塑造客体的崇高形象,创设了一个和现实状况迥然相异的社会图景——没有阶级剥削、没有贫富分化,只有人们团结合作、其乐融融的画面。人们乐于沉浸在这种有机体的整体意识中,甘愿像鸵鸟般忽略社会的分裂和冲突。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魔力,倒不是因为其本身真的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在于它处在社会对抗伤口的原质位置,能够巧妙地掩饰实在界的创伤,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和快感。
意识形态幻象的掩饰作用不是绝对的,它希图捕获所有,构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社会存在,但社会的现实存在并非实在界,实在界是象征符号无法抵达的彼岸,它总能逃脱象征符号对自己的控制。所以,意识形态无论如何完备、巧妙,都不可能天衣无缝,总会留下不能被同化的创伤性裂口并以“症候”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作为)现实(体验的东西)不是‘事物本身’,它永远已经被象征机制象征化、构成和结构——而问题就在于这么一个事实,象征最终永远失败,它永远也不能成功地完全‘覆盖’真实,永远包括一部分未处理的、尚未实现的象征债务。”[3](P27)齐泽克通过对“症候”的分析揭露了意识形态的残缺不全性及其可能导致的自我瓦解性。所谓“症候”就是蕴于普遍之中的特殊,这种特殊遵循在现实中发生作用的普遍逻辑最后有可能导致普遍的解体,严格说来,症候“是属(species),它颠覆了自己的种(genus)”。[1](P16)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方式也是症候式的,因为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虚假的,就在于它将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广大无产阶级这一特殊群体排除在外、不予考虑。在齐泽克的理论视野中,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距离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与其不被承认的特殊性前提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社会症候公然挑战意识形态的“真实”,颠覆意识形态表象 (ideological appearance),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点”。
齐泽克认为,既然意识形态得以成功架构的前提是“排除”,即为了维持社会机体的纯洁性、完整性,普遍性就必须将特殊性“杂质”予以排除,那么对被排除的特殊性的认同就是与之相对的被压迫阶级的政治斗争。穿越意识形态幻象就是要认同症候,承认社会特殊性存在的合法地位,并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将其提升到真正的普遍性高度。例如,要想推进人类社会完善、进步的伟大事业就需要认同无产阶级,将无产阶级提升到“所有人”的高度,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特殊群体能够代表全人类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遭受超负荷的体力和脑力消耗,是所受苦难最深、革命性最强的阶级,而在于它是现代社会冲突的体现,是失序的群体。但是,正如幻象不是消除也不是超越,而只是“穿越”,症候也只能是认同,即使它是由符号建构的现实世界通向未被符号驯化的原初真实世界的积极因素。社会症候的消除必将意味社会本身的分崩离析。也就是说,彻底消除症候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对抗性分裂只能被掩盖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弭,社会问题和所有关于人和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均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我们真正现实能做的事情唯有坦然接受。
齐泽克之所以不像左派理论家那样采取直接抵抗的方式而选择认同症候的原因还在于他清楚地知道前者的局限:反抗压迫性的大他者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积极主动,但不能带来宏观层面上的彻底改变,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问题,甚至造成的结果反而是维持资本主义的整体不变。任何没有真正动摇支撑大他者存在根基的零星式反抗实质上都不够彻底,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再度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勇敢肯定,在当今这种形势中,真正打开革命的可能空间的唯一方式,就是彻底摈弃对直接的行为的倡导。当今的窘况在于,如果我们屈从于‘做些事情’的号召(投身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帮助那些穷人……),就确定无疑地是在帮助既存秩序进行再生产”。[4](P72)齐泽克认为,抵抗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还有可能事与愿违,最终更难摆脱资本本身。齐泽克的这一态度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有关。在他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即否定之否定不是消灭差异,而是保持矛盾分裂力量的统一。因为矛盾、对抗等就是社会的本来状态,一切试图消除冲突的努力都注定不会成功。“否定之否定的基质,不是一种丧失和丧失的恢复,而只是从状态A向状态B过渡的一个过程:首先,对A的直接‘否定’否定了A的位置;但它仍然在A的象征限制的范围内,所以,它接下来必须被另一种否定所否定,这一否定可否定对A直接的否定以及与A共有的象征空间。在此,否定系统的‘真实的’死亡与其‘象征的’死亡之间存在的空隙很重要:系统不得不死亡两次。”[5](P80)按照这种全新的理解,微观层面的直接抵抗只否定了一次,即对资本主义内容的否定,这种否定还不能导致其彻底死亡,因为资本主义依旧处于自身的象征范围之中,依旧具有自我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故要挣脱“抵抗—反制”的周期性循环,就必须重构一种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规划,去努力进行再政治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齐泽克主张放弃抵抗,以非主动的方式来面对人类的不幸,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从反面证明事物的无意义,传达出意识形态批判的“空白”。“建立真正的彻底改变的基础的唯一方式是,从此类行为中抽身而退,‘什么都不做’,以此打开一种与之不同的行动的新空间。”[4](P72)齐泽克看到了抵抗的局限,并提出一种反向逻辑,即“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貌似消极,实际上它是对否定性的偏好,一个不依赖任何欲望对象的破坏。但是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齐泽克显然明确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目标,他所反讽式地提到的‘透明的、得到合理管理的社会’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憧憬的人类最终全面解放的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站在拉康立场上的齐泽克这里,这种最终解决方案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6]
与马克思所主张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观点不同,齐泽克坦然接受了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把所有试图打破现存不合理社会结构的构想都视为徒劳无益的意识形态式的崇高渴望。在齐泽克看来,反对现存状况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穿越意识形态幻象而后承认社会创伤性裂口。也许人类终将无法洞察清楚意识形态背后的真正谜底,但对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局限性却应当保持足够的清醒,这大概是理性发挥作用的最终边界,也是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价值所在。
三、妥协性批判与解放态度
作为一名后现代哲学家,齐泽克以冷峻、犀利的眼光发现所谓的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盲点”,重新运用由弗洛伊德开创,经过拉康、弗洛姆等人发展的精神分析法来剖析意识形态,洞穿了其所掩盖的真实短缺,不仅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认知,更为我们把握当代社会生活发展的新动向供给了富有活力的思想资源。
第一,齐泽克拓展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领域,揭示了意识形态背后的心灵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心理层面来捕捉自身,寻求改变外部环境以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道路。从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方法来探索意识形态是一大趋势。齐泽克将“欲望”这一心理学概念引入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之中,细致地考察了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激发、压抑主体欲望的手段来控制个体。我们可以将这一运作过程详细表述为:受意识形态询唤——生成意识形态图像——产生要与意识形态图像一致性的欲望——将意识形态图像当作是自我本真欲望的呈现。这一阐释发现了个体通过意识形态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所建构的认知框架来限定或引导个体体验自己所生活的现代社会的规律,从心理学角度完善了意识形态何以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巨大效用的机制问题。它启示我们:不仅要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研究人类解放问题,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现实的行为活动进行心理分析,合理引导人们从善向美的心理欲望。
第二,齐泽克敏锐地觉察到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回击了当前甚为流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指出我们正处于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表达、传播意识形态的时代。在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中,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否定意识形态,实则借助资本这一力量企图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向全球推广。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就有一种声音,即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意识形态衰落的社会,统治阶级已经绕过了意识形态,而直接凭借社会生活进行自我管控,如经济领域中的失业、薪水、竞争等。然而,齐泽克识破了这一阴谋,深刻地指出将意识形态虚无化的方式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设置”,就其本质而言,依然难逃意识形态循环的窠臼。在这一点上,齐泽克与拉克劳等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同,他秉持马克思基本的批判立场和价值取向,明确坚决地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揭示当今意识形态的幽灵性、隐蔽性、流动性趋势,使人们意识到在一个系统的暴力结构之中,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复杂性和其“理性的狡计”的真实面相。人们不能被意识形态幻象所“迷惑”,而要正视社会矛盾、社会对抗等“实在界”创伤。
齐泽克虽然对当前人类社会境况的批判入木三分,发现生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意识到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却无法放弃对其依赖的荒谬现象,但没能找到可以超越荒谬现象的切实可行路径。他尝试穿越意识形态幻象,最终却又无可奈何地选择接受并认可意识形态幻象,甚至干脆把意识形态当作客观的社会存在。这削弱了他的批判力度,淡化了其意识形态批判中的解放态度,显示出齐泽克理论的内在不足。
第一,意识形态幻象理论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它一方面把意识形态视为和实在相对立的幻象来抨击,另一方面又淡化甚至取消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而将其同化。这样不仅否定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更难真正找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因素。齐泽克拒斥意识形态分析的表象主义方式,认为意识形态和其扭曲的内容、颠倒的表征关系不大,他对于意识形态的考察不再仅仅停留于虚假意识的层面,而是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现实的幻象性,甚至其着眼点就是脱离物质生活的幻象。于是,齐泽克眼中的“社会现实”就“成了一个伦理建构(ethical construction);它由某个‘仿佛’支撑”。[1](P34)他在批判意识形态幻象掩饰对抗性分裂的社会存在的同时,又承认这种对抗性分裂的意义,即它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同其他后现代思想家一样,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了本体论的设定与方法论的探究策略之间的悖论。
第二,齐泽克以把马克思拉康化的方式来研究意识形态,从功能、结构等维度过分扩展意识形态的界限,最终把它泛化成一个和人类社会永恒相伴的文化现象。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意识形态,看到被表面美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掩盖的背后真正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目的在于让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主客体颠倒的世界。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根据。所以,马克思提出意识形态消失的条件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的全面实现,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然而,拉康的“大能指”“认同”“创伤的内核”等概念却使意识形态问题重新非历史化和形而上学化,最终把意识形态的斗争变成“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的永恒冲突,这样就否认了消除意识形态笼罩,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基于这种错误的理论,齐泽克有意无意地为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护,远未达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高度。
第三,齐泽克虽然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最新形式——犬儒主义给予了精辟的分析,却没有合理阐明其存在的背后根源,更没有真正理解人类当前社会的现实。在齐泽克看来,支撑人们行为的不是对现实的判断,而是越过人的意识恐惧而产生的幻想。因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危机就是知识和真理不再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反而与“无意识”亲密相连,知识和真理不再作为行动的精神动力,因此人们心甘情愿接受意识形态营造的梦幻世界。然而,真正的解放不在于词句中、也不在于幻觉中,而是人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摆脱各种束缚,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作为崇高客体的“意识形态幻象”虽然在主观上迎合了现代人的欲望,但能否将其完全指认为一种由无意识主导的行为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意识形态的方法论维度上,齐泽克强调的是具有审美与伦理色彩的穿越策略和精神分析方法,而马克思强调的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实践批判和改造、建构的方法,这就导致马克思与齐泽克各自理论发展具有截然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