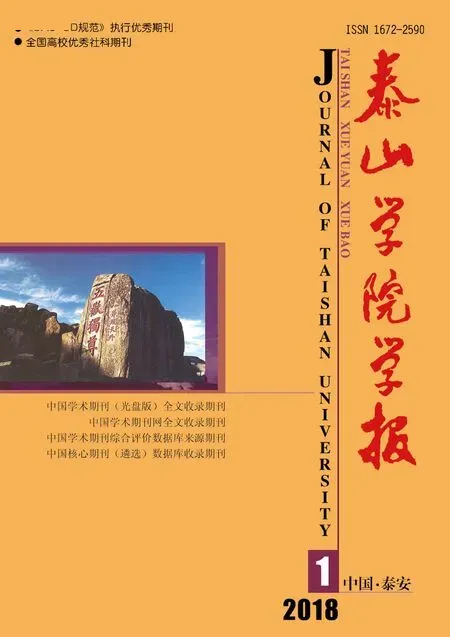论况周颐艳词观对其“重拙大”词论的影响
王 纱 纱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况周颐为晚清著名词人,论者对其“重拙大”的词学观点一般都给予很高评价。如朱孝臧认为况氏所著《蕙风词话》标举“重拙大”之旨,发前人所未发,实千年来之绝作。[1](P463)夏敬观云:“重、拙、大为三要,语极精粲。”①然而亦有批评者,如张尔田云:“《蕙风词话》标举纤仄,堂庑不高。重拙指归,直欺人语。”[2](P433)吴世昌云:“蕙风警语,曰重拙大。诚有重拙,未见其大。其词话摘艳,举梦窗之心事称睡妆红晕。今观其造语,明而未融;察其设喻,纤而伤巧。”[3](P8)也有学者认为况周颐所举例词不尽合其“重拙大”之旨,并分析“这是因为真正符合重、拙、大之旨的词其实并不多,这说明这个理论缺乏足够的创作依据”[4](P56)。有时恰恰是批评的声音更能引起思考,特别是当它们聚焦在同一点时。上述批评即有同样的认识:况周颐的论词主旨是“重拙大”,而他所举的词例是“纤仄”的、“艳”的,“重拙大”的观点缺乏理论依据,有欺人之嫌。对于“重拙大”为何会有如此迥异的评价?弄清“重拙大”与艳词的关系是找出答案的关键。实际上况周颐悟入、解读“重拙大”是以艳词为基础推及其他词的,并于“重拙大”的理解加入对艳词的独特体悟。从艳词的角度观照况氏“重拙大”之论,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明晰“重拙大”的含义,而且也有助于完善况周颐的词学理论及晚清民初词学理论的建构。
一、况周颐的艳词观
艳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艳词总括一切描写美女与爱情的词,狭义的艳词一般指写得淫亵而秾艳的作品。[5](P50)在《蕙风词话》中,不但涉及广义的艳词,并且也常常提及“淫亵秾艳”一类的艳词。如评荣諲《南乡子·咏梅》“似个人人玉体香”,况氏云:“‘似个’句艳而质,犹是宋初风格,《花间》之遗。”(卷二)又张孝祥《菩萨蛮·东风约略吹罗幕》:“佳人双玉枕。烘醉鸳鸯锦。折得最繁枝。暖香生翠帏”,评曰:“此词绵丽蕃艳,直逼《花间》。”(续编卷一)况周颐都是站在肯定的角度褒赏秾艳之词。况氏曾做比喻说明何者为“艳”:“词笔‘丽’与‘艳’不同。‘艳’如芍药、牡丹,慵春媚景;‘丽’若海棠、文杏,映烛窥帘。”(《蕙风词话》卷二)芍药、牡丹与海棠、文杏相比,花大色艳。“慵春媚景”让人联想到花朵之繁盛,色彩之秾艳、春日之生力、姿态之娇媚、色调之明朗,相较之下“映烛窥帘”则是朦胧隐约、清丽淡幽的。据此推至论词,蕙风认为如芍药、牡丹“慵春媚景”般直朗意秾的花间词当是艳词中的典范之作。正是由于对艳词的这种体认,况周颐对《花间集》评价甚高:
唐五代词并不易学,五代词尤不必学,何也?五代词人丁运会,迁流至极,燕酣成风,藻丽相尚。其所为词,即能沉至,只在词中。艳而有骨,只是艳骨。……晚近某词派,其地与时,并距常州派近。为之倡者,楬橥《花间》,自附高格,涂饰金粉,绝无内心。与评文家所云“浮烟涨墨”曷以异?(《蕙风词话》卷一)
《花间》至不易学。其蔽也,袭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所谓麒麟楦也。或取前人句中意境而纡折变化之,而雕琢、勾勒等弊出焉。以尖为新,以纤为艳,词之风格日靡,真意尽漓。……庸讵知《花间》高绝,即或词学甚深,颇能窥两宋堂奥,对于《花间》,犹为望尘却步耶。(《蕙风词话》卷二)
况氏曾言:“真字是词骨。”(《蕙风词话》卷一)夏敬观释之曰:“若夫以真为词骨,则又进一层,不假外来情景以兴起,而语意真诚,皆从内出也。”(《蕙风词话诠评》)蕙风论词以真情为本,他认为《花间》艳词就具有“真”的特质。五代多动荡,人心机巧善变,世风崇尚享乐浮华,只有《花间集》中表现爱情的艳词才“沉至”真诚。龙榆生对此解释得更为浅明,庶几可作注脚。龙氏说:“晚唐、五代之词,所以多为儿女相思之情,与留连光景之作者,处衰乱之世,士习偷安,月底花前,浅斟低唱,所谓‘不为无益之事,曷以遣有涯之生’也。”[6](P104)蕙风在批评某些效颦者“涂饰金粉,绝无内心”,“袭其貌似,其中空空”时,也是强调《花间集》成就“高绝”的至要因素是感情之“绝真”,真力充沛,词愈艳而情愈深挚。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车感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7](P64)二人所论主旨有相通之处。“亲切动人”、“真力弥满”正是蕙风所推崇的至艳之词的独特美质。
蕙风《餐樱词自序》记其词学经历云:“余自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在所不免。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阅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而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广蕙风词话》卷七)这则材料以往主要被用来说明王鹏运是况周颐的词学导师,或者“重拙大”的理论来自半塘。其实这段话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性灵”与艳词的关系。况周颐注重性灵,初涉作词(实际贯穿整个词学生涯)“性灵”即起到了重要作用。蕙风才高颖慧,出于性灵偏爱艳词,初学作词即成艳体风格。况氏词弟子赵尊岳所撰《蕙风词史》云:“先生初为词,以颖悟好为侧艳语。”他同时也承认,有一类“尖艳”的词艺术成就不高,“今日万不能道”。后来在王鹏运的帮助下,蕙风词的尖艳风格得到了改进。
第二,如何修正这些尖艳之词?况周颐渐渐悟出“重拙大”、“自然从追琢中出”的方法,用以提升词的体格。从他的自述中能看出,“重拙大”、“自然从追琢中出”,是对他原本尖艳词风的修正。换个角度说,他是在尖艳词创作的基础上,在尖艳词风的修正中悟入“重拙大”、“自然从追琢中出”的。况氏云:“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拙大。厚与雅,相因而成者也,薄则俗矣。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矣。”(《广蕙风词话》卷一)在《蕙风词话》中,不仅正面解说重、拙、大(厚、雅)标举了许多艳词,更举了大量艳词做为反面示例释义轻、巧、纤(薄、俗)。若有论者说况周颐“标举纤仄”、“摘艳”也不算有违事实,只不过没有领会蕙风恰恰以艳词阐明“重拙大”的苦心,而这又可作况氏是以艳词悟入“重拙大”的旁证。
第三,引文说“体格为之一变”,那么蕙风词究竟变为何种体格?其实况氏所作仍是艳词一路,只是由“尖艳”转为“顽艳”。蕙风虽然从王鹏运改塑词作的体格,但他对艳词坚持自己的偏嗜。他在《玉梅后词》自序中说:“半塘谓余,是词淫艳不可刻也。夫艳何责焉?淫,古意也。三百篇贞淫,孔子奚取焉?……吾刻吾词,亦道其常云尔。”(《广蕙风词话》卷七)况周颐是借用王鹏运的“重拙大”的观点来改造艳词,为自己原来所作的尖艳之词找一条解救之路,然而并未打算改变初衷,放弃艳词。王鹏运说“淫艳不可刻”,但况周颐为自己辩护:“夫艳何责焉?”他认为自己做艳词有理有据,有何不可?此集最终还是付梓。
艳词是况周颐所坚持不弃的“常道”。赵尊岳记况氏暮年曾“为词不能艳叹”,并说:“先生以少年之词,风流自赏,每见性灵,故郑重自惜者特深。睱日并作《浣溪沙》《恋绣衾》,以拟《新莺》《存悔》于二十年前。”(《蕙风词史》)蕙风自己也说:“唯绮语,则知其非宜而不能戒,第较有斟酌耳。”[8](P522)他喜作艳词,但也不固执拒谏。在不断地斟酌修正之下,词由少年时的尖艳蜕变成顽艳。况氏在《二云词》自序中说此集所收词“顽而不艳,穷而不工”(《广蕙风词话》卷七),然而遍览词集发现并非“不艳”,他拈出的“顽”、“艳”二字形容后期的词作却十分贴切。正可谓“性情与襟抱,非外铄我,我固有之”(《广蕙风词话》卷一),源于性灵心性况周颐至老仍衷情艳词,“重拙大”与他毕其一生对艳词的涵泳玩索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重、拙”与艳词
关于“重”,《蕙风词话》卷二云:“重者,沈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沈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沈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重”即沈著,是内源于“厚”的外现。“重”是在气格,而不在表面词句。吴文英词多爱情之作,芳菲铿丽,艳字隽句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然而因其中有气格、“沈挚之思,灏瀚之气”能笔端驱使艳字隽句流转,便可以做到“厚”。关于梦窗词的华丽典赡与“厚”的关系,蕙风评价道:“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琱璚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同上)清末学梦窗词者弊端丛生,原因就在于他们只学了梦窗的艳词丽字,却无由“厚”而生发出的魄力,无法作到情真理足,有笔力能包举这些艳丽词藻。由此可知,蕙风认为外在艳辞丽句并不会损于“重”,怕的是没有气格,没有魄力。并且,因为“重”可使堆砌的艳丽词藻得以生动飞舞,可以说“重”是艳词的一种救赎之法。
“轻者重之反。”况周颐也谈到“凝重”与“轻倩”两者于填词的关系:“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若从轻倩入手,至于有神韵,亦自成就,特降于出自凝重者一格。……或中年以后,读书多,学力日进,所作渐近凝重,犹不免时露轻倩本色,则凡轻倩处,即是伤格处,即为疵病矣。天份聪明人最宜学凝重一路,却最易趋轻倩一路。苦于不自知,又无师友指导之耳。”(《蕙风词话》卷一)这可视为是蕙风夫子自道的一段话。他少时作词入手即尖艳轻倩一类,其《存悔词自序》云:“余性嗜倚声,是词为己卯以前作,固陋。无师友切磋,不自揣度,谬祸梨枣。戊子入都后,获睹古今名作,复就正子畴、鹤巢、幼遐三前辈。”(《广蕙风词话》卷七)《餐樱词自序》云:“(于词)其得力于沤尹与得力于半塘同。人不可无良师友,不信然欤。”(同上)“从轻倩入手”、“苦于不自知,又无师以指导”之语,正与其自述学词经历相吻合。所言“填词先求凝重”、“从轻倩入手,特降于凝重一格”、“凡轻倩处,即是伤格处”等语,也可说是他自己创作艳词的经验与反思之谈。
“拙”也是结合艳词进行阐释的。关于“拙”,况周颐并未直接解释,而是举例加以说明。“巧者拙之反。”在评明末陆钰《射山诗余》时,他从正反面论及“拙”与“巧”,通过对比来展现“拙”的含义。《蕙风词话》卷五云:“《小桃红》歇拍云:‘终踌躇、生怕有人猜,且寻常相看。’因忆国初人词有云:‘丁宁切莫露轻狂。真个相怜侬自解,妒眼须防。’此不可与陆词并论。词忌做,尤忌做得太过。巧不如拙,尖不如秃,陆无巧与尖之失。”《小桃红》全词云:“十载风尘怨。两载私心愿。本拟当炉,更当庐□,恰逢冰泮。偶闻君容易画双眉,枉教人肠断。百里轻舟幔。十日青山畔。细语微挑,芳心再□,此情应见。终踌躇、生怕有人猜,且寻常相看。”②此词虽有两处阙文,但仍可明显看出这是一首爱情题材的艳词。词中以女子口吻写在爱情追求过程中殷切的期盼和深深的忧虑。“本拟”诉其盼望、“冰泮”是其挫折,“寻常相看”是其应对。词中“偶闻君容易画双眉,枉教人肠断”,“终踌躇,生怕有人猜,且寻常相看”,直言自己的深情,富有感染力。而“丁宁”句有刻意而为的曲折,叙情上欲说还休,“切莫”、“须防”的用词增重了遮掩躲闪意味,感情传达上就不如前者强烈。因此,巧不如拙,尖不如秃,“拙秃”的美感胜于“尖巧”。
在解释“拙”时,蕙风又与“质”连用。质,本真浑成之意。论及“质拙”,艳词同样被用作例证。
李蠙洲《拋毬乐》云:“绮窗幽梦乱如柳,罗袖泪痕凝似饧。”《谒金门》云:“可奈薄情如此黠。寄书浑不答。”“饧”、“黠”叶韵虽新,却不坠宋人风格。然如“饧”韵二句,所争亦止累黍间矣。其不失之尖纤者,以其尚近质拙也。(《蕙风词话》卷二)
《虞美人》云:“可怜旧事莫轻忘。且令三年、无梦到高唐。”余甚喜其质拙。(《蕙风词话》卷五)
前一条论《拋毬乐》《谒金门》二词差强人意,从反面举例说明雕琢太过有损“质拙”。“饧”“黠”为险韵,作韵字在诗词中并不多见,用饴糖比拟泪痕也算巧妙,然而求新之心太盛,则不免露出刻意求工的痕迹。蕙风说:“诗笔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为曲折”,“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词太做,嫌琢”(《蕙风词话》卷一)。此二词正是雕饰过多。唯写相思情真意切,掩盖了词中的“匠气”,因此蕙风仍许其“质拙”。后一条从正面举例何者为“质拙”的好词。“可怜”二句同样是写相思之苦,用常见之韵(忘、唐)写常有之事(梦),词笔朴素自然。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将黯然魂销的别情直接发抒出来,情感如自肺腑流出,也给读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动,正可谓“愈质愈厚”(《蕙风词话》卷三)。
总体说来,“拙”是指用朴质之笔写真挚之感,强调自然浑成,反对雕饰太过。蕙风选用大量艳词为例说明来解说“拙”,表明上乘的艳词符合“拙”的主旨意趣,艳词(以及其他词)也可借助“拙”来弥补雕琢太过的不足。可以看出艳词是“拙”的理论总结与创作实践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三、“大”与艳词
蕙风所论的“大”当为情而言,且在情前要加一个修饰语——真诚秾挚,即赵尊岳评蕙风词所用的“以真率之笔写秾挚之情”(《蕙风词史》),移用来说明“大”的内涵也非常适合。“大”以真率之笔所抒写的秾挚之情为核心,表现为由秾挚之情所具有的感人力量,使读者不由自主产生更广泛的联想(如同样坚挚的君国大义),从而形成更丰富的审美效果。
提及“大”且常被引用来讨论“大”的词话有两则,这两则均涉艳词。一则与欧阳炯的《浣溪沙》有关。《蕙风词话》卷二云:“‘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半塘僧骛曰:‘奚翅艳而已,直是大且重。’苟无《花间》词笔,孰敢为斯语者。”对于这首“莫艳于此”、艳到极致的词,况周颐认为它是包含“大”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况氏在这里以至艳之词来讨论“大”,仍然是以“真挚秾情”为出发点。他说:“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又引扬雄《解嘲》“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句,评到“略可喻词笔之变化……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同上)可见,蕙风的艳词观是与“大”相契合的,欣赏的是元气充沛,真性酣畅,语愈艳而情愈挚诚。重、拙、大是一个整体,况周颐认为《花间》艳词重、拙、大三者兼具。“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知此,可以读《花间集》。”(同上)欧阳炯的这首《浣溪沙》词即是浓穆的。因为静穆,所以能在若有似无的薰香中听到喘息之声,能凝视轻罗华服下肌肤的纹理。情爱的恣情欢畅,露骨真质,给这首词灌注了弥满之情。是为“浓”。在蕙风看来,这首极艳之词便是词中极高之境。
另外一则与况周颐自作艳词有关。《蕙风词话》卷一:“《玲珑四犯》云:‘衰桃不是相思血,断红泣、垂杨金缕。’自注:‘桃花泣柳,柳固漠然,而桃花不悔也。’斯旨可以语大。所谓尽其在我而已。千古忠臣孝子,何尝求谅于君父哉?”《玲珑四犯》序云:“寒食前二日,晚泊梁溪,是日咯血勺许,作浅脂色。”词云:“碧悄岸云,红愁渔火,客怀低黯如雨。早知春梦恶,不合吴城住。吟魂料量在否。为谁销、问花无语。忍更推篷,不如昨夜,犹见去时路。天涯漫赢羁旅。况韶光别后,须拌虚度。总然真薄幸,但保修眉妩。衰桃不是相思血,断红泣、垂杨金缕。常记取。多情是、相逢暂许。”[9](P194-195)此词原刻入《玉梅后词》,为蕙风悼念爱妾桐娟所作。词人在羁旅漂泊中,深念亡姬,病痛不已竟至咯血。词至下阙情愈转重。“总然真薄倖,但保修眉妩”,意味纵然对方薄情,但是“我”也要画眉梳妆。对自我容颜的珍视,也是对这份爱情的重视,表现了对待爱情的一往情深。桃花落红如泣,而垂柳漠然不理。想桃、柳本无情草木,如何“如泣”、“漠然”?所谓“感时花溅泪”,以人之多情视草木亦多情。蕙风评萧吟所《浪淘沙·中秋雨》“贫得今年无月看,留滞江城”时说:“无月非贫者所独,即亦何加于贫。所谓愈无理愈佳。”(《蕙风词话》卷三)“愈无理愈佳”用来评此词也很合适。而这一份情深意重、只为付出而不计所得的执著感情,能让读者自然联想到忠臣孝子的执著无悔。
“大”的理论承继了比兴寄托的遗则,但况周颐更注重真情的感发力量,尤为反对刻意寄托,强相皮傅。他说:“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于无变化中求变化,而其所谓寄托,乃益非真。……夫词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尝有寄托,何尝不卓绝千古,何庸为是非真之寄托耶?”(《蕙风词话》卷五)他认为填词首要的是真情自然流露,不能先存寄托之心而有意为词。《金荃》《珠玉》在写作时本无意寄托,但因为其中有词人身世遭逢的真意,故而具有巨大的感动力量。《金荃》和《珠玉》都以艳词精妙著称,正如蕙风所言“情者性之所发,臣忠子孝,皆缘情至,非忠孝人必不工言情”(《广蕙风词话》卷四),因此况氏将二集视为寄托的佳作,也是“大”的范例。
士大夫在易代之际忠孝观念反激强烈,“身世之感”尤其悲切。如金元之际的李治(《蕙风词话》卷三),明清之间的屈大均(《蕙风词话》卷五)等,况周颐也通过例举他们的词来解读“大”。而艳词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他评元好问的词为例:
元遗山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崔立采望,勒授要职,非其意指。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鹧鸪天》三十七阕,泰半晚年手笔。其《赋隆德故宫》及《宫体》八首、《薄命妾辞》诸作,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而其苦衷之万不得已,大都流露于不自知。……句各有指,知者可意会而得。其词缠绵而婉曲,若有难言之隐,而又不得已于言,可以悲其志而原其心矣。(《蕙风词话》卷三)
元好问金亡不仕,以故国文献自任,构筑野史亭,采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遗山的“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沉重挚诚,词中万不得已的苦衷令人不忍寻味,却又不由得去寻味。遗山词中多故国之思,况周颐特别举其中“蕃艳其外,醇至其内”的词为例,像《宫体》《薄命妾辞》都属艳词,诸词都情深入骨,他对艳词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蕙风选艳词来解说“大”,盖出于对艳词的偏嗜,或认为艳词解说“大”更具代表性,不当纯以无心之举视之。
叶嘉莹教授认为:“我以为在历代词评家之中,当以况周颐对艳词最有深切的体认,且曾做过大胆的肯定。”[10](P196)从况周颐对“重拙大”的讨论中能够看出,“重拙大”与艳词有莫大的关联。蕙风论词将“情”、“真”作为立足点,认为艳词凝结了至真至性,词愈艳而情愈真,所以不排斥那些一般人看来“淫亵露骨”的艳词。浓挚之情即是“重拙大”的内核,因为情之浓挚所以有气格,有“沉挚之气,浩翰之思”(重),所以朴质不做作(拙),所以“至真至正之情,有合风人之旨”(大)(《蕙风词话》卷五)。“重拙大”的理论是他对创作的反思与总结,是以艳词为生发点,进而推及其他类别的词。了解这一点,对于廓清“重拙大”的含义是有帮助的。
[注释]
①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见况周颐原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出版。下文所引《蕙风词话》、赵尊岳《蕙风词史》未注明者,亦据此本,随文括注文献名称(卷数),不一一出注。
②况周颐曾欲将《射山诗余》付梓而未遑,后将此书交给赵尊岳。赵氏又将《射山诗余》刻入其《明词汇刊》。事见赵尊岳的《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一文。见《词学季刊》1933第3期。本文所引《小桃红》(十载风尘怨)据《射山诗余》《明词汇刊》本(赵尊岳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
[参考文献]
[1]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
[3]吴世昌.《罗音室诗词存稿》初版自序[A].吴世昌全集(第11册)[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4]曾大兴.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得与失[J].文艺研究,2008,(5).
[5]叶嘉莹.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A].清词丛论[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龙榆生.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8]屈兴国.蕙风词话辑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9]秦玮鸿.况周颐词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0]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