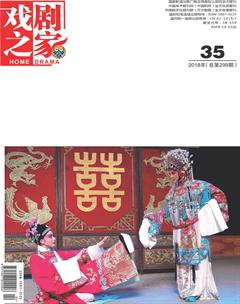欲望、暴力、法律交混下的乡村社会伦理镜像
刘好 袁智忠
【摘 要】《暴裂无声》作为一部犯罪类型电影,延续了前作《心迷宫》对乡村现实景观的叙事表达,进而深刻探讨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所暴露的利益纠葛、欲望之恶。本文从伦理的视域,探讨在欲望、暴力,法律的交混作用下,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的历史图景和伦理情状。
【关键词】欲望;暴力;法律;乡村社会伦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34-0081-02
一、欲望:万恶之源
从《心迷宫》到《暴裂无声》,忻钰坤善于在悬疑的迷雾中创造“恶”的故事。《心迷宫》面对的是现代乡村社会人际纠葛和个体挣扎的内在动因,揭示在封闭空间内乡村小民内心的欲望与“恶”行。如果说《心迷宫》中人性之恶还蒙着一层薄纱的话,《暴裂无声》则将这层薄纱大力的撕下,直面工业化进程中人性之“恶”的道德底线和种种面相。
在工业化进程中,物欲的迷恋会让人性变异,会产生昌万年这样肆虑掠夺的人肉“机器”,也会产生“抽洋烟”“喝瓶装水”底层贪腐的“村官”,也会产生徐文杰这样的受贿、自私、枉法、失语跌破道德底线一直违法犯罪的律师。而这一切欲念之果最终砸向的是落后、愚昧,靠着本能欲望和身体“暴力”自然生存的底层村民张保明们。乡村的官民、善恶对立扩延至城镇,当观众的视野漫过枯瘠泛黄的背坡处,便是导演超越乡村视点的城镇景观。于是,导演巧妙的将乡村的愚昧与无知,小偷小摸和个体抱怨转移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虚伪面目、歹毒可恨和金钱至上的鏡像表达中。这里就有了靠横行霸道、肆意妄为、疯狂掠夺财富的暴发户昌万年,他无疑是影片中最“恶”的角色,传统之“恶”与现代之“恶”纠混一体。昌万年的欲望在于对财富的迷恋,他拥有奢侈的办公楼,野性的悍马越野车,为了占取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不停的靠着行贿和非法收购煤矿以谋取暴利,采取不合作即暴力的手段争夺话语权,这是物欲之“恶”。当物欲得以实现并食以甜头之后,膨胀的昌万年享受着射杀的欲望,狩猎和商人的占有欲和剥削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也许放箭那一刻,就像又一次成功的对底层人民进行谋害和掠夺,可以给内心空虚的他带来嗜血的快感,也导致阴差阳错杀人的“恶”行;然而,昌万年为之困扰的“法律擦边球”行为衍生了对自由的欲望,于是他行贿律师,隐瞒杀人真相,编造环环相扣的谎言,这是自由欲望不法追求造成的“恶”行。
近年来,国产电影中的城市空间表达,高楼大厦柏油马路的都市感潜意识的取代了乡村朴素、无序、空旷的废墟感,“欲望”一词自然而然的存在于霓虹之中,成为城市的代名词。但若我们将目光转移至乡村空间影像,不难发现,追逐物欲的资本威权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采掘,人为制造了难以在短期内填平或消除的乡村废墟。[1]
城镇化的欲望表达也深刻影响着乡村意向,逼迫他们以“牺牲品”的姿态来迎接和承受这一社会转型期的欲望狂泻、道德践踏、恶行肆虑,而这一切似乎都必然上升到以“暴力”手段才能完成善恶对抗双方诉求的镜像化表达。
二、暴力:无声的挣扎
西装革履,头戴假发,身穿布鞋的施暴者昌万年享受着羊肉火锅的滋养,听着优美的音乐,肆意妄为。作风干脆狠毒的他有几分像韩国犯罪片中的黑帮老大,光鲜的躯壳下看不透内心到底有多狠。以一打多,倒下后不忘挣扎,厮杀出一条生路,也有几分《老男孩》中吴大修的干狠劲。相较于韩国电影生与死,恨与罚的极端情绪表达,甚至当消灭不了坏人时,不惜成为坏人,让恶人受到惩罚的价值观而言,《暴裂无声》中的暴力表达截然不同,它以“无声”的方式来呈现。导演刻画昌万年的犯罪,简单血腥,视他人生命于股掌间,在金钱和打手的保护下,为非作歹,他的存在就像是金字塔形状的艺术品,尖锐、锋利,可取人性命,指向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道德与良知。于是,昌万年的挣扎在欲望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无力自拔。他对他人又很又恶,对利益贪得无厌,追逐利益无法无天。但他也有爱与梦想,要给在国外读书的儿子寄羊肉,盼其成才。也有害怕与恐惧,要行贿俆律师,隐瞒罪证。要派打手帮凶追杀张保明,杀人灭口。
张保民为何“无声”?他不惜使用武力而非言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许在他的眼中,看透了社会的诟病,对当下社会话语权失望,深知即使发声呐喊也将被“无视”和“消音”。张保民是乡村压抑个体的人物镜像,在家庭中母亲是愚昧的,靠着唯心求神的方式盼望孙子回来,妻子是软弱、病态的,发现了井水日益严重的异味也由于贫穷而妥协,以药度日;对贪腐不公的村支书的横眉冷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的“官民”矛盾和对立情绪。张保民只有将拳头取代声音,变为说话的机器,激发体内的暴力基因,“打”出话语权,也企图“打”出真理与真相。
律师徐文杰摇摆于善恶两端,本该作为法律执行者的社会角色,却最终倒向了“恶”。他本该为社会和法律的公平、公正发声,除恶扬善,惩治犯罪,保护受害者和社会弱势人群。但他却贪收了他很“需要”的50万块人民币,不再正义呐喊,不再为公平发声,变成一个泯灭良知,丧失道德底线,走向犯罪深渊的失语者。于是,他既对张保明的儿子——磊子的生死默然以对,缄口不言,也对视为第二生命的无力保护,欲哭无泪,欲悲无声。
影片中“无声”且暴力的角色很多。丁海的儿子汉生也是“失声”孩童,甚至以代表正义的“奥特曼”面具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当山体爆破之时,观众深知一切真相将被掩埋,却出现了关键的“无声胜有声”的墙体画,真相“有声化”的浮出水面。其实,导演在刻意化的蓄力,让观众无法承受如鲠在喉的揪心,用以暴力为宣泄口,反衬“无声”之响。
三、法律:欲望、暴力的终点
就社会文明进程和人类的终极目标而言,法律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高也是最后的形式。作为一部犯罪片,《暴裂无声》决不单单是一部仅供欣赏的爆米花电影,它具有更深远的主题和意义表达。影片通过张保民丢了儿子一这一核心事件,展示了乡村社会底层家庭在面对重大变故时不知所措的生活镜像;揭示了与当今社会因个别不法村支书的贪腐治理下的社会镜像和世道人心;表现了以俆律师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自私、懦弱、枉法,上层利益获得者的可怕冷血带来的社会秩序失常镜像。这正是中国转型期乡村发展的现状图,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发展失衡的乡村式伦理书写。
《暴裂无声》中表达的乡村伦理,即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伦理生活,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伦理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影像世界伦理生活的失序,其实就是我们的社会伦理生活失序,不同的只是它映现在一个影像化的境遇中。[2]乡村图景不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秩序,它将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侵染和掠夺,旧时以暴制暴的乡村秩序是否依然适用于当下?只有依靠法律的规制,在充满铜臭味的施暴者和纵容贪财的法律见证者选择“无声”时,有一双隐形的手(法律)抓出真相,还心存善意的观众内心以暴裂“发声”。
总之,影片表现的是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欲望张扬、暴力本能的乡村伦理社会,在走向现代文明、社会规制的进程中一幅底层人生生活状貌、道德面相、伦理交缠镜像。犯罪虽然得以遏制,但蒙昧尚需进一步开启,暴力本能的治世行为还需进一步驯化,恰如张保明依然无声地走行在寻找儿子的旷野一样,乡村振兴道阻且长。唯有在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让法律规制社会,才能寻得乡村文明和现代伦理秩序建设的科学路径。
参考文献:
[1]杜梁.《暴裂无声》:乡村的话语失序与废墟景观[N].中国艺术报,2018-04-16(006).
[2]贾磊磊,袁智忠.中国电影伦理学·2017[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