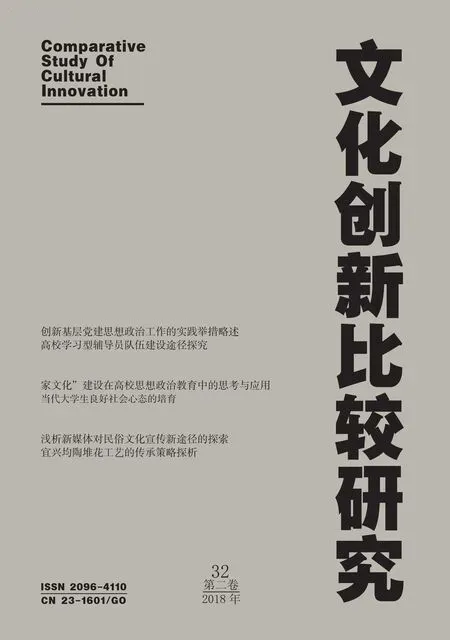“适”之三译
——苏轼心态的三重境界
温颖文
(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广东广州 510500)
苏轼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亦是美食家,他生活在对士子空前包容的时代,又是北宋相对繁荣稳定的时代,而其本人既是已极有文学政治地位的欧阳修的弟子,又与太后、神宗亦私交甚笃。并于其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一生经历了迷失到超然的精神境界,也留下了博彩众多的诗文。
东坡诗词历来都被认为是宋诗词中的正宗,东坡之前,大多文人认为诗是高尚文学,要精雕细琢,不可逾越儒家思想的规定;而词是供酒宴间歌唱所用,作者可不考虑身份地自由挥洒。唯有东坡将词的内容从酒宴闺怨拓展到生活的多方面,也将词的风格从哀怨幽婉变得可以豪放挥洒,打破前人对词“浅吟低唱”的固有观念。所以东坡的文风多豪迈豁达、情感开放真挚,又不乏细腻的生活情趣,并融合儒、释、道三家的精神哲理。
苏轼诗文中有诸多对“适”的诠释,该文尝试从“适”的多种理解与北宋生活情态之中,一窥东坡的精神境界。
1 努力“安适”阶段
“适”,《说文解字》中记载“之也”,即“去,到”之意。
“乌台诗案”可谓是苏轼人生第一次沉重打击,当时苏轼已做好赴死的准备,交代长子苏迈若收到皇帝赐死的消息,就在往日饭菜中加上一尾鱼。友人阴差阳错地送来一尾鱼,让苏轼万念俱灰写下“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诀别诗。这首阴差阳错的诀别诗引得“上览之,凄然,卒赦之。”此时的苏轼应是对命运的不解,应是皇帝态度的震惊,对于其兼济天下的抱负理想未能实现的深深地惋惜。此时苏轼写下“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自得罪后,虽平生厚善有不敢通问者”等语句。
另一方面,苏轼亦是对从小到大所浸淫的儒学,无法解决问题的不适。例如:自宋太祖时期就规定官粮物价,禁止私粮售卖。然而连年官僚体系日渐庞大,各级漕运官员中饱私囊。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看出,日渐正午,守备军员醉酒卧眠,有人公然从官粮漕运的舟中将粮食运入私仓,如此种种,至北宋后期,官府已经无法控制与私粮的竞争,粮价较之北宋初年也上涨百倍。苏轼在《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中就有论述政府选人不当,连年虚耗花费,官粮被中饱私囊等事实;在《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中也有叙述了官粮无米可售,粮价飞涨之患。百姓的生死却不及党派斗争的利害,朝中士子做事只认党争,不认对错,令苏轼也大大怀疑了儒学出身的真正意义。
在此阶段,“适”应理解为寻求一种安身之所,正如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中所言“将何适而非快”。所以每逢遭到打击,他只能努力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找到生活的乐趣,这是努力安适的阶段,也是儒家文化与之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2 寻求“自适”阶段
《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商君书·画策》中有“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墨子·辞过》中有“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此中的“适”应理解为适宜和舒适。
在现实中的不适,苏轼首先想到的是在精神哲学中寻求答案。首选的自然是道家。
首先道家是相对于儒家而言在当时的中原社会中的一大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且李唐王朝为固化其统治也将道教尊为国教。至宋代,宋太祖曾召集京师道士进行学业考核,并斥退品学不良者,以提高道士的整体素质。而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召见道徒更为频繁,并对黄白等术颇感兴趣。并不断地兴建宫观,积极搜集道书。北宋皇帝也有于正月十四、十五、十六驾幸道观,宴请群臣,恩赦罪犯的传统。百姓大到建屋祭祀,小到寿辰设宴,都会请道士赞颂祝祀,道家的影响可谓影响到当时世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苏轼自小就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苏轼在其诸多诗文中也体现其对仙人艳羡之意和追求飞升与超脱。如《南乡子·有感》中“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以及《前赤壁赋》中“驾一叶之扁舟,渺沧海之一粟”均来自《庄子》典故,映射着苏轼对仙人,对狂人的洒脱自由豪放的一种深深的艳羡。
同时此阶段的苏轼对尘世间的逆境和冲突存在有意的逃避和视而不见。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对于他与党派,与帝皇间的冲突,词中已然弱化,在寻求出猎的乐趣中达到了表忠心的目的。
当面对人世间的生死别离,儒家象征着入世意义的“人死灯灭”的哲学已无法解决苏轼内心的烦扰。苏轼只能在诗文中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我欲乘风归去”的惆怅。如《后赤壁赋》中梦见“适有孤鹤,横江东来。”“梦一道士,羽衣蹁跹。”亦是面对西北新败,神宗离世这双重打击无法解脱而寻法道家飞升的一种心态。
然而苏轼又从来不是道家的忠实笃信者,在仕宦阶段苏轼也尝试过青词的创作,在青词既定的格式中也有不少自嘲和自怨的个性之作。在《留题仙都观》中就有“学仙度世岂无人,餐霞绝粒长辛苦。安得独従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行。”其中崇入世轻飞升之意就显而易见。《宋史·苏轼本传》中记载,“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说明苏轼已悟出道家的精髓在于外物的虚无,看清骨肉表象的虚无,也许就能做到像庄子那样面对发妻的离世亦能释然鼓盆而歌。
3 安然“共适”阶段
《战国策·魏策一》中有“攻秦而适楚”,应理解为满足,享用。此解正是从客观行动到精神境界的升华,而苏轼的人生和自身哲学的发展,亦是如此进化的。
在接触儒道之学的同时,苏轼也接触到了佛家的经学。苏轼诸多友人之中就不乏佛家的高僧。在与苏轼与友人的诸多尺牍之中,也不乏论禅宗之辩。但苏轼也不是佛家的笃信者。苏轼在《宸奎阁碑》中写道:“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与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又在《祭龙井辩才文》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称赞怀琏禅师能调和儒与佛、老,指出佛教各宗派间应取兼容态度,其实儒、佛、道各家也应持兼容并包、事理圆融、二者都不偏废。他学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穷究其义理,以期“出生死,超三乘”,而是“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
这也许是因为当时社会对多种宗教的开发包容态度,也许是佛教虽盛却仍未占据主流地位。当时社会除了儒教和道教这两大主流宗教外,自唐代起还兼容并蓄地存在着景教(古天主教)、祆教(拜火教)、大食教(古伊斯兰教)、印度教(婆罗门教)等诸多教派。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就有一石碑刻记“景教迁入史”;自唐代起已有大型的袄祠,并长年有祆教的大萨宝作为宗教中心镇守管理;而宋元的泉州港(古称刺桐城)作为当时东方的第一大港口,每日有数以千计的阿拉伯商船,刺桐城中有数座清真寺,且始于唐代就有闻名遐迩的伊斯兰教圣迹——灵山圣墓。佛教虽于汉代传入中国,并于魏晋南北朝之际得到帝王的大力振兴,如梁武帝大肆兴建佛寺,北周武帝一年中三度组织儒生、僧侣、道士辩论三教优劣,但时至宋朝,佛教仍未在民众心目中成为正统地位。据《东京梦华录》中的《相国寺内万姓交易》一篇中记载,“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脯腊之类。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这哪里像一个太平盛世的皇家佛寺,道士冠、姑娘鞋袜都卖到佛祖的正殿里去了,俨然一个城隍庙。所以民众对佛教的认识并非如今人一般,认为遁入空门是逃避出世凄清孤苦的象征。
六祖慧能有偈语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此中在心灵上的安适正是一把开启苏轼哲学的最后一把钥匙。苏轼的哲学中,有儒家先天赋予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救世之心,有道家“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逍遥”之心,又有着释家的睿智和空灵。
苏轼在其《谪居三适》中以坦然之心面对物质的匮乏、客观条件的恶劣,并以调侃的语气向腰佩官印的同僚们炫耀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等闲适之乐,敢于提出“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的养生哲学。这是对外物的释然。
而在《前赤壁赋》中有“吾与子之所共适”,此间的“适”则是有超脱于物质上的安适而是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释然。苏轼在《定风波·三月七日》中写到“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算是苏轼旷达人生以及睿智的人生境界的最好体现。凡人面对苦难,最多期盼的是“雨过天青”,回望“风雨”,也是心有戚戚然。但苏轼在经历“风雨”之后能,对自己人生起伏的坦然回望,对挚爱阴阳相隔的释然,看清外物的虚无和找到内心的平静。人生本来就是如此,哪有一瞬间就找到释然和解脱,总是在一次又一次战胜艰难之后才能找到真正的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