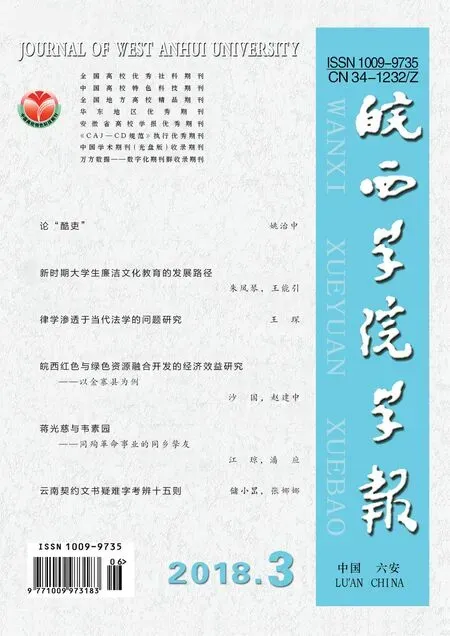车王府曲本中的“打朝戏”研究
谢实东,王 政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清代中后期,“打朝戏”在地方戏的舞台上呈现繁荣之势。何谓“打朝戏”?李修生等人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戏曲卷》认为:“‘打朝’是指在劝谏皇帝最后无效时,某位有特权的王公大闹朝堂,强迫昏君放弃对奸臣的庇护。”[1](P350)笔者认为,所谓“打朝戏”是指皇帝或皇亲国戚等人做了有违圣君之道或危害社稷民生之事,忠烈的大臣在劝谏无用之下,对皇帝本人、皇亲国戚或龙袍进行或骂或打或反的戏曲。“打朝戏”以选择独特题材和视角因而具有独特的戏曲结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美学特征,宜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主编的《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以下简称《全编》)为中心,对戏曲从如下几个层面进行探析,以期对“打朝戏”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一、“打朝戏”的叙事视域及结构
罗钢先生认为:“叙事就是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真实或虚构事件的叙述”[2](P2)。戏曲作为书面文本时,当属于叙事文学作品。“打朝戏”作为戏曲在叙事视域和结构方面均具有它的独特的性:在叙事视域方面,故事文本所体现出来的叙事主体有属于自己广阔的叙事视野;在结构方面,既包含虚实结合的模式建构,又将“二元论”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历史性视角
“打朝戏”取材历史,又有自己的历史视角,因而具有极为广阔的叙事视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直接对史料记载或小说进行改编。如《骂殿》取材于《宋史》卷二百一十《宗室世系一》和《宗室一》卷二百四十四。《骂齐》源自小说《东周列国志》第九十五回《说四国乐毅灭齐,驱火牛田单破燕》。《闹天宫》源自小说《西游记》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至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斩红袍》源自小说《飞龙全传》第四十三回《苗训英算服柴荣,王樸陈词报匡胤》。《打龙棚》取自清代小说《飞龙全传》第四十七回。《谤阎》胡迪骂阎事见明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三十二回,清代小说《说岳全传》第七十三回《胡梦蝶醉酒吟诗游地狱》亦叙及。第二、取材于历史记载和小说故事,合成一体。如《反五关》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及《封神榜演义》第三十四回《周纪激反武成王》。《骂曹》见《后汉书·尔衡传》《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和小说《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尔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明徐渭《狂鼓史渔阳三弄》杂剧即演尔衡骂曹事。《斩黄袍》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事见《宋史》卷一《太祖本纪》。清《飞龙传》小说即以赵匡胤、郑恩兄弟二人为主线展开故事。清小说《宋太祖三下南唐》第一回《惘忠冤赤眉示罚》有宋太祖酒醉杀功臣之事。第三、来源于传奇杂剧。《打朝》出自明无名氏《金貂记》传奇第十四折,元杨梓《功臣宴敬德不伏老》杂剧亦演此事。《打銮驾》故事据元《陈州粜米》杂剧改编而成。《打龙袍》故事见《三侠五义》,元汪元亨杂剧《仁宗认母》演此事。
综上可见,“打朝戏”题材具有包容性、多样性特征,从叙事角度看既有历史性叙事,亦有文学性叙事;从题材选择看,既囊括了历史史实、小说,也含有杂剧改编。其中,小说改编在“打朝戏”中最为常见,这说明在戏曲的生成、演进过程中,小说在故事题材方面给予了广泛、深入的影响和滋养,取材小说亦可使故事题材在社会认同度方面具有保障。
(二)虚实结合的建构模式
在戏曲叙事结构中,李渔还主张“审虚实”,他认为“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其中“虚”是指剧作中虚构的情节内容,“实”是指实录的史事。“打朝戏”中所叙之事多以历史中之一事作为叙事之端,其余的情节多为艺术虚构。这种以历史史实为引子的虚实结合建构模式,不仅在史事的基础上创设新的故事情节,而且让人物在新的活动环境中产生新的思想意义。
《打朝》演尉迟恭、李道宗在朝房相遇,因李道宗诬陷薛仁贵之事,二人言语相争,尉迟恭拳打李道宗门牙两颗。后来,尉迟恭被判斩刑,因徐茂公保谏,尉迟恭被贬为农,李道宗罚俸三年。这部戏曲取材于两《唐书》中“尉迟敬德列传”[3](P3754),史书记载中的尉迟敬德是开国元勋,他居功自傲,与他人争抢座位,李道宗因劝解尉迟敬德而成为受害者。而在《打朝》中,尉迟敬德之所以打李道宗,却是因为李道宗强抢民女、诬陷忠臣良将。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将故事发生的原委都做了极尽的改编和虚构,从而掩盖了尉迟敬德的无理取闹,目的是为了突出使尉迟敬德的行为具备正义性与合理性,使人物形象更加具有正能量。
《骂齐》演燕、齐交战,齐愍王兵败,为兵所追,逃至苏岱家中,苏岱问及交战情况,以麦仁米饭款待齐愍王。苏母得知,怒其无道,痛骂齐王诛杀忠臣,陷民于水火。齐王悔过,苏母亦重新拜见愍王并赔罪,共商退兵之事。苏岱进言有故友徐功辅,可劝乐毅退兵。《东周列国志》第九十五回《说四国乐毅灭齐,驱火牛田单破燕》载有燕、齐交战之事,乐毅“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齐愍王之败济西”[4](P349)。而《骂齐》戏中苏母痛骂齐愍王之事,在史书中并无记载,属于作者虚构的情节,但显然事幻理真,虚虚实实,引人深思。
清代“打朝戏”中的《斩红袍》《打龙棚》和《斩黄袍》,都演及赵匡胤之事。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载有宋太祖殴打大臣和武力决定状元之事[5](P44-45),但无赵匡胤打皇上的记载。但在《全编》著录的“打朝戏”却演及赵匡胤拳打国丈杜窑(《斩红袍》)与赵匡胤和郑恩用暴力手段逼迫柴荣封赏高怀德之事(《打龙棚》)。可见,戏曲中所演赵匡胤打皇帝或皇亲国戚之事纯属作者虚构。同时,作者也在戏曲中保留了赵匡胤尚武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增添了戏曲的魅力。
由上可见,“打朝戏”多从细节上对故事文本进行虚构,具有写意性;通过“打”“骂”等动作使戏曲场景充满闹热性,增添了戏曲的趣味性。这种虚实结合的建构模式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不仅能够突破现有材料的局限性,还可以打破剧作家思维的禁锢,有效地将历史与文学艺术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艺术创作的空间。
(三)二元思路
无论是道家老子的有无之辩,还是宋明理学的天理与人欲相协,二元关系及思维一直存在于中国哲学中。它们既是一种哲学概念,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倾向于事物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结构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原则存在于一切叙事文体中,具有普遍性。金圣叹也曾提出“二元对立”原则,这亦是分析“打朝戏”中存在“二元”思路的重要理论依据。纵观《全编》中的十三种“打朝戏”,可以将这种“二元”思路概括为三个层面:从题材上是君臣二元对立;从思考的问题域上应是正义与邪恶、大义纠结;从达于目的上在于超出纠结,重返和谐。它们既矛盾对立,又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
从题材上是君臣二元,他们之间的对立多因君王“君之不君”而引发。《骂齐》中,齐愍王因宠信佞臣,诛杀功臣,最后“陷黎民水火堪哀”,以至于苏母痛骂齐愍王为昏君;《打龙棚》中,大周天子因高怀德乃杀父之人,怀恨在心欲杀之,并与赵匡胤、郑子明发生争吵,赵、郑二人“怒气冲冲进龙棚把本来提”,“在金殿上立下唬王势”;《斩黄袍》中,赵匡胤因酒醉斩郑恩,从而引发郑妻陶三春“命众家将披挂整齐,杀上午门”;《骂殿》中,赵匡义受佞臣魅惑,杀太子,贬忠臣,以至于贺后“站在进阶一声高骂”,具陈赵匡义数条罪状;《打龙袍》中,因仁宗不孝,李国太怒,责令包拯“殿脚下去打那无道的君”。可见,君王的昏庸与不孝乃是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皇权与臣权自古就是不平等的,而在戏曲中,却受到臣权的限制与打压,这从侧面反映了被统治者反对昏君,期望明君统治的美好愿景。
从思考问题域上应是正义与邪恶、大义纠结,这种对立在“打朝戏”中最为常见。《骂曹》中,祢衡因不满曹操的作为,乃“破衣烂衫”,击鼓痛骂曹贼“狗奸贼朝中为首相,全然不知臭和香”;《打朝》中,尉迟恭因李道宗诬陷薛仁贵事,遂骂李道宗是“泼谗奸佞”,并将其“门牙打掉两齿”;《斩红袍》中,杜窑倚仗西宫受宠,嚣张跋扈,故而赵匡胤“将銮驾打碎”,把“父子饱打一顿”;《打銮驾》中,马娘娘为袒护二国舅克扣万担粮食,阻碍包公办案,包公命人“先打乱了他的珍珠伞,后打彩旗十二根”并念咒语杀死马娘娘。这一冲突模式在戏曲中最为常见,两者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因为正义对邪恶的打压和抵制,更在某种程度上影射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
从达于目的上在于超出纠结,重返和谐。在“打朝戏”中,《反五关》最具有表现力。该剧叙演纣王不念旧情,违逆君道,遂逼死黄飞虎之妻。黄飞虎虽痛恨纣王,但却无谋反之心,他道:“(生白)胡说。纵然朝廷昏乱,我岂肯做不忠不义之臣?多讲,多讲。”这说明他仍忠心朝廷。直到众人以“不反朝歌,必有灭门之祸”为由极力劝说,他方才说道:“(生白)反了的好?啊,也罢。即传随营兵马,反了,反了”,即便如此,言语之间仍是充满了纠结与无奈,忠与反对立凸显了黄飞虎不愿谋反却又不得不反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恰好完美地展现了黄飞虎这一类人超出纠结,重返和谐的新境界。
综上可见,“打朝戏”中的“二元对立”形式多样,充分地展现了君臣之间、正义与邪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实质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但从戏曲结果来看,这种对立冲突只停留于表面,受儒家和程朱理学“忠君”思想的禁锢,导致他们在精神格局上无法逾越统治者设定的范式,以至于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无法达到白热化的状态,注定是徒有其表的修补与纠正。对戏曲本身而言,“二元对立”的思路有助于戏曲冲突的展开,拓展了情节之间的张力,深化了戏曲的主旨。
二、“打朝戏”的矛盾冲突模式及诉求
“冲突是结构形式发展中内在的必然要素,如果一部戏里的冲突线索己经确定下来,那么它的结构框架也就大致有了方向。”[6](P138)“打朝戏”具有独特的冲突模式,这些模式的确立为戏曲的叙事结构奠定了基础。可以概括为“打、骂、反”三种[7]。
“打”的模式在“打朝戏”中主要有:《打朝》中,尉迟恭将奸臣李道宗“门牙打掉两齿”;《闹天宫》中,孙悟空与十万天兵、二十八星宿、九曜星君、十二元辰、四大天王、东西南北星斗、灌口二郎神、丧门地煞等大战;《斩红袍》中,赵匡胤将杜窑的“銮驾打碎”,并把他们“父子饱打一顿”;《打龙袍》中,“包文正打龙袍臣打君”;《斩黄袍》中,陶三春怒斩黄袍,并将黄袍“打下七七四十九天罗天大醮”;《打銮驾》中,包拯“打乱了他的珍珠伞,后打彩旗十二根。全副銮驾都打碎”。可见,“打”是表达此类戏曲冲突最主要的展现方式,被打的对象包括君王、皇亲国戚、龙袍等。“打”的行为不仅仅是释放矛盾的一个突破口,更是一种正能量的隐喻。
“骂”的冲突模式在“打朝戏”中表现得尤为激烈,是推动情节展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冲突模式在“打朝戏”中主要表现有:《骂齐》中,苏母骂齐愍王“无道的昏君”;《骂曹》中,尔衡骂曹操“奸贼”“曹奸佞”;《打朝》中,尉迟敬德骂李道宗是“泼谗奸佞”;《打龙袍》中,包拯斥责仁宗是不孝之人,李国太怒斥宋仁宗为“无道的昏君”;《斩黄袍》中,赵匡胤怒斥韩龙“这囚攘的也来进妃, 乃是国家不祥之兆”;《打銮驾》中,包拯大骂马娘娘为“小贱人”“奸妃”“毛寇女”“黄毛女”;《骂殿》中,贺后骂赵匡义“好比赵高指鹿为马”“好比汉萧何私造律法”“好比王莽贼称孤道寡”“好比司马师带剑不差”“好比奸曹操带工逼驾”“好比毛延寿怀抱琵琶”;《谤阎》和《骂阎》中,郭胡迪题诗谩骂阎君是非不分,不辨善恶。从“骂”的对象看,有昏君,有佞臣,有奸妃。与“打”相比,“骂”更刻意于铺陈其理,使冲突更具理性含融。“骂”的缘由多是因为被骂的对象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正是这种欠缺为正能量的舒展提供了缘由。
在《全编》所收录的“打朝戏”中涉及“反”的戏曲情节只有两种:《反五关》中,黄飞虎在儿子和部下的劝说下“反朝歌”“奔西邦”“趱出五关”;《闹天宫》中,孙悟空杀上灵霄宝殿,势必要“把玉帝让我做了,方得罢手。”“反”戏最为简便,其原因在于大臣们的一腔热血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从而引发这种正能量反的诉求。
综上,在“打朝戏”的戏曲结构中,戏剧冲突的核心是皇权与正义势力之间的正面交锋,冲突展开的行为模式主要有“打、骂、反”三种,其中“打”和“骂”为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些冲突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正能量的诉求。当这种正能量受到挤压时,就会寻求一个突破口,所以这种矛盾冲突的发生也是必然的。
三、对“打朝戏”的评估
从戏曲史可知,“打朝戏”繁荣时也是中华学术大转型之时。从正在日趋弩转的汉学与宋学的关系看,“打朝戏”的产生和发展与之有莫大的关联。首先,道学思想已工具化、民俗化,成为戏曲的价值标准。程朱理学所宣扬的“纲常伦理”“君臣父子”等思想,既有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体系,又有强化封建伦理观念的种种说教,最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再加上理学讲求“立志”“修身”,重视道德自律,倡导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清初政局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由此,程朱理学开始成为正统思想,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戏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自然要符合统治者设定的规范。但由于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士人的思想开始受到禁锢,他们为释放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开始不断地寻求突破口。这为“打朝戏”的萌芽奠定了基础。其次,一大批汉学家涌现,主张经世致用,冲破王学左派,将遗民情绪带到深思。随着清朝统治步入正轨,社会安定,经济繁盛。统治者开始提倡经学,而程朱理学空疏浅陋、循墨守程、寻章摘句等诸多弊端也不断地暴露出来。一大批汉学家涌现出来,他们开始猛烈的抨击宋学的不足。此外,他们还结合前朝灭亡的教训,开始思考封建的君主统治,并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思想。如黄宗羲抨击君主“天下为私”,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害;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唐甄打破了“君权神授”的桎梏,大骂君主是贼。这些进步思想的产生与传播为“打朝戏”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再次,随着汉学的声势扩大,“打朝戏”隐有理学对自己的深刻反思。皇权高压,导致儒学道统逐渐从儒学士人的手中丢失。为重新夺回对儒学道统的掌控权,儒学士人一方面开始不断地对君主专治、尊卑界限进行反思。这些都为“打朝戏”的创作提供了原始素材,于是便有了“打朝戏”中出现的君臣之间、正义与邪恶之间的矛盾诉求;另一方面,清代汉学狭隘的学术视野、怀疑作风和排斥思想使其逐渐偏离最初的轨道,未能将这些积极的思想进行下去。儒学士人开始从自身出发,思考由于人为卑劣性所造成的道统的丧失。这些无疑都丰富了“打朝戏”的思想内涵。综上所述,“打朝戏”的产生具有时代性:其一,汉学与宋学之争为其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它不仅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表达对公理和正义的呼吁,也是表达儒学士人对道统的追求;其二,“打”“骂”等冲突模式是士人阶层对自身理想、人格的释放,现实社会的思想高压让他们不得不在戏曲中寻求另一片天地;其三,“打朝戏”的冲突实质上是儒学士人和皇权在道统上的冲突。宋学的道统话语权被皇权垄断,导致宋学士人集体失语,而清代汉学便努力重建对儒学的争控权,这也是“打朝戏”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清中叶以后,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急剧动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接连发生,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为挽救危局、维护统治,统治者开始重新重视宋学,宋学由此得到短暂的复兴。宋学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士人的思想,这也是“打朝戏”未能取得较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总之,“打朝戏”作为花部戏的一种,其戏曲叙事具有独特的模式。二元论的叙事结构和冲突模式,不仅使情节结构、人物形象更加清晰,更有助于推动戏剧冲突的展开。这也是其具有传奇性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打朝戏”产生之后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深受民众的喜爱。一方面是因为“打朝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宗法制社会,君权神授的思想、森严的等级制度仍然让人们坚信君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因此,“打朝戏”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忠君爱国仍处于主要地位。这就注定“打朝戏”只能从表层对君权进行纠正和修补,不能从根本上推翻这一不合理的封建制度。总的来说,虽然“打朝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社会状况和君主制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君为天下之害的进步思想展现在人民眼前,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打朝戏”的仍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学术界却鲜有学者关注“打朝戏”,对“打朝戏”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因此,关于“打朝戏”的研究,我们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1]李修生,赵义山.中国分体文学史·戏曲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司马光.涑水纪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6]周安华.戏剧艺术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王芹.清代打朝戏探究——以《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为中心[D].宁波: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