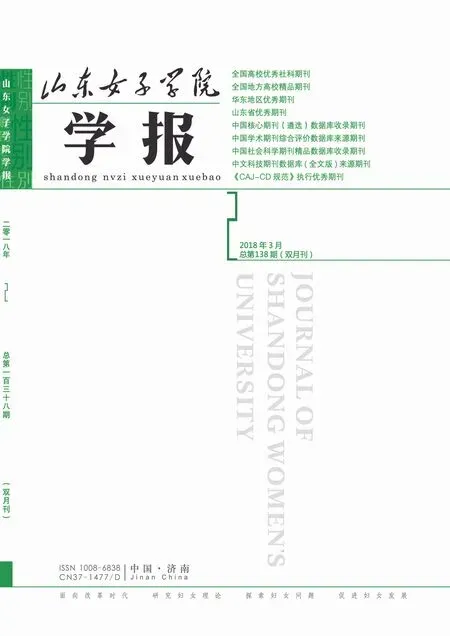性别与家族历史书写
——以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为中心
马春花,于安琪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历史叙事一直由男性神话的叙事传统所构建,男性被表述成历史真理的起源和主体,而女性则被放逐于历史之外,成为历史中缺席的他者,女性历史也呈现为“空白之页”的状态。但是女性历史所呈现出的“空白”并不能够得出女性无历史的结论,而是一种被历史叙事主体/男权社会有意忽略、边缘化的结果[1]。男权历史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意识的沉淀已成为标准,女性基本被排斥在男性文化的视野之外。
1990年代以来,在大历史书写中表现个人生命存在、体验及其意义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学思潮,特别是对于一批崛起于1980年代的青年作家来说,这个时期社会转型的完成、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引入以及重写历史的冲动,使其个体的自我经验在历史书写中重新获得了意义,新家族历史小说或新历史小说的出现即是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反映。与男作家解构革命宏大历史以重构新的(男性)个人主体历史有所不同,女作家则更多的是“探索妇女的角色、身份的复杂性,探索由种族、性别、阶级所决定的妇女角色和身份之间的交叉和矛盾”[2],自觉地从性别角度思考历史,对于“地表”之下的女性历史与边缘族群历史的叙述显示出迥然不同于主流男性历史叙述的性别和价值立场。
王安忆是这一家族历史写作的代表性人物,在她笔下,“个人不再只是纯粹的现实的物体,而是交融着历史体验与历史记忆的生命个体”[3]。她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伤心太平洋》与《纪实与虚构》,前者追寻来自“太平洋”的边缘父系家族历史,后者则将母系家族历史上溯至柔然边疆,将中心与边缘、个人与历史、女性与国族间的认同与冲突内化为小说的叙事动力,并建构起历史边缘与边缘历史的别一历史叙事。
一、此消彼长:“父”的去势与“母”的提升
在历史进程中,男性更多地体现着社会现实法则及其合理性,他们所表现出的力量与智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而居于从属边缘的女性则以软弱无力、浅薄无知的形象缺席了历史的创造。“她是附庸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4]而王安忆的历史书写则明显地颠覆了传统男强女弱的历史角色的既定模式,《纪实与虚构》中的外公抛弃家庭,置年迈的曾外祖母和年幼丧母的母亲于不顾,是不负责任的浪子,“外公弃家而走,是中断我们家历史、割裂我们家社会关系的关键一着,从此,旧的一页翻过去,新的一页展开”,而展开这“新一页”的是极尽各种办法抚育母亲的曾外祖母,“她是努力使我们家历史堂堂正正往下写的一人”;《伤心太平洋》中父亲家族中的男性形象也不再是强有力的历史开拓者,甚至几乎都不是正面人物,“我们家的男性全无宗教始终如一的素质,他们随心所欲,意志脆弱,还有那么一点儿莫名其妙,使我们家陷入混乱”,爷爷的狷急暴戾、父亲的漂泊不定、叔叔的浪荡软弱为家族和女性带来的只是无尽的苦难。而作为女性的曾祖母则“是我家功臣一般的人物,她开创了我家的出洋史”,此后奶奶、婶婶、堂姐三代女性又相继支撑起家族延续的重任。
在王安忆书写的父亲家族史中,女性不再是喑哑无声的男性历史附属物,而是开创和推动家族历史发展的关键性角色。女性形象的坚韧顽强、果敢有力与男性形象的软弱怯懦、粗暴无常形成鲜明对比,置换了男性作家所塑造的两性镜像关系。伍尔夫曾用镜子来隐喻女性的他者位置:“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是用来做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使男人在与女人的比照中获得优越感和自信心。”[5]男性将自我向女性投射,是一种通过作为女性的他者想象理想实现的心理机制,由此而知,女性他者的性别位置是在男性主体确立自我的过程中被强制给定的,而在王安忆处这种两性间的位置发生对调位移,女性不再只是映衬男性形象的工具,反而由男性承担了镜子的角色,成为一个凝缩了存在意义的镜像,软弱怯懦的男性映照出的是女性的坚韧顽强,在将男性界定为他者的同时树立起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
除了两性角色既定特质的对调外,在《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还采取了使父亲“缺席”的叙事策略来弱化男性、强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历史地位。在叙述“我”作为现代女性的成长史的部分,母亲作为权威的家长形象出现,对“我”成长过程中的言行给予规定和指导,“我的恶作剧对象总是父亲,母亲对我是教育的化身”,家庭中与外界的社交也都是基于母亲的人际关系,而传统意义上家庭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父亲,仅仅作为一个面目模糊的概念式角色,在提及“父母”时象征性地与母亲并列出场。在这个成长故事中,更多的是展现母亲对于“我”成长的影响,很少见到父亲的身影。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中的重要的伦理角色,父亲具有管理、教育、保护家庭成员的权力,而且作为权威的化身,上升为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代言人。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父亲之名”是象征秩序的核心,“作为纯粹的能指是一切约束性规则的来源和依据,对主体来说,是既定的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服从的一种标志”[6]。
“无父文本”的策略消解父权等级制对女性成长过程产生的影响,在完成对父权制的驱逐后,女性通过写作获得铭写自己成长的权利。作为生育工具或欲望对象的母亲角色则更多的是在父亲的背后,与儿女一起服从管训或作为父亲的“助手”传达着他的旨意。王安忆颠覆性地将至高无上的家长身份置换为母亲,排除了父权在家庭和社会中所代表的至高的秩序体系,瓦解父亲的权威性和绝对性,而使作为母亲的女性承担起父亲在家庭中的责任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象征权力,家庭的权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被移至母亲身上。在父亲“缺席”的叙述中,被解放的不只是女儿,处在边缘附庸位置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影响也同样得到强化。
无论是贬抑还是缺席,这种对男性“去势化”的书写模式无疑都破坏了正统宗法父权文化下男性主体的完满和理想化特征,在他者关系中生成的女性主体在男性的传统权威和历史地位被否定后,才能在此消彼长的两性位置动态变化中获得更大的文本空间建构主体意识,并进一步从压抑中的历史边缘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和书写权力的中心。
二、破而后立:男权神话废墟上的历史重建
与男性寻根作家进行家族史书写时尽力挖掘家族的辉煌历史,并以此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树立起家族、民族的自信的策略不同,王安忆呈现的父亲家族历史则是一个衰落难振的过程,显示出她对于那种不容置疑的父权中心历史的审视。小说题目《伤心太平洋》中的“伤心”二字就显现出了与其他强有力的家族史书写迥异的哀愁、无力的氛围,这样的表述完全悖离了以往家族史负荷着启蒙及道义的权力感。而小说中反复强调的父亲家族所处地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仅为东南亚一隅,时刻面临着沉没与冲击的小小岛屿也无法与创造了强大而稳定的历史文明的民族相联系。小说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战争环境中家族的衰落与民族的苦难一脉相承,祖父由被委以重任到黯然离职,家族成员由人丁兴旺到漂泊四散,曾经兴盛殷实的家族随着日本军队的入侵而尽显颓势。小说由父亲流浪的线索架构起来,父亲作为父系家族的象征,他的漂泊不定也象征着父系家族的衰败难兴,男性作为历史主宰者的权力话语在由盛转衰的过程中逐渐失效。王安忆在这里粉碎的不仅是“父”的象征秩序,同时也是中心之“父”的历史,那种基于男性自身想象而建构的强力的男性历史镜像在女性视域的写作中碎裂,其不再呈现出牢不可破的权威面貌,王安忆在破除了男性经典叙事的历史神话的同时,“历史”之下的女性得以“浮出地表”。
“对于母系社会的‘历史记载’只存在于尚有宇宙观而无历史观的洪荒时期,女性所面临的历史尴尬是:既有的历史文本遮蔽、涂改并消解着女性历史的‘本体性’。”[7]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将镜头对准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的女性,企望展现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围困下不被纳入观察视野的历史本相。在父权制的历史语境下,孩子被冠以父姓以象征血脉和身份从父亲处继承而来,家族历史由父亲处向上追溯的路径也无可非议。而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不是对父系/王氏家族追寻,相反是对母系/茹氏家族的溯源,对于母系家族的情感态度表现在小说中,是对母系家族历史的认同和皈依。而“父亲来自很远的地方,早已与他的家断了消息。对于他的身世,他是一问三不知,他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直到遇到我母亲,有了我,他才开始有了历史。”不仅是“我”,就连父亲的历史也是由母亲、由母亲的家族所赋予的,王安忆对于母系家族历史的记录不是将父母家族历史并置的笼统把握,而是抽离出与父亲相关所有内容,专注于搜寻散落在“父”的历史宏章中的“母”的意义。
《纪实与虚构》在奇数章节母亲家族历史的追溯中嵌入偶数章节的个体女性成长经历,个体女性琐屑细微的成长经历与严肃恢弘的家族史彼此交织,自我成长和家族历史演进不分高下地一同连接起王安忆的寻根愿望。王安忆使典型的女性写作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崇高的历史写作并置,是对于女性和女性写作亚文化地位的提升。在奇数章节中,王安忆对茹氏家族历史进行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长线追踪,从北魏一直写到当下,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里呈现战争、夺权、流亡、迁徙等多种历史话题,与其说这是茹氏家族的历史故事,毋宁称之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变迁,显示了王安忆誓要为母亲家族铭刻历史的决心。她将家族的起源追溯至北魏时期的柔然部落,这是一个来自北方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即使被贬为堕民也显示出其不肯屈服的强硬品格,以此作为构建茹氏家族强大有力历史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虚构给了王安忆为家族历史注入强力的空间,她私心地使柔然部落与蒙古部族合二为一,认成吉思汗为宗,分享其征服中原的功绩;明知追寻的线索可能出现了偏差,还是“将茹棻编进我母亲家的历史,其中所有的矛盾我都将努力地解决”,强行将状元拉入母亲家的历史以光耀门楣,以此虚构出一段强大的茹氏历史。
王安忆用虚构的形式尽力装点着母亲家族的历史,有意识地将其提升到与传统男性中心历史同等的高度,在破除了男性历史神话的基础上,建立起女性的巨型历史。父系历史的衰落与母系历史的强大,在一破一立中,终结了男权历史作为“元历史”的唯一合法性,压抑和掩盖在看似天经地义的男性中心下的女性终于作为主角登上历史的舞台,女性历史的“空白之页”也开始被填上文字。正如王德威所言:“王安忆不仅写作品如何再生历史,还写历史如何滋生抽象意念。由此类推,她滔滔不绝的议论,就算无甚高见,确实要以丰沛的字质意象,填补男家史作家留下的空虚匮乏。”[8]
三、女性边缘发现下的双向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虽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女性历史的“空白之页”,然而这种填补确乎是存在着限度的问题的。《纪实与虚构》中大笔挥写出的茹氏历史的确是为母亲的家族作历史正名,然而再向上追溯,母亲的姓氏也是从她的父亲处继承而来的,用尽心力追寻的“她”的历史本质上还是“他”的历史。同时,王安忆将个人家族史提升到气势如虹的民族史的宏大状态,而女性在这种宏大历史中只能委身于缝隙之中,“对于女性的寻根,一旦超离了生者的记忆,超离了口头的流传,而必须进入文字的历史,它便只能演化成经典的男性与权力的历史。”[9](P233)在历史传统与男权语境下,女性主体的历史意识是女性历史建构的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就这个层面来说,母系历史的书写意识和实践行为比具体的书写过程和成果更具意义。
建构母系历史或许并非王安忆写作所追求的终极意义,在早期的女性历史写作传统中,通常会强调女性作为政治化的公民主体或阶级主体介入历史,从丁玲到杨沫,参与到宏大历史场景中以收获主体感的史述方式一直在延续着。1990年代性别成为审度历史的一个向度,女性的历史书写与崇尚入史入仕的叙事传统有了很大差异,表现为女作家对她们曾参与构造的宏大叙事的反思和重述,王安忆的这种反思重述主要通过边缘发现得以实现。除却为处于历史边缘的女性正名,她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中,无论是父亲家族迁徙而去的东南亚岛屿还是母亲家族溯源而至的北方游牧民族,均非传统意义上中华民族的正统血脉,从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她书写的历史都是边缘地带的历史,这样的边缘发现绝非偶然,而是刻意拒绝进入汉文化的宏大体系中,这种拒绝“萌生出自我解构的力量,一种极为内在而有力的边缘化倾向,一种新的话语建构与话语空间”[9](P234)。她试图从两个向度对历史真相进行揭示,将镜头对准处在历史边缘的女性,是对父权制下男性主体历史书写空白的填补;而所处边缘地带的异邦异族的历史,则作为另一种资源在大写历史的内部进行着修正,挑战的是大一统历史的中心主义,历史的边缘和边缘的历史被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在两个向度上冲破了父权制大一统的民族/国族历史的藩篱,宏大的历史整体被裂解祛魅,崩落成无数个零散的“他”和“她”的历史,组成宏大历史图景却曾经淹没在公共叙述中的零碎的历史片段浮出,呈现出建立在个体日常基础上具有精神向度的另一种历史真实。
王安忆之所以能够成为边缘的发现者,固然与她实际的家庭背景相关,但更多的则是得益于她女性作家的身份。男性作家基于性别所产生的男性视域,与传统历史书写所谓的公共视域不谋而合,在获得了支配、书写自身历史的权利的他们看来,现有历史的“本文”对应的就是历史的“存在”,作为男性中心主义历史话语现实秩序内部的参与者、当局者,男性作家是无法体察到这种看似是天经地义的历史书写方式中边缘的缄默;而以王安忆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作为历史中的“他异因素”对边缘存在着切身体悟,身处男权历史的连续性的空白和断裂之处,女性作家才能以“旁观者清”的经验结构发现和揭露在历史叙述中被虚构和修辞所藏匿的性别政治和中心主义。
王德威曾将在中国大陆边缘地区的华语写作和华语写作中边缘地区的视点投射现象以“华夷风”来概括,他提醒华语写作中的话语想象:“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中国,但不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中国。”[10]如果说王德威强调的“华夷风”是在空间意义上的地域角度消解汉族/中国中心主义,王安忆对其的消解则体现在时间意义上的历史层面,剥除优位性和在地向心性统摄的历史话语后,历史书写中的“遗”和“夷”作为可与男权历史等量齐观的历史线索,在她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获得了重新定义,而她通过历史写作实践传达的是:看似以整体性状态存在的历史并不是致密不可分的,大一统的宏大历史叙事是书写历史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书写历史的唯一通道,更不是历史真相的唯一面貌。
[ 1 ] [美]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1-187.
[ 2 ] [美]朱迪思·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A].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05.
[ 3 ] 周新民.个人历史性维度的书写——王安忆近期小说中的“个人”[J].小说评论,2003,(3):40-45.
[ 4 ]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1.
[ 5 ]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41-42.
[ 6 ] [英]肖恩·霍默.导读拉康[M].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419.
[ 7 ] 王侃.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5.
[ 8 ] 王德威.中国小说二十家[M].北京:三联书店,2006.17.
[ 9 ]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王德威.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