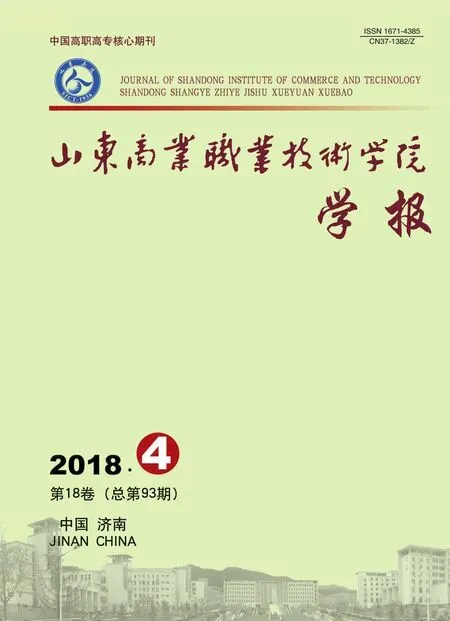“归潜堂诗”与金末元初文人心态
贾君琪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00)
刘祁(1203-1250年),字京叔,号神川遁士,大同浑源县(今属山西)人,金末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归潜志 序》中描述道:“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1]1由此可见,刘祁在世时交游甚广,所结交的都是金代有名气的人。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想象他在金末元初文人中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所以其在金朝灭亡这一特殊背景下的行藏足够成为众多金朝遗民关注的焦点。他自己起名“归潜”并题字的居所,也必成为当时交友文人笔下的谈资。诗歌作为文人表达志趣、传递信息的载体在此时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归潜堂诗”便在这此背景下产生。根据《归潜志》与《全金诗》收录,有20位金代遗民作“归潜堂诗”25首。笔者接下来将“归潜堂诗”的产生背景及原因、思想内容以及文人心态作细致探析。
一、“归潜堂诗”的产生背景及原因
金朝末年,元兵铁蹄涤荡金国疆域,时局艰难,义兵蜂起,动乱与战火纷仍。众多文人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在仕与隐之间作着艰难的抉择。刘祁作为金末文人兼金朝旧臣之一,此时已驰誉四方,并且因他交游广泛,其仕与隐的抉择便成为金代遗民关注的焦点。刘祁经历了残忍的战争与颠沛流离的生活,眼见了朝廷的昏庸与懦弱,金朝灭亡后,他毅然决定归乡隐居。“由铜壶过燕山,入武川。几一载,始得还乡里。乡帅高侯为筑室以居。”[1]171刘祁归乡,乡帅高侯即为他在以前居住的地方建造居所:
四面皆见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东为柏山,代北名刹。西则玉泉、龙山,山西胜处。故朝岚夕霭,千态万状。其云烟吞吐,变化窗户间。门外流水数支,每静夜微风,有声琅琅,使人神清不寐。[1]172
时值金朝灭亡,几经波折回到家乡,有乡人出资修建居所,居所环境又如此幽美,饱经战乱的刘祁为自己的居所提名曰“归潜”以表退隐之志。
据《归潜志》记载,刘祁出生在一个备受赞誉的书香门第世家。刘祁的高祖刘撝在金朝首次科举取士时,以辞赋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刘撝之后,连续四代八人考中进士。因为这件事情,中奉君到赵秉文那里索求“八桂堂”三字以表纪念,赵秉文回答说“君家岂止八桂而已耶”,就为刘家题写了“丛桂蟾窟”四字。赵秉文的书法在金享响誉一时,到他门前求字的人络绎不绝,赵秉文异常烦恼,无奈之下在自家宅门上书写“老汉不写字”。可见能得到赵秉文墨宝的人不是他交往密切的就是他所看重的,刘家在金朝的影响不言而喻。
刘祁的行藏能够受到时人的关注,他的家族背景是一方面,他个人的才华与人品亦不可忽略。《浑源刘氏世德碑》记载,刘祁以平民的身份在士大夫文人之间行走,他写的文章受到赵秉文、李纯甫、元好问等人的极力赞扬,视为“异才”[1]185;《归潜堂记》中记载:“以著述自力,颇为先达诸公所知。”[1]171从这些文献的论述中,我们便可以知道刘祁的才华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是时人关注他的原因之一;“又结交当世豪杰,未有不与以文字往还者。”[1]171由此亦可以推断刘祁与时人的交往密切,他的行藏众多的文人也应该是极其清楚的。
金末时期统治者之间穷兵黩武,生活在此时的文人们心中也是不安宁的。金被元灭,摆在这些文人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隐居山林;服务元朝统治者。当这些文人们还在仕元与否之间徘徊抑或是已经仕元内心还盘算着退隐时,刘祁回归乡里建成“归潜堂”便成了他们矛盾心理的一个宣泄点,他们的矛盾心理也在“归潜堂诗”中得以抒发。“归潜堂诗”诗人们的行踪并不能完全展现他们的心理状态,而他们在受到刘祁“归潜”这一行为的触动后发自肺腑的语言却成为他们内心最直白的书写。
由此可见,刘祁的“归潜”是“归潜堂诗”产生的外在原因,金朝灭亡后文人们人生出路的选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心理是“归潜堂诗”产生的时代大背景及最根本的原因。
二、“归潜堂诗”的思想内容
时值金朝灭亡之际,故国沦丧,哀鸿遍野,面对这般生存境遇,能够有一处安身之地便成为众多金朝遗民的向往,刘祁也不例外。新居四面环山,碧水自门前淌过,经历戎马兵戈后的刘祁想享受片刻的安然也是人之常情。作为享誉一时的才子,刘祁的行为受到一些乡人的误解:如此有才华的人在国家安危之际不去发挥自己的才干,而偏居一隅,真是令人气愤。刘祁则视之坦然,在新居题字表达“归潜”之情。从字面意思来看:“归”即返回、回去的意思,处于刘祁的角度就是回归故里;“潜”即隐藏、不露在外面,处于刘祁的角度即隐居。刘祁的故交们因“归潜堂”作“归潜堂诗”,表面上看与隐逸诗无异,目的是为了抒发隐逸之情。实际上,“归潜堂诗”远远超出“隐逸诗”的范畴——它与其说是对刘祁归隐这一举动做出的回应,不如说它是唱和诗。
《尚书 尧典》曰:“诗言志。”[2]12《毛诗序》认为:“在心为志。”[3]61志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且具有情感内容(情动于中),郑玄《尚书 尧典》注说“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由此可知,诗是阐发人的情感意念的。“归潜堂诗”也不例外,其中包含着作者内心真实的思想情感,下文将对“归潜堂诗”的主要思想内容作简要的归纳总结:
第一,点明归潜缘由,感慨世事易变。有史记载以来,每逢朝代更迭之际,就避免不了战火,战争给人带来的不只是物质的损耗更是一种内心的摧残。安逸的生活被打破,物是人非、时过境迁之感便涌上心头。“浩浩干戈里,怜君遂隐居”(李维寅)[5]522、“沧海成田后,携家返故乡”(李微)[5]522、“万里烟埃气尚炎,秋风携手赋归潜”(赵著)[5]523。这几句诗都直接点明了刘祁因战火决意“归潜”。“谁知天地遽翻覆,沧海横流陷平路”(李献卿)[4]431、“扰扰人世间,荧荧风炷光。谁能逃厄数?况复入吾乡”(吕大鹏)[4]455、“世路艰难已饱经,归来一事晦虚名”(勾龙瀛)[5]525,从这些诗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金末战乱诗人们对于世事易变的感慨。适逢战乱时期不管人的地位高下卑贱,都免不了战争的折磨,大多数人都不能够逃脱这样的厄数,亦可看出处于这样社会背景下诗人们的无奈。
第二,劝勉抛却浮名,赞同归隐山林。前文已有论述,刘祁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几代人都在朝为官,对于他来说,在朝为官施展才干才可能是他最好的选择。然而对于刘祁的友人们来说,在乱世有一安定的居所来躲避战乱,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他的友人在诗中纷纷劝说道“富贵于人真暂热,文章照世足为娱”(吴章)[4]170、“我有一言君试听,乾坤万古真陲亭。但教定宇天光发,区区世间富贵何异蜾蠃与螟蛉”(李献卿)[4]431、“功名真敝屣,轩冕等浮沤”(李惟寅)[5]522,告诫刘祁富贵、功名是转瞬即逝的,没有必要在这些事情上耗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也有友人将做官的辛劳和内心的煎熬与归隐时的情境作对比,如“惆怅朱门客,思归不得归”(刘肃)[4]429、“列卿太史尚书郎,五更待漏靴满霜。何如一身无四壁,醉踏残花屐齿香”(白华)[4]451,告诉刘祁归隐的好处,让他坚定自己归隐的决心。除了以上两种规劝方式外,亦有友人以身说法,表达自己的隐逸心境与选择,如“都无北阙功名想,且喜南山气象存”(张特立)[4]315、“岁月杯中物,生涯几上书。潜中有真趣,吾亦爱吾庐。”(李惟寅)[5]522、“我无玄豹姿,亦欲事隐沧。空歌紫芝曲,早晚由东鄰。”(高鸣)[5]535
第三,描写自然风光,想象归隐生活。刘祁归乡后,乡人就为他在故居盖了一座新居。据《归潜志》描绘,新居四面环山,郁郁葱葱,有水在新居前流过。对比未归乡之前的环境,兵戈不息,流离失所,身心所经受的摧残可想而知。当刘祁拥有这样一处风水宝地被众友人知道后,殷羡之情也是常有的,于是禁不住便将思维引向另一端:“喧无车马云迎户,静有琴书月挂檐。浑水清泠通竹过,南山苍翠与天兼。”(麻革)[5]279、“四围山水境何胜,一室琴书乐有馀。长啸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圃雨晴初。”(刘德渊)[5]536,新居的周围静谧幽美,洁白的云朵在青葱的树木上缓缓行走,一湾溪水清澈见底穿过竹林,闲下来的时候抚琴自慰,青山与蓝天衔接得恰到好处,新居的环境美得令人窒息。除了描写新居的自然风景外,他们也想象了居住新居后的日常生活,如“诗书足以教稚子,鸡黍犹能劳故人”(释性英)[4]423、“布衣粝食混鱼钓,妻孥粗足常熙熙”(李献卿)[4]431,自己教儿女们诗书知识,自己的妻子喂养牲畜、下地耕田,穿戴纯朴,老幼欢聚一堂。
第四,赞赏真才实学,鼓励著书立说。刘祁因出生于“丛桂蟾窟”的浑源刘氏家族而受人关注,更因自己的才华而受人赞赏。由上文的论述可以知道“归潜堂诗”实质上是一种唱和诗,友人间的附和当然免不了溢美之词,对于刘祁才学炫耀也是其内容之一。如白华的“有才不肯学干谒,便入林泉真自豪”[4]451,即是说刘祁才学很好却放弃仕途毅然归隐,这样的行为是真正的豪杰之士;李微有“经史胸中业,龙蛇笔下章”[5]522,这里是说刘祁作为一名儒士,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可谓炉火纯青,写诗论文下笔成章,和《归潜志》中的描述一致,可见这些诗人对于刘祁才学的赞赏。刘祁既然是这样一位饱学之士,那么诗人们对他的期望也是很高的,麻革的“遥知吟啸同云弟,剩有新诗洒壁缣”[5]279即是对刘祁继续创作的一种鼓舞,薛玄的“故山泉石稳棲迟,纬国才名恐四驰。节信情高方著论,渊明心远更能诗”[5]526,将刘祁比作“节信”和“渊明”,也即是对刘祁著书立说、以文章影响后世的一种期盼。
三、“归潜堂诗”体现的金末元初文人心态
“归潜堂诗”是金末元初的金朝遗民对于刘祁暂时归隐故乡的一种回应,实质上是一种唱和诗,但其诗作内容体现了中国绵延千年的隐逸文化。隐逸文化源于隐逸现象,既然是一种现象那就必然有表现这一现象的载体,先秦《诗经》奠定了诗歌王国的基础,诗歌便是表现隐逸现象的最为通用的方式之一。隐逸现象出现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变的;或是出于仕途艰难而选择隐逸,或是由于战乱而选择隐逸,亦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影响而选择隐逸……作为隐逸现象的一种总结的隐逸文化更是值得学者们去关注。
文献记载,“归潜堂诗”出现于金亡以后,创作“归潜堂诗”的20位作者皆为金代遗民,作为对于刘祁“归潜”行为的一种呼应,可以此来窥探金末元初文人的心理状态。现结合“归潜堂诗”诗作内容作探讨:
首先,“归潜堂诗”体现了文人们对于世事的厌倦。朝代的更迭必然带来战争,战争给统治者们带来的是无尽荣耀与成就感,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实现了征服对方的夙愿。但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统治者们的好大喜功是建立在普通人的痛苦之上。作为金末元初的文人,统治者们的穷兵黩武带给他们的只有身心的痛苦与煎熬。一直处于战争的高压环境下,文人们的内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理所当然他们也便对这世界感到疲乏、厌倦。张特立在其诗作中说“陵迁谷变海波翻”世事的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他“都无北阙功名想,且喜南山气象开”[4]315,世事的变化太过迅猛,致使诗人放弃求取功名的想法,转而去“南山”去观赏战争环境下不可欣赏到的风景。吕大鹏在其诗作中说:“扰扰人间世,荧荧风炷光。谁能逃厄数?况复入吾乡。”[4]455在金元征战的社会大背景下,没有谁能逃避战乱带来的灾难,体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无奈,也即是对着大社会背景的失望与厌倦。
其次,“归潜堂诗”体现了文人们仕与隐的艰难抉择。中国文人无一例外是受儒家文化侵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6]186是文人们心之所往的,建功立业博得功名也是他们读书的最为现实的目标。即使处于金朝亡国之际,金朝文人们的心并不是完全趋向于隐居山林的,他们依然想在仕途上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这些诗作的作者除张特立真正退居山林,吴章、释性英、白华、李惟寅、李微、张纬、薛玄行踪不可考外,其余的诗人在金朝灭亡后都有仕元的经历,刘祁由“归潜”后而在元为官的一段经历可以为此说法提供一点参考。释性英的诗中描写到“因君益觉行踪拙,又为浮名系此身”[4]423,这里是说刘祁可能因世事艰难、战火不断得不到片刻安宁而选择“归潜”,但他又心中惦念着做朝为官的事情,所以内心会有仕与隐的矛盾;张特立的“才大到头潜不得,已传华萼出蓬门”[4]315是对刘祁“归潜”的一种怀疑,也更体现出金末元初文人在仕与隐之间的挣扎;兰光庭和薛玄分别说“祗恐池中非久处,竚看雷雨起天津”[5]523、“只恐葛龙潜不定,一声雷雨跃天池”[5]526,也是对“归潜”这一决定的怀疑。如果一个诗人表明对“归潜”的怀疑,可能是偶然事件,但从笔者的举例中可看出至少有四位诗人怀疑“归潜”的可能性,可见金朝的文人们在“仕与隐”之间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相反,相对于“隐”他们对“仕”更加向往。
最后,“归潜堂诗”体现了文人们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失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这一爱国名言可谓是中国千百年来对于广大人民社会责任感的呼吁与总结。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深入骨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文人志士的生活准则,家国情怀是他们心中不可撼动的真理。屈原是我国爱国主义的典型形象,他的爱国情怀喷薄出《离骚》,不忍见故国灭亡投江殉身成为妇孺皆知的佳话;曹植身处战乱频仍的魏晋时期,看到战争,他谱写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慷慨之语;爱国诗人陆游经历北宋灭亡而南渡,在其去世前,心中挂念的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见其对国家的一片赤诚;文天祥在元军进攻南宋,四次劝和不从被俘后,作“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自己对故国的忠诚。反观金末遗民所做25首“归潜堂诗”,他们所纠结的并不是如何为亡金平反或如何保全名节,而是在仕元与否之间徘徊不定,即使规劝隐逸也仅是从生活环境、个人享受等层面出发,与同时期的文天祥相比缺少民族、国家气节,不得不说是一种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失落。
结语
“归潜堂诗”可谓是金代灭亡后展现遗民心态的典型诗作,通过分析“归潜堂诗”的创作背景与原因、思想内容,有助于我们清晰地把握金代灭亡后广大士大夫文人的心态,也利于文学研究者将金末元初文人心态与其它朝代的遗民心态进行比较,探究遗民心态的异同。今后我们的研究可以侧重于从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角度去分析这一时期遗民心态不同于其它朝代遗民心态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应拓宽研究视野,分析金代遗民诗作所特有的美感特质,促使今后的研究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