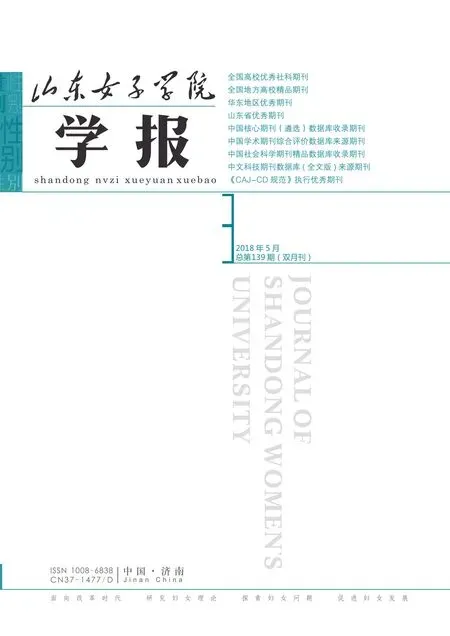考琳·麦卡洛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欲望表达
徐 梅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北京 101400)
自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将女性界定为男性的一部分——肋骨开始,女性便丧失了独立话语权;同样,自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将“男性/女性”进行“阳/阴、天/地、土/水”的二元对立性的定位始,女性便丧失了自我追寻的权利和机会,沦陷为男性窥视的对象和其权力的附庸。
出身于殖民地国家、经受女权主义思想熏陶的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麦卡洛看清了男性权力对女性进行规避的历史轨迹,她通过小说创作梳理了不同历史空间中女性意识和女性欲望被抑制的事实,呈现了女性在男性权力规避之下对自我的追寻,对爱情、性、人生意义、两性关系、事业等话题的追问。考琳·麦卡洛作品中的女性形形色色,有勇于追寻自我的玛丽·班纳特,有以色相为生的妓女迪伊·迪伊,有以国家政治使命为人生目标的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有疯狂的母亲们,有个性鲜明的知识女性内尔·金罗斯、朱丝婷,还有以美貌改写历史、追逐个人情欲享受的海伦。考琳·麦卡洛从她们所处的历史时空出发,肯定了她们追问的勇气和奋起抗争的胆识,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指出了她们自我追问的历史局限性和有待提升的空间。
一、掌控性话语的主动权
曾有研究者指出,在传统的父权文化中,“男性的欲望占据了叙事的中心,女性需要做的只是被动的提防和自我保护”[1],强调了在传统男权社会里,男权意识对女性欲望进行遮蔽的事实。由于男性长期垄断着性活动的主动权,以至于女性的本能性欲求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有关研究者对于女性被规训的事实进行了总结,“所有妇女从很小时候起就被灌输一种观念,即,她们最理想的性格是与男人截然相反的性格:没有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我克制来管束,只有屈从和顺从于他人的控制”[2]。
考琳·麦卡洛通过小说创作对女性的性欲求被扭曲、异化的悲剧进行了呈现,但她也通过失却文明话语束缚的安娜和男性权力规避下海伦生动、强烈的性欲求,表达了女性性欲求存在的客观性及其鲜活力。作为一名受女性主义思想熏陶的知性女作家,考琳·麦卡洛还通过对女性们主动寻求性愉悦行为的赞许,表达了对女性主动寻求欢愉行为的支持态度。在《呼唤》中,考琳·麦卡洛对女性应该在性生活中保持什么样的姿态,进行了详细探讨。
在《呼唤》中,考琳·麦卡洛首先通过伊丽莎白在性生活中受难般的举动,谴责了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本能性欲求进行异化的悲剧。该作品中的伊丽莎白是在宗教为代表的社会规约的禁锢下,逐步对自我进行消解,并将男性标准内化的时代牺牲品。长老教会的默里牧师利用“牧师”的身份对伊丽莎白进行着性罪恶的“教育”,“女人如果喜欢干那事儿,就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上帝只让丈夫快乐,女人是诱惑和邪恶之源,因此,男人如果沉湎于声色口腹之乐,就应该责备女人”[3](P22)。伊丽莎白婚前性教育的第二位“导师”玛丽是“性痛苦论”的支持者,她认为性生活是女性不可逃离的原罪,是痛苦不堪的代名词:“这事对女人来说没有任何快乐可言……明智的妻子应该把新婚之夜发生的事情同丈夫分开……”[3](P22)饱受“性罪恶论”“性痛苦论”侵袭的伊丽莎白在新婚之夜的性生活中做出了受难般的举动。伊丽莎白在性生活中对痛苦的忍耐表明:她完全接受了传统文化赋予她的“性罪恶论”和“性痛苦论”,将自己的女性身份诠释为性痛苦的源泉。
在该作品中,考琳·麦卡洛通过失却文明话语羁绊的安娜对性的渴求,强调了女性的性欲求存在的客观性。与被“性罪恶论”“性痛苦论”禁锢的母亲相比,虽然智障但身体发育良好的安娜却对性愉悦充满了渴求。安娜对性愉悦的主动寻求颠覆了伊丽莎白对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受害者”定位。安娜渴求着、追寻着以母亲、玉等为代表的“正常人”所认为的男性对她的猥琐和侵犯,对于周围“文明人”的焦虑浑然不觉,可以说未被社会规约浸染的她对性欢娱的渴求和追寻是人的本能反应,正如作品中所言:“这个姑娘全然没有对性欲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抑制,然而,又纯洁得像天上飘下来的雪花”[3](P306)。
在该作品中,考琳·麦卡洛还通过茹贝·康斯特万形象的设置,强调了女性不仅仅是性侵犯的对象,女性不仅可以对性愉悦充满渴求,也可以掌控性话语的主动权,并依据个人欲求选择自己心仪的性伴侣,可以敞亮地表达自己的性需求。从出身及人生经历讲,茹贝·康斯特万是英国殖民文化的牺牲品,作为移民与其他少数族裔不合法婚姻的后代,茹贝·康斯特万自出生便经受着苦难,在经历了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强奸、嫁给老头、做妓女等苦难后,经济独立的茹贝·康斯特万开始珍视自己作为独立女性的本能欲求,她从纯粹性愉悦的角度,为自己物色了魅力四射的亚历山大,并掌控着他们俩之间性生活的主动权。考琳·麦卡洛通过茹贝·康斯特万形象的设置,表明了其对完全自主的女性性行为的支持态度。
二、爱情应该立足于自我独立之上
爱情、婚恋是考琳·麦卡洛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关于爱情问题,她通过不同的作品、不同的女性形象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对于女性们应该如何对待爱情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她认为爱情不是女性人生的全部,女性也不应该将自己全部的人生意义作为爱情的赌注,爱情应该立足于女性自身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女性自我实现的基础之上。
《荆棘鸟》是考琳·麦卡洛对女性的爱情问题探讨得较为深入的一部作品,在该作品中,她既探讨了爱情在女性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也指出了爱情不是女性生活全部的事实。同时,还强调了,女性应该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基础上再去追寻两性和谐的爱情。
《荆棘鸟》中的菲奥娜经历了《海的女儿》中小人鱼一样的爱情悲剧:为了爱情,她舍弃了所有,包括自我。在该作品中,菲奥娜出身高贵,但是,年轻的她因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与已婚政治家帕吉汗的爱情,而遭遇家族的驱逐,被迫带着私生子弗兰克嫁给了剪羊毛工帕迪。造成菲奥娜痛苦一生的不是现实婚姻的不和谐,而是菲奥娜对已逝爱情的沉迷和守护,以至于她无暇顾及自己现实婚姻中的孩子们,造成了男孩们的不婚不育、女儿梅吉在婚姻问题上的偏狭。通过菲奥娜的爱情悲剧,考琳·麦卡洛否定了女性为了爱情丧失自我独立性的作法。
与菲奥娜相比,玛丽·卡森是一位出身低微,为了名利、地位,不惜牺牲作为一名女性本能欲求的女性。自卡森死后,玛丽·卡森成了富可敌国的女庄园主,虽然出于本能欲求,她也渴望婚姻、家庭和爱情,但是她不愿意以牺牲自己既有的财产、社会地位为代价,而走进婚姻的“轭”里。直至拉尔夫的出现,她才对自己昔日拒绝情爱、婚姻的作法充满了忏悔,因为此时的她虽然极度渴望征服拉尔夫的情感、渴求拉尔夫的温情,但此时的她已经年迈、无法身体力行。考琳·麦卡洛通过玛丽·卡森的忏悔,否定了女性对爱情的疏离态度,强调了爱情在女性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
该作品中的朱丝婷是考琳·麦卡洛设置的一个有自我寻求意识的新女性,她既摆脱了祖母菲奥娜、母亲梅吉为了爱情牺牲自我的做法,也摈弃了玛丽·卡森为了名利、事业牺牲爱情的做法。当她没有完全的把握掌控爱情时,她选择的是等待。在与她相处了十年的雷纳表示不会丝毫改变她,并尊重她的演艺事业之后,她才完全接受了雷纳的爱情。通过朱丝婷形象的设置,考琳·麦卡洛表达了自己的爱情与事业兼顾的爱情观,并强调了女性独立和自我实现在爱情生活中的重要性。
三、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自我实现方式
作为昔日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曾全盘移植了英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模式,造成了澳大利亚女性他者处境的延宕。因此,澳大利亚女性的自立问题便成了社会问题中的焦点。作为一名出生于殖民地国家的女性作家,考琳·麦卡洛比同时期的男性作家更能体味到澳大利亚女性所遭受的种族、性别的双重压抑。作为一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女作家,考琳·麦卡洛自身所遭受的家庭创伤和文化创伤也促使她对女性的自我实现问题进行深入思索。
《班纳特小姐的自立》是考琳·麦卡洛对《傲慢与偏见》进行续写而产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考琳·麦卡洛将原著中最不起眼的玛丽·班纳特设置成了女主角,并围绕着她的成长历程,探讨了女性的自我实现问题,颠覆了原著中的诸多观点,其中包括爱情观、婚姻观、女性价值观等。
作为原著的延续,故事开篇时,玛丽·班纳特已经是一位因为容貌丑陋、性格倔强,及照顾母亲的职责而被排斥在爱情、婚姻之外的38岁的老处女,但是,被隔离在爱情、婚姻之外的玛丽·班纳特可贵的地方在于她对现实的不满、对知识的渴求、对人生意义进行追问的勇气。得益于偶然的机会,玛丽·班纳特去掉了龅牙和满脸的脓包,实现了华丽转身,变成了比姐姐伊丽莎白更有韵味的美丽女子,而母亲的猝然离世,也给她的自我寻求愿望提供了践行的契机。
起初,心怀天下的玛丽·班纳特按照自己的理解开始了单枪匹马的自我寻求旅程——揭露当时英国社会的黑暗面、写一本关于英国腐朽社会的书。但社会的复杂性和当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冷酷地讽刺了她拯救社会行为的幼稚和可笑,因此,她不仅没能接近她想揭露的腐朽社会的本质,反而遭遇抢劫,被邪教组织囚禁。她通过抨击社会黑暗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梦想在冷漠人性的映照下,愈显不切实际。经受多重创伤的玛丽·班纳特逐渐成熟起来,在以查理、安格斯为代表的男性世界的帮助下,她放弃了当初通过写作来揭露英国黑暗现实的梦想,着手社会慈善事业,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四、相互帮扶的两性关系才是和谐的
因为受父母之间不和谐婚姻的影响,作为一名自幼便因为女性身份而备受父母嫌弃的女性,考琳·麦卡洛曾经萌生了拒绝异性、拒绝婚姻、拒绝孩子的极端想法。但在女权主义思想影响下成长为知名神经病理学家和著名作家的考琳·麦卡洛也对两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索,改变了自己曾经极端的看法,认为作为一直被“他者”化的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男性的帮扶,而女性在对男性的凝视过程中也应该学习男性身上的优秀品质,而不是一味地拒绝和疏离。
考琳·麦卡洛在《恺撒大传·十月马》中塑造的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无论在情感管理、性生活,还是在政治统治策略等方面,均是在恺撒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首先,坠入了恺撒情网的克里奥帕特拉,无力抗拒自己热烈的情感。在恺撒的眼里,克里奥帕特拉对情感的过分投入近似疯狂、不计后果,不是一个埃及法老应该所为之事,因此,恺撒提醒她要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负责。其次,在性生活方面,克里奥帕特拉也是师从于恺撒,逐渐学会了享受性的愉悦。再次,对于如何管理埃及,恺撒也是以一位导师形象出现,从克里奥帕特拉的穿衣打扮到政策纲领的制定,恺撒都给予了其悉心指导。
在考琳·麦卡洛的笔下,女性也有了凝视男性的机会,这种凝视摆脱了传统男性凝视目光所携带的权力和充满色情意味的欲望,并在对男性凝视的过程中,从男性身上获得了某种启迪。在《呼唤》中,她通过伊丽莎白从李·康斯特万身上获得的启迪展示了男性魅力对女性自我意识萌发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该作品中,伊丽莎白因为偶然的机会窥视了李·康斯特万在深潭中自由沐浴的场景,他无拘无束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沐浴行为和健康、充满魅力的裸体使伊丽莎白获得了生命的启迪。相爱多年的李·康斯特万和伊丽莎白之间第一次深入骨髓的融合则让伊丽莎白得以重生:“一股巨大的快乐震撼着她,深入骨髓……”[3](P412)这种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快感源自伊丽莎白被禁锢已久的灵魂,觉醒后的伊丽莎白认识到了23年无爱婚姻生活的愚昧之处,体味到了何为幸福,明确了人生所求,感受到了身体对灵魂的回归。
在《荆棘鸟》《恺撒大传·十月马》等作品中,考琳·麦卡洛则通过男性目光的审视发掘了女性特质对男性自我寻求所具有的震撼意义。在《荆棘鸟》中,拉尔夫为梅吉身上迸发出的坚韧生命力而折服;在《恺撒大传·十月马》中,恺撒则因为克里奥帕特拉对爱情无所顾忌的投入而感动,并进而获得了“新生”;在《遍地凶案》中,考琳·麦卡洛通过卡尔米内探长的目光,赞叹了女性身上诸多超越男性的优良潜质和勇气。
考琳·麦卡洛通过小说创作,呈现了传统女性在爱情、性话语、自我实现、两性关系中曾经遭受的禁锢及痛苦,同时也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阐释了女性在爱情、性生活、自我实现、两性关系中应该持有的立场和态度,表达了一种较为先进的女性意识,也为当代女性的自我发现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板。
参考文献:
[1] 武田田.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中的温馨小品——与狼为伴中的两性欲望与自然之关系[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4):116-119.
[2] Mill,John Stuart.TheSubjectionofWomen[M].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21.
[3] [澳]考琳·麦卡洛.呼唤[M].李尧,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