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荒野”概念的嬗变与后现代建构
马 特
“荒野”(wilderness)概念是美国精神的重要范畴,对美国的现实社会与文学想象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自16世纪时“五月花号”初次登陆美洲大陆,“荒野”概念便已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荒野经验作为美国环境运动的核心,促成了美国荒野保护法与国家公园的设立*See for instance, Samuel T. Dana and Sally K. Fairfax, Forest and Range Polic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0); Craig W. Allin, The Politics of Wilderness Preservation (Fairbanks: University of Alaska Press, 2008).。此外,美国独特的荒野叙事对边疆文学、超验主义等文学创作流派影响深远,可以说“形成了美国文学的传统”*杨金才:《论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意象》,《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直至进入后现代时代的今天,“荒野”概念依然是人们理解美国社会文化的关键一环。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荒野的概念有着众多争论。例如,研究荒野史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荒野是一种文化建构,即受制于观者的文化;与之相对,环境运动的激进分子则会强调,荒野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有学者采取了较为中立的立场,指出荒野既是一种真实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人为建构*Michael Lewis, American Wilderness: A New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人们曾从美国文化史*See for instance, Roderick Frazier 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Fifth Edi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美国文学*See for instance,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代表性人物*See for instance, Max Oelschlaeger, The Idea of Wildernes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Age of Ec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社会学*See for instance,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以及国家公园发展史*See for instance, Alfred Runte, 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3rd e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等角度进行过重要的讨论。虽然这些讨论所涵盖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但目前对荒野概念的研究尚有推进的空间: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荒野研究专注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荒野的破坏,在讨论中往往将荒野世界与人类世界分为两个严格对立的阵营,强调用生态中心主义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并未充分思考“荒野”应当如何应对来自后现代世界的挑战。这类以一种“中心”代替另一种“中心”的做法,实际上与后现代世界的“解构一切中心”的主张相悖,同时也折射出荒野概念的后现代建构的缺失。第二是在有些研究中,人们对荒野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如纳什便将“荒野”(wilderness)与“野性”(wildness)相混淆,而理解这两个概念恰恰是荒野概念完成后现代转变的核心一步。基于此,本文将审视传统的荒野概念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嬗变历程,以及这一概念在后现代世界中所经历的消解与重构。
一
在《荒野与美国精神》一书中,罗德里克·纳什曾这样阐释荒野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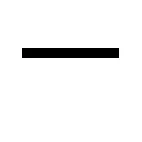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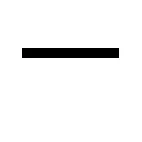


这些欧洲移民离开原本居住的发展成熟的欧洲城市,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后登陆美洲大陆。相比于旧式的欧洲城市生活,未经开发的美洲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蛮夷之地,是“可怕而萧条的荒野”。这种荒野以“野兽”和“野人”为代表,显然是与文明相对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存在。在生态批评话语中,此类叙述即属于格里格·加拉德所言的“旧世界荒野”叙述。“旧世界荒野”叙述将荒野自然描述为超越文明界限的地方,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威胁”,是“流放”之地*Greg Garrard, Ecocritic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62.。 这种荒野类型多见于早期文学文本,如圣经故事和早期英国文化中。在早期的美国文学中,“旧世界荒野”也常常与邪恶的行为相联系。例如,在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布道文中,便将“尚未开垦的黑暗森林”比作“恶魔的嬉戏场”,是来自于旧世界的美国荒野地区*Paul Elmer More, Shelburne essays on American literatur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3), 7.。因此,在欧洲移民的第一印象中,北美大陆的原始荒野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神秘区域,人们应当用宗教和欧洲农业将其征服。
早期文本中的荒野除了与神秘和威胁相关,还呈现出另外一种形象,即花园的形象。利奥·马克斯在《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中指出,最初人们关于北美大陆的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其看作可怕的荒蛮之地,而另一类则将其看作花园。这两种意象“都是一类根比喻(root metaphor),这是一种诗的理念,展示了一种价值体系的本质”*[美]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马海良、雷月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相比于充满敌意的、陌生的、神秘的荒野意象,一些早期作家将荒野描绘为一种美丽的、友好的、令人愉悦的存在。例如,在亚瑟·巴罗威的《北美大陆首航记》中,作者塑造的荒野意象便不同于布雷德福;他将弗吉尼亚描绘为一座异域的花园,甚至连当地的土著也都“非常英俊而友好”:
这座岛上有许多美丽的森林,里面有大量的鹿、兔子和野禽,甚至在盛夏时节,动物的种类依然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森林不是……贫瘠而荒芜的,而是拥有世界上最高最红的雪杉树……第二天,有几艘船向我们驶来,其中一条船上是国王的兄弟;他的身边带有四五十名随从,这些人都非常英俊而友好,他们的举止行为也像欧洲任何地方一样文明有礼。*Arthur Barlow, “The First Voyage Made to the Coasts of America,” in Joseph Black et al. eds., The Broadview Anthology of British Literature: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vol. 2 (Peterborough, ON: Broadview Press, 2010),365.
在这段叙述中,巴罗威描写美洲荒野的笔触更多强调其异国之美和新奇感。无论是对当地的居民,还是对各种动植物,都没有任何的贬低之意,反而表现出一种亲近感,甚至带有伊甸园的色彩。早期的荒野描写对当地的动植物、土著居民、气候和其他自然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建构了美洲大陆独特的地理空间,也促进了人们对这一地域的认知与认同,使“荒野”成为北美大陆的决定性特征。


直至19世纪,启蒙时期这种理性至上的情况才开始发生转变,美国“荒野”概念也迎来了第一次重大转型。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19世纪的美国文学界出现了超验主义潮流。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与约翰·缪尔(John Muir)等人作为超验主义流派的重要推动者与继承人,在各自的自然书写中对荒野意象进行了新的阐释。自此,不同于殖民时期的美国文学,荒野的意象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出现了“新世界荒野”(New World Wilderness)的概念。
二

相比于对原始自然的观察,梭罗对“荒野”概念的认知恐怕更多地源于关于美和真理的浪漫主义理想。有西方学者认为,“吸引他(梭罗)的或许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自然,而更应说是一种理想化的、梭罗本人称之为‘荒野’的自然类型”*Robert Kuhn McGregor, A Wider View of the Universe: Henry Thoreau’s Study of Na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93.。在这一方面,梭罗受到同时代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的很大影响。爱默生在探讨荒野与文明、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时,将荒野自然定义为“未被人类改造的精华”,认为文明是“人类意志”与这些“精华”的混合*Ralph Waldo Emerson, Natur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9), 2.。换言之,对于浮躁的现代人而言,荒野是人们在文明的重压之下得以寻求慰藉的庇护所,是一个远离喧嚣的精神世界的桃花源,这种对荒野的浪漫化建构也成为19世纪美国“荒野”概念的重要维度之一。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荒野文化也逐渐凸显出与欧洲自然经验的不同。在“寻找‘美国’特有的物品”时,美国民众意识到,“至少在一点上自己的国家是[与欧洲]不同的:那就是在旧世界中,没有与荒野相对应的存在”*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67.。 虽然高级文化与悠久历史是美国所欠缺的,但是在景色雄伟的荒野自然方面,美国甚至可以说比欧洲“明显更胜一筹”*Barbara Packer, “‘Man Hath No Part in All This Glorious Work’: American Romantic Landscapes,” in ed. Kenneth R. Johnston et al. eds., Romantic Revolutions: Criticism and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9.。这种对荒野自然的民族自豪感也反映在美国艺术家兼博物学家奥杜邦的一段旅行书信中:“虽然这里[欧洲]过剩的精致本身便是一种无穷的奇迹来源,但是我所偏爱的将永远是深爱的美国那无限的自由[大地]。”*qtd. in Richard Rhodes, John James Audubon: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04), 297.奥杜邦在欧洲旅行时,见到了修剪整齐的欧洲花园,虽然这种精致的田园之美非常吸引人,但是他本人还是更喜欢狂野不羁的美国荒野。此外,原生态荒野的生物多样性也是吸引美国人的另外一个原因。例如,奥杜邦便认为,伦敦动物园中精心饲养的自然生物还不如他一个早晨在美国湿地中能找到的多。因此,身处欧洲时的奥杜邦热烈地宣称“美国将永远是我的祖国”,这也折射出荒野书写不仅对美国独特的地理空间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也使荒野成为“爱国者的热爱对象”*朱新福:《美国文学上荒野描写的生态意义述略》,《外国语文》2009年第3期。。
经过浪漫主义时期自“旧世界荒野”到“新世界荒野”的过渡,人们对荒野的态度从最初的厌恶与惧怕,逐渐变为热爱与尊重。可以说,19世纪上半叶,人与荒野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形成一种模式”*Hans Huth, Nature and the American: Three Centuries of Changing Attitud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84.。文学界对荒野的崭新评价强调荒野与人类社会相比的纯净与美丽,而这也导致了以荒野为代表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随着19世纪后半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原生的荒野地区开始遭到迅速蚕食。朴素荒野所面临的威胁使一部分人感到荒野经验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批卓越的荒野活动家在美国应运而生,其中约翰·缪尔“作为美国荒野的宣传者堪称无出其右”*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123,在荒野保护运动中发挥了无法忽视的重要作用*Daniel G. Payne, Voices in the Wilderness: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6), 85.。缪尔对荒野保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主张人们应当重视世界上所有的生物,认为即使是“最小的显微的生物”(smallest transmicroscopic creature)*John Muir, The Wilderness World of John Mui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6), 317.也具有内在价值。缪尔如其本人所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说客。1890年,在他的呼吁下,优胜美地(Yosemite)被联邦政府列为保护对象并建立了国家公园。自此,美国掀起了第一波大规模建设国家公园的浪潮,促使荒野成为美国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地理空间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荒野概念的建构、评价与书写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例如,有的学者开始重视荒野在心理层面的涵义,提出人们“应当强调的不是荒野究竟是什么,而是人们认为什么是荒野”*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5.。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荒野,其共同点是荒野意象带给观者的体验,如有的学者认为“任何让人感到失去方向、迷失、无助的地方都可以被称为荒野”。在这个范畴内,“荒野”概念本身丰富的修辞可能性使之超越了原本的用法,甚至人造产物——如人工的花园式迷宫——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荒野”。总之,随着人造空间的不断扩张和文明社会的发展,“荒野”概念本身也遭受着更多的冲击,原始荒野的概念逐渐消解,重新建构为后现代世界的荒野。
三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与原始荒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迫使人们重新冷静思考人与荒野之间的关系。此前,人们关于荒野自然的想象强调“无人涉足”这一特征,是人们基于对野性与原始的幻想而创造的一种印象。这种构想中的荒野拥有朴素、洁净等特征,容不得一丝杂质。有的学者认为,荒野必须彻底远离人类文明。如罗伯特·马歇尔提出,荒野应是在不依靠机械工具的情况下无法一天穿越的区域*Robert Marshall, “The Problem of the Wilderness,” Scientific Monthly 30.2 (1930): 141.,利奥波德的标准则是可以“消耗为时两周的背包旅行”的地带*Aldo Leopold, “The Wilderness and its Place in Forest Recreational Policy”, Journal of Forestry 19. 7 (1921): 719.。如此一来,荒野的概念强调其纯粹性,甚至像是为了与城市空间所象征的文明和工业相对比而制造出来的概念。

然而,这样一个原始而无人的荒野自然的形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许多问题。譬如,它完全忽视了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存在——荒野只不过是美国白人眼中的无人生存的原始环境,而不是印第安人多年生活的家园。如此一来,荒野的概念便带有了殖民主义色彩。另外,城市与社会的发展也对荒野的概念造成了影响。以上文提及的国家公园为例,国家公园作为荒野保护运动的产物,本身便受到了许多人为的干扰与管理,因此似乎已经不再符合人们关于纯粹荒野的传统想象。这里便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一个区域究竟有多‘野’(wild)才能被称之为‘荒野’(wilderness),或者反过来说,‘荒野’可以允许多少来自文明社会的影响”?正如纳什所指出的:
如果我们坚持绝对纯净的“荒野”,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荒野只能是人类足迹从未沾染过的地域。然而,对于很多人而言,与人类或人造产物的少量接触并不会毁坏荒野的品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印第安人或野牛的存在是否会破坏一个地区作为“荒野”的资质?一个空的啤酒瓶罐呢?天空中的飞机呢?*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4.
在20世纪末,人类已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仍然严格遵守荒野是“无人的原始自然”这一设定的话,那么包括国家公园等在内的许多自然环境似乎都将被排除在荒野自然的范畴之外。但实际上,正是这些区域构成了美国现在主要的荒野地区。美国后现代作家加里·斯奈德在散文集《荒野实践》中也直白地指出,对于大部分北美人而言,荒野是“官方认可的公有土地,或是由森林服务处和土地管理局掌管,或隶属于州立公园与国家公园。有些小规模土地则由一些私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持有……这是整个北美大陆保留下来的圣地……这类土地只占整个美国领土的百分之二。”*Gary Snyder,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90), 14.换言之,这些荒野区域或是公有的,或归私立组织持有,都是受到人类管理的。
即使除去目前这些由人类管理的荒野自然,更早时候的荒野中是否完全无人呢?斯奈德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在荒野文化中生活的经历一直是人类基本经验的一部分。从来没有一片荒野几十万年都不曾留下过人类的足迹”。也就是说,在斯奈德看来,并不存在真正“无人的”荒野自然,但这一点并没有让荒野不再是荒野。斯奈德宣称,“文明是可以渗透的,正如荒野会有人入住一样”。换言之,文明与荒野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而是可以彼此渗透的。在这个渗透过程中,荒野并不会因为文明的渗透而改变自身的属性。显然,当今社会人们关于“荒野”的概念,已经距离最早的“朴素而无人的自然环境”有了一定的偏差。
旧有的荒野概念强调荒野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建立起文明与荒野之间的二元对立,这固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思想潮流有关,蕴含了人们对纯净的朴素自然与田园乡愁的向往,也表达了人们保护荒野的迫切诉求。表面看来,以荒野为代表的自然环境与象征了人类文明的城市空间似乎大相径庭。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宏观环境的一部分。在《荒野的条件》一文中,纳什曾将环境比喻为一个在荒野与文明的两极范围之内波动的光谱(spectrum),当刻度偏向荒野一方时,人类的干涉便不那么频繁;反过来,当刻度更加靠近文明一侧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便增强了。因此,不论是朴素的荒野自然还是人造的城市空间,都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波动的环境类型。即便自然环境中有个别的人造产物也不会损害其作为自然环境的属性,只不过会使该环境整体更靠近文明一点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对环境的影响愈来愈大。在后现代的城市化社会中,人们不可能一边居住在城市空间中,一边始终假装无人的荒野才是自己真正的家。现代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是城市无形的大网中的一环,城市环境对人类的空间认知也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相反,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居住的城市环境并不是荒野所代表的需要保护的自然环境,那么人们便会不免在对这个环境进行破坏的同时而毫不自知,并且将人类自身置于荒野自然之外。实际上,人类本身及其生活的城市环境都与荒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奥波德在强调荒野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时,曾将荒野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指出“荒野从来不是一种具有同样来源和构造的原材料。它是极其多样的,因而,由它而产生的最后成品也是多种多样的”*[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第178页。。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城市空间,便是这“多种多样”的成品之一。因此,文明本身便源于荒野,具有荒野的属性。

这种对“野性”的关注,构成了后现代世界中“荒野”概念的新维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个概念曾被研究者所混淆。纳什在《荒野与美国精神》中引用梭罗时,便将“世界存乎于野性”(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Henry David Thoreau, Natural History Essays (Layton: Gibbs Smith, 1980), 112.误作“世界存乎于荒野”(In wilder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Thoreau, Natural History Essays, 114.。由于《荒野与美国精神》一书影响深远,因此很多后来的研究者在引用梭罗时都延续了这一谬误。实际上在梭罗的原文中,梭罗强调的是“野性”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将“野性”视作一种抽象的属性,而非某种遥远的自然环境。在梭罗看来,“生活与野性相循”*Thoreau, Natural History Essays, 114.,并宣称“具有野性的事物……中含有自然的骨髓——自然神圣的琼浆玉液——那才是我热爱的酒”*Henry David Thoreau, I to Myself: An Annotated Selection from the Journal of Henry D. Thoreau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2.。“野性”作为一种存在状态,是“荒野”的原始属性;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却又是两个不可互相替代的概念。换言之,荒野是野性的衍生物,在荒野中我们可以发现野性;但是反过来,荒野并不一定是野性的唯一避难所。
关于荒野与野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借用斯奈德对自己的一番评价来进一步理解:

在这里,斯奈德所说的“醉于山”指的也就是醉于“荒野”,而“醉于野”则指的是醉于“野性”。此处的“野”不止存在于“山”中,并不仅仅指向无人的、原初的、真实的荒野,而是也包括了“城市和政府、大学和公司”等与人类文明紧密相关的区域。在《荒野实践》中,斯奈德也强调称,“野性”并不只存在于占据美国国土百分之二的官方认定的“荒野”区域,而是“无处不在”的*Snyder,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14.。 如果人们改变一下界定的标准,就会发现野性“不仅存在于我们周围,而且也寄居在我们体内。”也就是说,相比于日益减少的荒野,野性却是广泛存在的;荒野可能会暂时缩小,但野性绝不会消失无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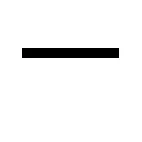
斯奈德所言的“一个世界”是一种开放的生态视域,并没有封闭于原始荒野的范畴之内,他对人类文明与荒野自然一视同仁,在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之间寻找平衡点。换言之,斯奈德认为乡村、郊区和城市之间并无区别,都是属于“同一个领地”。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曾指出:“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区分为两种环境是错误的……只有一个世界”*J. J. Gibson,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130.。在“一个世界”中,对整体性的强调是一个关键的特征。这也就是斯奈德所提出的,“谈及荒野便是谈及整体性(wholeness)。人类便是自那种完整性中而来的”*Snyder,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12.。后现代的“荒野”概念打破了自身与文明之间的边界,使二者逐渐融合为“一个世界”。这种观点与纳什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契合的。纳什在试图解构荒野与文明之间的隔阂时曾提出,是“文明创造了荒野”,认为人们对荒野的赞美始于作为后现代西方文明中心的“城市空间”*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xiii.。在这里,文明不再是人类驯化荒野的产物,反而似乎成为了荒野的源头;或者说,文明与荒野本身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文明与荒野之间的隔离是可以解构的:“有一条依稀可辨的界线,文化入侵者能从此跨过:走出过去的历史,进入永恒的现在,这一生活方式适应于一种更为缓慢而稳定的自然进程。”*Gary Snyder,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14.在后现代世界中,文明与荒野的逐渐融合便是这样一个消解“依稀可辨的界线”的过程,人们从“过去的历史”中的“荒野”走出,最终迈入了关注“野性”的“更为缓慢而稳定的自然进程”。

之所以说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是因为在思想意识层面,几百年来人们对荒野内涵的认知的确存在着较大的起伏变化,尤其是从最初的憎恶与恐惧,转变为歌颂与保护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在现实世界层面,随着欧洲移民登陆美洲大陆,人类文明在这片大陆上逐渐繁荣与扩张,荒野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与人造空间彼此杂糅在一起,后现代世界中已不再存在原始纯粹的朴素荒野。原始荒野的概念强调淳朴自然的无人涉足性,折射出西方世界中持续已久的荒野/文明的二元对立思想,深化了现实与文本之间的矛盾。在后现代世界的挑战下,后现代荒野建构的缺失愈加明显,最终导致了原始荒野概念的解构与后现代荒野概念的建构。与之相对,从旧世界到后现代世界,荒野的概念并没有发生改变。梭罗在1849年写下的“世界存乎于野性”,依然适用于现今的后现代荒野叙述。野性作为荒野的原始属性,成为人们在后现代空间中获得自然经验的重要特征,也是后现代荒野概念的核心维度。后现代世界中荒野概念从强调“荒野”之表象到重视其内在之“野性”的蜕变,并非单纯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通过超越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后现代荒野叙事解构了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达到了对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的统一认同,将二者融合为“一个世界”,建立起一种缓和的、更加成熟的后现代话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