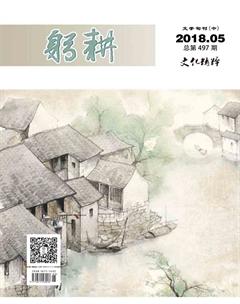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区别认定
刘佳慧
摘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行为对象等方面存在区别。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任某,男,24岁,S省X市某村人,无业。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无行政、刑事处罚记录。
犯罪嫌疑人孙某,男,26岁,S省X市某村人,在X市市政公司工作,系临聘人员。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无行政、刑事处罚记录。
2017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任某伙同孙某在X市Y区西延路以虚报土方回填底票的方式骗取受害人李某12000元。2017年8月李某在西延路购买土方回填,由于自己忙不过来便叫来朋友任某帮忙购买回填土方,任某便伙同孙某虚开土方底票,每次少送两车,每车为400元,由任某全额在李某处报账,两人共虚开30车土方总计12000元,每人分得6000元。
受害人李某于2017年10月20日报案至某市公安分局,该局于2017年10月21日对任某、孙某涉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于2017年10月20日将此二人抓捕归案。同日,李某收到任某、孙某人民币各6000元,并对其达成谅解。
认定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构成犯罪的证据有收条、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辨认笔录、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任某和孙某的供述。
二、审查批捕分歧
本案在审查批捕期间,关于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构成何种犯罪,办案检察官之间产生了分歧,分歧观点及理由如下:
(一) 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构成诈骗罪
这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孙某不属于市政公司的单位工作人员,任某、孙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到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构成诈骗罪。
(二) 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构成职务侵占罪
这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孙某作为市政公司的临聘人员,属于市政公司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务非法占為己有,数额较大,其同伙任某作为共犯,二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
(三)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既构成诈骗罪,又构成职务侵占罪,成立想象竞合。
三、评析意见
上述三种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区分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从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主体不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行为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并未从事公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主体。
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是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从形式上说欺骗行为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职务侵占罪的行为内容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数额较大的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其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
三、行为对象不同。诈骗罪的行为对象是任何他人占有或者所有的公私财物。职务侵占罪的行为对象是行为人所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本单位财物。
在本案中,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虚报30车土方,骗取12000元人民币,涉嫌诈骗罪移送检察院审查逮捕。经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虚报30车土方,即犯罪数额为12000元人民币,现有证据土方底票、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而予认定。受害人李某、证人王某(市政公司领导)都称发现从2017年8月份以来的底票数目有问题,后来发现是任某和孙某一起虚报土方车数,骗了12000元。根据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一款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000元至1万元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12000元的犯罪数额符合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情形。因此,根据《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本案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争议的焦点在于犯罪嫌疑人孙某是否为公司的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孙某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单位财物的行为。
首先,临聘人员指的是与全日制正式职工相对具有临时、短期性质的工人。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主体是指在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中从事职务的人员。在日常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临时雇用人员能否成为职务犯罪的主体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公司或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即构成职务进展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具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管理职权的人员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在此案中,本文采取的是第二种观点,本案中经依法查明,孙某虽然在市政公司中承担开发票的职责,但是这种职责的来源是一种临时劳务合同关系,是孙某依靠出卖劳动力从而获取市政公司报酬的关系。其工作内容由其老板或者领导安排,即孙某的职务只是劳务性工作,并非管理性工作,所以更称不上是受委托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判断孙某是否属于单位工作人员,可以从形式上和实质上两方面来判断。从形式上看,孙某并没有与市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从实质上看,孙某也没有因履行特定的工作任务而承担特定的职责。所以,孙某并不属于市政公司的单位工作人员,在主体上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其次,成立职务侵占罪,除了判断行为主体是否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客观行为是否符合该罪的判断标准也是很重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的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职务,指依据单位的授权、分工指派,依法从事特定的事务。但这里的“管理”、“经营”、“经手”并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经手,应是指对单位财务的支配与控制;或者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所具有的自我决定或者处置单位财物的权力、职权,而不是利用工作机会。若行为人仅仅因为在单位从事某项工作而熟悉了单位的工作环境、地理位置,容易进入作案场所等条件而不是利用了自己职权的便利条件,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就不属于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应以相应的盗窃罪、侵占罪、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孙某的身份并不具有职务性,其只是临时从事开发票的工作,并没有主管、管理和经手单位财物的权力,而只是利用熟悉单位工作环境的便利条件,和任某一起非法占有了本单位的财物。所以,孙某也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司财物的行为,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内容。
综上所述,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的欺骗方法,骗取到数额较大的财物,构成《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因为孙某不具有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也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司财物,所以,犯罪嫌疑人任某、孙某不构成《刑法》第271条的职务侵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