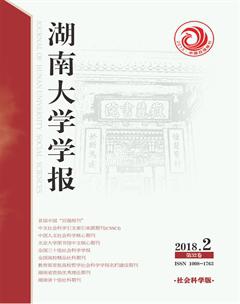论弘赞律学撰述及《鼎湖法汇》之编纂
李福标
[摘要]明清之际广东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弘赞禅师,一生致力于律学的理论研究与普及实践,撰述宏富,成绩可观,地位崇高,影响颇大,至有“岭海之间以得鼎湖戒为重”之美誉,后世被尊为中国戒律的厘定者。他学有渊源,远绍唐南山道宣律师,追踪云栖袜宏,其著述均有单行本流通,后被汇编为《鼎湖法汇》。《鼎湖法汇》之编与成鹫《鼎湖山志》之修相关,为整顿庆云寺道场、提升庆云寺的文化自信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鼎湖戒”的理论基石,《鼎湖法汇》中多种著述在岭南和全国佛教界影响深远。
[关键词]律学;鼎湖法汇;鼎湖戒;鼎湖山志;云栖法汇
明清之际,岭南迎来了禅宗的振兴。其教徒规模之庞大、弘法之热忱,前所未有,可与江南、滇南并称三大法窟。时活跃于岭南者,要之有曹洞宗博山下以道独、函星为领袖的海云系,和以道丘、弘赞为初祖的鼎湖系,两派高僧辈出,龙象蹴踏,佛教著述颇伙,影响甚巨。近人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著录此期释氏文献60余家178种,其中曹洞宗海云系著述38家96种,鼎湖系8家54种,基本反映了当时佛教著述的面目。然清中叶以还,因政治、文化等诸多外缘导致佛教衰落、佛门文献之被轻忽,故遗佚不为冼氏登录者仍有。近二十年学界对海云系文献整理与研究有较大进展,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对鼎湖系文献则未加重视。鼎湖文献一大宗即弘赞撰述,《广东释道著述考》虽已就其大部分予以着录,然未提及弘赞撰述合编《鼎湖法汇》的存在,这就使学界对于弘赞在佛教戒律学上的影响和地位的认识,缺少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故有加以揭橥的必要。
一《鼎湖法汇》简介
《鼎湖法汇》是弘赞禅师著述之总录。
弘赞,字在糁,广东新会朱氏子。崇祯六年(1633)年二十三弃儒而人鼎湖诛茅建庵,并人广州蒲涧寺参博山元来无异下鼎湖栖壑道丘蕹鬟禀戒。先后住英德西来山、南海宝象林,继席庆云寺为二代住持,康熙二十五年(1686)示寂,年七十六。生平勤于笔耕,撰述数十种。
全书分上、中、下三部。上部:《四分律名义标释》四十卷;中部:《四分戒本如释》十二卷、《梵网经略疏》八卷、《沙弥律仪要略增注》、《沙门日用》各二卷、《沙弥学戒仪轨颂并注》、《礼佛仪式》、《式叉摩那戒本》、《比丘尼戒录》、《比丘戒录》、《供诸天科仪》、《礼舍利塔式》各一卷;下部:《解惑编》四卷、《鼎湖山木人居在糁禅师剩稿》、《六道集》各五卷、《准提经会释》、《归戒要集》、《兜率龟镜集》、《观音慈林集》各三卷、《沩山警策句释》二卷、《心经添足》、《受持准提法要》、《八关斋法》各一卷。合二十三种九十九卷。
各种撰述刻印时间不一,刻印地点在西来山、宝象林寺、庆云寺三山之间。后汇印人《嘉兴藏》又续藏,版心上镌“鼎湖法汇”,卷首有《鼎湖法汇》目录一纸。
二弘赞撰述的内容及特点
弘赞作为曹洞宗博山下传人,参禅自是其本分。今传最早的撰述是疏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并旁通他经如《楞严经》、《大悲经》、《法华经》等,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刻成《心经添足》一卷,那时他刚从江南参学返回鼎湖山。
弘赞对小乘戒律《四分律》的研究是从临坛受具足戒开始的,人手即对其中各戒法(个体比丘、比丘尼受持的防非止恶的戒条)及犍度法(僧团仪轨及修行、传教、日常生活的规定)进行选择性标释,称:“赞始临坛,还同昏穴,惟此奋翅三藏,猎目群章,稽彼西天之梵言,释此东华之音义。端取昙无德律所有文句难通者,仅标其名,缵释其义。”“今时初学习律,每以事相为艰,多释卷高阁,故律学渐废,持犯无不昧然,释子要法,而成故典矣。余因观此,惧正法灭无多日,乃举《四分藏》中华、梵文句奥者标而释之。”最初成《四分律名义标释》二十八卷,后续成四十卷。
弘赞对四分戒本的注释工作最为重视,称为“律之首钥”他广泛参阅唐道宣《四分律含注戒本疏》、《新删定四分僧戒本》、定宾《四分比丘戒本疏》、怀素《四分比丘戒本》及宋、明二代高僧四分戒注本,撰为《四分戒本如释》一书。凡例称:因《四分律》六十卷“疏工颇宏,非日能就,欲使初学急知持犯,爰取戒本如律释之”,“中有文句简质,恐初学难顺,乃取翻译本一二字以易明之。然于每戒下附余部律文并诸传论,意欲互相发明旨趣,及补所未备,全非取轻替重,以开易遮。……若欲广明,须阅全藏始得。倘为师范,必要广学精研,乐简厌繁,律教乃有大诃。”弘赞注释选择的底本是怀素本,而所遵循的方法则遥承道宣而来,大量吸收其它诸律之长,引用律典如《观佛三昧经》、《昆昙》、《华严经》、《止观》、《佛说犯戒罪轻重经》、《文殊问经》、《舍利弗问经》等达四五十种之多,广征博引,而不滞于文,重在使律文义理清晰,且兼容大、小乘戒律。旧律藏惟明比丘二百五十戒法,不载诸真言咒语,咒语归之密部。而弘赞因兼擅梵音,对咒语亦录之并加音义,这就使其注本华梵胡言,无不洞贯,超出他本。
以上二书互相发明,且与其它律学著述穿插进行。如《四分戒本如释》卷七“覆屋过三节戒”云:“若比丘,作大房舍,户扉窗牖及余庄饰具,指授覆苫齐二三节。若过,波逸提。”释云:“不应以男女形像文绣庄校堂宇,听用余杂色禽兽文。”小字注:“庄画堂屋,备在《标释》中。”此条即与《四分律名义标释》卷三十四“庄校堂屋”条互见。这两部融会四部、兼通华梵的大撰疏是崇祯十六年(1643)在英德西来山最终完稿并付印的,此时他出世才十年。可见其天赋异禀,起点甚高,经历过一个艰苦的参方绩学过程。
除此二大部之外,弘赞就传教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做了一些专题性的律学疏释。具体有:(一)撰《沙弥律仪要略增注》,针对初学沙弥律仪的不如法,述戒律与威仪;撰《沙弥学戒仪轨颂注》,以沙弥戒经并事师法等文句结为颂,与经、论中以三十二、二十八等字为一颂者不同,而例以二十字为一颂,共百余颂,并述经律之言,更便于初学者唪诵;撰《沙门日用》,乃重订旧本《毗尼日用》,分持诵门、资具门,为初受具足戒、未能即阅大律藏者详细解说僧人之行住坐卧之戒律仪轨;撰《沩山警策句释记》,以禅宗“佛祖三经”之唐灵佑《沩山大圆禅师警策》(另有《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为初学必读,故加疏释以警策沙弥。(二)撰《礼佛仪式》,针对佛门礼拜仪则乖乱不经而不知忏悔发愿回向,就普礼三宝,礼释迦世尊及各菩萨、尊者及五悔法一一作释;撰《供诸天科仪》,主讲二十四诸天位座次序、忏法恒式、设供位次尊卑等;撰《礼舍利塔仪式》,条列香赞、持咒、修供养、赞礼、赞叹旋绕、发愿回向六法,附舍利故事及释义、供斋赞。(三)撰《比丘受戒录》、《比丘尼受戒录》。略序得戒缘由,次录得戒和尚、阿阁黎、临坛尊证僧伽,并记自生年、受戒年月日时,以识戒腊之尊卑,告诫初学尊重师道,叙受戒所应注意的二十余法并作法仪轨。(四)撰《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会释》,为指示杂部密教准提佛母法之本轨,依金刚智本,参以不空本,加以会释,首揭七俱胝佛所说陀罗尼及三十余种咒诅法,次及“十八道立”所成的七俱胝准提陀罗尼念诵仪轨、本尊陀罗尼布字法及种子义,再次是四种护摩法,最后是准提佛母画像法,并附五悔仪并持诵法要;撰持诵准提真言法要》,述持诵仪轨。(五)撰《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下略疏》,针对明末清初大动荡局势下岭南削发为僧者大增,在家居士念佛也极普遍的现象,疏释大乘佛教“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菩萨戒本《梵网经》二卷,尤其是下卷说菩萨戒相部分的《梵网菩萨戒本》,使见之者逐事明理,随理达旨,以身、口、意三方面的戒规(三聚净戒)来约束四众。《梵网经》受戒法虽有在佛、菩萨像前自誓受戒和请受过大乘戒的法师或居士为自己授戒两种,但弘赞反对“自誓受戒”法,可见戒律之精严;撰《式叉摩那尼戒本》,专述大乘律教学法女于二年中具学之根本四事、六法、二百九十二行法诸戒威仪;撰《八关斋法》,详述佛陀为在家清信男、清信女所制定暂时出家之八关斋戒的戒学律仪;撰《归戒要集》,阐述受三归法、五戒法、八戒斋法之仪轨。(六)撰《兜率龟镜集》,为方便信众修持慈宗法门,捡诸经论传记并所见闻之种种事迹,又录“应化垂迹”、“上生内院”故事并“经咒愿文”若干篇以明其义;撰《观音慈林集》,因民间观音信仰渊源久远,信众广泛,感应之迹颇伙,弘赞列藏经中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十一篇之外,在历来录观音感应故事之书的基础上,又采集印度及中国自秦晋至清顺治间感应故事百余则,其中以耳闻目睹的岭南感应故事为多;撰《六道集》,每卷首列诸相关经文并稍加音释,次列天竺、西域及中国自汉晋至清康熙问的天、人、阿修罗、鬼神、畜生、地狱六道故事二百余则,阐明佛教劝善惩恶的六道轮回理论;撰《解惑编》,因解释世问众生疑惑者历来不乏其人,而无专着,故弘赞编录吴太宰嚭以迄于明人物故事百余条,“集大成以寿梓流通于六合寰中,普使人人咸皆属目”。(七)以上撰述之外,又有《木人剩稿》结集,录随机接引四众之法语及往来尺牍、偈颂、诗赞、记铭、序文等。
有学者将弘赞著述归为六类:律学著作、日常行为规范及佛教礼仪的著作、劝善类著作、禅学著作、密宗类著作、开示书信偈颂类汇编等。就人《鼎湖法汇》者观之,显然是以律学为主线而贯通禅、净、密之学的,将其全部纳入律学的大范畴是不会有问题的。其上部固然专是对佛教根本经典四分律进行阐释与弘扬;中部涉及大小乘律学,偏重于实践层面的律法仪式,属于专题性的阐释;下部看似非律学之专门,如《六道集》惩戒杀、妄说等恶行,《观音慈林集》、《兜率龟镜集》向四众倡导净土慈宗之学及其念诵功德与基本仪轨,初读之下似乎律学色彩不浓,其实是以具体人事证明戒律持犯的因果。《木人剩稿》虽为杂录,然亦可考察和尚戒律思想和实践活动。要之其对诸经典之撰述,无论禅、净、密等,均以发扬律学为出发点,并以律学为重心,为结穴,为培植岭南遵戒如律的僧材而设。非从律学角度而从事的著述,如《般若心经贯义》一卷,也人《嘉兴藏》,但不在《鼎湖法汇》之录。即便如此,这部禅学著作仍附录讲明受持仪轨之文。
弘赞各律学撰述,旁征博引各种典籍,且注明材料的来源。如《解惑编》卷上之上“阚泽”条下注:“《广弘明集》并宗炳《明佛论》。”“何尚之”条下注:“出《宋史》。”即使援引故事说理时,要讲明故事的出处,以无征不信为极则。每卷末特设音释一栏,尤是弘赞和尚注疏优长之处,霍宗瑝《第二代在糁和尚传》云:“尤善梵音,会不空三藏、金刚龙树诸家之秘。也最能帮助一般读者,尤其能为岭南在家居士解释疑惑。总观之,弘赞是一个通才,正如《木人剩稿》程化龙序云:“经律禅净,各擅一能,兼善之材,无多屈指。甚矣,得人之难也。东粤何幸,迭产圣僧,向大鉴而下,石头、仰山等辈皆法门角虎、觉苑飞龙,今也则亡,殊堪慨叹。犹喜线传未灭,旋而崛起至人,经律禅净,咸称独步,今见我在犙和尚其人也。”惟其能通,故能提起要領,纲举目张。弘赞著述从文释、理释兼事释等多个方向、多重维度,为四众疏通了艰奥难通的律学,无疑是岭南禅门祖师对戒律学最集中、最深入的一次探求,也是岭南佛门律学的最高成就。
三弘赞撰述活动的背景与渊源
弘赞是曹洞宗博山下无异元来的再传弟子,以岭南禅学正宗的身份,而毕其一生弘扬律学,且在明清之际的大动荡中,在西来山、鼎湖山等偏僻处,取得如此成就,颇不可思议。这其中必有特殊的背景和渊源。而其背景之最迫切者,则是当时禅门律学空气的稀缺。律学虽至唐道宣融通大小乘,弘扬了《四分律》的精义,奠定了中国律统的基础,然律藏本是秘而不宣的,律文既枯燥无味,又讲究字面的逻辑与涵义,繁奥难懂,加之中国所传的大乘佛教各宗派大体以严持戒相为事、为有漏,以开发佛智为理、为究竟,故习律者少之又少。南宋后禅宗一度盛行,律学无人问津,唐宋问诸家律学撰述散失殆尽。至元、明二代,律学几成绝学。特别是明嘉靖至万历间,朝廷为杜绝白莲教等民间宗教活动,期间五十余年禁止讲经、开戒坛,律学更形没落,以至“老师素德终其身焉卷怀不讲”、“后生晚学研习轻华,公行犯戒”。明末佛教僧团人数激增而素质普遍较差,教团弊病丛生。虽朝廷准许戒坛重开,而大多数僧众已不知戒律为何物。鉴于混乱和无知,大德如莲池、藕益、元贤等乃相继而起,掀起一股回归原典、正本清源的思潮,从事于各宗经典的疏述,尤以律宗文献为最急。据释圣严《明末中国的戒律复兴》一文统计,明清之际被收入《卍续藏经》的律学著作就有26种44卷;另从《新续高僧传四集》中所见,尚有21种未被收人《卍续藏经》中,足见此期戒律学的发达。如馨古心律师及其门徒性相、永海、寂光、澄芳等专弘戒法,寂光律师又传弟子香雪、见月二人,他们推波助澜,佛教戒律得以复兴。
在糁弘赞和其师栖壑道丘都有参学江南的经历,又遭岭南禅风大煽之机,故他们特为痛心丛林之浮夸不实,深刻认识到律学的重要性、迫切性,也有能力提倡律仪戒行。尤其是在糁弘赞禅师,他痛念“今之禅者,呵教为如来禅,诋律为声闻学,灭教败律,无所不至”亟思解决之方法。弘赞律学的渊源,可以说是遥承南山道宣,而近师云栖袜宏的。《六道集》为唐道宣律师立传,对其行实叙述甚详,其篇幅亦超过任何一篇,此可反映弘赞对道宣南山律学的尊崇。见月律师有《上庆云方丈书》即称赞云:“南山一宗,湮没多年。间有先德,弘演惟艰。久续可见,道在人弘,有人则兴,失人则废矣。……屡有比来禅衲传闻鼎湖智人,覃精禅教,律愿密弘,读体不胜千里望空歎服也。”有学者指出,明末的弘戒以云栖袜宏与古月如馨为二大系统,而云栖授戒法系正流行于寿昌下博山系。从收入《鼎湖法汇》中的弘赞著述目之,显然受了莲池大师《云栖法汇》法乳之滋养。《云栖法汇》乃莲池大师寂后门人所编,计二十五种(或有二十九种者),包括《禅关策进前集、后集》一卷、《僧训日记》一卷、《缁门崇行录》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略记》一卷、《往生集》三卷、《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五卷附《事义》一卷《问辩》一卷、《具戒便蒙》一卷、《沙弥律仪要略》一卷、《沙弥尼比丘尼戒录要》一卷、《皇明名僧辑略》一卷、《西湖高僧事略》一卷、《自知录》二卷、《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六卷、《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仪》一卷、《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仪补注》一卷、《楞严摸象记》十卷、《正讹集》一卷、《直道录》一卷、《半月诵戒仪式》一卷、《放生仪》一卷、《戒杀放生文》一卷、《云栖大师山房杂录》二卷、《云栖大师遗稿》三卷、《云栖共住规约四集附嘱语、再嘱》、《云栖纪事》一卷附《孝义无碍庵录》一卷、《云栖大师塔铭》一卷附《行略、祭文、偈、颂》一卷。今传嘉兴藏本袜宏撰《半月诵戒仪式》版心刻“云栖法汇”字样,末有“古秀口弟子大胜、孙洪基捐资共五两六钱助锓《云栖大师法汇辑古》中《具戒便蒙》、《沙弥要略》、《诵戒仪式》三种,少报佛祖拯度之垂恩,并志大师维世之遗范末法良猷与愿无敦。崇祯庚辰岁孟夏八日佛诞日谨识。大清雍正甲寅年比丘与川补刊”之刻书小识。从此小识看,崇祯十三年(1640)孙洪基所刻三种书,乃是有选择性的从助刻《云栖大师法汇辑古》一书中的零种,说明《云栖法汇》在崇祯以前即已编辑成书,并刊印流布。
弘赞撰述中多有步武莲池大师之撰述,如《沙弥律仪要略增注》二卷,就是在袜宏所辑《沙弥十戒经》的基础上加以注释的。此书清海幢经坊刻本前心鉴序云:“在昔云栖法师搜经律之秘诠……草堂在参和尚复为增注焉。草堂兼疏通之学,具情洽之才,以发云栖所未发之余。约者广之,微者显之,幽者喻之。采辑精要,重注详明,诚人圣之津梁,后学之旨归者也。”又,《比丘尼受戒录》后特附南山、灵芝、云栖法语十五则。传播于百姓阶层的是净土,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是禅宗,这是中国佛教的普遍趋势。明末袜宏为了挽救轻忽实修、卖弄证悟的禅风,大力提倡净戒合一。弘赞亦着意于此,而从事多种有关在家菩萨戒的著述,《八关斋法》即其一,卷首云:“有二种人:一者不信三世善恶因果,在儒不修五常,宁信如来出世五戒?由是人天路绝,道果无分;二者顽痴无知,不识君臣父子,孝悌忠信,惟知食息,畜生无异,宁晓迁善?是二种人,枉得人身,一生无善可记,肆意非为,一朝业果现前,追悔何及。其有智者,速宜受持。”又尤其关心在家学法女菩萨戒的受持,《式叉摩那尼戒本》自序云:“出家五众,共遵戒法。……而女性闇钝,烦惑偏厚,乃制以六法,令其二年预学大尼一切诸戒威仪,戒体渐成,方听受具。然其所依必以知律大尼为师,但大尼不得向说五篇七聚之名,惟听语令不淫、不盗等诸戒威仪。”而于大乘戒提纲挈领式的著述,即《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下略疏》一书,孙廷铎序赞云:“昔天台智者着《义疏》,以明其宗趣,标其大纲。云栖大师复注《发隐》,以发天台之所未发。今鼎湖在和尚综理《略疏》,又补《发隐》之未尽者,珠珠交映,次第灿然。”从这个角度而言,时人谓弘赞设教“一禀栖和尚与云栖、博山遗教,多以戒律绳束后学”的确不虚。只不过《云栖法汇》偏重于净土宗的弘扬,而弘赞的《鼎湖法汇》更着重于律学的阐释,在律学研究的路上走得更远。
《梵网经》孙廷铎序:“师之教人,言经律则必兼于禅,言禅则必兼于经律。余见今之参禅者,多略于经律,犹如儒者但谈经义而不及躬行也。”其躬行之途即深隐于西来山、鼎湖、宝象林等地,专意著述。《六道集》李龙标序称赞和尚“与其一期说法,度有限之众生;孰若多着要书,利无穷之后学”。然庆云寺、宝象林是弘赞亲手创建的新寺,西来山亦无闻焉。弘赞着书,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在无任何文化积淀的寺院,且交通亦颇不便利,那么供其参考、征引的图书资料和时事见闻如何而来?江南的参学经历固然会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但更多的外缘恐怕是来自于诸方大德、四众弟子的鼎力帮助。故其更为具体而直接的交游背景情况值得深入考察,然限于篇幅,此处姑从略。
四《鼎湖法汇》之编纂汇印及其意义
弘赞甫一完成《四分律名义标释》、《四分戒本如释》即“海内宗之”,其余《比丘受戒录》和《比丘尼受戒录》等为各地传戒时所遵用。后人亦誉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戒律厘定者,无疑是佛教界对其律学研究的肯定。弘赞律学虽放眼整个佛教界,但立足点在岭南,特别专注于鼎湖系禅门。鼎湖庆云寺自道丘开法以来,即兼行博山、云栖之道,禅、净、律三教并举。道丘示寂后,弘赞主庆云,其责任更重,撰述更有目的性、方向性,从其撰述的内容、特点就可明白这一点。弘赞撰述大都有单刻本行世。崇祯末有《四分律》二大部之刻印。人清后,刻印之书有顺治七年(1650)一种,康熙二年(1663)一种,康熙五年(1666)二种,康熙七年(1668)一种,康熙九至十年(1670-1671)四种,康熙十三年(1674)二种,康熙十八年(1679)一种,康熙二十一至二十三年(1682-1684)三种,和尚寂后康熙五十二年(1713)一种。有些撰述多次传刻,如《解惑编》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民国元年(1912)刻本;《六道集》有民国九年(1920)北京刻经处刻本;《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会释》有宣统三年(1911)常州天宁寺重刻本;《沩山警策句释记》有清广州海憧寺经坊本、清杭州昭庆寺经房刻本、同治十年(1871)清莲刻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等;《兜率龟镜集》有宣统三年(1911)常州天寧寺刻本;《沙弥律仪要略增注》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海幢经坊刻本、民国八年(1919)扬州藏经院刻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添足》有民国十九年(1930)释印光刻本。对佛门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其版本分散单行而受阻,反而传播渠道更多、方式更灵活便捷,受众也更多。弘赞撰述多个零种亦人《卍续藏经》、《卍新纂续藏经》、《大正藏》、《中华大藏经》、《中华律藏》等大藏流通。然作为弘赞撰述合集的《鼎湖法汇》,却没有像袜宏《云栖法汇》那样再版过。
每一撰述的出现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受众,说实话,一般情况下并不是特别需要一个合集性的《鼎湖法汇》以供流通,有无此合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并不重要。别的藏经里均无《鼎湖法汇》这一合集,仅在《嘉兴藏》又续藏中见之,这个貌似“孤立”的现象,或许仅仅与鼎湖山庆云寺的寺众和护法居士相关。弘赞撰述的人藏工作,在弘赞生前就已基本完成。《鼎湖山志》卷三《本师在糁和尚行状》称:“前后著述凡百有余卷,板藏浙江嘉兴楞严寺行世。吉旦,弟子开螭、传海、开沩、传调、传意、传懏等和南仝述立石。”又,《鼎湖山志》卷三《第五代空石意和尚塔志铭》称述鼎湖山第五代祖师空石传意禅师的行实云:“未几,随杖人金陵,礼报恩寺阿育王诸塔,设供舍利,营诸胜膳,备极庄严,得大如意,师之力居多。既而归岭南,侍老人尤谨,事无巨细,悉肩任之。时草堂《律部疏注》告成,师奉命送板人嘉兴藏流通。前后跋涉,不辞劳瘁,不致陨越,老人深为嘉叹。”而据霍宗瑝《第二代在糁和尚传》称:“年七十余,犹以未酬宿愿,复往金陵、宁波,礼长干、阿育王二塔,广陈妙供,筛以珍宝。都人环观赞叹,得未曾有。”综合以上信息可知,弘赞在七十岁以后、康熙二十五年(1686)示寂前的二三年,已命法子将其撰述送人嘉兴藏中。然人藏时尚未提及《鼎湖法汇》之名,而模糊地统称“前后著述百有余卷”为“律部疏注”。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让著述“不致陨越”而已,而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心愿,即能像《云栖法汇》那样完整而永久地保存在嘉兴藏中。
然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在嘉兴藏《鼎湖法汇》中有弘赞寂后的康熙五十二年(1712)印本《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会释》。这个印本的出现,或与前后不久鼎湖庆云寺一个较大的文化事件有关,即迹删成鹫人住庆云寺并主持完成《鼎湖山志》之编印。其实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代祖契如和尚就发愿修志,成鹫被请人鼎湖主其事,惜契如翌年圆寂,志稿未成而成鹫离山。十年之后因续前缘,寺志之纂得重新启动。现存《鼎湖山志》书首最早的序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最晚的序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可知弘赞示寂后鼎湖山有连续三次寺志编刻印与补刻印。
成鹫,俗姓方,番禺世家子。年四十一,从鼎湖离幻和尚披剃,继法于硕堂禅师,系憨山大师徒孙。与陶璜、何绛、屈大均、梁佩兰等粤中名士交。为人豪放倜傥,诗文亦如其人,沈德潜誉为诗僧第一。撰《楞严直说》、《鼎湖山志》、《咸陟堂集》、《金刚直说》、《老子直说》、《庄子内篇注》等。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三年(1714)间住持鼎湖庆云寺。成鹫接任住持时,庆云寺已开山七十余年,寺院建设日善,香火日旺,生活也日安逸,常住达数千指,随之僧众矛盾纷争日多,戒律日松弛,成鹫到来不久即遭排挤。庆云寺面临一桩何去何从的公案,要得解决,必借本寺开山祖师法力与外护之助,而纂修《山志》乃其大契机。可见纂修《山志》之举是有一个关乎庆云寺发展命运的背景的。此次修志根本目的在于以祖师开山之传统教育僧众,申明大义。为了不让昔之严谨戒律仪轨因今之安逸而隳败,成鹫订立了《重申祖训约》,又着《僧铎》让寺僧于禅堂、老堂等处时时提唱,以重振戒风。并将其编人山志,形成定制。另者,成鹫还亲自选定鼎湖山“十景”,邀集各方文士賢达览胜观光,唱和题咏。其主观目的是为庆云寺在鼎湖山的清修正名安分,排除外界干扰;客观上也为相传黄帝铸鼎处的鼎湖山增加了新的、实际的文化含量。
如果联系到这一事件,则《鼎湖法汇》的汇印就有了前后因果关系,不再是孤立现象。在《鼎湖山志》修纂前后,尚有释开沩编《鼎湖山庆云寺外集》(版心书名为《鼎湖外集》)之举,可以说三书是相辅而行的。成鹫和庆云寺的这一系列举措,得到官府和护法居士鼎力支持,康熙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修志时,肇高廉罗道丁易冠名修纂并为之作序,云:“正法方兴,群邪侧目。有盗常住一杯土者,惧其不利于己也,合众口以烁金。”又孙毓砼《序》云:“(成鹫)时为群犬所吠,予奉上命,力为驱除。自后鼎湖一席,无复有窥窃常住之人。”康熙五十六年《鼎湖山志》补刻时,两广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赵弘灿、兵部左侍郎陈元龙、高凉守吴柯、端州守宋志益为撰序,可见动用资源之多、反响之大,也达到了预期目的。《志》前孙毓玜序云:“(宪府丁公)乃取山中旧本,亲为总裁,三月告竣……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予于斯《志》亦云。”成鹫刻意向世人昭示庆云寺一代祖栖壑道丘、二代祖在糁弘赞与云栖大师的渊源关系,无非是突出庆云寺律学、鼎湖戒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藉以增强其文化自信力,一方面也可加大整肃丛林的力度。尽管弘赞生前“岭海之问,以得鼎湖戒为重”,然其地位在岭南佛门的巩固不移,鼎湖诸祖重视戒律的研究与实践作为传统历代延续,是与《鼎湖山志》之宣扬密不可分的。煌煌百余卷的《鼎湖法汇》,作为《鼎湖山志》强大的背景支撑,无疑是“鼎湖戒”的律学基石,岭南佛教界的理论标帜,隐隐与杭州云栖袜宏《云栖法汇》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