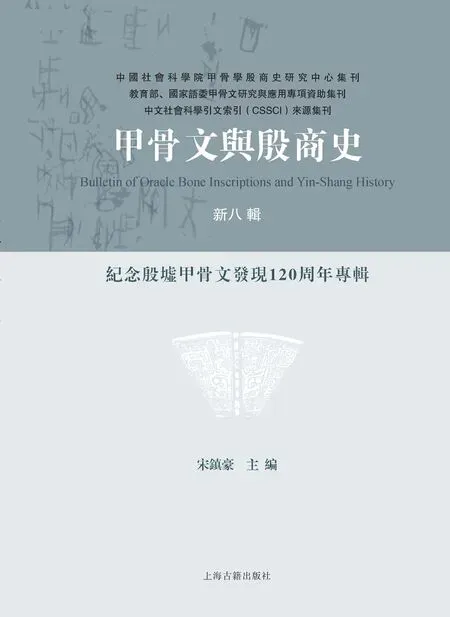鄉飲酒禮源流考
晏 青
(山東大學儒學院)
鄉飲酒禮是一種特殊的飲酒儀式,其儀節與禮義區别於通常的燕饗禮。有關鄉飲酒禮的記載,主要見於《儀禮·鄉飲酒禮》、《禮記·鄉飲酒義》等先秦典籍。傳統觀點認爲,鄉飲酒禮是由鄉大夫主持的飲酒儀式,目的在於考察賢能或敬養老人。前人研究鄉飲酒禮,多側重其儀節與禮義,很少論及其起源。直到近代,學界對其起源問題的討論才多了起來。很多學者認爲,此禮起源於原始的聚落會飲,(1)很多學者都認爲鄉飲酒禮起源於聚落會飲,如楊寬《西周史》、馮天瑜《中華文化辭典》、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等。應當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此禮是怎樣發展至周代的鄉飲酒禮儀式呢?學界對這一發展脉絡尚缺乏有關的梳理。其實,若能釐清這一問題,那麽一直以來關於鄉飲酒禮的一些争論,比如種類、禮義等,都將很容易得到解决。筆者藉助甲骨文與金文中的可靠資料,對鄉飲酒禮進行了相關的文獻梳理,試圖釐清商、周間此禮的發展脉絡。目前,禮學研究在學界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已呈現明顯的復興之勢。藉助鄉飲酒禮來研究周禮的發展演變,也可以給學界提供新的思路。
一、 對鄉飲酒禮起源的傳統認識
在傳世文獻中,尚未發現專門針對鄉飲酒禮起源的討論。前人多把周禮看作一個整體,進而研究其起源。在此問題上,前人争論較多,主要有周公製禮説、托名周公説、周因殷禮説等。
周公製禮説,屢見於先秦兩漢典籍,如《禮記·明堂位》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左傳·文公十八年》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 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其他如《逸周書·明堂解》、《史記·周本紀》、《國語》、《尚書大傳》等也有記載,不再遍舉。周公製禮的説法,爲後世多數儒者所推崇。清代胡培翬《儀禮正義》、陳澧《東塾讀書記·禮記》、邵懿辰《禮經通論·論孔子定禮樂》等著作中也都提到了周禮爲周公所製作。周公製禮,這一説法寄托着後世儒者的理想。他們把周公看作聖人,既有平定天下之武功,又有製禮作樂之文治,並且輔政成王,流傳千秋美名。在儒者的眼裏,只有周公這樣的聖人,才具備製禮作樂的眼光與韜略,就如只有孔子才能够删訂六經一般。這一説法,自先秦至清代,一直備受推崇。但是很明顯,這種説法的缺點是太浮於表面,没有深究歷史事實,故而後代不少學者都懷疑它的真實性。
托名周公説,是對“周公制禮”説的一種反駁。一些學者認爲,周禮這樣宏大的體系,絶非一人一時所能完成,當爲幾代禮官合力所製,然後托名於周公。如朱熹認爲,《周禮》一書“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朱子語類》卷八十六)。又楊華先生《先秦禮樂文化》一書,談到周公制禮時認爲:“周代前期的‘製禮作樂’應該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西周前期的周公、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幾代統治集團都有創制之功。……後代儒家崇拜周制,‘法憲文武’,把‘制禮作樂’的締造之功托附於周公旦一人身上,顯然有悖於歷史。”(2)楊華: 《先秦禮樂文化》,長沙: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頁68。楊華先生亦認爲周禮經過了數代禮官的完善,然後托名於周公。近代以來,由於疑古學風的盛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懷疑周公製禮的真實性,開始考證周禮産生的歷史事實,在此不再備舉。
周因殷禮説,是當今較爲流行的一種觀點。孔子曾説:“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即已意識到周禮當是藉鑒殷禮而成。《尚書·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孔穎達正義:“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3)《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北京: 中華書局1980年版,頁214。孔穎達也認爲周禮從殷禮損益而來。從甲骨卜辭等文獻可知,殷商時期禮儀已經具備一定的規模,祭禮、喪禮等皆成系統。周朝建立以後,統治階層製作了一整套分封制、宗法制、婚姻制系統,使周部族的影響力遍布全國,有效地控制了殷商舊地及其他部族領域。所謂的周公製禮作樂,就是在殷禮的基礎上增改損益,使之適應周初的政治環境,服務於分封制、宗法制、婚姻制系統。顧頡剛先生對“周公制禮”與“周因殷禮”兩説進行了比較,説道:
“周公製禮”,這件事是應該肯定的,因爲在開國的時候哪能不定出許多制度和儀節來;周公是那時的行政首長,就是政府部門的共同工作也得歸功於他。即使他采用殷禮,也必然經過一番選擇,不會無條件地接受,所以孔子説:“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爲政》)即然有損有益,就必定有創造的成分在内,所以未嘗不可説是周公所製。不過一件事情經過了長期的傳説,往往變成了過分地誇大。周公製禮這件事常説在人們的口頭,就好像周代的一切制度和儀節都由他一手訂定,而周公所定的禮則是最高超的,因此在三千年來的封建社會裏,只有小修政而無大變化,甚至説男女婚姻制度也是由他所創立,那顯然違反了歷史的真實。(4)顧頡剛: 《“周公制禮”的傳説和〈周禮〉一書的出現》,《文史》1979年第6輯,頁4。
顧先生實際上是糅合了這兩種説法。他認爲,周公作爲周王朝的主要行政首長,領導着周人對殷禮進行損益改革,那麽後人把“製禮作樂”的美名歸屬於他,也未嘗不可。不過我們要辯證地看待這一個問題。“製禮作樂”是一項政治工程,規模龐大,其内容涵蓋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周公作爲領導者,可以提出總的决策,甚至可以親自修訂某些重要的禮儀,但要説每種禮儀制度都由他一手訂定,則有違事實。從顧先生這段話可以理解,周公製禮這種説法,其實是浮於表面的一種説辭。在這種表面説法之下,隱藏着的是“周因殷禮”這一事實。作爲對前述兩種觀點的補充與發展,“周因殷禮”這一説法明顯更爲合理,更能科學地解釋周禮何以在短時間内形成。
周禮形成於周初,然後經幾代人努力逐漸完善,此觀點應比較接近史實。周禮的完善應當在西周中期以後。到了春秋時期,《儀禮》逐漸成書,我們才得以瞭解周禮的具體内容。也就是説,到了《儀禮》的成書,《鄉飲酒禮》成爲固定的篇章,我們才可以確定鄉飲酒禮最終定型。關於《儀禮》的成書問題,由於這牽扯到鄉飲酒禮的最終定型時間,所以在此需要加以説明。現今學術界比較認同的觀點是,《儀禮》成書於春秋末期。沈文倬先生在《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一文中指出:
《儀禮》書本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的撰作年代,其上限是魯哀公末年魯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際;其下限是魯共公十年前後,即周烈王、顯王之際。它是公元前五世紀中期到四世紀中期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後學陸續撰作的。(5)沈文倬: 《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54。
沈先生通過文獻所得出的考證結果,與考古發現得出的結論不謀而合。國家博物館馮峰先生的《從出土器物看〈儀禮〉的成書時代》一文,通過對出土器物中的敦、甒、壺的使用年代進行考察,判斷出《儀禮》的某些篇章産生於春秋中期以後、戰國晚期以前。(6)馮峰: 《從出土器物看〈儀禮〉的成書時代》,《海岱學刊》2014年第1期,頁189。王輝先生的《從考古與古文字的角度看〈儀禮〉的成書年代》一文,從禮制、職官、器物、詞語、用字特點等角度對《儀禮》的成書年代進行考證,得出的結論是:“《儀禮》應成書於春秋以後、戰國中期以前。”(7)王輝: 《從考古與古文字的角度看〈儀禮〉的成書年代》,《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頁54。結合以上比較科學的結論,我們可以大致斷定,《儀禮》的成書時代就是春秋晚期左右,鄉飲酒禮在那時已經最終定型。
基於以上信息,並藉助甲骨文與金文資料,我們將對鄉飲酒禮的形成與演變作進一步的研究。《儀禮》記録的是春秋晚期的鄉飲酒禮,與西周時期的鄉飲酒禮相比已有所不同。至於殷商時期是否有鄉飲酒禮,目前還是學界尚未確認的一個問題。筆者查閲甲骨文與金文文獻,發現了一些有關鄉飲酒禮演變的材料,現加以介紹。
二、 從甲骨文中“鄉”字看最初的對飲

“鄉”字在甲骨卜辭中主要有三種用法: 一是饗祀先祖,如“庚子王饗于祖辛(文293)”;二是宴饗,如“甲寅卜彭貞其饗多子(甲2734)”;三是向背之向,如“……于西方東鄉(粹1252)”。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把“鄉”的字義解釋爲:
從卯從皂,皂爲食器,象二人相向共食之形,爲饗之初字。饗、鄉(後起字爲向)、卿初爲一字,蓋宴饗之時須相向食器而坐,故得引申爲鄉,更以陪君王共饗之人分化爲卿。《説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已非初義。(8)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成都: 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頁1014。
結合用法來看,“鄉”的本義應當爲兩人相對共食。後來,逐漸延伸出宴饗、饗祀之義,又可藉用爲“向背”之“向”。爲區分不同字義用法,人們製造出新的字形,用“饗”字表示宴饗、饗祀之義,用“向”字表示面向之義。又分化出“卿”字,表示與君王相對共食之人,即周人所稱“六卿”。六卿各治天子畿内一域,其所治之域因其名而作“鄉”。蓋天子六鄉,由此而來。鄉作爲行政單位出現,當與“卿”這一官職有着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商代甲骨文與金文中已有“卿史”或者“卿事”出現,即所謂卿士,李學勤《論卿事寮、太史寮》一文已有論述。不過,甲骨卜辭與商代金文中尚未發現“鄉”作爲行政單位的用例。或許,商代並没有出現由卿大夫統領的鄉。這一制度,到了西周,隨着禮制的發展才得以産生。
從卜辭可以看到,商代的饗禮已經十分發達。而鄉飲酒禮,極有可能就是從這種饗宴儀式分化而來。饗禮的最初形態,如甲骨文“鄉”字所呈現的那樣,是兩個人對飲。兩人對飲進一步擴大,就發展爲聚落會飲。到商代時,已經出現了由君王主導的大型饗宴。饗宴的對象很多,有王婦、臣僚、戚屬、邊地諸侯、方國君長等;饗宴的場所也多種多樣,有大室、祊西、北宗、宗、庭、召庭、召大庭、射宫等。(9)宋鎮豪: 《夏商社會生活史》,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488。饗禮又可稱作飲,如聽簋銘文曰:“辛巳,王飲多亞,聽亯京麗。”(10)《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卷三,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頁218。饗與飲,其區别大概在於,饗宴重食,飲宴重酒。酒又分多種,有通常所説的糧食白酒,也有醴酒、鬯酒等。這充分説明了飲酒在商人的饗宴當中占到了很大比重。
在《尚書》等先秦文獻的記載中,殷商諸王十分勤政,並不好酒。《酒誥》曰:“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可見商王飲酒十分節制,並無濫觴之飲。只是到了殷紂王時期,隨着王政崩壞,才出現了奢靡的飲酒風氣。周人代商之後,一改商末好飲之風,嚴令禁止濫飲,《酒誥》就記載了周人對濫飲行爲的處罰準則。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周初統治者極有可能進一步規範飲酒禮儀,從而促進了鄉飲酒禮的成型。周人在飲酒儀式上的改變,我們可從金文中窺見端倪。如果説商代的鄉飲酒禮還只是處於萌芽階段,那麽西周就是鄉飲酒禮逐步成型的時期。這時期出現了鄉飲酒禮的雛形——“鄉酉”。從西周前期的“鄉酉”到中後期的“鄉飲酉”,再到《儀禮》中的鄉飲酒禮,或許就是鄉飲酒禮發展的清晰脉絡。
三、 甲骨文與金文中的“鄉酉”、“鄉飲酉”
有幾件晚商銅器,銘文中出現了“王鄉酉”這一儀式。一是“尹光鼎”,又名“乙亥父丁鼎”:

再看西周銘文,也多次出現“鄉酉”、“鄉醴”。周穆王時製作的“遹簋”,其銘文曰:
西周中期“師遽方彝”:
隹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寢鄉醴,師遽、蔑曆侑王。(16)《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卷六,頁22。
西周中期“大鼎”:
以上兩處銘文,都是獨立舉行飲酒禮的情况。無論“鄉酉”或是“鄉醴”,都已經是非常隆重的飲酒儀式,否則受賜者不會把所得的“貝”製造成禮器,讓後代世世流傳下去。飲酒的目的,或是慶祝祭祀、田獵等活動的成功舉辦,或是單純的舉行飲酒宴會。從時間跨度看,這種儀式在殷商晚期就已經存在,一直延續到了西周中期。這幾百年間是否演變出了《儀禮》中的鄉飲酒禮呢?西周早期的“天君簋”給了我們很大啓示:
與其他銘文僅稱“鄉酉”不同,天君簋的銘文當中稱作“鄉飲酉”,其含義爲“鄉以飲酒之禮”。這種變化值得格外關注。説明在西周早期到中期這段期間,“鄉酉”也可以稱作“鄉飲酉”。總體看來,“鄉酉”是比較流行的名稱,“鄉飲酉”是極少情况下出現的。
綜上似乎可以發現,“鄉酉”這一儀式呈現這樣一種發展脉絡: 起初,在祭祀或田獵等大型活動之後,商王爲了賞賜有功人員,舉辦專門的飲酒儀式;到了周代,不確定是在哪一時期,周王開始舉行獨立的飲酒儀式,使之不再依附於祭祀或田獵等活動;而名稱方面,或稱“鄉酉”,或稱“鄉飲酉”。這種由商王或周王舉辦、由卿士侑王的飲酒活動,就是鄉飲酒禮的雛形。《儀禮·鄉飲酒禮》中已經很難找到這一儀式痕迹。相比較而言,《大射儀》中的飲酒儀式倒是與此更類似。《大射儀》中,周天子或諸侯國君爲主人,大射正爲儐以佐禮,大夫爲賓。又天子祭祖,諸侯佐禮,如《詩經·周頌·雍》所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即銘文中“侑王”之類也。也可以説,鄉飲酒禮是從“鄉飲酉”進化而來。鄉飲酉本是周天子的儀式,後來由於某種原因,此禮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廣,延及到了諸侯或大夫階層。又經過了百年至數百年的演化,到了春秋時期,終於有了我們所熟知的鄉飲酒禮。而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就是周代鄉遂制度的建立。
四、 從鄉遂制度看鄉飲酒禮的定型
關於鄉遂制度的起源,楊寬與于省吾兩位先生曾有過專門的討論。在楊寬先生《論西周金文中六八和鄉遂制度的關係》與于省吾先生《關於〈論西周金文中六八和鄉遂制度的關係〉一文的意見》兩文中,兩位前輩對鄉遂制度是否起源於西周初年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楊寬先生認定鄉遂制度起源於西周初年,《周禮》中所體現的鄉遂制度還保留有西周時期的特點。(19)楊寬: 《論西周金文中六八和鄉遂制度的關係》,《文史》1964年第8輯,頁414。于先生針對楊寬先生文中的幾個主要觀點一一做了反駁。楊寬先生認爲《尚書·費誓》中的“魯人三郊三遂”可證明西周初年即設有鄉遂制度,于省吾先生則認爲《費誓》爲春秋魯僖公時所作,記載的是春秋之事;楊寬先生把《國語·齊語》管仲設立“十五士鄉”看作是齊國保留了西周時的鄉遂制度,于省吾先生則認爲“叄其國而伍其鄙”是管仲所創立的新制度,只能説明春秋早期齊國已經有了鄉遂制度。于先生認爲:“在已經出土的幾千件青銅器銘文中,雖然有不少處敘及軍隊、土地、人民、奴隸之事,然而從没有一處以‘卿’或‘’用作《周禮》‘六鄉’之‘鄉’或‘六遂’之‘遂’。這是鄉遂制度不起於西周時代的一個有力的證明。”又:“以上所引《尚書》四篇以及其他《尚書》中屬於周初的篇章,都找不到鄉遂制度的迹象,這又是周代初期没有鄉遂制度的一個證明。”(20)于省吾: 《關於〈西周金文中六八和鄉遂制度的關係〉一文的意見》,《考古》1965年第3期,頁131。于省吾先生總的觀點就是鄉遂制度起源於春秋時期。從于文中列舉的種種例證來看,于省吾先生的觀點更爲合理,鄉遂制度應當起源於春秋時期。
不過,隨後的考古發現更新了我們對該問題的認識。1986年發掘出土的“史密簋”銘文中,出現了“遂人”一詞,讓我們對于省吾先生的觀點産生了懷疑。銘文内容如下:
據考古測定,史密簋爲西周中期器,銘文中的“王”當爲懿王。大意爲,周懿王命師俗、史密會合各諸侯國東征,齊師、族徒、遂人負責完善城池;師俗、史密各自率軍分路進攻長必,獲俘百人。這裏的遂人,史學家們一致認爲即《周禮·地官》中的“遂人”一職。“遂”這一行政單位的出現,預示着鄉遂制度極有可能已經産生。如果西周中期也有“鄉”,那麽就應當出現了由鄉大夫發起的鄉飲酒禮。由周王發起的“鄉酉”與由鄉大夫發起的“鄉飲酒”,是鄉飲酒禮發展的兩個重要階段。要實現這兩個階段的跨越,“鄉”的出現是重要條件。
關於“鄉”的出現時間,學界尚無明確的結論。據楊寬《西周史》,鄉的來源很是古老,“大概周族處於氏族制時期已經用‘鄉’這個稱呼了,是用來指自己那些共同飲食的氏族聚落的”。(22)楊寬: 《西周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頁750。不過,這一説法缺少足够的證據來證實。甲骨文中不見“鄉”作爲行政單位來使用,那麽極有可能殷商時期尚無“鄉”的稱謂。即使在西周金文中,也没有“鄉”的這種用法。只是,史密簋銘文中的“遂人”,讓我們有理由推測,鄉遂制度大概産生於西周中期。在新的證據出現之前,我們暫且支持這種説法。
至於鄉遂制度的具體模式,《周禮》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周禮·地官·遂人》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簡單來説,鄉就是國都及城郊區域,遂就是郊外村野區域。這是一套比較完整的行政體系。楊寬先生在《古史新探》中對鄉遂制度進行了十分詳細的解釋:
《周禮》把周天子直接統治的王畿,劃分爲“國”與“野”兩大區域,對整個王畿的經營布置,稱爲“體國經野”。在這“國”與“野”兩大區域中,“郊”是個分界綫。郊以内是“國中及四郊”,“郊”以外即是“野”……在“國”以外和“郊”以内,分設有“六鄉”……以王城爲中心,連同四郊六鄉在内,可以總稱爲“國”。在“郊”以外,有相當距離的周圍地區叫“野”。在“郊”以外和“野”以内,分設有“六遂”,這就是鄉遂制度的“遂”。此外,卿大夫的采邑稱爲“都鄙”……大體説來,王城連同四郊六鄉,可以合稱爲“國”;六遂及都鄙等地,可以合稱爲“野”。(23)楊寬: 《古史新探》,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版,頁135、136。
據上,鄉是設立在國都及其周圍的行政區域,遂是設立在距離國都較遠地區的行政區域。鄉遂制度的出現,對鄉飲酒禮的最終定型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儀禮》中鄉飲酒禮的發起者爲鄉大夫,而鄉大夫的設立自當源起於鄉的設立。鄉大夫設立之前,只有天子“鄉酉”;鄉大夫設立之後,或出於天子的授權,或是其他原因,鄉大夫逐漸舉辦了更多的鄉飲儀式。久而久之,天子之“鄉酉”,發展成爲燕禮,即《儀禮·燕禮》所載;鄉大夫之鄉酉,發展爲鄉飲酒禮。
五、 結 語
至此,可以得出結論: 鄉飲酒禮名稱中的“鄉”,其起始意義並非“鄉遂”之“鄉”,而是“饗燕”之“饗”。最初的“王鄉酉”擴展到鄉大夫階層以後,鄉大夫得以定時舉辦“鄉酉”儀式。或許經歷幾世之後,流傳既久,此儀式之名逐漸定型,便被史官們稱之曰“鄉飲酒禮”,而約定其主人爲鄉大夫。名稱之中的“鄉”字,其原始意義“饗”已被忽略,而據其主人鄉大夫之稱,改爲鄉遂、鄉黨之“鄉”。從金文判定,西周中期只有“王鄉酉”,不見其他公、侯有行此禮。若諸侯國君以鄉酉儀式賞賜某臣,亦當有鑄器紀念的可能,而金文中絶無此類例證,或可説明此時的鄉酒禮只限於周王。那麽鄉大夫舉辦鄉飲酒禮,當發生於西周中期以後。由西周中期至春秋末期,在這大約四百年間,鄉飲酒逐漸演變成爲鄉大夫必須履行的職責。在孔子生活的時代,鄉飲酒禮之“鄉”,已經不再具有“饗”義,而只是“鄉遂”、“鄉黨”之“鄉”。鄉大夫的這一職責,也被記録在了《周禮》當中。《周禮·地官·鄉大夫》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此禮賓之事,即鄉飲酒也。”
自清代以來,禮學研究一直以考據學方法爲主,所運用的材料集中於傳統文獻與傳世器物。其所用之文獻,遍及諸經、子、史之類,不局限於三禮;所用之器物,如器皿、兵戈、服飾等,多用來輔證文獻所載之禮制。直到甲骨文被發現,禮學研究才出現了一次大的變革。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即利用出土文獻與器物來補正傳世文獻的内容,引起了學界的强烈共鳴。此後,甲骨文與金文的釋讀成爲了禮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點。尤其是近些年來,以甲骨文與金文内容爲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越來越多,取得的成果越來越大。如浙江大學的賈海生先生,多藉用鐘鼎銘文考證周禮,其《周代禮樂文明實證》一書,利用考古學、歷史學的最新成果,運用實證的方法,對周代禮樂文明進行復原式的研究,成果卓著。又如吉林大學等金文研究重鎮,近年也多有以金文補證禮制的佳作問世,如張秀華《西周金文六種禮制研究》、張亮《周代聘禮研究》等。總的來説,以甲骨文、金文補證禮學已經是非常流行的研究方法。但是,甲骨文與金文的研究仍有很大提升空間。首先,已經識讀的甲骨文與金文數量仍然十分有限。如甲骨文已發現三千餘字,可識讀者僅一千七百餘。其次,在已經識讀的甲骨文與金文中,仍有許多的禮學信息還没有被學界發現並加以利用。甲骨文與金文包含祭祀禮、軍禮、射禮、聘禮、飲食禮等各種禮學信息,但目前學界的研究還比較零散,多以某一件器物的銘文爲研究對象,藉以輔證某一種禮儀的研究。也就是説,其研究仍然集中在“點”,未能延伸及“面”。若能從整體上把握甲骨文與金文中所包含的信息,然後用歷史的視角去研究禮,那麽禮學研究必將會取得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