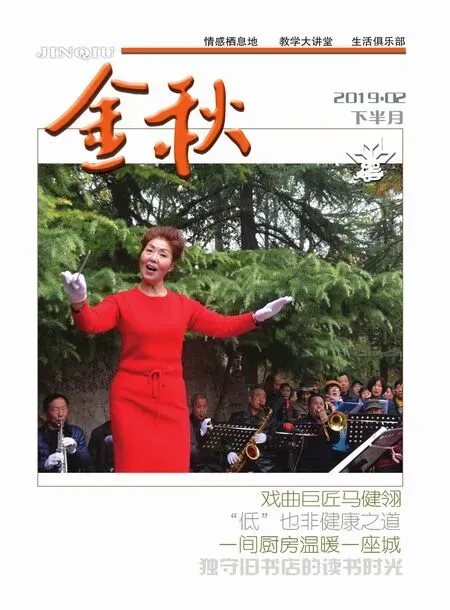父亲的城里生活
◎文/马超和
女儿到了上学年龄,妻子在乡间中学工作,而我工作头绪多,女儿的接送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母亲去乌鲁木齐给弟弟带小孩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央求父亲外包土地、出卖牛羊,把各色家什收拾到屋子里锁了起来,进城帮我照管女儿。
尽管父亲对他的离乡进城早有预料,也做过些规划,可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无所适从。我知道,父亲是极不愿意进城的,即便一段时间以来,他在乡里过的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孤寂生活,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在乡下,父亲是一家之主,熟门熟路,任意东西。在城里,父亲则处于从属地位,大事小情,没有太多话语权,左邻右舍,面孔陌生,感情疏离。再者,父亲舍不得丢弃土地,他觉得,他身体尚且强健,种几亩地没什么问题,自个儿种,自个儿收,攒几个钱,花起来洒脱。
我的工作负担重,常常加班,没有太多时间陪父亲,只能给他足够的零花钱,让他在接送女儿之外的时间想逛哪儿逛哪儿,想吃什么吃什么。因为是临时租住的房子,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搬离,我们没有开通有线电视。闲来无事,父亲就翻看书架上我的书籍。看时间久了,眼睛自然承受不住,就到小区里转悠。父亲也是个比较开朗的人,他很快与小区的老人们熟悉了起来。午后,他们聚在一起晒太阳、聊天、打牌、下棋。老人们在一处通常会聊一些关于孝道的事儿,就像小媳妇们待在一处细数公公婆婆的不是一般。老人们笃守“家丑不可外扬”,自然不会讲自家的事儿,便贩卖些道听途说的信息,尽管听起来有鼻子有眼的。老人们中间也会流传一些“小道消息”,满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的成分。我下班回来,父亲总是瞅空儿向我求证。我叮嘱他,这些事儿,听一听,乐一乐,也就算了,不要人云亦云。
父亲有时也到街上转悠。他喜欢在街边收购古物的摊点前驻足,久而久之,也有了一定的积累,谈起收藏一套一套的。听人说,很多无所事事的老人抱着为儿孙积财攒富的心理涉足其中,往往被骗得惨不忍睹。我不得不经常嘱咐父亲,那水深着呢,听听看看就行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忍不住买了只所谓的银碗回来。瞅着他惶恐和失落的表情,我开口安慰:既然买了,就保存着吧——过他个三五十年,谁能说它不是一只古董呢!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下班回到家,父亲早已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并做好了饭。以前,没怎么见父亲下过厨房,家里来了客人,都是母亲忙里忙外。原来父亲深藏不露,一旦出手,无论是花式还是味道,都不含糊,丝毫不比哪一个巧妇逊色——父亲这辈子没有机会上得厅堂,却有进得厨房的绝对实力。居家过日子,我不怎么做饭,但我知道,做饭的男人通常厌烦和面,于是,我叮嘱他,不想和面了就去压面店买点,可他却总是嫌那样不划算,没有自己动手来的实惠。
父亲老是嫌城里的菜价贵,他总是讲,若在乡下,无论在哪个犄角旮旯撒一把菜籽,就不愁没菜吃了,哪像在城里,即便是喝口凉水,也是要钱的。每当此时,我只能笑笑,说寸土寸金的城市自然不能跟天高地阔的乡村比,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但我着实错了:那种朴素的消费观念是深植在骨子里的,怎会轻易改变?
我和妻子不想给孩子太多压力,不想让她过早地陷入社会竞争,都主张满足孩子玩的天性,给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童年。一次,父亲参加幼儿园组织的开放日活动,女儿因为表现欠佳,被老师点名“批评”,父亲受了些许刺激,回来后,就张罗着让女儿数数、认字。想来父亲方法得当,女儿倒也兴致勃勃,不到十天,就能熟练数数,会写会认近三十个简单的汉字。父亲说,教育孩子需要耐心,要允许孩子的低效与反复,不能动不动暴跳如雷,狠声厉色。想想觉得委屈,我上学那会儿他怎就没有这般“觉悟”呢!
女儿年纪不大,脾气不小,吃饭、穿衣时常常犯拧,我免不了训斥几句,父亲总觉得不入耳——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家长里短的纠纷很难辨识谁是谁非。爱孩子在心里,爱老人在脸上。有时,我因为工作上的不如意,回家时也虎着脸。父亲察言观色,也跟着忐忑,言行举止小心翼翼,一如我小时候他不高兴时。所以,下班回家,我总要站在门口理一理情绪,尽量不把工作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带进家门。
周末,我们总是要睡会儿懒觉。对此,父亲很是看不惯,常常在妻子上班不在家时训教我。起先,我不遗余力地加以解释,说平时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周末自然要多睡会儿。后来慢慢发现,这关系着两代人不同的生活理念,不容易调和,于是,静静地听,狠狠地点头,保证尽量改正。
尽管可以跟老人们打打牌,聊聊天,可以四处逛逛,可哪有在乡下同那帮老哥儿弟兄聊聊天、打打牌的闲适快意。给伯父们打电话时,父亲对村里新近发生的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事无巨细地询问,然后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如果乡下有事需要回去处理,父亲总是显得很高兴,那神情,平时很少见到。有时,他也会找寻借口回去小住几天。在乡下,他东家走走,西家转转,唠唠家长里短,吐吐喜怒哀乐,日子短促而快意。回来以后,总是兴致勃勃地讲村里新近发生的事——我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人”,自然十分乐意听。
父亲原本是戒了烟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吸上了,晚上睡不着,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早起来,屋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因为怕我数落,在我面前躲躲闪闪的,那举止,一如小时候做了错事的我。我看着不落忍,只好松口:吸就吸吧,尽量少吸点,毕竟快六十的人了。
看他闷闷不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主张让他去乌鲁木齐,我想,跟老妈待在一处,或许就没那么单调与无聊了。没成想,他在乌鲁木齐待了不到三个月,就吵嚷着要回来,说在那里,别人说话听不懂,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懂,还不得憋出病来?
回就回来吧!不久以后,妻子通过选调考试进城工作,我旋即归还了父亲的“自由”。我知道,我的父辈是最忠诚于乡村的,他们将乡土气纳归到自己的骨子里,不离不弃。他们的根在乡村,他们的魂亦在乡村。他们为子女贡献了光和热,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在自己熟悉的村落里坚守平淡的日子,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