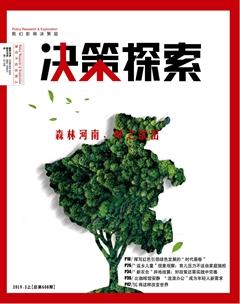彭希哲:人口不是个小问题
夏斌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数量比2017年减少200万,为近10年来新低。这一趋势,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挑战?面对“养老”和“养小”的压力,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对此,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希哲带来他的看法。
要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
问:2001年起,您就参与起草调整生育政策的集体建议书。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最终是怎样促成“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
彭希哲: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并提到未来可能出现的老龄化等问题。公开信中明确表示: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就着手研究人口政策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人口统计模型、统计方法都开始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些调查原始数据之间存在偏差。对人口数据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口政策调整的“举棋不定”。记得在讨论“单独二孩”怎么放的时候,有一个方案是说,让10个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省市,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东北三省以及四川等先行试点。但“低生育水平”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是否准确,一直面临争议。
到2014年年底,人口政策调整的紧迫性愈发明显。因为老龄化加速的程度比想象中快,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到达顶峰并开始下降。在此前两次建议书的基础上,包括我在内的39位人口学者于2014年年底联合发出“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限制的建议”,最终获得了中央重视。
问:“不愿生、不敢养”的现象依然存在,是否还应出台其他鼓励措施?
彭希哲:我们做过很多调研,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生孩子?结果表明,最主要的原因包括:一是经济上的压力,包括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二是照料上的压力,周围没有好的幼儿园,尤其是没有托儿所;三是担心生育会影响妇女的自身发展。
现在的生育主体多是“80后”“90后”,这两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加快,他们的就业、生存压力大大增加,同时,养育子女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没有公共服务的介入,可能生二孩真的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比如,是不是可以配套完善针对0~3岁幼儿的托幼服务设施?又如,是否可以让男性和女性共享产假,从而让男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对子女的养育?
就政策方面而言,我认为下一步的调整重点应该放在全面减少生育限制上,要确立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的目标导向,推行“有计划的自主生育”和“有责任的家庭养育”的政策立场,以平衡人民的生育权利和义务,尽可能实现《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设定的人口发展目标。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望收获新的人口红利
问:日前,有研究机构称,我国将在2027年提前出现“人口负增长”。对此您怎么看?
彭希哲:人口学中有一个基本规律:如果平均一对夫妇生小孩数低于2.1,总人口在一定时期后肯定要减少。按照现有的趋势,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趋于下降。但只要不是所谓“断崖式”或“雪崩式”的下跌,这种“人口负增长”并不可怕。
问:“人口负增长”是不是意味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彭希哲:我们讲人口红利,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机会窗口。当某一个年份,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超过2/3,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窗口打开了。但是,如果大量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不能创造经济财富,“数量”自然就不会转换为“红利”。
从宏观数据来看,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未来20年将稳定在9亿以上。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正在下降,对高端劳动力需求则在逐步上升。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将推动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
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各地区延长人口红利窗口的开启时期。同时,全球范围内还有很大比重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力的增强,若能利用好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一带一路”等重大契机,中国将可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收获新的人口红利。
问:要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延迟退休是不是一个“选项”?
彭希哲:延迟退休不仅是趋势,而且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一方面,它不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或发展。事实上,老年人最主要的财富是职场、人生经验以及社会资本,年轻人最主要的财富在于新的知识和创新能力,二者的“用武之地”是有差别的。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还会给社会减轻负担。我们现在的养老金制度,是正在工作的人交钱来养活退休的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有助于切实降低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
“传统”和“未来”,互相磨合、互相补充
问:过去两年,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实现了“瘦身”。但透过两座城市的生活垃圾产出量、手机用户数据等,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京沪两地的人口状况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彭希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不断在调整完善。最初希望发展中小城市,其后是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然后是控制特大城市过度蔓延,现在的关键词是一体化发展、城市群联动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京沪两地的人口数量微调,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指标意义。
问:从家庭层面来看,伴随人口领域出现的各种宏观变化,未来家庭似乎也将逐渐告别传统的模式?
彭希哲:在中国,“传统”和“未来”并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相互对立,而是相互磨合、相互补充的。
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家庭规模虽然在变小,但并不是简单的“核心化”。“夫妇—子女”家庭结构尽管已成主流,却有形而欠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核心化”,其功能的完成仍需亲属网络的参与。
还比如,我们眼下对劳动力的判断,基本是以工业化时代为标准的。在智能化的未来,劳动力需求模式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过去汽车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装配工人,未来基本都可以交给机器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更多思考的不是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是劳动者如何去适应新的产业结构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以及怎样控制结构性失业。
对照这个要求,现在对孩子的教育,可能學一门具体的知识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掌握学习的能力以及应对变化的能力。只有这样,人类和机器才能联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