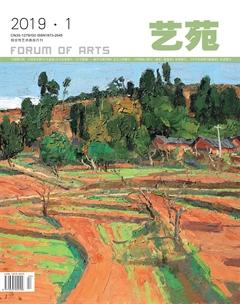笑与泪:来自新编梨园戏《陈仲子》的黑色幽默
王艺珍
【摘要】 新编梨园戏《陈仲子》是一部颇具黑色幽默的剧作。一方面,陈仲子为求绝对的贞廉,不断避离世俗,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物质也加以否定,充满荒诞意味;另一方面,陈仲子的求索表达的是民族的一种精神追求在时代中的变奏,闪烁着哲思的光芒。此外,剧中“门子”的插科打诨与“歌队”的设置,也在不断消解舞台与现实的阈限,完成对现实的指涉。《陈仲子》一剧,笑中含泪,引人深思。
【关键词】 《陈仲子》;新编梨园戏;黑色幽默;人格范式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陈仲子》本事出自《孟子·藤文公章句下》和《七十二朝人物演义》。陈仲子,战国时齐国人,出身官宦世家,一生追求贞廉,最终活活饿死。对此,孟子提出了质疑:“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王仁杰以陈仲子入戏,却自有另一层深意:“一个生于战国乱世,不堪于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竭力追求独善其身而终于不能的古代‘士的形象……作者欲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以表达自己处身于商品大潮中百感交集的内心感受。”[1]222 2018年该剧重演(1),王仁杰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塑造陈仲子是为了树立一个‘道德标杆,把民族当年的圣贤在舞台上表现出来。”[2]此次搬演,王仁杰为陈仲子增加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台词,其坚定执着的性格特征显得更为鲜明。但是,对照本事与作者的立意,我们不难察觉陈仲子这一人物形象在历史场域中价值评价的游移与不确定性。“蚓者已归土里眠,唯余仲子逐迷烟。千秋一案留君说,讵识斯人愚与贤?”
战国是一个诸子争鸣、“苍生黎庶正悬悬”的时代,入世用世是其精神主流,但出身显贵的陈仲子却以“贞廉”为人生坐标,特立独行。头出,陈仲子自剖心迹,家族荣光的庇荫有违“贞廉秉性”,于是他“辟兄离母”。“碎坛绝食”一出,陈仲子为其他汲水者“捷足先登,抢先一步”一语惊醒,先将水全数分与众人,又将坛子一摔而毁,而其自罚三日绝食,更是以身体上的自戕来达到精神上的忏悔。物质利益一旦与追求“贞廉”的精神追求有所牴牾,陈仲子的处理方式无一例外就是毫无留恋地弃绝,自此,一个具有精神洁癖的古代“贤士”跃然于台上。“半李三咽”是本剧的一个小高潮,此时的仲子,吃一个烂李,还需考虑是否有与虫蚁争食之嫌——“虫若爱吃,因何会留下一半?虫留下一半分明是不吃了。虫既不吃,我吃谅也无妨。娘子,你说,我吃得吃不得?”一言一行,俨然孩童稚子,让人觉得可笑又可叹。正如仲子妻内心独白:“是怜是怨?是爱是慕,于今难分别,唯有悲欣泪,夺眶出。分不清,冷与热。”其可笑者,在于此时的陈仲子将绝对化的“无争”作为界定“贞廉”的核心观念。这种不与人争,不与物争,已不是隐士文化中的淡泊名利的洒脱,而是逐渐变异成一种精神上的焦虑症——急于确证自己的精神的“贞廉”却又无法从根本上确证,所以他只能从他者——妻子的话语中确证自己行动的合法性。
如果说“辟兄离母”“碎坛绝食”这两出陈仲子更多是从外在物质与自我关系的层面上来追求“贞廉”,以退避俗世求得精神上的“廉”,那么,“灌园拒相”,则是面向社会宣告自己的“不合时宜”。楚君慕仲子之“贞廉”,欲拜之为相;此时,陈仲子陷入悖论之中:往么?岂不悖离“无为恬淡”的本心?拒么?浊世颓风,谁挽狂澜?在这里,王仁杰先生的处理尤为巧妙,前半出,陈仲子在妻子的劝说下,一腔豪情意欲应召;后半出,因马失半途,陈仲子终悟出:楚国为相,实为富贵所诱,最终不为楚国相,甘为灌园佣。这一出本是陈仲子精神裂变的关键,作者却设置了“马失半途”的小插曲,借灌园主诙谐的调侃——“时未变,人在变”,将陈仲子抛入了“草鞋先生”和“相国”两重身份的艰难抉择之中,也促成了陈仲子再次完成精神上的自我烛照。“食鹅呕鹅”可以视作仲子与自身欲望博弈的过程。食本是人之本能,鹅本无辜,奈何出之不义——乃专务趋捧的王欢大夫所送,于是陈仲子欲呕之而后快。食鹅事件是为陈仲子历经的精神“严重时刻”,它松动了陈仲子对外界物质的界定——“物力维艰”,而转向了一种不断怀疑的悖谬之中:口腹之食“未免以无易有”,其“义”与“不义”就难以确证。物质上的廉洁无法保证,则精神上的自立就难以完成,于是陈仲子“不得不对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地进行挤压与收缩,”[3]乃至于与蚯蚓为伍。此时,陈仲子已迷失了追求的本质,堕入了荒诞的处境——视蜕化蚯蚓为人生理想。对名、利乃至生存欲望也加以否定,陈仲子最终欲将自己异化为物,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无疑是一曲迷失自我的笑剧。演出当晚,当演至陈仲子意欲化身蚯蚓而不可得时,现场观众发出了善意的嘲笑。
《陈仲子》中其他角色也尤为“可爱”“可笑”。剧中,门子汲汲营营,“傍官气”、索要贿赂。其扮演者郭智峰先生将门子左右逢迎的形象演活了。门子以闽南语方言的谐音,将“上大夫”“中大夫”与“豆腐”并列,嘲讽当朝者专务趋奉,充满了黑色幽默(2),让人会心一笑。“食鹅呕鹅”一出,当门子将微信、支付宝亮出索要贿赂,现场观众笑声哄然。门子的插科打诨既调节了剧场气氛,也将阿谀奉承、因利而动的世俗风气展现无疑。充满谐趣的“笑料”在门子与众家丁、送鹅者(皆为歌队担当)的对话中随处可见,给剧场带来莫大的欢乐。
然而,这真的只是一场笑剧吗?“贞廉”对陈仲子来说,是一团先天存在的光圈,他循着她的指引,不断叩问,从弃离显贵出身、摔坛自罚到食鹅呕鹅,一层层剥离世俗的外衣,以至最终连最基本的生存物质也加以否定。他从一个坚定的贞廉主义者,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怀疑主义者。贞廉的精神性追求降格為对物质来源的怀疑,这就是陈仲子的荒诞之处。越是想摆脱物质的束缚,越是在意物质他者的困扰,陈仲子就越陷入他者的泥潭,怀疑自我存在的合理性。这也是陈仲子这一人物形象所生发出来的黑色幽默。
异化为物让人不难联想到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区别在于前者主动异化,而后者被生活胁迫。我们不妨剥开陈仲子欲与蚯蚓比廉的荒诞外壳,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幅弥漫悲剧性的寓言图景。陈仲子“辟兄离母”“灌园据相”乃与俗世分流,“碎坛绝食”则是一种道德自省,“蚯蚓比廉”则是其对“贞廉”终极境界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之中,陈仲子不断做出选择,不断躬身自省,不断做出行动。他的语默静动,蕴藏着人类对自身精神探索的复杂脉络,在这一层面上,陈仲子对“贞廉”的追求是一种追求极致的精神范式,就如夸父追日,长河在即,悲歌却起。所以王评章先生认为陈仲子:“作为一种精神范式,表达着的是精神理想而不是现实理想。它的意义不在于自身的普遍、完整实现,而在于永远彰显人类、历史、时代的非完整性。”[4]陈仲子无疑是时代的“精神病患者”彰显着时代本身的精神病症。而当代,众生汲汲营营、熙熙攘攘,我们对陈仲子的哂笑不正折射出时代精神的症候。陈仲子的自我救赎始于精神的自我觉醒,而终于自我的覆灭,是一出悲剧,更是一种寓言,“在表面近乎荒谬的‘以廉立身而几不可为的逻辑下面,是一个近乎悲怆的人生终极关怀”[5]144。反身观照自身,我们与陈仲子一样常处于抉择之中,但更多时候,我们会迷失在生活之中,与其说是我们嘲他,毋宁说是自嘲。这也是陈仲子这一人物形象带给观众的黑色幽默。
这种嘲他与自嘲的反转同时也发生在门子这一角色的安排上。借门子之口,剧作者巧妙地将地域方言和口音笑料融入陈仲子的人生悲剧之中,笑声愈响亮愈显得陈仲子人生图景的荒凉。当门子亮出收款码时,台下观众无不会心一笑,这一笑是轻松更有无奈。将现实赤裸裸地搬上舞台,以温情脉脉的“喜剧性”指向现实,实现陌生化的同时也完成对现实的嘲讽。舞台与现实的交融,不仅体现在现实图景搬上舞台,还在于此次演出匠心独具的设计上。此次舞台演出,杂色主要由歌队充任。歌队与乐池相对并列舞台两边。歌队的功能不仅限于传统的舞台帮腔,且时而充当剧中角色,如化身汲水者,与陈仲子进行对话,如成为陈府门的家丁和送鹅者,嘲讽门子的势利。台下与台上互相交融,打破了传统的舞台空间,且歌队置于舞台前方,实现了观演的间离。台上、台下的界限不再严格区分,观众不再沉溺虚无的戏境之中,而不时地被拉回现实,观照现实本身。戏即人生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实现。
每个时代都会有基于当下的生存世界和现实境遇而产生新的关注点,恰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作品解释的年代,而是解释作品的年代。当这样的陈仲子置身于极具现实指向性的环境之中,《陈仲子》所传达出来的恐怕不再是单纯的一种历史指涉,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人格范式,表达的是民族的一种精神追求主题在时代中的变奏。陈仲子如此悖于时宜,却仍不断追寻。当连蚯蚓都不接纳他时,他更像一位英雄,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为盟誓,即将开启唐·吉诃德的第二次精神之旅,可能周遭笑声四起,但他置若罔闻。“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探索自我与追问自我,我不相信在那光明的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找,而且总是由具有人类荒谬性的某个脆弱的成员来寻求。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至少总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6]156陈仲子们昭示着人类精神世界的非完满性,“种族必须有这种超越精神的智慧和牵引,才能自我挽救、自我提升”。[4]76
注释:
(1)新编梨园戏《陈仲子》初创完成于1990年,只在泉州、福州演过几场,后因有所争议,停止演出。该剧于2018年10月在泉州梨园古典剧院重演。
(2)黑色幽默,取其荒诞之义。就《陈仲子》来说,这种荒诞来自于陈仲子这一人物行动上最终走向异化的悲剧,另一方面源自舞台塑造上的成功,剧中丑角艺术对自我的嘲讽,实现了对现实的指涉。
参考文献:
[1]福建省文化厅.新时期福建戏剧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 第8册(下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2]梨园戏《陈仲子》首演[EB/OL].
泉州午间新闻网.https://www.iqiyi.com/v_19rr5agqro.html.
[3]方李珍.沉入草野——王仁杰梨园戏道德形象的民间特征[J].福建艺术,2001(6).
[4]王评章.关于《陈仲子》[J].剧本,2008(7).
[5]叶曉梅.梨园戏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6]威廉·福克纳.福克纳随笔[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