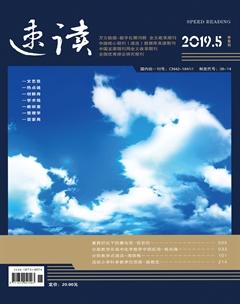美丽与丑陋是一对双生子
摘 要:电影《芳华》带领观众追忆上世纪的文工团岁月,电影中,出现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本文将由文化分析的角度解读《芳华》。
关键词:《芳华》;文工团;美与丑;文化
“文工团”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具备神秘的色彩,电影《芳华》的镜头下,它是歌声昂扬舞姿挥洒,是荡漾的青春荷尔蒙,是红色山河下极具活力的一隅。美固然令人怀念的,但是,美丽和丑陋是一对双生子,有美丽的地方,必然有着丑陋的阴影,文化浪潮的变迁亦是如此。
《芳华》的第一叙述者是萧穗子,其讲述平和,最后,主角刘峰与何小萍生活在一起,看似大团圆结局,但这是导演对观众的一种“欺骗”。情绪没有起伏,创伤却是存在的。70年代,“学雷锋”风潮席卷全国,“雷锋”由一个牺牲了的解放军战士,变成一个被神化了的道德榜样。刘峰就是一个有求必应的“活雷锋”:吃饭只吃破饺子、英勇抗洪砸伤了腰、主动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帮助被奚落的何小萍,最后为了守住战友的尸体失去了一只胳膊。文工团里学雷锋的人不在少数,从郝淑雯说的“人人争着打扫猪圈”可以看出来,可遭遇“捧杀”的只有刘峰一人,被捧上了神坛,又跌落至尘埃,只因他是唯一把“雷锋精神”贯彻得如此彻底的人,人们忘记了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青年,“谁都能追求,就刘峰不能追求”。当刘峰袒露私心,向爱慕的林丁丁表白时,毁灭的不仅是他的个人形象,同时也是雷锋文化在文工团内的直接幻灭,是对雷锋本人的腐蚀,令人“恶心、惊悚”的远不是“触摸”这一行为。刘峰是美与高尚的化身,受到驱逐时,外表还是平静的,直至他在边境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才直观地把内心的创伤展现在身体上,英雄的落魄,反映的恰是看客的残忍和荣辱观念的变形。
在何小萍、刘峰这样的“异类”心中,文工团岁月似乎不值得追忆。何小萍和刘峰的人生轨迹相反,她是从地底被扶上神坛的,她从未受过善待,自小遭遇的磨难和突如其来的荣光反差太大,导致她发了疯。文工团文化注定是狂热的群体文化。根据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形成群体之后,个体不论多理性、智慧,他们在群体中的智力被统一抹平,变成轻信、易怒、冲动、极端的个体。文工团的众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因为何小萍出汗严重、偷拿林丁丁的军装拍照等一系列小事,她被认为“有品质问题”,被排斥,连舞伴也不愿意和她合舞。每个人都无判断力可言,她的存在和刘峰一样,只是一个符号,相当于众矢之的,是群体共同的攻击对象,可以使群体变得更加紧密,也许众人不曾觉察自己的恶意,今后可能还会嘲笑自己的荒谬,但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每个人都被愤怒遮蔽,变得盲目,争辩不可能奏效,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逃避,所以何小萍选择了离开。其他看似高尚的人又如何呢?最为义正辞严的郝淑雯,得知陈灿同为高干子弟,无视好友对他的爱慕,果断选择了与其结合;林丁丁在文工团解散时,把热恋的宣传干事抛在脑后,嫁给了华侨。
充满信仰的时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芳华》展现了新对旧的冲击。曾经,军装是最美的外衣,父亲在农场劳改的何小萍,想用自己的军装为父亲带来尊严。改革开放以后,港台流行文化涌入,文工团里的女孩意识到白衬衫、喇叭裤这样的衣服才能尽显身体的美丽。萧穗子等人偷偷地用收音机听邓丽君的歌,感慨:“歌还能这么唱啊。”连自律的刘峰,也被邓丽君缱绻的歌声打动,“词都往心里钻”,“都是为我唱的,都是我想说的”,并冲动地向林丁丁表白。在封闭的年代,新式的服饰、音乐使年轻人的头脑解放,犹如长期守孝的人脱下孝服。舶来文化在当时是小众的,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萧穗子说,政委看见她这样穿,会把她送上军事法庭。但任何文化都要被历史化地理解,港台文化在七八十年代算是异类,到了新的阶段,它的地位发生了转变,成为大众文化,电影尾声的时间是90年代,郝淑雯和萧穗子的装扮已经明显地西化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计划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必定不同于市场经济。文工团解散之际,刘峰从部队返回,镜头拍到墙上的可口可乐广告,象征着文化的消亡与兴起。另外,如果不是新时代来临,文化始终是一种特权,少数人才能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恢复高考使萧穗子改变人生,若非如此,她成为作家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文化的更迭解放了人们的身体,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两个层面的美,同时,丑陋也是存在的。
1991年,刘峰因无法缴纳巨额罚款,被联防队员殴打;联防队长不作为,只顾罚款。倒退十年,同样事件不可能发生,新的社会给了人们机遇,也在减损着良知与道德。小号手陈灿早已放下小号,成为了疏于陪伴家人的精明商人,文工团赋予人们的情怀也在一天天地消逝。金錢成为了安身立命的标尺,浮躁、贪婪蔓延广泛,社会精神成为空谈,谁还会像当年一样争相恐后做好事?刘峰般的老好人,如不肯降低道德底线,落伍是意料之中的事。歌颂自由和机遇的同时,其负面后果也不能忽视。
《芳华》是一辈人、两个时代文化的真实写照,两个时代一新一旧本无优劣之别,但是我们要清楚看到,《芳华》不是只赞扬不贬抑的,两个时代的美与丑,就像一对双生子,如影随形,二者皆不能忽略。
参考文献
[1]柯弄璋.电影《芳华》:个体青春与记忆创伤[J].四川戏剧,2018(10):136-138.
[2]史新玉.电影《芳华》的形式策略与文化意蕴[J].衡水学院学报,2018,20(05):121-124+128.
[3]勒庞著.乌合之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邱嘉仪(1998.08—),女,广东省广州市人,广州市番禺区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