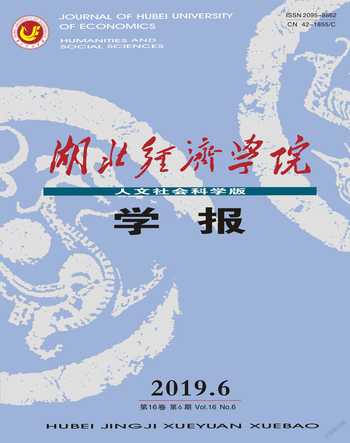论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制度改革与居住权的关系
陈琪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分编 (草案)》(以下简称《民法典(草案)》)已基本完成,但是,该草案关于居住权的却仍缺乏必要的现实基础,也缺乏普遍适用空间,这可能会使居住权立法再次失去其应有之义——在过去《物权法》制定时曾为居住权立法有过激烈争论,但是因为缺乏了现实基础及普遍适用性而未能落实。当前,若对继承篇的进行制度改革,可为居住权确立为物权法上的新型物权提供立法前提,而居住权的确立反之又能推动继承编的制度改革的落实,两者相辅相成,而在继承编制度改革的方向下居住权可参照国外法设定法定居住权和意定居住权,使继承编与居住权同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继承权;继承顺位;居住权;制度改革
在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立法中曾对是否设立居住权有过很大的争论,但最终因居住权欠缺现实的基础而没能落实。而现在,《民法典(草案)》突破了《物权法》原有规定,在草案物权篇中对居住权进行了规定。但是该草案未将居住权与继承编之间联系起来,很可能让居住权失去立法基础。因为继承编进行制度改革,可为居住权的确立提供前提,居住权的立法又反之可推动继承编制度改革的落实,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一、继承编辑制度改革可为居住权的确立提供立法前提
在之所以《物权法》在制订过程中居住权不能确定下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我国历史背景下,居住权缺乏确立的必要基础。因为居住权制度的主张者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父母、离异后没有居住房屋的前夫(前妻)和保姆等群体[1]。而尚无基础的主要理由在于尽管在外国民法典中有很多建立居住权的例子,但是,在他们的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之后,没有继承权的母亲通常可以拥有居住权。而在我国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一是因为我国规定了配偶相互间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同时子女有义务赡养父母。故父母和离婚后的夫妻不需要居住权来救济。二是在过去国内的保姆是属于极少数的一类个体,即使是有,也很少需要在雇主家来养老终身。所以不需要为了解决少数人的困难而来创立居住权①。
但是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制定的已有30多年,基本内容还没有做过修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然成为了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同时也带来了价值观的变化,继承法的价值目标已不能满足价值主体的要求期望,继承制度到了须进行制度改革的时刻。在过去居住权不能确定下来是因为没有必要的现实依据,那么现在可以随着《民法典(草案)》的编撰来进行继承编的制度改革,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为居住权的设立提供立法前提。
(一)父母法定继承顺位的制度改革建议
在继承相关的法学观点中,死后赡养说是主流的观点,该观点的法理是如果被继承人在生前因负有赡养家庭成员的义务,那么他的遗产也应当同时用于赡养家庭。而在颁布于《继承法》的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养育老人等原则则变成继承法的主流观点[2][3][4]。在这种思想下,故而将父母列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才能显示出中国尊老的传统美德。
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提出观点反对父母的第一继承顺位,其中有观点认为,将自己的财富留予晚辈直系血亲是由人性所决定,而且将父母作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遗产则很可能经过父母再转由旁系血亲继承,甚至于由血亲之外的旁人所继承[5]。这种与人性相背离的继承逻辑对于被继承人来讲是不符合人性意志的。也有学者对国内多个省市就父母继承顺位的观点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父母第一继承顺位是不太合理的[6]。学者在其《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的文章中也是建议把子女及其晚辈血亲列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同时把父母列为第二顺位继承人[7]。另有学者认为可以把中国古代继承制度当作现在制度改革的启示,在传统中国,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一般是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而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才是父母[8]。另外在继承编的民法室室内稿也将父母作为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可以看出,学者的主流观点大认为父母放在第一继承顺位是不尽合理的。
因此,综上所述,由于目前父母第一继承顺位存在的现实不足,同时参考中国的民族传统和各外国法中的有關继承顺位的普遍规定,建议在民法典(草案)继承编中将父母确定为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第一顺位仅为子女及及其直系血亲,这可为居住权的确立提供立法前提。
(二)继子女、继父母继承权的制度改革建议
我国《继承法》规定了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享有继承权。但是,有观点表明让继子女享有对继父母的继承权会损害继父母亲生子女的继承权[9]。因为从传统习惯和感情上来说,大多数人都不太意接受非己亲生的孩子进入自己的家庭,如果法律再强行规定继父(母)接受再婚配偶的子女并形成抚养关系后,不但要承担继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且继子女还会作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与自己的亲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的遗产继承,这样必定会影响到其他法定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尤其是会损害到亲生子女的利益。还有观点认为,强行规定继子女享有继父母的遗产继承权是违背被继承人的个人意志的[10],也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是相背离的[11]。同理,继父母继承继子女的财产也会损害到亲父母的利益。国外也很少有规定继子女可以同亲生子女享有一样继承权。有学者提出建议,认为应修改现行的继承法,在继子女对继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后,或者是继父母对继子女尽了抚养义务后,他们方才具有继承权,是为附条件的继承[11]。
因此,建议把继承法中“子女”的内容限定在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内,“父母”的内容则限定在生父母、养父母。而对继承人以外的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人(如继父母,继子女),则依据实际抚养等情形,酌情分配适当的遗产[8]。
(三)配偶对先亡配偶的父母遗产继承权的制度改革建议
在继承法的历史上,继承权利的法理源于人们之间血亲关系。让与被继承人最具血亲关系的人享有最优先顺位的法定继承权,是符合其人性意志的。而让配偶之间相互享有继承权的规定曾经是继承法的一项较大的改革。但在各国外的继承法中,继承权的范围并未扩大到夫妻关系以外的有姻亲关系的人。而我国继承法规定,让生存配偶对先亡配偶父母遗产享有继承权。这种遗产流向的制度是存在明显缺陷的。第一个缺陷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7和18条中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继承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则除留有遗嘱以外,配偶可以继承对方父母的遗产并且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被继承人的子女继承遗产后比其配偶更先离世,那么其儿媳(女婿)就可以取得遗产的全部或者大部。第二个缺陷就是是依据《继承法》第12条的表述,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会让本有继承权利的被继承人的配偶和其他的晚辈直系血亲失去继承权。更加不公的是,如果再把父母法定继承顺位调整至前述改革的第二顺位,那么被继承人的丧偶儿媳(女婿)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权将完全占据排挤掉父母的继承权利。
当然,让生存配偶享有对先亡配偶的父母遗产的继承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家庭和谐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带来的财富的飞速增长,让一些不怀爱情真意的人纯粹为了钱财而去缔结婚姻,而这些以金钱为目的婚姻是极不牢靠甚至于会导致命案[12]。可见如果《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仍然继续沿用现有规定,可能不仅不能促进家庭的和睦,反而有可能会恶化家庭成员间关系。而且让生存配偶享有对先亡配偶父母的继承权还会与代位继承制度间发生矛盾,损害继承人的合法利益[10]。
故而建议参考一些学者主张[8],取消丧偶儿媳(女婿)第一顺位继承权,但对于公婆(岳父母)尽了赡养义务的儿媳(女婿),可以酌情分配部分遗产。
(四)生存配偶对先亡配偶遗产继承权的制度改革建议
在改革父母法定继承顺位变动的同时,建议配偶应当设立为不固定继承顺位。其规则为当存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时,配偶则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共同继承遗产,当不存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时,配偶与第二顺位的继承人按照份额继承遗产。
当在以下两种特殊的情形时,生存配偶对先亡配偶的遗产继承建议如下:第一种情形是事实婚姻中继承制度问题,关于配偶的继承权,各国的继承法规定,有效的继承是以婚姻的合法性为条件的。与此同时,我国也不鼓励事实上的婚姻。因此,以夫妻双方的名义共同生活的“配偶”没有继承权。但事实上的婚姻确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且也不是个别存在的,虽然法律不承认事实上的婚姻,但男女之间的真实感情不容忽视。继承的法律依据有两个原因,即血缘和情感,它们都是继承人的真实想法。换句话说,以事实婚姻的名义将配偶的继承权与配偶的继承权分开是不合情理的的,它也违反了继承人的个人意志。当然,对于事实婚姻的认定应当予以明确规定②。因此,建议酌情分给事实婚姻的生存“配偶”部分遗产。
第二种情形是在生存配偶再婚后对其前妻或前夫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丧偶后再次寻求个人幸福。如果父或母进行再婚,且如果婚后又先于再婚配偶死亡的,那么再婚的配偶则会享有部分财产的继承权。所以,许多子女不同意也不希望父或母再婚,在这些现实面前,使有些父或母不得不选择割舍幸福。因此,可以建议规定,当丧偶后再婚,与前妻(前夫)的共同财产是他的个人财产。如果配偶在再婚配偶之前去世,则再婚未亡配偶不能继承个人财产。与前妻(前夫)之间共同财产为他的个人财产,如果又先于再婚配偶死亡的,再婚的生存配偶则不能继承这项个人财产,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上述关于继承制度改革建议的要点可归纳为一点,当继承制度改革后,存在这么一个群众,这些人与继承人关系密切,在继承制度改革后不能享受继承权时,他们的客观存在让居住权具有了存在必要性。因此,这些继承权的制度改革方向可以为居住权提供立法的制度前提空间,给了居住权存在的土壤。
二、居住权的确立可推动继承编制度改革的落实
如上文所述的继承权的改革,包括父母、配偶、继父母等被继承人的亲属,在选择他们的利益和选择被继承人的直系晚辈亲属的亲属之间的继承利益对比时,优先考虑了晚辈的直系血缘亲属。在做出了这些利益选择之后,是不能忽视在这些人失去继承权或优先顺位的继承权后的生活上的问题尤其是居住问题,除了继承权之外,法律应合理地处理,以保障他们的生存生活需要,这既尊重他们和继承人的真实的情感感受,也体现了对被继承人个人意志的尊重。因此,居住权的确立是确保了遗产继续流向直系晚辈亲属,保持婚姻的稳定,并让无权继承的亲属住有所居。所以居住权的确立是既能确保遗产流向直系血亲、维护婚姻的稳定,又能让没有继承权的亲属住有居所,安享晚年的最优方法。因此,居住权立法又反之可推动继承编的制度改革的落实。
(一)居住权权能分离的特征可推动继承编的制度改革的落实
居住权可追溯到罗马法。这是罗马法律中的一种人役权,与用益权和使用权相并列。德国法上也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居住权,有一种和罗马法上的居住权是一致的[1]80。居住权的基本特征是占有、使用和所有權的分离,即它的权利持有人不享有房屋的所有权,但有占有和使用权,直到居住权消灭为止。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影响由继承权转化的房屋所有权。
所有权人的归我所有的主观性要素是所有权本质上的要素。当占有离开所有权时,只要所有权人在精神上对所有物享有归我的个人意志,权利便依然存在。而居住权却因却缺乏所有权人这种归我所有的个人意志,它仅仅是享有对物占有或使用的权利。这种占有、使用权和所有权中的分开的权能分离的特征是居住权的本质特征,即所有权人没有占有物,但却在所有权人的意志掌控中,在居住权终止后他有权利收回标的物然后占有它。
如上文所述的继承编的制度改革建议,是为了实现遗产流向晚辈的直系血亲,而限制部分与被继承人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人取得遗产的所有权。因为被继承人的普遍的个人意志是让晚辈的直系血亲获得遗产所有权,同时再让财产由父母、配偶、儿媳、女婿以及其他对其生前进行生活照料的人占有使用,可让被继承人的普遍性的人性意愿获得最大化的需求。
所以让有权能分离的基本特征的居住权确定为物权法中的新的物权。可为继承编的制度改革提供推动力。
(二)居住权解决利益矛盾的功能可推动继承编的制度改革的落实
居住权既能依遗嘱设立,也能依据法律的规则产生,但不管如何产生,权利人不需要支付价款,因为它是免费使用权[13]。居住权有这个特征,是因为它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被继承人的亲属间或特定身份的人之间利益矛盾,具言之,居住权有平衡利益矛盾的功能,它将遗产有条件的无偿使用与遗产所有权进行区分,可较好地解决法定继承人与需要使用被继承人房屋的人之间的利益矛盾。
而在上文所述制度改革建议中的情景中均存在亲属关系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如被继承人的血亲与姻亲的利益矛盾、血亲长辈与血亲晚辈的利益矛盾、直系血亲与旁系血亲的利益矛盾等。利益矛盾的背后实质常常包含着民法的价值冲突,或者说,这种价值冲突在多数情形下是利益矛盾的更深层次的体现。[14]“民法上的利益位阶的序位是解决利益矛盾的根本方法”。[15]有不少学者曾对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原则发表观点③,但是在尊重被继承人的个人意志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价值之间的利益矛盾之间,应当把前者即尊重被继承人的个人意志放到更优先的地位。理由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赡养老人等家庭保障的功能已经不再是财产继承的最主要的功能,而最高价值位阶应当是尊重被继承人个人意志的这种思想自由的价值。当我们在继承关系中的冲突中做出了尊重被继承人个人意志的价值后,可以有两种实现该价值的方法,即完全抛弃与晚辈直系血亲有利益冲突的人的利益和在不损害晚辈直系血亲的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其他相关之人的利益。无疑,后一个方法无疑是更具道德与正义的选择。
总而言之,居住权的确立可以将有利益冲突矛盾的各个人的利益损失降到最少,并形成一个兼具正义而稳定平衡。例如,没有继承权的父母,继父母等可以免费使用房屋直至死亡;没有继承权的配偶或儿媳可以免费使用房屋,直到再婚,这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而且保障了继承权人的利益没有减损。
三、继承编制度改革方向下的居住权的设计建议
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第十四章中第159至162条规定了居住权,将其规定为意定居住权。若依此规定,居住权将失去它应有的立法价值。因为如果要实现意定居住权不需要使用居住权物权属性,即没有物权性质的居住权,人们相互之间同样亦然可以直接约定房屋占有、使用的权利等,同样可以实现居住权价值。
如上所述,继承编的制度改革可以为居住权提供立法基础,那么,居住权的制度设计也就可以以继承编的改革的方向上来展开。
(一)权利的设立
纵观国外法有观居住权的设立,如《法国民法典》625条规定,使用权及居住权依用益权同一的方法设定与消灭。《法国民法典》第579和580条就又规定,用益权的设立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设立或人的意思规定。既可以是无条件的,也可以是附期限的,或者附条件的。又如《德国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在排除所有人的情况下,将建筑物或者建筑物的一部分作为住宅加以使用的权利,也可以作为限制的人役权加以规定。”
关于我国居住权的设立,在我国继承编制度改革的情境下,则可借鉴参考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居住权的立法经验,同时确立法定居住权和意定居住权。法定居住权可规定,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时,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将享有作为遗产的全部或部分建筑物内的居住权利。意定居住权则由遗嘱确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让不具有法定居住权主体资格的人在被继承人死后对建筑物房屋享有居住权。
法定居住权与意定居住权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权利主体的资格是否是法定的。在特殊情况下,当被继承人在遗嘱中确定或者合同约定具有法定居住权主体资格的人就某一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即使约定的房屋的面积等,不会改变法定居住权的权利性质,所以在这种情境下的居住权还是为法定。只有明确的约定赋非法定居住权的主体予以居住权的情形下,居住权方为意定。
因此,在继承编制度改革的方向下,我国居住权的设立的主要部分应是法定居住权,意定居住权作为补充。
(二)权利的主体划分
居住权的主体可以进行意定和法定之分,其中意定居住权的主体可以由遗嘱来指定或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被继承人既可以指定继承人享有居住权,也可指定继承顺位在后不能繼承遗产或者与其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者是其他任何人。法定居住权的主体则应是与被继承人有一定身份关系且无权继承遗产却又需要这些遗产来照料其生活的的人。继承编可视具体规定情况来规定法定居住权的主体。则如在上述的所述的继承编制度改革的视域下,以下几类与被继承人具有一定关系的人可定为法定居住权的主体。
第一类是是对被继承人尽了抚养教育义务的人,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继父母等。如果父母已无权继承该遗产且父母无房屋可住,那么父母享有居住权,而继承了遗产的晚辈直系血亲及配偶应当依规给予被继承人的父母一定的赡养费。如果祖(外)父母把被继承人抚养成人,在有晚辈的直系血亲作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时,则(外)祖父母和父母一样的享有居住权或是赡养费的债权。如果被继承人父亲或母亲已经离婚由继父或继母的抚养,则在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继父或继母则应同样享有房屋的居住权或是赡养费的债权。
第二类是被继承人的儿媳(女婿)或继子女。如果被继承人的已丧偶的儿媳(女婿)对其尽了赡养义务的,那么当其去世时没有房屋居住的,已丧偶的儿媳(女婿)对被继承人的房屋享有居住权。如果继子女对被继承人也尽了赡养义务的,当被继承人去世时又没有房屋居住的,则对房产享有居住权,再者如果没有第一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的,那尽了赡养义务的继子女可以享有直接的继承权。
第三种是被继承人的配偶。按照上述的制度改革建议,配偶是不定顺位继承人,具有继承权,因此配偶通常非法地确定居住权的主体。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配偶可以成为法定居住权的主体对象。一是被继承人生前和他未进行婚姻登记的名义“配偶”一起共同生活,生存的名义“配偶”不享继承权,但是,对于共同居住的房产,应该享有居住权。二是,被继承人在死亡前与配偶就财产分配达成协议,被继承人指定将遗产留给其他继承人。那生存的配偶对共同生活的房产具有居住权。如果又有证据表明生存配偶对夫子女的抚养付出了主要的贡献,那么还应当享有酌情分配的请求权。
(三)权利的消灭
居住权的性质是人役权即依附于人而存在的,且权利不得转让和继承。在法律规定或者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居住权消灭。
其中法定居住权利的消灭按照不同的主体方式有所不同。一是与被继承人有血缘关系的人(如父母等)享有的居住权后,在权利人去世自动消灭。在权利的有效期内权利人可以和家属在房屋内共同居住,如果居住权人一旦死亡,那么权利消灭,原居住权人的家属等均须自权利人死亡后搬出房屋,此时,继承人取得了该房屋的占有,取得得权能的统一。二是与被继承人有姻亲关系的居住权利人。在居住权人进行再婚时权利消灭。
对于意定居住权的消灭,由遗嘱或者合同来确定。遗嘱或者合同确定居住权的权利期限的,则权利期满时消灭;遗嘱或者合同规定附条件的,在条件达成时居住权利消灭。遗嘱或者合同未明确规定权利消灭条件的,可依照法定居住权消灭的规定。当被继承人遗嘱或者合同指定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有居住权的,在居住权利人有经济能力购置房屋或者承租房屋的时侯权利消灭[16]。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法典草案居住权的立法与继承编的制度改革之间两者在关系上是相互依存的。故民法典草案居住权的确立要立足于继承编的制度改革的基础之上,在法律条文上应把物权编的居住权与继承编结合起来。居住权的具体内容可以规定包括权利产生根据、权利内容和消灭原因等。继承编则可以对居住权的规则进行相应的补充,可以同时在规定父母第二法定顺位继承权和父母的法定居住权。
注 释:
① 参考梁慧星:《对物权法草案(第二、三、四次审议稿)的修改意见》,中国法学文档;2006;梁慧星:不赞成规定’居住权’[N],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12日。
② 事实婚姻的实质条件:(一)主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二)无婚姻关系或同居关系障碍;(三)无禁婚的亲属关系和疾病;(四)共同生活1年以上或共同生育子女。(参见阚凯:非婚同居的法律问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法学院2012年博士毕业论文:278-281。)
③ 利害原则是古今中外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然而,价值冲突很多情况下不都是以利与害可以评价的,即便是有些场合可以利与害进行评价,也是十分困难的。还有学者主张应当建立某种可以精确量化的法的价值的位阶体系,遇到价值矛盾冲突时,以等级确定价值选择。这是一个极易操作的价值选择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完善而令众人接受的价值等级体系的建立。(参见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17-618。)
参考文献:
[1] 申卫星.视野拓展与功能转换.我国设立居住权必要性的多重视角[J].北京:中国法学,2005,(5):77-9.
[2] 刘春茂.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30-31,43.
[3] 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M].北京:中國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651-653.
[4] 张玉敏.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确定[J].上海:法学,2012,(8):15-20.
[5] 郑倩,房绍坤.父母法定继承顺位的立法论证[J].吉林: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31-35.
[6] 陈苇.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査实证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1-660.
[7] 陈苇.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22.
[8] 肖洪飞.中国古代继承制度及对当今继承立法的启示[J].甘肃:社科纵横,2008,(8):81-83.
[9] 张玉敏: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2.
[10] 陈苇,冉启玉.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立法的思考[J]. 山东:法学论坛,2013,(2):52-57.
[11] 房绍坤,郑倩.关于继父母子女之间继承权的合理性思考[J].吉林:社会科学战线,2014,(6):203-207.
[12] 曾青.一起杀人案引发的思考——谈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缺陷及其完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184-186.
[13] 周枏.罗马法原论(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98.
[14] 李国强,孙伟良.民法冲突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从民法方法论的进化到解释规则的形成[J].吉林: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1):58-66.
[15] 王利明.民法上的利益位阶及其考量[J].北京:法学家,2014,(1):80.
[16] 马新彦.居住权立法与继承编的制度创新[J].北京:清华法学,2018,(2):163-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