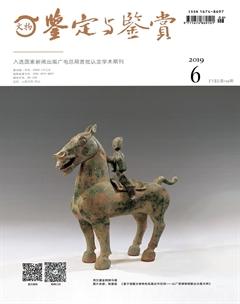以《崇祯历书》修订为切入讨论明末历法改革作用因素
彭侃

摘 要:以明末崇祯历法改革的《崇祯历书》修订为中心,在考察明末改历的史实基础上,探讨引起明末历法改革的主要因素。指出明末历法改革不是一项现代意义上纯粹的科学活动,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历法改革,它是以西方科学理论为基础开展的一次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政治活动。
关键词:明末;崇祯历书;历法改革;作用因素
“历”是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法的根本任务在于科学地安排年、月、日,使它们既符合天体运行的规律,又适合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1]。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同古代社会的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先后产生过约百部历法,但诸多因素使得中国古代历法的论争与改革持续不断。历法的不断革新是推动明代以前天文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并在元代达到高峰。但是明代统治者固守郭守敬《授时历》而改的《大统历》,使得洪武至万历时期的二百多年间,历法停滞不前,可以说“有明一代,历无一改,甚至倒退,濒于萎缩”[2]。伴随着交食预报的一再错误和修历呼声渐起,万历年间揭开了明末历法改革的序幕。
明末历法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以崇祯二年(1629)为节点①,在此之前的历法改革,实际上以中国传统历法方法为主,而崇祯二年后的历法改革以引进西方历法为主。《崇祯历书》则正是崇祯年间历法改革的核心所在。但幾乎每一部新历法问世的前后,都会引起一场争议,历法的争论并不是局限于对历法精度的校验,而是存在着多方因素的影响。
明末历法改革的缘起,既有直接的导火索,也有其他深层次的因素存在。对于明末历法改革的直接缘起,主要依据《明史》记载:“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妻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3]根据这段表述,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崇祯改历缘起于西法推测崇祯二年(1629)日食优于《大统历》。而当时历局领导者编辑校刻,汇集呈给崇祯皇帝的奏疏《治历缘起》中保存的史料显示,《大统历》推算日食时刻误差过大是进行历法改革的主要原因,崇祯皇帝、徐光启等人从未有过预测崇祯二年(1629)日食数据优于《大统历》的表述;同时,进入清代后,汤若望上奏的改历缘由也是“崇祯二年间,因旧历舛,奉前朝敕旨修政历法”。因此,改历缘起于西法推算优于《大统历》的判定是不够严谨的。
改历的直接原因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应当是钦天监推测日食数据误差过大,与西法无关;另一方面是礼部将推算日食的误差放大,以达到修改《大统历》并进行历法改革的目的。崇祯二年(1629)的日食预报,钦天监所预测的食分、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同礼部主事黄鸣俊的观测结果“食分三分余,初亏午初一刻,食甚午正一刻,复圆午正三刻”相比,食分、复圆基本相同,初亏、食甚误差为两刻。同时,礼部侍郎徐光启亦在礼部观测日食,徐光启的推算为“食分二分有余,不及五刻,已验之果合,亦以监推为有误”[4]。西法的具体推算数据为“食分二分有奇,初亏巳正三刻二分,食甚午初二刻六分,复圆午初四刻六分”。徐光启与钦天监观测数据食分、复圆均不同,且徐光启先前推测的初亏、食甚也在两刻以上,西法的误差具体数值:初亏误差16.8分钟,食甚误差31.2分钟,复圆误差28.8分钟(表1)。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礼部侍郎的徐光启在呈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上,使用了自己的测量结果作为最终上报观测的日食复圆时刻,这使得钦天监的推算结果尽数误差在两刻,其误差也进一步被放大。礼部的奏疏同样强调修改历法符合天行,是必须要施行的。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崇祯皇帝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十三日同意改历。
但仅仅一次观测数据的错误和礼部的一次奏疏,并不能使崇祯皇帝下决心开设历局,修订《崇祯历书》,进行历法改革。明末历法改革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且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皇权统治的需求,有西方天文、历算的输入与明代历法发展的先天不足,从改革技术层面上的原因到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呼声,还有唐顺之、顾应祥、周述学、朱载堉、邢云路等人的努力等。
明末历法改革,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明代历法的先天不足。明代的官方历法,实际上是直接使用了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的历法系统。且自明初,在历法的政策上,就以“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5]来压制民间天文历法的发展。同时“(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学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6]。这两道诏令既断绝了朝野研习天文历法的通路,又把天文历法的传承局限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同时,明代使用的元统所编的《大统历法通轨》,将天文计算的过程变得标准化、简单化,同时翻译《回回历法》作为参用,形成两个历法系统,但这两部历法有过于强烈的实用性质,也就未为理论的发展和探讨留下任何空间,以至于“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7],这时明代历法的危机已经初显。伴随着明代历法的先天不足,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完成,开始向外传教,为使传教事业得到明朝政府的支持,采取了以介绍西方科学为媒介来传播天主教的策略,这也使得西方的天文学、历算在明神宗时期开始逐渐输入中国。西方的天文、历算学也影响了明朝的诸多学者与政府官员,“中国人从之游且崇信其学者颇多,而李凉庵、徐元扈为称首”[8]。他们为修订《崇祯历书》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明末历法改革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明初,太祖施行禁学天文的政策,明代天文学止步不前,倒退并濒于萎缩,而其最终目的是巩固皇权统治的需要。古人认为天文历法可以窥知天命,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是远超单纯的科学活动范畴的。《史记·历书》中“改正朔,易服色”的观点,正是为了建立起一套有本朝特色的历法系统,同时历法也是“敬授人时的国家时间计量工作、预测国家前途命运、同国家礼仪相关的工作”的必要前提,就如明代前期禁学历法是为了巩固皇权统治,明末历法改革的目的,从崇祯皇帝自身角度上来看,也正是为了励精图治,通过一番作为,来达到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明末的历法改革在这一点上,虽然同前期对于历法改革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同样是为了政治服务,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而开展的。
政策和发展先天不足,使得明代历法念旧失修,误差越来越大,《明史》中记载,钦天监官员利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对于交食的预报,从景泰年间至万历年间屡屡失误①。交食预报的不准确,历法工作对于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使得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改历的呼声日益高涨,从成化年间开始,不断有改历或修历建议出现,但是均被礼部或者钦天监拒绝而未付诸实践,直到万历年初,多次的改历建议均遭到了拒绝,或者拖延而未真正被实施。从嘉靖年间开始,民间学者和官方学者皆开始了针对历法的学术研究活动,民间学者以唐顺之、顾应祥和周述学为代表。在历法研究中,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历法原理问题,这也是明末历法改革和《崇祯历书》所十分注重的。万历年间朱载堉和邢云路针对历法中存在的问题,主张以观测和算法为基础,对传统历法进行改革,虽然成效并不是很明显,但是这对于后来的历法改革,以及修订《崇祯历书》时采用西方原理,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除去以上几点因素的分析之外,还有一些观点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如明末宫廷中天主教的传播及其宗教地位的提升,是否也影响了明朝政府决心引用西法进行历法改革;明末频繁的气候异常与自然灾害,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末历法改革的进程等。
在谈及明清之际的中西天文学之争时,人们往往会提到“精度”在其中的“裁判准则”作用,即以历法在天象预报方面的准确程度作为判定其优劣的标准。自西汉时期开始,利用科学手段来校验不同历法的疏密,以此来判定优劣的方式就屡见不鲜。精度在表面上是专业天文学家所公认的判断历法优劣的标准,但却不是决定人们对中西天文历算之学进行最终取舍的唯一因素。历法改革不是一项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科学活动,而是一项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政治活动[9]。决定历法改革成败的判定性因素是多元化的,从交食精度的准确性而言,明末历法改革是成功的,但未得到崇祯皇帝的認可,而未能颁布实施,这一点上明末历法改革又是失败的。正所谓“争论之胜方未必正确,败者未必错误;后颁行的历法未必就优于先前的历法;颁行的历法也未必精于未颁行之历法”[10]。对于明末历法改革成败的判定性条件分析,应该是从多角度去理解明末历法改革的性质。
参考文献
[1]崔石竹,肖军.追踪日月星辰:中国古代天文学[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
[2]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3](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5](明)徐光启,李康先等.崇祯历书·奏疏[M]//周岩.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6](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M].扬州:广陵书社,2007.
[7](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9][10]钮卫星.汉唐之际历法改革中各作用因素之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