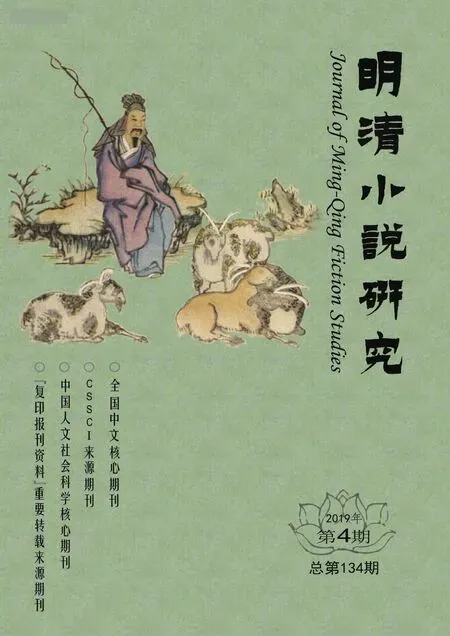试论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动态与动态人物的谐隐性动作隐语∗
·乔孝冬·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小说谐隐性动作隐语作为非语言表达方式的一种,可分为三类:一是迷人耳目,以式通情的微妙型动作隐语;二是以势示禅,禅机妙悟的禅语型动作隐语;三是以形作比,偏重心智的谜语型动作隐语。小说采用非语言表达叙事技法,彰显出文本深隐的艺术魅力,反映出作品人物动态与动态人物特殊的审美内涵,对小说人物的塑造及其作品的理解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有着一系列“运思于谐辞隐语间的作品”,谐隐乃诙谐与隐语两种手法的合一,要而言之,其类型约有以下五种:一、体物型;二、字辞型;三、谐音型;四、反切型;五、叙事型。但还有一类特殊的用身体动作表示隐语的类型,笔者将此命名为谐隐型动作隐语,谐隐型动作隐语不同于以往的“图象品物”“体目文字”和“谐音双关”,而是用身体语言的非言语叙事,直接用动作如手势表情、眼神传递、姿势妆容或人际空间等代替语言叙事,设置隐语(机锋),阅读者与当事人都面对叙述者设的隐语(局)寻求“解悟”,而阅读过程又类似猜哑谜,达到“游戏神通”的境界。中国古代小说的谐隐型动作隐语起源极早,内涵极其丰富,按照动作与内容,笔者将谐隐型动作隐语分为三类:一是迷人耳目,以式通情的微妙型动作隐语;二是以势示禅,禅机妙悟的势禅型动作隐语;三是以形作比,偏重心智的谜语型动作隐语。谐隐型动作隐语用于小说非言语表达具有特殊性,展现了中国小说特有的技法与谐趣。
一、微妙型动作隐语
微妙型动作隐语起源很早,与古代祭祀礼仪的“尸”以及“巫舞”的表演紧密相关。在中国古代祭礼仪式中,每个祭礼仪式的参与者有明确的分工,互相之间恪守各自的执掌,不得逾越。宗伯、祝、尸、巫、瞽等是主持、参与祭祀的主要成员。简而言之,祝,以诗颂神,主语言一项,不装扮人、鬼、神等“人物”。尸,是神灵或鬼雄的替身与代表,以接受祭祀者对亡灵或神明的敬祭。巫,以歌舞祭神娱神为主,又分为大巫、小巫。在祭祀时,大巫、小巫各有分工,大巫舞,小巫歌,或反之,小巫舞,大巫歌。可以看出,古代的祭祀礼仪综合诗、歌、舞、乐为一体,由不同的人员分工执掌,各司其职。《诗·齐风·猗嗟》:“美目扬兮,巧趋跄兮。”“跄,巧趋貌。”跄字连用之“跄跄”,用在朝礼或祭礼中,形容走路有节奏的样子,这里以“跄”的礼仪动作隐喻了敬意。
《史记·乐书》中有“大武之乐”的记载:
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
这里的“成”,就是每次“队伍变化成”的意思。“始而北出”,表示向北攻打封王;“再成”表示消灭商朝;“三成”表示武王南面称王;“四成”表示疆土已经巩固;“五成”表示分茅列土奖励功臣。这“三成”“四成”“五成”的动作表演,隐喻记载了具体的事件或情景,属于较早的表演性动作型隐语。
又《神仙传》“孔元方”条载:
孔元方,许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实等药,老而益少。眉批:服松苓。道家或请元方会饮,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竖,头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饮,人莫能为……后东方有一少年,姓冯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寻窟室,得见。曰:“人皆来,不能见我,汝得见,似可教也。”乃以素书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传一人,世无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无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顿接二人。可授不授为闭天道,不可授而授为泄天道,皆殃及子孙。我已得所传,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岳。后五十余年,暂还乡里,时人尚有识之者。
孔元方会饮时的绝活类似杂技表演,他把拐杖拄在地上,手扶着拐杖上端,整个身体竟然倒立起来,头朝下、脚冲上,一头长发都垂到了地上。然后,孔元方从桌子上拿起一只酒杯,就这么倒着喝酒。发掘的甘肃省酒泉市丁家闸五号墓前室西壁的壁画,上部绘跪坐的乐伎一排,男伎头戴帻(头巾),身着宽袖长袍;女伎头上高绾三髻,身着桂(宽袖长袍),右起依次为弹奏箜篌,弹奏琵琶,吹箫,拍腰鼓。乐伎的下面绘百戏:两女伎头绾双髻,身着窄袖掩襟衣裙,赤足,双手倒立,左侧伎昂首,右侧伎垂首。这种倒立的技巧,在《旧唐书·音乐志》中称作“掷倒伎”。会饮时孔元方的倒立姿势竟是一动作令,作这样的动作酒令既展示孔元方的神仙姿态,又设置了悬念,起到引起注意的效果。
微妙动作型隐语的源头还与优戏的“象人”表演相关。“戏”的繁体字是以“虚”“戈”组成,本义为角力,后引申为扮演故事之意。“戏”还有玩笑、假扮、作戏的意思,《说文解字》段注称:“以其戏言之,谓之俳。”《左传·襄公六年》“长相优”句下,杜预注:“优,调戏也。”优戏是古代专以乐舞戏谑的艺人。又称倡优、优伶、伶人等,统称为优。优的记载,最初见于《国语》。《国语·晋语》:“我优也,言无邮。”《史记》“优倡侏儒,为戏而前”,表演乐舞为主的称倡优,以表演戏谑为主的称俳优。这类“诙笑类俳优”要达到“言无邮”“谐”的目的,就必须学会“隐”的技巧。刘勰在《文心雕龙·谐讔》“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意有所指,但不明说,通过譬喻的手法来暗示。“优戏”有两种,一是“语言谑戏”,即以诙谐的话语进行打趣;二是“扮演谑戏”,即由伶人作表演的谐戏。由伶人作表演的谐戏在秦汉俳优戏中称为“象人”。据《汉书》载,郊祭乐人员,初无优人,唯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有常从倡30人,常从象人4人,诏随常从倡16人,秦倡员29人,秦倡象人员3人,诏随秦倡1人,此外尚有黄门倡。此种倡人,以郭舍人例之,亦当以歌舞调谑为事;以倡而兼象人,则又兼以竞技为事,该自汉初已有之。可见,“象人”是一类专业模拟角色的分支优伶,王国维在“象人”后面追加了两个解释:“孟康曰:象人,若今戏鱼虾狮子者也。韦昭曰:著假面者也。”孟康认为“象人”多模拟动物禽兽,类似今天的马戏。而韦昭指出象人“著假面”,假面即面具,古代面具多用以表现一类特定性格的人物,而模拟动物禽兽多不戴面具而套用模型。可见,象人者应是模拟动物禽兽和人物兼顾的。俳优象人通过模拟人物造型及行为,形成滑稽的视觉形象,旨在引人一笑。而扮演谑戏的优伶主要通过动作以达到戏谑的目的,推究起来这种通过微妙动作有意扮演的隐语也是中国哑剧最早的源头。
“哑剧”一词源于希腊语,是一种舍弃台词而以动作和表情表达戏剧情节的戏剧。“哑剧”艺术被称为“无言的诗人”,又被称为“模仿者”。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哑剧的概念,哑剧也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但是通过形体动作说故事却由来已久。刘向《列女传·辨通·齐钟离春传》记载了丑女无盐的故事,刘向先极力渲染无盐的丑,“其为人极丑无双,臼头深目,长壮大节,卬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就这样一个女子,却毛遂自荐,要嫁给齐宣王,这本身就造成了极强的喜剧效果,而她见到宣王后,并不急于表白,而是投其所好,用“扬目衔齿,举手拊肘,如此者四”的三个微妙的隐语动作引起宣王的兴趣,然后对这三个动作加以解释说:
“今大王之君国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仇,外有二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玕笼疏,翡翠珠玑,幕络连饰,万民罢极,此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强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饮酒沉湎,以夜继昼,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
这一席话让宣王惕然心惊,如梦初醒。于是去奢华,招进直言,齐国大安。丑女无盐可能是当时广泛流传的一个传奇故事,元代郑光祖根据刘向的记载,演绎了这则故事,改编为戏曲题为《钟离春安齐》。无盐安齐的叙事看点在于“我没有奇能,特有隐语之术”的机智,而隐语之术是身体语言的动作展示,这种身体动作叙事的吸睛作用远远超过了话语叙事。
《太平广记》载汉武帝巧妙地将动作与隐语结合起来,通过动作设置谜面,让东方朔破解谜底:
汉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槛,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见《太平广记·俊辩二)书中称出“东方朔传”)
可以看出,汉武帝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这则哑谜在心理上偏重“隐”,用谜语的拆字法;但形式上辅以动作和象声,获得“上林献枣四十九枚”的顿悟。

裴启《语林》有则由表层动作关联深层寓意的笑话:

另《全唐诗话》载:

“动手”是行歌舞令,“回身”也是舞蹈动作,与“伸手要钱”混异同,由此关联到“贪贿”的深层寓意。
动作手势用作隐语叙事还具有迷人耳目,以式通情的暗示功能,唐人成功地将这种暗示运用到男女情爱的表达上。如唐代裴铏传奇《昆仑奴》巧用微妙型动作隐语表达爱情:

所谓暗,语义有隐蔽、含蓄、不公开的意思;示,语义有启示,告知,影响的意思。合起来,表示不公开地隐蔽地给人以启示。从社会心理角度看,暗示是在无对抗条件下用含蓄、间接的方法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心理学家认为,用含蓄、间接的方法,对人的心理乃至生理会迅速产生影响,有人比喻说,暗示不是从正门,而是从后门进入人的意识,一般不会遭到人们意识的抵制和批判,使人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在心理上和行为上接受他人的影响。红绡身为一品宅中歌姬,身心不能自由,不能对崔生公开表达爱慕之情,只能通过眼神、表情、动作暗示对方,红绡的“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这三个动作的动作暗示比语言暗示更为丰富和复杂,不仅崔生“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一般的读者也难晓其意,而这爱情暗示的核心环节,虽然迷人耳目,却能以式通情,这种特定情境中的非语言交流,显示了爱情的含蓄隐蔽性,又强化了昆仑奴过人的机智。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其中《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用动作手势变化的隐语叙事设置误会,从而写文若虚命运由倒运到乘运的戏剧性变化:


二、势禅型动作隐语
禅又称禅那,意指静虑,即使心灵摆脱一切干扰,达到无所挂碍的境界。因此,所谓参禅就是指通过特定手段摆脱妄执,使心灵解脱,从而明心见性,体悟禅机,成佛证圣。禅是一种认识,也是一种境界。所谓知行明止,了却烦恼。需用机锋引导,以至灵光一闪,达到顿悟的目的,佛典中如拈花微笑、折苇渡江、面壁九年都颇具动作性、隐喻性。《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写道:

猴王从须菩提祖师学道,连续用隐语动作写美猴王的禅机妙悟:“祖师打他三下者,叫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美猴王打破“盘中之谜”,三更受道故事源本于《坛经》五祖弘忍大师“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的典故。

冯梦龙《古今笑·丘浚》条载:

释珊的“接是不接”,貌似借“不接”与“接”的动作说明禅机,实为自己的行为做强词夺理的辩护,而被丘浚识破,丘浚用“打是不打”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文人化、世俗化的参禅转为一种游戏。又如《儒林外史》杨老六用了权勿用的银子,反过来借用权勿用的名言“你我原是一个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甚么彼此?”可见明清小说参禅世俗化、谐谑化的普遍性。
乐天大笑生《解愠编》《不语禅》和李开先《打哑禅》院本,进一步对和尚的参禅展开戏谑和讽刺,造成极强烈的戏剧效果。

李开先《打哑禅》院本大概是化用乐天大笑生《解愠编》中的《不语禅》而来,写汴梁相国寺僧悬帖打哑禅,胜者可得十两黄金,一个完全不懂参禅的屠子竟然撞了大运,令长老输得心服口服。参禅过程是:


三、谜语型动作隐语

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中对“谜语”的起源及其作用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

谜语型动作隐语以形作比,展示游戏精神,表现心智。谜语作为一种游戏,它也预设了一个社交的圈子,进入这个圈子,就要懂得并遵守其中的语言游戏规则。
《三国演义》第九回《除凶暴吕布助司徒,犯长安李傕听贾诩》谜语型动作隐语是:

董卓听到的拆字型文义谜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不悟其义,道人的谜语型动作隐语暗含玄机,毛宗岗评“明明是吕布二字”“葫芦提的妙”,董卓的“葫芦提”使得他很快成为游戏规则里的悲剧人物。这里的动作语言成为一种标记性语言,道士手执两头“口”字的缚布长竿,作为一种旗语,形象地预示了董卓将被吕布杀死的命运,旗语作为标记性语言传达的信息比语言表达的信息更为丰富、形象、生动。采用字谜和旗语动作的隐语叙事,让读者找到事物关联的方面而瞬间获得感悟,设谜解谜的过程自然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
清代李汝珍《镜花缘》写了谜语六十九则,其中不乏即景创作的动作型谜语。小说第八十回写到:

李汝珍善于通过一系列动作演示设置谜语并通过动作变化解释谜语,并谈到如何巧妙地设置谜语,什么才是好的谜语,谜语是一种具有娱乐作用的游戏语言,大凡做谜,自应贴切为主,谜语除了具有娱乐性而外,还要具有隐秘性,谜面没有遮蔽谜底的功能,叫做“对景挂画”或“面糊未干”。同时谜面又要具有导向谜底的功能:“因其贴切,所以易打。那难猜的,不是失之浮泛,就是过于晦暗。即如此刻有人脚指暗动,此惟自己明白,别人何得而知。所以灯谜不显豁、不贴切,谓之脚指动最妙。”并通过春辉与玉芝用身体语言解释难猜的谜语是只有自己明白的“脚趾动”。如此深奥的谜学理论,是通过才女们一连串的即景动作表现出来的,因而动态地展示了才女的聪明博学。
四、谐隐性动作隐语展示非语言表达的特殊魅力

注释:

②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42页。
③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75页。
④⑩ [宋]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2、1292页。
⑤ [汉]班固《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3页。
⑥ 王国维、吴梅《宋元戏曲史·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页。
⑦⑧⑨ [汉]刘向《列女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