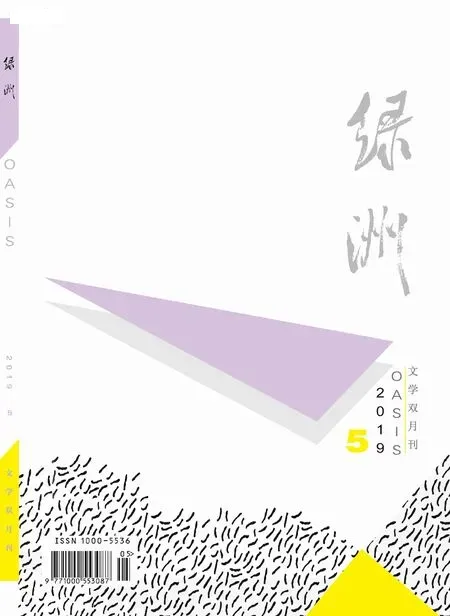“流动”的学校
吴新平
高中毕业40年了,我的中小学生活,是跟随父母所在的工作单位在迁徙中度过的。当年,父母所在单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三师23团是一支建筑工程部队,在南疆浩瀚的戈壁滩上走南闯北,承接工程,学校随着连队“流动”四方。
1969年春天,我们连队工一队正在南疆泽普县修建东岸大渠。有一天,两位具有初中文化的女同志挨家挨户去登记适龄孩子,原来她们是连队里挑选出来的老师。太高兴了!我们连队准备办学校了。到了我家,我还不足7岁,老师说,连队孩子不多,可以入学。登记我的名字时,父亲想了想,说:“叫吴新平吧。”母亲说不好听,去掉“新”字,单名叫“平”就行了。父亲是志愿军转业干部,他说:“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为了新的和平,还是叫新平吧。”就这样,“吴新平”成了我的学名,我的小学生活开始了。
大约读了一年,连队合并,我们被合并到工三队。由于有新任务,连队的男职工搬到了巴楚县农三师53团去施工,一时没有搬走的家属们被合并到工二队,我又到了工二队小学上学。在这里,由于我学习及各方面表现突出,我居然还成为学校“三结合”领导班子成员。所谓“三结合”,就是学校领导、家长和学生共同管理学校。一个二年级的孩子懂什么呢?只不过是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形势的一个需要罢了。在工二队小学读了两年,我们便搬到巴楚县农三师53团,在15连住下了。这个连队小学一共有十几个孩子,各年级都有,一年级学生有十几个,可以组成一个班。另外我们6个孩子中分别有3个四年级、1个三年级和2个二年级,于是就让三年级的孩子留级到二年级,我们6个人分成2个班在一间教室里开展复式教学。老师给二年级上课时,我们四年级的做作业;给四年级上课时,二年级做作业。我们就一位老师,名叫谢经式,语文、算术、美术、体育……什么课都是他一人教。
这位谢老师是山东人,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读大二时被错划为“右派”,后来“发配”到我们连队改造。他有极好的古代汉语功底,非常喜欢孩子,热爱教书育人的事业。学校仅有一排房子,三间是教室,一间是老师宿舍。他带着我们学生去割沙漠红柳,给校园筑起篱笆围墙,又请连队的木工做了一个秋千,还用土块搭了乒乓球台,一个像模像样的连队小学校诞生了。在当时,引来了其他连队多少双孩子们羡慕的眼光啊!每天下课后,他都带领我们开展体育、文艺等课外活动。吃过晚饭,他给我们讲《水浒传》,讲《三国演义》。即使到今天,他生病了躺在床上,我们围在他的床边听他讲故事讲古诗文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当时物质奇缺,一块挂在墙上的铁皮就是我们的黑板,课前课后我们要到处去捡土疙瘩当粉笔用,但是我们的眼界被打开了。谢老师请连队里有特长的北京、上海知青到学校,有的教我们唱《三弦》、唱京剧、排文艺节目,有的教我们打乒乓、荡秋千、下象棋,校园成了当时连队繁重枯燥的劳动后最轻松、最有文化气息的聚集地。孩子们吃过饭就想去学校,职工们劳动之余也愿意去学校,那里有人读书,有人排练节目,有人打乒乓球,有人打羽毛球,有人荡秋千,有人下军旗、跳棋和象棋……多么生动丰富的生活场景。至今想起,我仍觉得心有余热。我们小孩子排好节目后会到劳动工地去为大人演出,我们唱的《三弦》还被选到团部去演出,非常受欢迎。这样的小学生活虽然只持续了一年多,却给我留下了最丰富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
是的,我们又搬家了。国家要建设南疆铁路,兵团组建铁路工程局,把原工三师23团抽调到阿拉沟。按惯例男职工先去打前站,家属们集中到53团团部等待随后搬迁。于是我在53团团部学校上了五年级的下学期。在这里我见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魔术表演,农三师文工团来学校慰问演出,魔术师在舞台上变出鸽子,变出钱,简直太神奇了!
男职工在阿拉沟盖好半干打垒的房子后,我们就跟着搬到阿拉沟。可是到了9月1日,学校没有盖好,直到10月中旬,我们才开学。我的初中一年级就是在阿拉沟开始的。
印象最深的是数学老师,她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上海知青,人长得十分漂亮,课也讲得好。只是刚上初中的男同学十分调皮,常常搞出各种恶作剧。他们会在老师进教室前,把扫帚放在虚掩的门上,老师一推门,扫帚正好掉在老师身上,引来他们哄堂大笑。男孩子不爱学习,满肚子的坏主意,把课堂搅得上不下去,常常看见老师忍住委屈的泪水,继续为我们上课。不过,更多的记忆是老师带我们去爬山,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讲很多的格言警句。她教育我们不要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个比喻多么形象,一下就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可能是考虑到建筑工地经常搬迁,团里决定建一个基地,把家属和学校固定在基地。地址选在焉耆四十里城农二师27团一个叫炮台的地方。初二的时候,我们就搬到基地学校了。这个学校距离我们父母工作的阿拉沟600余公里,当时的交通条件很落后,坐汽车需要一天的时间。我们这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就这样离开父母开始了住校的独立生活。
在焉耆基地学校的宿舍是苇拱房,就是用椽子先搭成类似窑洞的半圆形,然后用芦苇扎成的长长的苇把子挨个紧密地搭在椽子上,再在苇把子上糊上泥巴,就成了一个窑洞式的苇拱房。我们一到学校,老师就组织我们打土块、砌火墙。火墙是北方的一种取暖设施,它由炉灶、火墙体和烟囱三部分构成。火墙体是用土块砌成的空心曲回烟道,墙内可砌成竖洞、横洞、独洞、花洞等多种形式的烟道。热烟气通过火墙体向屋内散热。烟囱是火墙的排烟通道,必须有足够的高度,火墙的炉灶可以做饭。打火墙可是个技术活,炉灶、火墙和烟囱设计合理,炉火熊熊,屋内热气腾腾。如果设计不好,火墙烧不热,还满房子倒烟。这时才发现男同学是多么能干,他们也只有十三四岁,不仅能打出标准的土块,还能砌成十分像样的火墙。十三四岁的孩子,既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如洗衣服等,还要帮助学校的食堂做事。食堂需要的煤炭都是我们一车车卸下来,食堂冬储的大白菜,也是我们一棵棵卸下车,再一棵棵码好。那时我是学生会主席,样样要带头。送煤车、送白菜的车半夜三更到,我立即起床招呼同学们卸车。卸完了,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但令人欣慰的是,和以前我们随着建设部队搬来搬去,没有固定的学校,从来没有按时开学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了。现在学校有了固定校址,每学期都能按时开学,学校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最难忘的是我们的迎新年联欢会和全校运动会。学校老师大都是上海、温州知青,个个多才多艺,他们教我们唱歌、跳舞、排小品。逢年过节,老师带着我们用彩纸装扮教室,做迎新年黑板报,班班都开联欢会,击鼓传花,师生同乐,笑声满堂,十分开心。
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土操场,开运动会之前,团里派了宣传科的同志专门为我们画宣传画。开幕式上,国旗队、会标、彩旗队、裁判员、运动员依次入场,我们迈着正步走过主席台,无比兴奋。运动会三天,操场上热闹非凡,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同学们龙腾虎跃,你追我赶,创造了很多惊人纪录。后来我们曾派代表队参加了焉耆县的中学生运动会,我们学校运动队的成绩遥遥领先。每每想起上个世纪70年代的这场运动会,我都觉得十分感动。我们的老师以他们在大上海的标准,在新疆边远偏僻的学校认认真真指导学生参加体育运动,让健康、青春、激情、竞技扎根在孩子们心底。它在我心里没有任何缺憾,是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奥运会”。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团里把平反了的“右派”选派到学校做老师。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物理老师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化学老师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他们都是在上大学时被错划为“右派”的。虽然大学没有毕业,但他们的基本功扎实,特别是他们的教学态度令我们终身难忘,受益一生。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我们除了教科书,什么复习资料也没有。老师们千方百计地通过自己在内地大城市的同学、家人,找来复习资料,刻钢板用油墨印刷,手工装订一本本复习资料送给我们每一个同学。有的老师因为刻钢板把手磨出厚厚的老茧,有的老师装订时把手扎出血,却不曾有半句怨言,只想着让我们学到更多知识。
我们学校1978年有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当年考取了2个本科大学生。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的,当时我们12人参加高考,5人考取了本科院校,黄明奇同学以新疆数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我和韩玲玲考取了石河子农学院,金文同学考取了塔里木农垦大学,马金富同学考取了新疆工学院。
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这一年,中国高考步入正轨:从这一年开始,高考试卷由1977、1978年各省、自治区分别出题改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并一直延续到2000年;从这一年开始,高考考生由历届生为主向以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过渡;从这一年开始,高考时间定为7月7日至9日,并一直延续到2003年;从这一年开始,高考模式稳定在二十年以上,直到新千年。据马国川、赵学勤所著《高考年轮》披露,1979年高考,汹涌如潮的报考大军不亚于前两届,全国有近470万人报考,六百多所高等学校共录取新生27万多人,录取率为5.74%。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远偏僻建筑单位的子弟学校,高考录取率竟达到41.6%。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况且我们其他同学有的考入中专,有的参加工作后通过成人高考继续学习,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后来也逐步取得大专学历。虽然我们的学校一直在迁徙流动,但因为有了那些优秀的老师,文化依然在荒漠戈壁中流动传承,所以,我们虽生活在蛮荒之地,却依然能脱颖而出。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母所在的单位决定在石河子红山嘴建立基地,于是又在那里新建了学校。那时我已经在石河子农学院毕业留校工作了。有一回,我专程回去看望老师和学校,整整齐齐的校园,分成中学部和小学部,我十分开心,我们团终于有一所固定的、初具规模的学校了。但是,后来随着企业改革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把学校、医院等社会事业交给了地方政府,学校逐渐萎缩,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子弟学校就这样在“流动”中汇入社会发展的洪流之中,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