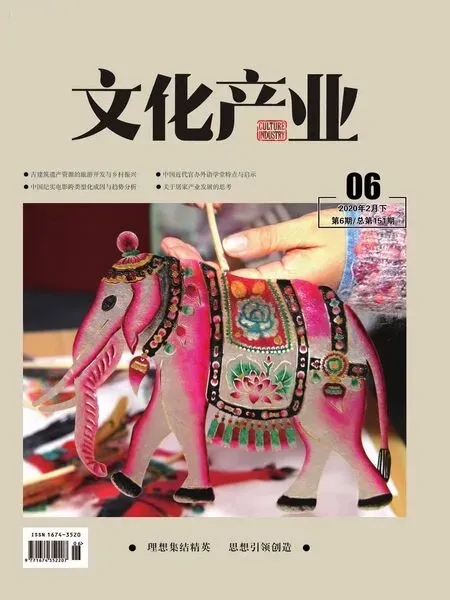满文化翻译掠影
——历史上的满族翻译家
◎吕 晖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我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满族是我国的古老民族之一,原居白山黑水一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1]。
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离不开翻译,我国的满文翻译工作至今已有逾四百年的历史,学者任世铎与屈六生将其分为两大阶段,清代至民国是以汉译满为主的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则是以满译汉为主的第二阶段。其中,季永海将清代的满文翻译工作以1644年为界,分为入关前与入关后。国外有关满文翻译的历史可追溯至17、18世纪,由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发起[2],清王朝覆灭后,国外的满学研究几乎止步不前,直至20世纪60年代,萨满研究重新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如今,随着对满语资料的挖掘、整理、翻译和开放,满学及清史研究逐渐成为显学。
本文以民族身份为满族的翻译家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脉络结合满语发展为主线,在皮姆翻译史研究方法指导下,参考《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翻译通史》《中国翻译家研究》等专著及相关论文,共搜集、整理到25位民族身份为满族的翻译家,以期勾画出满族翻译家的群体特征和发展流变。
一、清代的满族翻译家
清代的满族翻译家主要以达海、希福、阿什坦、和素等为代表[3],他们本身精通满汉两种语言,主要进行的是汉籍满译工作,目的是丰富满族历史、语言及文化,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朴素的翻译理论。
达海(1595-1632)是满族文化史上的翻译之祖,学界对其研究较多。达海改进老满文,创制新满文;精通满汉语言,是皇太极所设文馆的首领,深谙翻译之道,翻译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汉语著作,其中尤以《三国志》著称,其译作备受皇太极推崇,成为满族统治者政治知识的来源。希福(1589-1653)是另一位曾获得“巴克什”(满语博士)称号的翻译家。希福在内国史院供职,除担当文字工作以外,还负责考察军队事务,这与其翻译著作的内容不无关系。阿什坦(?-1683)是清初有名的儒学者和翻译家,他任职于管文事的内院,十分重视教育风化。其所翻书籍亦可分为两类:儒家经典与教育启蒙,包括《大学》《中庸》《孝经》《通鉴总论》《太公家教》等书。阿什坦主张推行汉化,但反对翻译小说,称其“杂书无益之言”。和素(1652-1718)为阿什坦次子,任武英殿翻书房总管、皇子师。在翻译领域,他是《御制清文鉴》的主编之一,翻译了《资治通鉴纲目》《醒世要言》。与其父翻译的儒家正统书目不同,和素偏爱更具教化意义和娱乐价值的小说剧本等,其语言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4],据称,和素曾翻译过《金瓶梅》和《西厢记》。
此外,还有国史院大学士刚林(?-1651),奉命翻译《洪武宝训》,校对《辽史》《金史》《元史》的满文译本,总校《三国志》满文译本;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鄂尔泰(1677-1745),将《四书》翻译成满文,另满译了《钦定八旗则例》《钦定兵部则例》和《中枢政考》等;傅恒(约1720-1770),虽译著不多,但其贡献主要在于编纂了多种重要的词典类工具书,如《西域同文志》、大型分类满汉辞典《御制增订清文鉴》。清末,满族已多采用汉语文,满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已不复存在,满汉互译的工作也随之渐无声息。
二、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满族翻译家
民国时期满族翻译家的民族身份意识由清晰变模糊,译事活动并不局限于汉籍满译,所译语种更为多样,涉及满汉互译、满外互译及汉外互译,所译题材也更加广泛。国民党反动派实施民族压迫政策,满文濒临灭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有力保障使大批人恢复满族身份,满文的复兴才得以看到曙光。这一时期满族翻译家代表有老舍、罗信耀、傅维慈、金默玉、兴万生、赵洵等,他们所译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涉及体裁广泛,有些人虽并非知名翻译家,但其针对翻译理论的总结更加科学客观。
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在留英期间曾帮助克莱门持·艾支顿将《金瓶梅》译成英文。1936年,老舍辞去教职后,专事写作,此间翻译了法国现代小说《战壕脚》。1946年老舍赴美讲学,期间着力于中国文学的译介,他和甫爱德一起将《四世同堂》译成英文,并组织郭镜秋、熊德倪翻译了《鼓书艺人》《离和牛天赐传》,积极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为纪念萧伯纳诞辰,老舍还翻译了萧伯纳的话剧《苹果车》。老舍的译论主张包括:应保留原文风格,译文应符合中国文法,文学翻译适宜单个人翻译等。傅惟慈(1923-2014)是近代文学翻译家,50年代后期主要从事德国文学的翻译。其代表作有:毛姆的《月亮河六便士》、格林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亨利希·曼的 《臣仆》及散文随笔集《牌戏人生》。翻译家杨武能评论傅老翻译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有人敢动另起炉灶的念头。”[5]傅惟慈的翻译方法以归化为主,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体现原文的风貌与精神。
此外还有法国莫里哀喜剧的中国译介者赵少侯(1899-1978),从事科技论文英汉翻译的罗信耀(1908-1992),从事俄汉翻译的南致善(1910-?)、佟轲(1925-2002)、作家赵洵(1917-1988)等,从事日汉翻译的金默玉(1918-2014)、剧作家赵明(1919-?)等,著名戏剧翻译家英若诚(1929-2003),儿童文学译者邵焱(1939-?),医学领域译者郎景和(1940-?)以及致力于百科全书事业及满语研究的清太祖努哈赤之十三世裔孙爱新觉罗·文蓬(1922-2013)。
三、改革开放至今的满族翻译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就十分重视满语人才的培养,相继在大学、博物馆和各地方开设满语学习班,培养了一大批满语研究骨干,使之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满语研究和翻译的储备人才。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系统地开展了对满文的整理、翻译、校点和出版工作。目前,中国从事满文档案整理与翻译工作的人数约占全部满语文工作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主要工作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和黑龙江省档案馆及各大高校[6],如关纪新、赵志忠、赵令志、关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