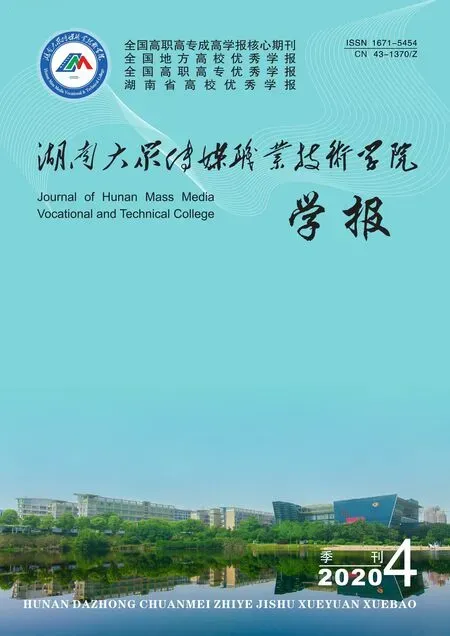改编策略与文学反哺
——张艺谋电影的文学改编研究
段金龙 孙 琦
(信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一直以来,文学作品经常成为电影导演创作的基础,它是电影故事内容的支撑。同时,电影是文学作品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二者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第五代导演开创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新时代,他们的成名作大多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其中张艺谋最具代表性。在他的早期电影作品中,大部分改编自优秀的小说作品,从1987年改编莫言的《红高粱》,到2000年改编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再到2014年电影《归来》对《陆犯焉识》的改编,足以看出他对文学作品的青睐和倚重。在张艺谋导演的23部电影中,14部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他准确抓住各种题材文学作品与电影的契合点,并运用纯熟的策略进行改编。
一、张艺谋电影的文学改编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电影传入中国,一些文学作品、历史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其中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审美特质等方面都受到文学经典的影响。同时,电影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拍摄方式诠释文学经典。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版本在声效、色彩、图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其改编方式也由忠实原著到戏仿、大话。[2]在根据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早期电影中,凌子风执导的影片最多,《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狂》都是改编比较成功的影片。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第五代导演学习、借鉴当时国外的先进电影创作理论,并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用新技巧尝试不同的风格,并在电影影像化方面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新时期电影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从20世纪80年代对先锋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开始,张艺谋着力于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他先后改编过不同作家、不同题材的小说,并在文学作品影像化的过程中完成了从文学的抽象语言到电影的镜像语言的转换,从小说人物到电影人物的转换,从小说线性时空到电影多维交叉时空的转换。
张艺谋认为,中国电影与文学难以分离,两者存在直接的共生共荣关系,诸多作家的优质小说为电影开启了再创造的空间,否则中国电影的很多作品将不复存在。[3]电影需要文学作为支撑,文学为电影提供养分。著名电影理论家巴赞认为:“电影是年轻的,而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却同历史一样古老。儿童靠模仿周围的人得到教育,同样,电影的演进也必然受到各门成熟艺术的影响。”[4]文学是电影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二、张艺谋电影的文学改编策略
在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中,张艺谋通过叙事视角的变化、故事情节的删减、叙述方式的转变,使得电影在文学的滋养下实现升华。
(一)叙事视角的变化——以《红高粱》为例
电影《红高粱》根据莫言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无论在精神气质上还是在电影形态上,这部电影都表现出与文学原著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叙事视角。在小说《红高粱》中,作者打破了常规的叙事手法,将多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这样的叙事视角直接把“我”带入故事语境,带入历史现场。所以作为叙事者的“我”,不仅不是局外人,反而能够知道“我爷爷”“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甚至知道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莫言在创作上有着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视角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5]从这一点来说,小说《红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是作者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借鉴和创新。但“我”又并不是从始至终都全知全能的,在对许多场景的描写中作者又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这就由“我”讲故事变成了“他们”讲自己的故事。
小说原著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主人公,电影《红高粱》则以“我奶奶”九儿为主线,故事线索由多重叙事转为单一叙事,并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事。九儿19岁时,不得不嫁给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50多岁的李大头。九儿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鳌产生了感情。李大头死后,九儿独自撑起了烧酒作坊。九儿的儿子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九儿去看望余占鳌,却被鬼子的机枪击中。愤怒的余占鳌和大家一起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最后电影定格在九儿的儿子在她身旁唱起童谣:“娘,你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影片一开始,在全黑的画面中传来“我”的叙述:“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这是一个以现在时进行回述的视点,“我”此时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我”并没有在电影中出现,按理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但“我”同时是电影中人物的后代,这使得“我”具有某种参与意识,从而具有被叙述者的意义。这一新颖的叙述视角,给予了导演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随着叙述的闪回和将故事作为背景的处理,影片中的历史场景产生了一种间离效果。
(二)故事情节的删减——以《归来》为例
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的结尾部分。张艺谋在改编过程中的重新架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删除多余人物。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等待他丈夫归来的爱情故事。人物很少,两位主人公撑起整部影片,并且只保留了冯婉瑜的女儿丹丹、邓指导等几个主要人物。在影片后半部分,丹丹的戏份也不多,导演把一切无法衬托男女主人公感情的人物都进行了弱化处理。陆焉识是上海旧知识分子,本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少爷,后遭到文革迫害,逃狱后又被抓住。文革平反后他回家,此时的妻子冯婉瑜已经不认得他了,但他不放弃,坚持使用各种方法唤回她的记忆。冯婉瑜是人民教师,深爱自己的丈夫,因受到过革委会成员的伤害而失去记忆。两人分离的导火索却是女儿丹丹,出于自私和虚荣心,丹丹作出伤害父母感情的抉择。张艺谋摒弃其他人物,仅以极其简单的人物关系表现了一个细腻、坚贞的爱情故事。
二是删减情节。电影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情节,抓住主要人物的情感,层层递进,呈现简洁而厚重的情感戏。电影改编自原著小说最后30页,截取陆焉识回家的片段,并进行重新架构。电影将横跨68年的爱恋缩减为45年,内容集中在陆焉识越狱回家、平反释放后帮助冯婉瑜找回记忆上。张艺谋抓住了整部作品的“魂”,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来推动故事情节。大量删除原著情节,使电影具备了简而又简的极简主义风格。在这种极简主义中,有限的情节高度集中,在高密度的凝炼中,“归来”的意象被反复渲染和叠加,甚至成为荣格所说的原型。[7]影片最后,每到“5号”这个特殊的日子,陆焉识陪冯婉喻去接那个永不回来的自己,一家三口在《渔光曲》的背景音乐中举着牌子,等待那个“未归来的人”,白雪皑皑,音乐轻柔。这个结尾,成为这部极简主义的电影最浓墨重彩且意味深长的影像。电影《归来》也完成了一次社会语境、文学语境、电影语境的共振。
(三)讽刺意味的凸显——以《活着》为例
电影《活着》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与小说原著相比,影片中对“活着”的解读显得不那么残酷,但张艺谋根据自己的理解融入了一种独有的讽刺意味在其中。例如,救凤霞的教授因为太饿被馒头噎着,而不能去动手术,眼睁睁地看着凤霞因大出血而死亡。相比原著,电影《活着》有种入世的味道,展现出那个时代一个个生离死别、风风雨雨的农民家庭。在电影中,生活给福贵带来的变故和痛苦,使他不停地寻找依靠。“你可要好好活着啊”“咱们要好好活着”的台词反复出现,与小说形成鲜明对比。
在小说《活着》中,作者通过把人活“死”了来表达活着的意义。电影《活着》则侧重大环境下所产生的时代产物,其主旨用句俗语概括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一种让人在夹缝中求生的无力感、压抑感油然而生。
三、电影对文学创作的反哺
张艺谋曾表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存在。”[8]第五代导演善于挖掘文学经典这个富矿,把文学作品搬上荧幕。同时,随着电影事业的快速发展,电影所产生的社会热点效应也带动了文学传播的跨媒体发展,进一步促使文学原著及其作者名声大噪。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改变了整个世界,媒介改变了一切。”[9]电影特有的媒介优势使其具有超越文学的影响力,进而在文学与电影相互依存关系的基础上,电影对文学又形成了一种反哺。
首先,文学影视化带动文学作品的传播。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让文学原著及其作者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电影的宣传力度及口碑效应会促使观众重温原著,提高文学作品的受关注度。张艺谋的电影就成功推动了莫言、余华、苏童、刘恒、严歌苓等作家及其作品持续受到社会关注。其中《红高粱》的成功改编,不仅让中国电影走向国际,更掀起了一阵文学影视改编的风潮。可以说,电影受惠于文学,又反哺文学。
其次,文学影视化影响文学创作剧本化。受到电影的影视化理念影响,一些作家直接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将视听语言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用光线、声音、音响、色彩等来营造环境、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心理。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文学作品可以用大量的篇幅来进行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而受时长限制,电影只能专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例如,严歌苓的小说带有较强的镜头感,在《陆犯焉识》中出现了类似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的表现手法,这部小说因此初步具有了电影化的情节、镜头和语言。
最后,文学影视化促使文学作品经典化。例如小说原著里颠轿的过程,在电影《红高粱》里中呈现出了长达5分钟、令人过目难忘的经典场面。电影的改编,让文学作品在赢得更多受众的同时,也促进了对原著的“回读”和学界(包括文学界、影视界等)的多元学术解读,让这些文学经典焕发出新的光彩。莫言认为,经典作品的改编需要与时俱进,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与时俱进的,而他自己“一直非常支持自己作品的改编者大胆想象”。[10]
由此可见,张艺谋在使电影与文学实现共赢的同时,也给予了电影创作发展的空间。对张艺谋电影的文学改编进行研究,亦是一次对电影艺术与文学艺术二者关系的探讨。
——刘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