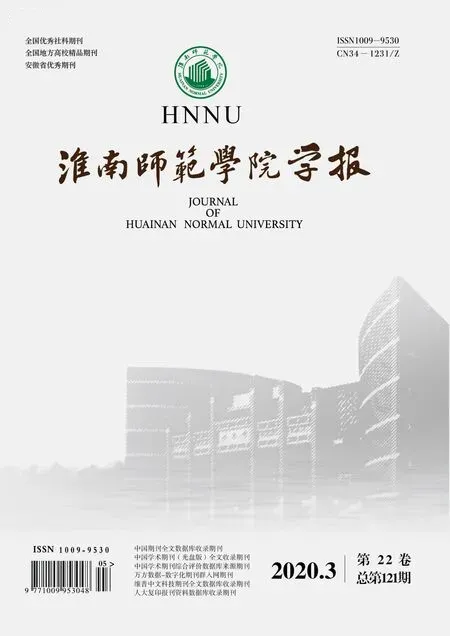简洁与隐喻
——丰子恺漫画的再解读
毕非易
(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丰子恺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文学家和艺术教育家,其漫画蕴含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无论是童真童趣、 人间情味还是事态惨象,都是其文学与美学思想的物化表现。在丰子恺创作的漫画作品中, 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影子。 “气韵生动”是对画面意境的渲染,而“似像非像”则是其造型特点的表现;同时,我们也可看到西方写实主义对漫画题材选择的影响, 写真的技法使丰子恺漫画在线条造型方面更加精简凝练。中西绘画的融合,加上丰子恺先生的美学思想浸染,使其漫画流露出“简洁性”与“隐喻性”的共生关系。
一、“融合中西”,表现笔墨情趣
上世纪初漫画传入中国,中国本土的画家根据中国社会情况和人文背景,开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漫画创作。 当时漫画是国画的分支,画面注重意境而非华美的视觉刺激,画面寓意具有讽刺、象征的意味。 中国漫画注重内涵和文化修养,这是来自于传统国画的文化烙印。漫画无论是选题、内容、表现方式还是基础造型, 都与传统绘画有着很大区别。丰子恺先生于1925 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其漫画作品,编者代为注明是漫画,这种画作的名称也被沿用至今[1](P63)。丰子恺漫画的创作风格在其留学东洋时,受到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著名漫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与启发,在技法上也多有吸收。 甚至后来评论漫画“只要不为无聊的笔墨游戏,而含有一点人生的意味,都有存在的价值。 ”
(一)漫画内容充满人生感悟
丰子恺漫画的内容多来源于现实生活,作品常用温馨简单的方式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 所感、所悟表达出来。 例如漫画中常出现的场景,无论是树叶轻点在湖面上形成的涟漪, 落日下盘旋的飞鸟,还是孩童手中牵住的风筝,都只是人民在平凡生活中最不易察觉到的日常小欢喜。而恰恰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录,成了丰子恺笔下妙趣横生的漫画世界。丰子恺曾将自己的漫画以四个不同表相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主题,可以大致概括为:描写古诗句的诗词相、描写儿童生活的儿童相、描写社会环境的社会相以及描写自然风光的自然相。四种表相互相错综交织,相互影响,共同筑起了丰子恺先生以“真善美”为核心,追求“多样统一”的审美观。
(二)漫画风格“贯通中西”
丰子恺的绘画风格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烙印,同时又受到西洋油画以及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丰子恺留学西洋回国后于立达学园一边教西洋画一边研究西方文艺理论。 在西方众多艺术流派中,写实主义无论是变现技法还是题材形式,都给丰子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多次赞赏西方绘画的写实精神,将其比作近代绘画升起的“朝阳”[2],认为写实主义对于革新中国绘画, 是很好的理论支撑。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日本浮世绘,丰子恺在写意手法上充分保留了中国画“气韵生动”的精神内核,运用毛笔勾勒寥寥数笔线条,便将画面要表现的韵味与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相较于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漫画风格,丰子恺在创作时淡化了传统漫画讽刺、诙谐、娱乐等主题,更多地加入了富有诗意的自我情感表达,而这种情感表达是“克制的”,是无声的真情流露。
二、丰子恺漫画造型的“简洁性”
丰子恺漫画的“简洁性”是指其在处理画面意境时“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独特造型的表现手法。丰子恺的漫画以中国水墨画作为外在的物化表现手法,但无论是构图、造型还是线条都与传统的中国画有着较大的区别,其中的特点之一就是其遵循“简洁性”的处理方式。
(一)构图巧妙,结构层次清晰
在画面构图及景物的透视关系上,丰子恺巧妙地结合了西方绘画的写实技法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表现。 他认为文人的透视是美学思想的表现,应高于追求空间真实性的画理透视,在绘画创作时他更倾向于用诗人的视角来进行画面布局。丰子恺曾在文章《绘画改良论》中提到如何融合中西方绘画技法的七个要点,其中第四点“重透视”、第五点“重构图”便是借鉴了西方绘画科学、严谨的绘画方法。 但是在丰子恺看来,中国绘画中的透视问题并非是错误的,而是中国画为了作品的艺术性而创造出的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画通常以诗人的视角去观察和记录画面, 因而有意忽视了透视的原理。 如王维在《山水论》中说的“丈山尺树,寸马分人”[3], 其目的是为小小的人物观看山水画提供线索和指引,这样人们在品画时目光能够游历于画中场景,达到精神上的愉悦。 因此丰子恺的漫画简化了复杂的人物场景关系,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加入了透视与框景构图,并且尤其擅长以近实远虚的表现手法表现诗词中的意境美。这种框景构图的方法在其漫画《豁然开朗》《警报做媒人》中均有表现,虽然一个是描绘春光湖色,一个是表现战争时代下的浪漫爱情,但两幅作品都通过层峦叠嶂的山石表现出画面的纵深感,将画面中心的景物或人物聚焦于人们眼前。
(二)造型概括,画意表现悠远
丰子恺漫画的“简洁性”还体现在其巧妙地将人的情感思绪凝练成具有可读性的视觉符号语言,以此展现漫画的主题。 画面中的自然景物、动物植物、甚至人物动态都成为具有图形化、指示性特征的符号语言。 例如枯树、大雁、明月日出等,经常出现在丰子恺漫画的场景之中,作为画面景色的描绘来烘托整体氛围,表现出萧瑟黯然或春风和气的意境之美。 丰子恺漫画较常见的画面形式之一,就是近景的人物背对画面,目光则向远景眺望。 人物的动态牵引着读者的视线,也牵动着人的思绪。 而在描写童真童趣的儿童漫画里,丰子恺则常常将枯树换成春意盎然的柳树、青草,再画上风筝、蝴蝶、飞燕等美好的景物以尽量捕捉那个时期未被淹埋的人间情味。
丰子恺漫画中一些人物的造型并不局限于细节描绘,而是着眼于概括地表现人物形态。 特别是某些人物的五官方面,有时甚至连眼睛、耳朵、鼻子都不去勾勒。即使描绘,也是“一折为鼻,勾点为眼,两点为嘴,斜扫为须,一左一右两线跌宕起伏,又将人物的衣袍生动的表现了出来。 轻描两线,宛然于眼前”[4](P7)。 他通过写意的方式去刻画人物,特别是儿童的活泼、生动,从画面的整体表现来看,也是和谐、空灵和充满诗意的。 这种含蓄曲折的减法手段突出了画面的意蕴,让读者在品画的过程中通过想象在脑海中自己勾勒出“残缺”的画面,从而品味出漫画的意味与韵味。 不以细节为重,而从整体关系把握画面效果,这一逻辑也符合中国古人在明辨是非时的大局观。 在这种逻辑影响之下,丰子恺漫画风格表现出“简洁性”。在《笑问牵牛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中,一家人在庭院中围坐一起,吃瓜摇扇赏月。 女儿依偎在母亲怀中,指着钻出云层的一弯月牙,喜笑颜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欢快氛围,便通过摇扇、明月、竹凳等简单的视觉符号营造出来。
(三)线条简练,引人细细品味
丰子恺的漫画中笔触笔法上线条的作用不仅仅是对客观事物轮廓的勾勒,他没有刻意追求中国传统绘画所讲究的粗、细、曲、直、刚、柔、轻、重的变化,而是简笔出新,运用简约的线条将原本事物的造型简洁化和概括化,这与丰子恺天真自然、古朴纯正的书法造诣分不开。“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家的独得之秘,丰子恺在创作漫画的过程中每当停滞不前时,亦会练习书法来调节心境。 丰子恺的绘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写意性,线条中流露出他在书法创作中小、巧、精、秀、拙的书写趣味。因此无论是对人物还是风景的描绘,丰子恺都通过线条的聚散离合、穿插错落来表达孩童般的真情、真趣。 在《轻罗小扇女子图》中,丰子恺用简介的轮廓线勾勒出女子抱扇依靠梁柱,猫儿蹲坐在台阶上的画面。 虽然没有五官表情的刻画,但这一人、一猫之景,仍能让读者感受到女子望向远方时思绪万千的心境。
三、丰子恺漫画画意的“隐喻性”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富有韵味,具有浓郁的“隐喻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上运用“古诗新画”的形式呈现画意,二是在利用漫画批判现实时内在心理表现出情感的克制。
(一)“古诗新画”中表现出形式感
丰子恺漫画作品中运用了“古诗新画”的表现形式,为漫画赋予了新的意义。 “古诗新画”以图画为背景,诗词文字为点缀,使作品富有诗情画意而又耐人寻味,并富有生动的哲理感。 画面构图时经常使用“留白”赋诗词于其中,让读者诗画共赏,透过诗词文字来点明漫画的“象外之意”。丰子恺的目的是运用诗词文字和漫画结合的方式渲染画面的意境,同时,诗词在漫画中也起到叙事抒情的作用。丰子恺漫画的特点之所以被称为“古诗新画”,正因为漫画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对诗词所描述场景的再现,甚至并非原诗之意,其或是融入了丰子恺个人的所思所想,或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新解读,这样,诗词可从某种程度上点明漫画图像的朦胧意境,也正因如此,每个人看丰子恺的漫画都会有不同的感悟。如在《明明如月,何时可掇》中,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原本表达了贤才难得的忧思,但经过漫画的处理,明月之上出现了和平二字,意在突出战乱时期人民对于和平景象的殷切期盼。
丰子恺漫画蕴含着疏密对照的留白之美。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素来就有“画留三分空,生气随之发”的说法[5],主要指的是在画面布局时,通过留白的形式对画面内容进行意境之外的情感延伸。丰子恺漫画构图时就讲究整体画面的布局,以期做到疏密有序、张弛有度。 其整体构图大胆,常常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往往利用精妙的留白和突破视觉习惯的透视,使画面增添空灵而又悠远的意象之美,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留给读者自由驰骋的想象空间,让人在欣赏画作时获得超越画象之外的审美感受。 在局部细节部分,特别是对于人物五官,不多做刻画,而是以貌取神,利用肢体语言丰富人物的心绪情感。《春日游》描绘的是一家人登山赏杏花的场面, 其中近景是人们行走在山间石阶,小路两侧柳树依依,杏花随风飘散;而远景则是山峰耸立云海之上,画卷的上半部分便是作为天空的大片留白。观画者的目光会先留意到台阶上游玩的众人, 随后会跟随飘落的杏花注意到杏树以及远处的山峰,这样随着视线的游顾,思绪亦会跟着留白的天空飘向远方,享受画面所营造的意境之美。
(二)情感克制下的批判性
丰子恺漫画题材的选择除了诗词意象以外,多以生活的琐事、 玩闹的儿童以及社会百态为主,带有写实主义的色彩。他以漫画的形式揭露旧社会的丑恶一面,但从内容的表现形式来看,又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 因为无论是对儿童的喜爱与同情,还是对旧社会的批判与厌恶,在丰子恺的漫画里表现得都相对“克制”。丰子恺在《不宠无惊过一生》一文中谈道,“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6],正是这种内心温柔悲悯的心境,使他在看待事物时往往保持心性的纯粹,将淳朴平淡的诗句和画风浸润在其漫画作品中。 他的六本《护生画集》则将其大爱、善良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画会让人心生伤感之情,但又会巧妙地将这种情绪包裹在情趣莞尔的画面之中,使人转瞬间会心一笑。他极力把孩童身上与生俱来的美好天性展现出来,借儿童的世界观同现实世俗化成人世界相比较,把成人世界滑稽、虚伪、阴险等病态“暴露”出来,这其实是一种人性的呼救,是通过至真至善的人性来影响现实人生,选择的途径则是选取了孩童般浪漫的表达。
丰子恺先生经历了民国旧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历史重大变革阶段,其对于战争时期的苦难情境刻骨铭心。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受“漫画必须针对群众的思想问题” 这一政治路线的影响,丰子恺的漫画主题开始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描写。 他的方式不是批判,而是开始拿起画笔描绘出他理想中的乌托邦世界。 丰子恺含蓄且真实地用“艺术美”揭示了苦难、丑恶及残酷的事实,他从艺术与人生的角度发出一种深刻的感悟,通过对孩童理想之境的礼赞、向往,反衬现实中成人世界的虚伪、残酷,以此表达他自己对人生无常的感慨。 此外,也许是丰子恺在弘一法师影响下深悟佛性的缘故,其作品中处处可感受到仁爱精神。
例如其作品《最后的吻》,丰子恺进行了多次修改,每一次都有着不同的心绪。 第一次是丰子恺看到育婴堂的“接婴处”门口徘徊着怀抱婴儿的男子,男子的惨淡愁容与婴儿天真的笑容触动到了丰子恺,随之创作了漫画《接婴处》。 过后,丰子恺觉得“接婴处” 这个名字未能体现孩童要与生父就此离别的悲惨命运,于是重新创作,改名为《笑涡》,以笑写泪。 再后又在弄堂口看见一位年轻的母亲,因为生活困难养活不起孩子,只能忍痛将孩子送往育婴堂。在分别之际,母亲依依不舍地亲吻孩子的脸颊,而与这对即将分离的母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墙角处的狗和它的幼崽。 随后,他又进行第三次重绘,最终取名《最后的吻》。 《笑涡》主要表现懵懂无知的孩子将要被自己年轻的父亲亲手送入接婴抽屉时其脸上的笑容;而新作《最后的吻》欲表达的是年轻的母亲准备将心头肉送进接婴抽屉时,给孩子的最后的爱。 从首幅作品《接婴处》到终稿《最后的吻》,丰子恺三易其稿,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丰子恺就是用这样的作品,表达出自己对于饱受战争折磨的普通百姓的同情和其爱国救亡之心。
丰子恺认为过于“触目惊心”的作品内容反倒会让世人逐渐麻木, 他想做的是站在审美的角度,利用温情的画面唤起人们心中的“真善美”。因此他在反映苦难、悲惨甚至丑恶时往往是“克制”的,他用自己最真挚的艺术美的表达, 涵养着人的慈悲,这升华了他对于生命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四、结语
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丰子恺的漫画作品,从中既能看到“气韵生动”的形象美与意境美,也能看到他摄取西方绘画对于透视和构图的运用。他推动了20 世纪中国绘画的革新,为后人开辟了漫画这一新的绘画创作表现形式。 美在至简,使得丰子恺漫画呈现出自然质朴的“简洁性”;而在创作漫画的过程中丰子恺先生悲悯、温和与博爱的人生观浸润其中,让其作品表现出独有的“隐喻性”。 也正因此, 丰子恺先生的画即使放在今天,仍然能传递出“仁爱”的思想,无论是其造型上对具象物体的符号凝练,还是利用“诗词新画”的形式对于气氛意境的渲染,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