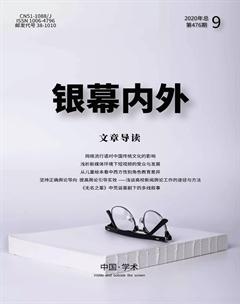当文学走向荧幕
摘要: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大众传媒方式的进一步改变,使得文学作为一种原本以文字为主要传播媒介的艺术越来越多的以影视改编的面貌介入人们对于文学的接受。影视剧的改编使得文学本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其对于文学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随着多种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介入,未来的文学应该朝何处去?这都是现如今文学面临的亟待讨论的议题。
关键词:文学本质;大众传播;影视剧改编
一、关于文学本质的讨论
“何为文学?”“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文学理论研究的本源及终点何在?”弄清楚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在文字出现初期到现在一路的发展历程,以及这种发展历程之下亘古不变的本源,是一个无论是初读文学作品还是文学理论家一直在如火如荼地探讨和感兴趣的问题。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大众传播媒介方式的不断改变,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以影视剧改编的面目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眼中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这类现象,自然也有着不同的地位。
(一)本质主义的“最大公约数”
本质主义坚定的认为,无论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何演变发展,以及非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如何去判定有文学性的存在,都是因为文学的本质有着历史建构的基本规定——“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基本媒介而进行的人类审美情志只创造,传达和接受,其关键词为‘语言文字、审美情志、创造、传达和接受”。
顺着杜书瀛老师的本质主义旗帜所带领下的这一“概念”中不难看出,所有可以称之为“文学”的作品中的最大公约数被寻找到了,其中“审美创造”更是重中之重。没有审美性质的文字只可以作为文字存在,因为有“美”才有了文学的基本底线。
于是,本质主义所给予文学的基本定义直接将文学的本质锁定在“语言文字”创造的领域中去,任何非文字的呈现都不是文学所应该拥有的原初定义,文学只能在语言文字的领域在“审美性”上寻求更多的突破点。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什么是“审美”,对于文学理论家来说的审美是什么?对于平民百姓而谈的审美又究竟是什么?影视剧的应运而生是否是审美的直观化的体现,是否是审美走下神坛,角色走出文字具体化、生动化的代表?如果将文学单一的放置于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的今天,它的“审美”又如何实现最大化的呈现?
(二)在博弈的發展中寻找落脚点
南帆老师一直以来所持观点却不尽相同,“公约数”的观点在这里被认为是静态的图像,而任何静态的图像都摒弃了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创造和再定义。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不断地赋予文学新的定义,指出新的发展方向。学科的分界与融合一直是在博弈中不断确定自身的定位,如果是单一的独立个体的存在,其发展如果迎合个体发展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僵化的,不断围绕自我的发展必然很难找到创新与突破的存在。本质主义将文学传统认为是文学定义的必由之路,混为一谈,完全忽视了历史的发展赋予文学新的定义。人们从未想过纸质书的逐渐陌路会是在未来不可避免的问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时间长河的推移会给文学的定义带来影响,同时非本质主义学派更重要的观点是在博弈和比较中推演出文学不断变化的视角。学科之间的分界更大意义上给文学带来了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学科之间的融合不可忽视,从文学作品的电影电视改编,我们无法给文学框定一个狭小的空间任其独立的自我发展,文学作为个体在线性发展的同时必须与其他学科在相互的交汇与融合中逐渐显现自己存在的独特意义。文学作品即使改变成快餐消费下的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的演绎,即使87版《红楼梦》的演员选的多么贴近人物,表演多么真实无暇,都无法改变《红楼梦》原著的魅力所在,在一定意义上电视电影的改变还推动了文学作品的进一步传播,人们在看完电影电视后,更期待的是回归文字去品味文学塑造中人物的独特魅力。文学为影视提供了优秀的题材,影视则为文学走进大众提供了更为感性和直观的方式……由于作者与导演的审美视角不同,影视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编……小说和影视、文字和影像各有各自不同的取向,也有各自的限制。”学科的融合与博弈带给了文学和影视相同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机遇,文学冲破了传统定义的桎梏,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明天。
二、文学改编的现状与未来
(1)从原著—剧本
如果想把文学作品搬上大荧幕,绝对不是简单的将文学原著作品按照人物关系,再找到符合人物的演员加以演绎的结果。文学作品作为一个作家个人情志的自由抒发,带有作家生长环境、创作环境以及创作习惯等等的“原生态”,而而影视作品却要受到传播媒介和市场需求的限制,导演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实现作品主题、故事情节的展示,必然要对镜头语言、叙事手法进行独到的理解和诠释。此时,原著到荧幕的距离,是剧本改编者作为桥梁所体现的独特且突出的意义所在。原著当中的叙事背景与故事发生的大环境,原著中的人物关系的进一步调节,人物关系发展情节要按照时间和适合大荧幕的方式推动,一些文学作品的语言带有较强的地方性或者是文字因为时代的原因较为晦涩难懂,都要在剧本改编者的手中变为更易于荧幕表达、演员演绎和观众接受的样子。
同时,剧作者与原著作者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既然原著作者在写作时必然带有自我对于所描写事物的清晰认知,剧作者的存在就是将这一认知逐渐清晰化、明朗化的过程,剧作者在改编时自然也逃脱不了自我个体潜意识的影响,所以改编绝不是站在绝对客观角度的描写,如果能保证符合绝大多数读者心目中的原著应该有的样子已属难得。
在文学作品改编成剧本时,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类型都地位相当。诗歌、散文就很少有改变成剧本的实例,题材的限制是首要因素,小说作为一种人物关系、情节脉络、故事发展都较为完备的题材就更容易被导演看中,被剧作者所改编,也更容易演绎。
在小说中,不同的风格也是改编的重要依据。由于影视剧的受众较为广泛,因此在改编时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现实主义题材往往最容易被选择,这一题材大多发生于人们的身边事,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如张艺谋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 《秋菊打官司》( 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 《活着》( 改编自余华同名原著小说《活着》) 《一个都不能少》( 改编自施祥生的小说《天上有个太阳》) 等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运用民歌、方言及民俗道具,彰显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浓郁的地域文化,作品多表现女性的内心冲突与裂变。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大众接受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风格和题材都可以在影视剧中焕发自己截然不同的色彩。如2019年贺岁片《流浪地球》,就是改编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科技的发展使得作者在原著中所写的很多外太空和高科技的设想成为了现实的演绎,人们在电影院跟随电影完成了一次刺激的生死逃亡,这是文学作品,尤其是这一类科幻作品仅仅通过文字阅读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2)从剧本—演员
无论是提起《红高粱》的电影版还是电视剧版本,相信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九儿都是巩俐和周迅留在荧幕中的样子,她们传情而灵动的演绎成为了这一著作走向荧幕并获得巨大成功不可缺少的存在。同样,在87版《红楼梦》中,陈晓旭所带来的林黛玉仿佛就是真的林妹妹下凡,是无数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白月光。
不难看出,除了成功的改编以外,演员的选择也是从作品到荧幕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一个演员对于作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如何在几十分钟一集的电视剧或者仅有两个小时的电影中如何诠释主人公,同时,在一些经典的电影电视剧作品中,一些演员甚至带给了观众难以替代之感。欧阳奋强那多情但不滥情的眼神就注定了87版《红楼梦》的贾宝玉是不可替代的,以至于之后无论有再多的改编,观众的接受度都较低,甚至持一种排斥的态度。经典影视作品无论在影视圈还是在观众心目中的定位和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与文学经典在文学传统与惯例中所起的作用媲美。演员的塑造作为故事时间发展的灵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当今娱乐圈的浮华之气对于影视作品难出经典不免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这另当别论,期待有更多的演员专注演技,塑造出更多的经典角色。
(3)导演—荧幕
影视剧对于文学作品的叙述方式不同于文学作品本身,如果说文学作品的幕后英雄是作者一手的自编自导的话,影视作品的呈现中,导演是最为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导演的风格与喜好决定了一个影视剧的整体呈现风格。冯小刚的电影《1942》、《唐山大地震》,关注的是以国家大事件为背景的芸芸众生之态,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孕育着对于人性的揣度与思考,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
电影电视剧的演绎在导演的总调度下,通过不同的影视剧表现手段,给文学作品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剧作者、导演、演员等多方的努力之下,文学作品完成了从文字表达到影视表现的华丽转身,被越来越多的受众所接受和传播。
三、影视的归途,文学的未来
(1)文学作品改编的优缺点分析
1.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如果将文学与影视剧作为单独的学科来看,学科的分野固然不容忽视,如果没有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区别所在,大学的设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研究生博士更是在某一個学科某一领域某一观点上追求终极意义的存在。但是学科的分界是复杂交错的,并不是快刀斩乱麻式的一刀切可以决定的。学科在分界中显现出自我的独立性的同时,又在融合中体现了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和当今统治声音下的共同追求。
《甄嬛传》的成功让很多观众开始关注原著,这样的现象在当下已经成为常态,如果说曾经是因为文学作品已经成为经典后它才具有被改编为影视剧的资格的话,现在更多的影视剧的成功给予了文学作品很大意义上的反哺作用,让人们在当下这个纸质作品逐渐消亡的年代将目光再次转回到文学作品本身,这是影视剧的改编带给文学作品在如今不容小觑的意义。同样,当我们认为2019年贺岁片《流浪地球》一定是一部好片的基础,就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在与好莱坞科幻电影、漫威系列电影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对比和映照下,才显现出其作为中国科幻电影的不同意义和传达的不同精神内涵。同样,把这部电影与刘慈欣的原著再做对比,原作者没有表达清楚地科幻场景在电影中以高科技的手段一一呈现,而演员的演技再精湛,也无法表现出语言文字所表达的细腻情感。这又是电影艺术与文学艺术在对比之中更加确立了其在精神文明的塑造中所拥有的独特魅力与法宝。相互交织的学科,必须在分界中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又再融合中再度显示自己的优越点。文学与影视剧在相互融合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在相互博弈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忠诚”与“利益”
早期的影视剧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虽然有固然存在的距离感,但是大部分都本着最大程度上忠于原著的想法的开展。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四大名著的翻拍,已经成了许多人心目中不可逾越的经典翻拍作品。以至于后来出现的新版观众难以接受。但是,随着电影电视剧的表现手法的不断革新,影视行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影视行业越来越趋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越来越多的导演和剧作者在改编文学作品时,要么为了标新立异而尽量求得偏离原著,亦或者为了尽快拍摄并出成片而草率改编。这就导致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影视剧是否真的带给了文学新的生命,原著作品是否是影视剧改编最后的底线。一些作者甚至开始抵触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荧幕,过度的阐释甚至是偏离原著主流思想的阐述,都脱离了文学作品作为改编基础应该有的意义。
另一方面,过多并且泛滥的改编使得观众对于文学经典甚至有了视觉疲劳和抵触的情绪。就拿最简单的例子《西游记》来说,这一经典作品因为家喻户晓并且易于改编,近些年成为了导演的刀上鱼肉,任其肆意改编。仅仅是百度百科上显示的《西游记》改编系列电影,就有:《大话西游》、《西游·降魔篇》、《西游记女儿国》等等十余部,这些改编作品大多是拿准了师徒四人取经成功前作为凡人应该具备的七情六欲然后大肆渲染,过多情爱色彩的描写究竟是对于成神前师徒性格的合理想象,还是为了迎合当下低俗、快节奏的恶趣味,以及这样的改编究竟给以后我们的后代看到《西游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都值得我们一一商榷。
四、结语
“快”与“慢”是形容文学与影视带给这个社会,带给人们最真切感受的最直观的一对反义词,快节奏的社会带来的是快节奏的消费与接受,很难有人慢下来从字里行间咀嚼一个作者带来的一个大时代或者一个小人物的思考;“得”与“失”又是文学作品与影视在这场博弈中最贴合的一对反义词,文学究竟带给了影视什么?影视又将把文学引到何处去?无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能带给作者、剧作改编者、导演、演员、观众最大的收获应当是:永远不忘初心。
参考文献:
[1] 南帆,王伟.文学可以定义吗?——关于“文学本质论”问题的通信[J].文艺争鸣,2016(08).
[2] 杜书瀛.文学可以定义吗,如何定义?——兼论南帆、陶东风文学理论教材的功过是非[J].文艺争鸣,2016(06).
[3] 南帆.文艺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J].文艺研究,2007.
[4] 南帆.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J].文学评论,2015(06).
[5] 孙静,胡雪颖.论“读图时代”文学与影视的共生关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4).
[6] 郑云海.文学与影视:从文本到画面[J].戏剧之家,2015(02).
[7] 朱传欣.文学与影视应相互成就[N].光明日报,2016-07-15.
[8] 胡文生.论新世纪影视改编”是否忠于原著”争论的真伪[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作者简介:金兰(1995—),女,甘肃临泽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