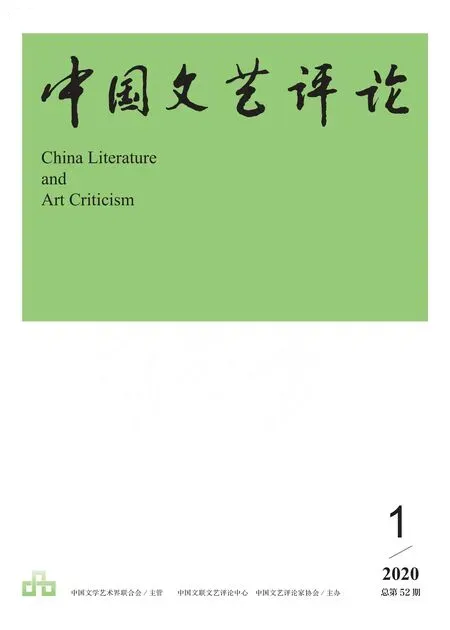厅壁传统与看待书法展厅的理性视角
杨 频
对展厅时代以及所谓“展览体”的批评意见不少[1]批评“展览体”的文章比如傅玛丽《“展览体”泛滥烘托书法圈虚假繁荣》(见《北京商报》2015年11月6日),梁厚能《惊人的相似——谈馆阁体与展览体》(见《书法赏评》2016年4月15日),续鸿明《李刚田:展览体书法需要文化反思》(见《中国文化报》2015年2月8日)等。续文总结李刚田先生的观点,提到近代和之前是“书斋时代”,1979年以后书法成为独立艺术门类,进入全新的“展览时代”。吴绍学《“展厅时代”献疑》(《书法》2014年第12期)则批评展览太多太滥,同时质疑了“展览时代”的提法,他认为,“展厅书法”不过是古代题壁书法的一种自然延续和现代展示形态,二者没多大本质区别,但古代并没有“题壁时代”或者“书斋时代”的提法。,而独立思考与深度辨析的文章却很少。批评的声音当然重要和宝贵,可以提醒书家保持良好的创作心态,注重读书学养与文化底蕴,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作品的内在品格。但严格说来,“展览体”的概念本身是含糊和矛盾的,将进入各级各类展厅的作品一网打尽,眉毛胡子一把抓,并不能概括各种层次书法作品的水平、特点与面貌。因此,这更像是一个业余书写者和批评者使用的词汇,其本意指向众多跟风浮躁、不耐品读的作品,但是这其中也包括和打击到了那些才华横溢、功力深厚和引领审美风气的自然书写,所谓一篙打翻一船人。
实际上,对于努力在书法艺术上不断深入与突破的引领型书家而言,只有作品表达的境界高下,不存在“书斋体”“展览体”这样外在的标签与概念。换句话说,展厅不是这个时代书法存在的消极词语,相反的,“文革”结束之后,展厅带来了传统书法全面复兴的蓬勃生机。从近5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因为有了展厅作为竞技与交流的平台,大家开始重视笔墨技术水准与视觉美学效果,书法领域的精英们在艺术创作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笔法、墨法、章法,尤其是形式构成方面的探索经验,丰富了传统书法的面貌。
同时,展厅/厅壁观赏本身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不完全是由西方现代展览模式嫁接来的产物,而是汉魏以来与案头观赏并行的一种审美习惯。
一、书法存在及展示的基本形式
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古老中国最重要、最牵动人心的艺术,显然在于它既附着于开辟鸿蒙的文字教化功能之上,又有着极为丰富的视觉审美内涵与人文感化力量。教化与审美,都是交流与传播的产物,这是书法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本质特征,展览展示因此成为必须。书写者若自鸣得意、闭门造车、老死不相往来,只能导致书法艺术的衰落甚至灭绝。
明确关于书写审美从实用中独立出来的较早文献记载,是西汉末期的陈遵和东汉早期的刘睦,他们的草书尺牍,当时已经成为贵族乃至皇室收藏的艺术品。尺牍材料的草书手写件,当然可以看作案头或者手头把玩之物,从此以后,2000年书写实践留下并记载了难以计数的案头作品,构成了一部延绵不绝的书法史。案头,似乎成为世人对于传统书写的当然想象之处,也有论者用了“书斋”一词,意在强调与案头类似的书卷气息,以此与当下的“问题展厅”相区别。对于案头书写的内涵,我们都可以心领神会,自然、便捷、忘我、日常,也带有一些精巧个性的味道。概言之,笔精墨妙、蕴藉风流。今天我们熟知的三大行书,包括过去文人手写的书信、各类手写的文档笔记等,基本都是案头的产物。案头似乎可以看作是书卷气、文人气的代言。
但是,书写行为必然伴随着书者内容默读和视觉反馈的问题。而书写面对的对象只有两种:自己和他者。写给自己看,与写给他者看,无论向内还是向外,本质都是一种展示和观赏。因此,除传递信息之外,展示、观赏与交流,是书法艺术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本质。
如果仔细梳理的话,就能发现一条不曾被显性描述过的线索,告诉我们传统书法存在的另一种类型,那就是展厅,确切地说,是厅壁,也包括大自然中的题记、刻石与摩崖。
从大量的古代文献和作品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掘出这条被忽略的传统线索。侯开嘉先生曾有一篇专文《题壁书法兴废史述》,讨论古代书家题壁问题,并总结说“题壁书法是宋代以前书法艺术主要的表现形式”[1]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自序,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这里的题壁,就是题写在墙壁、厅壁之上的书法作品。宋元以后,直接题写厅壁的情况慢慢减少了,但是明代以来悬挂的书画作品的尺幅越来越大,笔墨的写意挥洒程度越来越高,各种建筑中的厅壁,尤其是一些具备社交功能的堂屋与书斋,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小型的展厅。从这个角度说,一味地强调案头审美,强调蕴藉平和的尺幅小品,是比较单一的历史视角。
因此,传统书法的展示方式既有案头,也有厅壁(大至摩崖)。所谓案头与展厅在当代的“冲突对立”,也因此可以看作是一个审美伪命题,因为这两种方式很早以来就共生共存、互为补益、内核相通,皆以高水平的书写为旨归,是相互启发和促进的关系,不存在哪个一统天下、囊括万殊。明清以来的一些书斋里,悬挂的一些作品更加类似今天展厅的感觉,比如王铎、傅山及其流派后学的巨幅涨墨草书,乾嘉以后众多碑派书家的大字楹联,或者篆隶魏碑四条屏、八条屏等,都不是案头美学能够涵盖的。将当时书斋中这种强烈的厅壁视觉追求,遮蔽于案头平静唯美的小情调之下,自然不妥当。
因此,厅壁展示与观赏的历史线索,是值得梳理的,这也是在近现代西方艺术展览方式传入中国之前,我们自身所内含的一种重要的书法存在语境。
二、案头之外的厅壁传统
传统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了书法展示与观赏的“厅壁”式存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衙门、驿站、旅舍、交通要道等处壁间的布告、法令、月令等行政治理内容,宫庙、宗族或墓葬等地石碑与山野摩崖上的训诫与歌功颂德,街市的店招、广告,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师资安排(如近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两块东汉石碑),权威颁布的儒家经典版本(如洛阳太学门口林立的熹平石经),至迟到碑刻蜂起的东汉,各种厅壁类空间的展示与观赏,已经成为书法存在语境的重要内容。
静态的厅壁展示与观赏之外,我们从文献中还可以读到很精彩的动态展示过程:大书家即兴题壁书写,而观者云集如堵墙。最早的有意思的记载是东汉末期的著名书家师宜官,其书写水平在高手云集的鸿都门学书家中号称第一,既能写径丈大字(可见已经带有炫技和表演性),也能在方寸之间写下万千小字。有很多书史记载,都提到他令人莞尔的题壁行为。作为一个嗜酒的书写高手,他从不带钱进入酒肆,但总能饮足而归,原因是只要他动手题壁书写,便有观者云集,成为酒肆的当然消费者。师宜官觉得大家消费足偿酒钱后,“计价偿足而灭之”,把大家都叫好的满壁书法全部擦掉,这样,下回来喝酒又可以尽兴表演一番了。[1]窦臮撰、窦蒙注《述书赋·卷下》,“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余兴”,其注云“后汉师宜官工书,嗜酒,每遇酒肆辄书于壁,顾观,酒因大售,计价偿足而灭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页)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卷八有注云,“师宜官书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6页)
类似的名家记载还有一些,比如王羲之看到儿子大字题壁而观者如堵,感到非常欣慰,比如他临行题壁,走后献之悄悄擦掉并换上自己的书写,比如王献之以帚泥书壁,观者如市。帚泥不比墨汁,难以细腻精妙,显然,大家围观的主要还是形式与气势,也可见这类展示与观赏的场面不小。
同样,“饮中八仙”之一的张旭,酒酣不羁,回眸之间,壁无全粉,都被他风卷残云般的速度写满了。满壁张扬豪壮的狂草及其娴熟飞动的挥运节奏,带来的视觉享受强烈而刺激,远比观赏案头静态作品更加过瘾。
李白名诗《草书歌行》也记录了怀素和尚草书题壁的激情,以及当时他在湖南地区书写屏幛作品的普遍程度:“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1]《李太白集》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除了表演性,唐代题屏的风气也很兴盛。[2]史忠平:《唐代屏风书法小考》,《中国书法》2015年第7期,第191页。
李白在山东任城县一带居住游历时,曾写过一篇考证县史、赞颂县令的记颂文字,应是写在县衙或者相关处所的厅壁之上,文章因此题名为《任城县厅壁记》。文人游历应酬中的很多即兴文字,也都是直接写在厅壁类的空间上,不论有无现场围观者,他们心中自有跨越时空的观者。
《书小史》卷十载,五代大书家杨凝式的书法几乎题遍洛阳寺壁,“西洛寺观二百余所,题写几遍”。《珊瑚网》卷二“法书题跋”也说,杨凝式“喜作字,尤善颠草,居洛下十九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不但书写时观者云集,游客也常常流连忘返。几十年后的书家李建中,就喜欢到洛阳寺庙里观赏杨凝式的题壁书法,“一回入寺一回看”。再后来很多寺庙修缮,题写的粉壁没能保存下来,到苏轼、黄庭坚这一代书家,尽管也很向往能够观赏到杨凝式的题壁作品,却只能遗憾而返了。
题壁的传统后来虽然有所减弱,但依然还存在,清代翁方纲有诗句描述在驿站厅壁观赏王铎草书的感慨,[3]翁方纲撰《复初斋外集》诗卷第四,《驿壁见王觉斯草书》,民国嘉业堂丛书,第57页。类似厅壁的场景当然不是孤例。晚明以来高堂大屋决定了书画作品的尺幅往往是高屏大轴,故宫博物院所藏王铎的草书立轴中,有的作品高达四米多,可以想见其展示场景与当时书斋或者堂屋的空间气象。类似高大立轴的情况很多,以王铎、傅山为代表,比如《爱日吟庐书画补录》中记录的一件傅山草书立轴,绫本,高九尺八寸一分,阔一尺七寸四分。[4]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三,民国二年葛氏刻本,第59页。在那个时代形成了连绵大草,带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潮流,更早一些还有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一流高手醉心于此。这样的笔法、尺幅、气势及其视觉张力,包括跌宕起伏、宏大崇高的审美倾向,即今天概称的“明清调”,就绝非案头把玩作品的类型可比。
乾隆时期扬州八怪引领风潮,为首的郑板桥自创六分半书,号称乱石铺街,多有六尺、八尺、丈二整纸的书法作品卖给盐商藏家,颇有巍然之势,视觉张力很足,相信也是悬挂于高堂大屋以为观赏之用。碑学兴起以来,作品尺幅之外,作品风格不再以“二王”精细的帖学笔法为宗,而渐次过渡到雄强厚重的碑体审美,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一直到于右任等,都是以碑学笔法、线质与气象挺立书坛,他们当然不会把自己局限于案头空间及其美学。很多作品,尤其是大幅的楹联、条屏等,都是为了厅壁悬挂欣赏而创作的,与今天的展厅场景要求并无不同,也需要好的点画线质、结构与视觉效果,特别是邓石如、伊秉绶、吴昌硕等人的作品,风格雄浑壮美,就极为适合厅壁悬挂展示与观赏。

图1 于右任对联作品
三、理性看待“展览体”
今天的展厅已经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展览也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书法工作者和爱好者们重要的交流形式。随着视觉经验积累和笔墨技法水准的不断提升,佳作也是精彩纷呈,笔精墨妙并不只有某个时期的古人才能做到,钟张之后,有二王,再后来又有欧褚颜柳,宋代人觉得唐法不可超越,但还是出现了苏黄米三家别开生面。碑学审美兴起后,邓石如、伊秉绶、吴昌硕的篆隶,其雄浑壮美恢弘的一面,也是与古人交相辉映的。今天一些高水平的书家笔下的精到与味道,在笔墨功夫和风格韵味方面展示出的才华、创意与状态,并不弱于元明清时期大多数知名书家,只是在个人风格的原创性、内涵和价值高度方面,还需要一一经受艺术史的检验和筛选。其中固然有很多尚欠火候、跟风追潮的展厅作品,形式有余而内涵不足,但是,希望用案头风雅来要求、乃至约束厅壁作品的张力与表现力,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当代书家在笔墨技法和形式张力方面的丰富与突破,就是对这个不再追求实用、纯粹艺术探索的时代的一大贡献。
尽管不可能每一位书法高手都能留名于史,但是乐观和公正地说,今天五体书法领域分别达到的书写与创作水准,还是不容否定的。每一点进步,都源自书家们真诚而艰辛的努力与探索,而不是靠所谓“展览体”的那些缺陷积累起来的。展厅不可能完美,甚至只是短时限的部分书家的集中,既有一些精品力作,也有大量跟风模仿或平庸苍白之作。人们总是拿那些并不高级甚至众多追风的作品及其缺陷,来批评所谓的“展览体”,而忽略艺术创作引领者们的探索智慧与时代贡献,显然是不够全面、不够客观的。因为,每个时代,内外兼修、素养全面的大书家总是极少数,但这些人的高度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同时,每个时代注定是引领者少,跟风者众,“二王”时代已然如此,遑论后世,这是艺术生产在人才比例方面的必然规律,今天我们也无法求全责备。所谓悟者自悟,只要书法不被人为禁绝,那么江山自有才人出。

图2 泰山经石峪题刻遗迹 (王德全摄影)
平心而论,我们这个时代已不缺乏真正的高手,既重视读书学养,也修炼得笔法高明、味道深淳,既有精妙蕴藉的案头书写,也有极富视觉魅力的厅壁作品。真正写得好的书家,无论参不参展,无论案头还是厅壁,都能写好,写得精彩有味道;而写得不好的,特别是“馆阁体”之类,即使天天趴在案头却仍然写不好。所以书法的创作与表达能力,跟展示形式关系并不大,书写者的艺术天赋、人品、学养与勤奋程度,才是最关键的。我们需要批评书家们过于重视技术、读书不多、学养不够、风格标识度不高,或者跟风媚俗、作品缺乏内美等问题,但是无视展厅时代的进步与成就,单纯用案头美学标准来要求空间日益高大、注重视觉效果的厅壁美学,还是削足适履、捉襟见肘的。
实际上,对当代书法艺术而言,展厅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呈现与交流方式,这既是书法艺术也是当代书家的宿命,甚至也是古典作品的保存方式——比如故宫博物院的系列古代书画展,那些昔日案头的结晶,如今都统统放置于宽敞阔大的展厅之中了。时代语境已经改变,由于观者太多而展期较短,观者对个别经典作品只能靠排队匆匆看上一眼。这是无可逆转的确切的展厅展示时代,艺术创作可以吸收案头美学中好的特质,在内涵上下足功夫,但是案头美学从来没有一统天下,在今天的传媒时代似乎更有些难以承载了。
四、数字虚拟技术对厅壁与案头融合的推动
然而有意思的是,百余年来,照相术的发明、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出版事业的发达,某种程度上又逐渐将厅壁(乃至石窟山崖)大作品,缩印投射到了案头,成为与展厅并行存在的一种方式。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开放了部分古代珍藏书画的展览,同时也印制发售了一些作品图录,以供世人观赏临摹。展厅里可以看到很多细节,但抵达现场是不容易的,毕竟看展的时空条件因人而异。因此,尽管细节已经消失不少,但是能在案头翻开缩小印刷的图版,其大致的风格信息仍然可以给观者带来丰富的视觉收获。

图3 于右任对联作品
再后来,电脑网络技术的飞速迭代,尤其是手机拍摄功能的进步,以微信为代表的新社交媒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打破了之前艺术作品观赏的时空与资源限制。在这样的科技条件下,任何展览,只要图文报道出来,便可足不出户、便捷免费地从手机上迅速浏览、观赏到海量作品。而高清扫描和高速网络,也使得作品局部能够即时传送、放大,有些放大效果甚至比展厅现场或案头所见更为清晰细微。这样一来,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媒介的普及和支撑下,网络展、微信展逐渐成为书家们展示最新创作状态和水准的最便捷模式。以前通过报刊杂志传送展品图版的方式,受到发行渠道和成本的制约,已经难以达到微信等网络媒介传播的速度和普及率。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5G技术的推广应用,视频传输的快速与数字图像生成的便利,加上人工智能不断深入开发所带来的技术推动,书法的参与实践、学习交流、展示与观赏都将发生划时代的变革。很可能,带有权威和中心意味的展厅的重要性也会逐渐降低。只要展厅现场数字信息足够丰富完整,那么去中心化的虚拟展厅将能够被各地观者在适宜的空间里随时和反复打开,不用舟车劳顿,就能身临其境,真切感受作品本身,随手调节作品的尺幅大小与细节呈现等级,并可能与作者及相关参与者进行实时联络、深入沟通,这将是书法艺术展览和交流的未来模式之一。同时,展厅与案头两种观看与欣赏传统将可能逐渐和解、合流,界限不断模糊。这个有可能消弭展厅与案头隔阂的书法艺术展示与观赏的新趋势,或许正在慢慢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