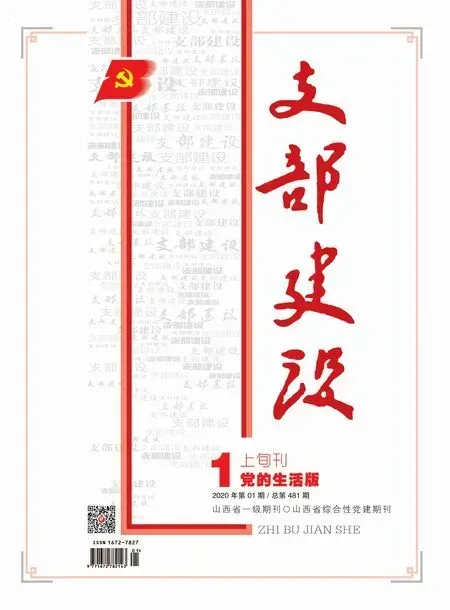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
——读蒋殊《再回1949》
徐文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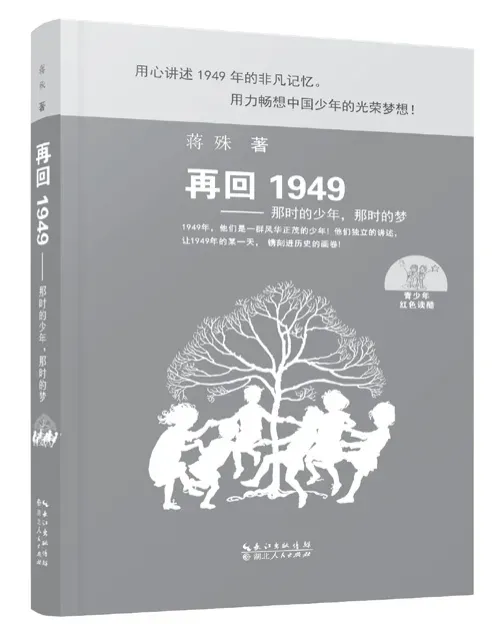
1910 年秋,毛泽东离开闭塞的湖南韶山冲,外出求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韶山冲走出的中国少年,以这样的雄心,开启了人生的重要转折。
1936 年,逝世7 周年的梁启超的著作《饮冰室合集》由中华书局出版。煌煌1400 万字的巨著中,收录的《少年中国说》广为传播,“少年强则国强”至今溢彩流芳。
2019 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举国上下,一首《我和我的祖国》飞越山河,穿过城乡,成为大江南北、男女老少的至爱,唱出了十四亿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国庆节前夕,《我和我的祖国》同名电影上映,七个家国情怀故事,七位著名导演,携手豪华的演员阵容,让国人泪目激昂,热血沸腾。蕴藏在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国深情,犹如山呼海啸般的磅礴力量,气势如虹,达到巅峰。
数不清的创意,难以计数的形式,都在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我爱你,中国!
在浩如烟海的媒介形式中,一本《再回1949》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面世,副标题是“那时的少年,那时的梦”。24 个小人物,共和国元年的中国少年,活脱脱再现于世人面前。
那是中国少年的代表,那是少年中国的缩影。
它的作者叫蒋殊,也是中国最美期刊《映像》杂志的执行主编。
蒋殊去年刚刚出版过描述红色土地武乡抗战老兵的《重回1937》,直面战争的残酷和老兵的不屈,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血与火的洗礼,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
而细读《再回1949》,感受到的,却是另外一种风格和步韵。
共和国元年,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三座大山分崩离析在即,正在顽固地做最后的挣扎。少年中国的裂变呼之欲出。
《再回1949》中,从8 岁到18 岁,24 个中国少年,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科研工作者、画家、曲艺家、歌唱家、作家……来自10个省份20 个县市村庄,在同一年的时空下,次第绽放。70 年前中国少年的内敛和羞涩情态,被作者温婉地收着、压着,以白描的手法,2000字左右一篇的篇幅,跳跃勾勒和细节呈现,吐露出压缩饼干一样的凝练信息。它是中国少年的一个年度切片,没有故事的延续,读不到故事中高超人物的尖儿,就戛然而止。阅读还没缓过神儿来,就是一片白茫茫巨大的想象空白,定格在那里,无法自拔,无法转场。当你怔怔地回过神来,另一篇章就开始了。
那时的少年,几乎没有传奇人生的任何预兆,懵懂过,青涩过,张皇过,少不更事过,甚至也胆怯过。就像鲁迅曾经说过的,不能指望一个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就是美妙的诗篇。它就是自然而然,普通寻常,新鲜嘹亮。这是人性的天然流露,也是逼近人生的本质和真实。
但就在这寻常之间,有一种力量在涌动,在积聚,在隐忍,也在不经意间迸发出火星。1949,注定是一个超大的年份。滚滚时代浪潮中,中国少年们,虽然身处不同的时空和背景,禀赋各异,男女有别,但不约而同地绽放星星点点独有的光华,很渺小,极易被忽视,但极其可贵。好在,点点滴滴的纠结和聚合,竟汇集成一股力量,从枝枝叉叉、分流分野,逐渐有了共同的走向,推着社会往前走。70 年后,恍若隔世,各自有了别样的人生,甚至天翻地覆,不堪回首,无以言说。当作者蒋殊走近他们,在渐臻佳境的访谈中,他们从当下耄耋老人的视角,和时下的年轻人们一起云淡风轻,一同回望从前,激活记忆,叫醒历史,不仰视,不俯视,平视对话,平常心看待,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观察维度:发现一些从前的独特,从时代裹挟的洪流中,打捞一些生活本质的碎片,撺掇成一个年度的图谱——共和国元年的中国少年群像。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会发现,蒋殊在简约跳脱的文字里,并非在时代边缘或者一隅,专门描述小人物的寻常烟火。动荡的年代,注定遭遇一些惊心动魄的场景。烽火连天,步入绝境,风鸣草衰,刀光剑影,饥饿贫穷,刀起头落,诸如这般触目惊心,这些生活不堪承受之重,隔一会儿就蠢蠢欲动,跃然纸上。而毎每结尾处,却又水落波平,挥手作别,举重若轻,何等洒脱!如此天壤之别,落差巨大,似乎毫无违和感,集于一身,令人讶异,真有点儿骇人!不过,我也相信自己的眼力,蒋殊的创作毕竟有延续性,不装,文风率真,更无故弄玄虚。笔,汩汩流淌;心,随之驿动。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书,我书即我心,我心是我思。
如果再仔细阅读,每一篇都是感性跳跃文字,并非理性逻辑之范式语言。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些形态各异、富集信息量的时光故事,都有类似章子怡、巩俐、李保田、陈道明一类无声胜有声的演员来演绎,每一篇都可以是一部很好的微电影。
这让我又一次联想到阵容豪华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影片分为《夺冠》《回归》《前夜》《相遇》《护航》《北京你好》《白昼流星》七个部分。七位导演分别取材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以来,祖国经历的七个历史性经典瞬间,讲述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聚焦大时代大事件下,小人物和国家之间,看似遥远实则密切的关联,唤醒全球华人共同回忆。
不过,请注意,电影是大事件下的小人物。事件的高光度,调动了万众瞩目。名导名演员的知名度,吸引了粉丝无数。
蒋殊显然另辟蹊径,关注的是大背景下的“小”事件,“小”事件下的小人物。事件之小,是相对于国家的大事件;但对于当事人,文中的小事件,绝对是天大的事件!而大背景,则无论大事件还是小事件,均为共同的背景,绝无二致。蒋殊以这样的方式,把文章的起点,和电影的取材,拉到了一个起跑线,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聚焦。
也许,很多人从未想过芸芸众生的小人物,和国家的联系是如此休戚相关。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不仅仅是叱咤风云之关键少数,从其精神本质亦是多元。毛主席曾有言“人民且只有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并不单指少数振臂一呼的英雄。
蒋殊,以盈盈一握之娇小身躯,蜀葵之形其外,石头之坚其内。兀自一禺,兀自前行,兀自盈盈,兀自东西。奔走寻访,沙里淘金,金里淘铂,凝练出的24 个柔嫩温暖的故事,与七位名导七个故事的鸿篇巨制,数比悬殊,形成强烈反差,犹如天色朦胧下的神女峰与远山名岳的遥相对峙,隔空呼应。虽极不匹配,不能相提并论,但其坚硬的英雄特质內核,何其相似乃尔!
身逢大事件,或者所谓小事件,是人生的不同际遇;遇事秉持铮铮风骨,是英雄的共同标配。
《再回1949》所写的人物,现在怎么样?限于篇幅,书中没有讲。不过据蒋殊讲,老人们热爱生活,心态平和,对世界的好奇和温良,竟然惊人地相似。其中有两位,我见过或熟悉,刘改鱼和曲润海。他们都是宝刀不老,青春永在。刘改鱼是民歌大家,出演小妹妹依然窈窕少女,情态自然,前不久还在央视舞台上;曲润海每天创作到凌晨,文思泉涌,大戏佳作不断,频频活跃在台前幕后,在全国戏曲界是响当当的学者型离休官员,德高望重,自称“三外闲人”。我想,按照先贤梁启超的说法,“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以国力民心观之,70 年的共和国,何尝不是少年中国,英姿勃发?24 位尊敬的老人,又何尝不是中国少年,“壮丽浓郁翩翩绝世”?!
试看东西南北中,举目追梦中国人。《再回1949》,一个经典年份的人性群像读本,以文学的形式,发挥独特的笔法,发掘非凡的记忆,发现平凡的力量,发扬守正的意念,发散熠熠的锋芒!